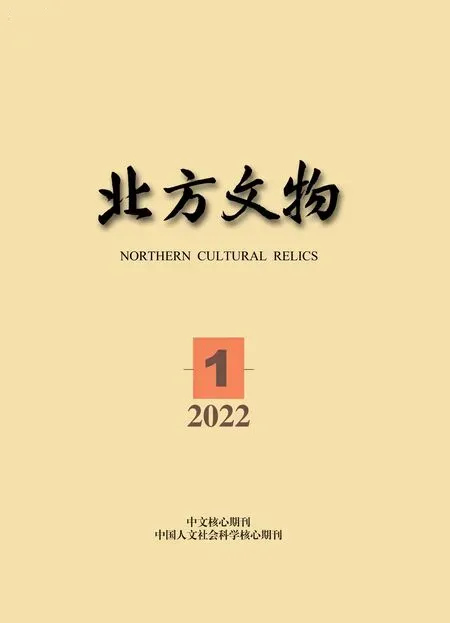高句丽赈贷法发微
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
〔内容提要〕 面对自然灾害时极易发生民变等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情况,高句丽初期弱小时,采用的是单一的赈济制度,但随着国家实力的强大,其统治区和人口的激增,故国川王时颁行了赈贷法,用以解决年景不佳,贫民困苦时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灾后恢复生产的绝佳农业法。正是赈贷法的实施,保证了高句丽此后近5个世纪内,历经数次灾害,但却未发生民变骚乱等内部危及政权统治的情况。赈贷法是面对“无所佣作”的情况,当出现较大灾乱,发生“民饥”甚至“饥人相食”的状况时,仍会辅以“赈给(济)”“赈救”或者“抚恤”等并用手段。因此,赈贷法可谓是高句丽统治者制定的一项成功保全农业生产的法政,有利的保障和维护了高句丽政权的统治和延续。
高句丽(公元前37—668年)是汉唐时期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民族政权,国祚长达705年。在漫长的7个世纪时间内,经历过无数次自然灾害和年景欠佳的情况,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灾情,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是保全其政权稳定的关键所在。在经历了初期经验摸索和效法中原救济制度之后,于东汉末年之际,高句丽故国川王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完善的赈贷法制度,这是一种辅助于发生突发性的重大灾害后、国家实施例行赈济制度之外的另一种常规性惠民法制。从此,高句丽虽也多历灾害,但均未发生民变事件动摇政权统治的根基。可以说,赈贷法对于稳定高句丽政权意义深远,是使其政权可以存续7个世纪之久的成功制度之一。
关于高句丽的赈贷法,因在《三国史记》中有明确记述,故而在学界的研究成果中多有提及,中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的“下户”性质①、食邑制度②、财经制度③、社会救济④及土地所有制⑤等问题时,韩国学者在探讨高句丽的财政⑥、农业技术和生产力⑦、税制⑧等问题时,都言及高句丽赈贷法的存在,但对该法具体情况却长期未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近期,韩国仁川大学申政勋就高句丽赈贷法发表了专门性的研究⑨,得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但就其中一些结论,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可以明确的是,该法条是高句丽面对灾害和荒年时采取的荒政,所以,对于高句丽政权的稳定和延续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因其长期未得到学界的重视,故笔者不揣浅陋,欲针对申政勋的研究结果,对高句丽赈贷法继续进行探究,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赈贷制度的产生与性质
灾害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便是文明与政权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灾害的妥善处置和应对手段,考验着一个族群文明和国家政权的延续能力,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自古以来经历了无数次大小不等的自然灾害的洗礼,在应对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并卓有成效的处置手段,使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为了应对灾害的侵袭,维持政权的稳定,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较为重视农业灾害管理和灾民安抚问题。而向灾民发放赈贷则是统治者应对灾害的一个基本举措,在我国荒政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统治者彰显自身道德正义和政治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手段。
所谓“赈贷”,即赈济性借贷,是中国古代灾荒救济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传统的救荒政策,主要包括赈粜⑩、赈贷、赈给三种,史载:“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赈)给之,无分于主客户。”其中,“贷以种食”即为赈贷的主要措施。它是国家将钱物在特定的时候出借给农户以渡难关,而农户需要在特定的期限内再归还本息的一项信用行为,是一种带有救灾性质的借贷。该法自产生之日起,便被历朝历代继承和发展,成为一项维护政权统治、维系社会安定、体现统治者“道义”的重要举措,在荒政中占据重要地位。
赈贷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指官府借贷钱物给百姓,各地以其特色产品为利息,此为赈贷的理论源泉。至西汉时,赈贷开始较为广泛的实施。如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发布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所谓“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意即百姓受官府赈贷种食而没有归还或者没有完全归还的,皆赦免蠲除之。可见,当时已有赈贷、蠲免的相应措施了。此后,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章帝等,文献中皆有其赈贷或者蠲免赈贷的记载。汉以后赈贷的实施散见于各处,文献中所载不多,唯言“以后,以各处水旱、饥馑,赈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虽则不书,而实际可见赈贷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实施。
赈济和赈贷之“赈”,许多文献写作“振”,尤其是在有系统赈恤制度的宋代,所以,《宋史》将有宋一代的救荒、抚恤等社会救助通称作“振恤”。这里的“振”是先秦、秦汉时期救助的原本意义。南宋人吴曾对“振”和“赈”的流变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颜师古《匡谬正俗》曰:“赈济,当用振字。”《说文》曰:“振,举也,救也。”诸史籍所云:“振给,振贷,振业者,其义皆同,尽当为振字。今人之作文书者,以其事涉货财,改振为赈。按《说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赋》曰:‘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此则训不相干,何得混杂。诸云振给、振贷者,并以饥馑穷厄,将就困毙,故举救之,使得存立耳。宁有富事乎?”以上皆颜说,予以颜说甚当,但未有据。按《春秋传》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师,自庐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庐,今襄阳中庐县也。振,发廩仓也。同食,上下无异馔也。”然则振济,当以左氏为据。今字书止云赈,言其富,盖言于利,能不失时,则可以致富矣。汉《汲黯传》:“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亦作此振字。
所以,可知赈贷、赈济之“赈”与“振”通用,其本意就是如《说文》中所言的“举也,救也”,以及《春秋传》中所言的“发廩仓也”。由此可知,赈济制与赈贷制很早便在中原王朝产生并实施,是两种应对不同状况施行的荒政措施。随着中原王朝向周边地区政治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和加强,这些制度文化也渐次被边疆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并效仿,这其中东北各民族便深受汉地影响。
二、高句丽赈贷法的产生
据《三国志》载,高句丽初期的地理环境“多大山深谷,无原泽”,居民“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说明直到三国时期,高句丽的粮食产量仍比较低,因此,在遭受自然灾害打击之时,亦非常脆弱。当发生饥荒时,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引发民变,动摇或倾覆政权。所以,面对灾害发生时,高句丽统治者只有出台更为妥善和顺应民意的解决方案,才能保障政权的稳定和持续。
赈贷法,在高句丽建国前便是中原王朝成熟的荒政制度。如前文所述,先秦时期便有赈贷制度的萌芽与雏形,进入到封建王朝后,该法成为了封建统治者重要的治国准则。据史料载,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就曾以国家名义,公开发布《振贷诏》,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此后,赈贷法成为国家面对灾害时应对的常制,如汉“昭帝始元二年二月,遣使者赈贷贫民无种食者”。同年“秋八月,诏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债),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在时人的著作中多见其法,如《盐铁论》便载:“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民务时也。”可见,赈贷法自汉代起,成为国家常法,后代王朝亦因袭此法。如新莽地皇三年(22年)二月,“霸桥灾,数千人以水沃救,不灭。莽恶之,下书曰:‘……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四月,王莽又下诏曰:“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于春尤甚,予甚悼之。今使东岳太师特进襃新侯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太师公所不过道,分遣大夫谒者并开诸仓,以全元元”。
高句丽建国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其后中原各种典章制度随着双方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渐次传入高句丽,但是,从文献看,高句丽建国的前2个世纪内,曾遭受过多次自然灾害,面对一些小的或局部的灾害,高句丽统治者未见有救济措施,只有在遭受较大的灾害、引发“民饥”的情况时,才会遣使开仓,予以“救济”。很明显,这个时期的救济方式是“赈给(救)”和“赈恤”,还没有出现“赈贷”的方式。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
闵中王二年:夏五月,国东大水,民饥,发仓赈给。
慕本王二年:三月,暴风拔树。夏四月,殒霜雨雹。秋八月,发使赈恤国内饥民。
太祖大王五十六年:春大旱,至夏赤地。民饥,王发使赈恤。
太祖大王六十六年:秋七月,蝗雹害谷。八月,命所司举贤良孝顺,问鳏寡孤独及老不能自存着,给衣食。
故国川王十六年:秋七月,堕霜杀谷。民饥,开仓赈给。
虽然上述文献中还未见“赈贷”出现,但却可以看出,在闵中王和故国川王救灾过程中分别有了“发仓”和“开仓”的记载,这说明高句丽最迟在1世纪中期,便有了国家粮仓的设置。“仓”者“谷藏也”,《礼记·月令》“季秋,命冢宰举五谷之要藏”。有了粮仓,就有了对其予以管理的官员。《周礼·地官》曰“仓人掌粟入之藏”。可见,高句丽有所谓“发仓”和“开仓”的举措,其国家机构中必然已经齐备执掌仓管的官员。如上述文献中慕本王和太祖大王救灾时都申明了国王专门“发使”前去专办,该“使”最大可能就是掌管国家粮仓的官员,但因为文献极简,未能记录下这些官员的官号。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故国川王开启赈贷法之前,高句丽已经具有了齐备的国家管理机构,王家仓储的管理和灾害赈抚都有专门负责的官员。
东汉是中原文化制度广泛传播至高句丽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量中原人士或是通过战争手段被掳掠至高句丽,或是因躲避汉末战乱而主动移民至东北乃至高句丽境内。如太祖大王时期便时常侵扰东汉边郡,劫掠人口,在建光元年(121年),太祖大王薨逝之际,东汉便讨论过要趁机征伐高句丽,即位的次大王“遂成还汉生口”,以免被讨伐。对此东汉向其下诏曰:“(高句丽)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可见,尽管高句丽刷还了部分人口,但还有更多的汉民被留在了高句丽。这些被掠至高句丽生活的汉民并非全部沦为了奴仆,除手工业匠人外,很多是掌握农业技术的农民,这也是高句丽为何要大量劫掠汉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们来助力高句丽的农业发展。这些人没有固有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便要用一种国家有偿获利的方式予以解决,由此促生了高句丽学习东汉已经成熟的赈贷方式的产生。除了武力掠夺,东汉末年还有很多人为避战乱主动迁徙至东北或高句丽,如名士管宁因“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相同情况的世家大族绝非个例,而未著于史者更是为数众多。这些来到高句丽或者辽东的汉人,对于高句丽的文化影响必定是极为强烈的,面对中原边郡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对于大量涌入人口妥善解决的方式,都是极大刺激并触动高句丽政治改革和学习的巨大动力。高句丽应当正是在周边各郡安顿流民的手段中,进一步学习到了除直接赈济手段之外的“赈贷”之法。
东汉时期同时也是高句丽在东北诸族中逐步强大的阶段,随着高句丽国势的增强、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政治制度也日臻成熟。面对时有发生的灾害,务必要有一套健全并完善的荒政措施,倘若发生大型灾害,引发“民饥”,施行应急措施发仓赈济是必要手段,但更多发生的是小规模的、引发民众困苦的灾害,抑或如上文提到的对于掳来的新人口或主动投赴的新国民的安置,这就要求统治者不能置民生于不顾,任其自求生存之道,这样极有可能引发民变,但此时便开仓予以无偿赈济,对于国家来说则又是极大的经济负担,而且极易造成部分民众的“惰劳”行为。面对这种情况,2世纪末的故国川王开创了高句丽历史上的赈贷法,从此解决了高句丽荒政制度中,面对未引发举国“民饥”状态下的中小等级的自然灾害年景下,对国民的救济方式。
(故国川王)十六年,秋七月,堕霜杀谷。民饥,开仓赈给。冬十月,王畋于质阳。路见坐而哭者,问:“何以哭为?”对曰:“臣贫穷,常以佣力养母。今岁不登,无所佣作,不能得升斗之食,是以哭耳。”王曰:“嗟乎! 孤为民父母,使民至于此极,孤之罪也。”给衣食以存抚之。仍命内外所司,博问鳏寡孤独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救恤之。命有司,每年自春三月至秋七月,出官谷,以百姓家口多少,赈贷有差,至冬十月还纳,以为恒式,内外大悦。
上述文献较为明确的记述了高句丽赈贷法出台的背景和经过。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和探究。
其一,是关于赈贷法出台的推行者。在上述的《三国史记·故国川王本纪》中,非常清晰地记载了故国川王面对“民饥”型的大灾后,采取了以往实施的“赈给(济)”方式,但在此后经历了路遇贫民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故国川王显然对这样的“贫民”而非“灾民”的救济方式有所反思,因此,在赐给了该贫民“衣食”之后,回去命令官员采取了两种救济方式:即对于“鳏寡孤独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仍旧施以“救恤”;而对于其他尚能“自存”但“无所佣作”者,“出官谷,以百姓家口多少,赈贷有差”,这是一种借贷的方式,春三月或秋七月出借,冬十月则要“还纳”,并且从此以为“恒式”。这便是赈贷法出台的过程。很明显,该政是由故国川王本人制定并颁行的,所以,中国学者对此并没有更多的延伸。但很多韩国研究者却依据此前故国川王广纳贤良,从民间征纳了贤臣乙巴素,并以其为国相的记述,认为提出并推行赈贷法的人是乙巴素。诚然,乙巴素是高句丽历史上的一位贤臣,史籍中言其“至诚奉国,明政教,慎赏罚”,故而高句丽“人民以安,内外无事”。然而,文献对于赈贷法与其有关一事只字未提。笔者认为,在文献记述如此明确的情况下,非要将该惠民的法令置于乙巴素身上,而枉顾故国川王体恤民生进而出台该法的史实,应该拿出更多有力的证据,要依文献为据,避免揣测的成分过重。
其二,是关于故国川王推行赈贷法的经济来源问题。前文提及的韩国仁川大学申政勋有专文探究高句丽的赈贷法问题,其中一个结论便是高句丽用以赈贷的物资主要是于畀留和左可虑被没收的财产。这里涉及故国川王在制定并推行赈贷法之前发生的一场平叛事件。史载,故国川王十二年(190年),“中畏大夫沛者于畀留、评者左可虑,皆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其子弟并恃势骄侈,掠人子女,夺人田宅,国人怨愤。王闻之,怒欲诛之。左可虑等与四椽那谋叛”。次年,故国川王平定了左可虑等人的叛乱。但对于左可虑等人的财产如何处置,史料并未记载。但悉读文献便可知晓,左可虑、于畀留等人,系外戚秉权,叛乱被诛后外戚势力不仅没有被削弱,甚至可以在故国川王死后决定继承者的人选,其王后于氏不仅未受到本次叛乱事件任何牵连,甚至在后继王位的山上王时,仍被册立为王后。可见,王后于氏的外戚势力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打击。那么,罚没外戚于畀留、左可虑的财产用以赈贷便不能成立。至于于畀留、左可虑“夺人田宅”的部分,应当是归于原所有人才对,而不是被故国川王充进国库,如果是这样,那么,故国川王与于畀留、左可虑之流又有何异?如何取得人民爱戴,得以依赖“畿内兵马”平息叛乱?所以,高句丽赈贷所用物资主要是于畀留和左可虑被没收的财产这一论点亦不能成立。如前文所述,既然闵中王时已有国家仓储可以用以赈济,那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高句丽的国家仓储制度应该更加成熟和完善,所以,故国川王时可以实行赈贷是因为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经济基础。
三、赈贷法在高句丽的实施及“赈贷”与“赈济”的并用
赈贷法自故国川王十六年(194年)颁行开始,便“定为恒式”,令高句丽“百姓大悦”,显然是一项得到举国拥戴的惠民政策,是高句丽重要的荒政,解决了其面对灾年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民情的困境。此后近5个世纪里,高句丽虽屡遭灾害,而未见爆发民变,相信就是这一法政长期维系的结果。然而,在申政勋的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结论认为,高句丽的赈贷法自产生之日起,有反复废立的情况。其认为,赈贷法在高句丽有四个时期。
1.故国川王代(179—197年)——中川王代(248—270年):赈贷法的实施;
2.西川王代(270—292年)——故国壤王代(384—391年):赈贷法的废除;
3.广开土王代(391—412年)——文咨明王代(492—519年):赈贷法的恢复;
4.安臧王代(519—531年)——高句丽灭亡(668年):赈贷法的废除。
即申政勋认为,赈贷法在西川王和安臧王时期曾两次被废除,在此期间的广开土王到文咨明王时期被一度恢复,而正是因为高句丽后期战争频仍,“由此带来的军费过度增长,就需要百姓来承担。并且连续出现荒年,使得老百姓不能自食其力。在没有实行赈贷法乃至没有临时救恤的情况下,高句丽灭亡了”。笔者认为,显然这是申政勋曲解文献得出的错误结论,系没有对高句丽文献仔细研读的结果。
这里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赈贷法的出台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强调其为“恒式”,作为如此明确且重要的法条,在后世文献中没有任何“废止”的确切记载;第二,如何理解在后世文献中再未有“赈贷”的记述,而只零星记有“赈给(赈济)”“赈救”和“抚恤”的文字。
显然,因为赈贷法“定为恒式”后,高句丽在遭遇灾年恢复生产等活动中都会以此为常规法制予以实施,故在此后文献中再未提及“赈贷”一词。如前所述,《文献通考》便言:“各处水旱、饥馑,赈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显然,高句丽在海东地区疆域最为辽阔,倘若是举国遭灾,必定是极为严重的灾害,此时的情形是“赈贷”方式不能得以解决的,而只能用“赈济”手段才能缓解。所以,在一些大灾后便会出现“赈给(赈济)”“赈救”和“抚恤”的记载。而申正勋根据这些史料记载的出现年份,配合一些经济现象论断高句丽的赈贷法有两次废止一次恢复的过程。有必要分析一下,史料中这些赈济情况的记述和类型。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
西川王四年:秋七月……民饥,发仓赈之。
故国原王二年:春二月,王如卒本,祀始祖庙,巡问百姓,老病赈给。
故国壤王六年:春,饥人相食,王发仓赈给。
安臧王五年:春,旱……冬十月,饥,发仓赈救。
安原王六年:春夏,大旱。发使抚恤饥民。
安原王七年:春三月,民饥,王巡抚赈救。
平原王二十三年:秋七月,霜雹杀。冬十月,民饥,王巡行抚恤。
申政勋认为:西川王和故国壤王、安臧王时期有“发仓”“赈给(救)”的记述,这就意味着在西川王时期,高句丽一度废止了赈贷法。而396年广开土王征伐百济而占据了汉江北部地区和南汉江流域,这意味着高句丽确实掌握了高句丽和百济交战地区的黄海道和平安南道一带,实现了该地区的稳定局势,确保了该地区积极的农业经营和水产品供应,从“广开土王碑”记载看,广开土王时期国富民殷,这一点意味着赈贷法的复兴。广开土王二年(393年),开始在平壤建造9座寺庙,可以说明广开土王曾是崇尚佛法的君主,赈贷法的复兴,应该是受到了强调慈悲的佛教之影响。文咨明王之后的安臧王和安原王时期,由于内政不稳、王权弱化而再一次废除了赈贷法,安臧王和安原王时期曾实行了四次临时性的救恤,这种临时性的救恤可能是因为高句丽占领了汉江流域,汉江流域的人力、物力等资源和临时性救济恤是有关系的,汉江流域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的丧失对高句丽有一定的打击,汉江一带的资源和税源在高句丽整个财政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通过本文开篇陈述可知,赈贷与赈济都是临灾时的救助措施,是古代政府荒政措施。但是,赈贷与赈济又有所不同,“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有曰贷粮种子者;有曰借助振贷者,以息振济者也……有曰振济者,直与以振之也”,具体是施以赈济还是赈贷,要根据对象和情况的不同而分别实施。南宋人指出:“朝廷荒政有三:一曰赈粜,二曰赈贷,三曰赈济,虽均为救荒而其法各不同。市井宜赈粜,乡村宜赈贷,贫乏不能自存者宜赈济。”后人归结为“救荒……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赈贷”。
显然,无论是赈米,或是赈钱,都属于赈济(给),这些人已毫无生计能力,是为“饥民”,因此,所赈之粮物不需要偿还。而予以赈贷之民的情况要稍微好些,是为“贫民”,所以,这种救济不仅需要偿还,有的甚至还要收以利息,只是这些利息相对少一些而已。
再就高句丽对汉江流域的控制而言,申政勋过分夸大了汉江地区对高句丽国家财政的影响,因为就史实看,高句丽对于汉江流域的控制从始至终都谈不上完全的控制。虽然长寿王在475年一度攻破汉城,迫使百济迁都熊津,但从后来百济东城王四年(482年)靺鞨对汉山城袭击记事、武宁王七年(507年)和二十三年(523年)百济戍守和国王巡幸汉城相关的记事可知,汉江流域很快重归百济所有,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百济一直保持着对汉江流域的控制。起码从文献可以看出,高句丽对于汉江地区的占领从来都不稳定,也不持久,该地区长期处于与百济之间的军事拉锯战,而一个战火频仍的地区,何谈稳定的税收和资源开发,认为“汉江一带的资源和税源在高句丽整个财政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显然是错误的认识。如此,以汉江地区得失来判定赈贷法的存废则无从谈起。
通过上面罗列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赈济措施的文献记载可知,在上述这些时期,高句丽施行了开仓救济的措施,这也便是申正勋氏认定的赈贷法被废止的时期,然而,通晓古代赈灾荒政便会明白,显然申政勋氏并未明晰赈济与赈贷的区别与联系。
上文所列之文献,很容易发现,均是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除故国原王二年(332年)条未注明灾情状况外,其余灾害均有共同特征,即引发了“民饥”,甚至发生了“饥人相食”的惨况。这种情况国家是不可能以“赈贷”方式予以救济的,此刻灾民并非生活困苦,而是无以为生,需要无偿的救济口粮。所以这种情况下,高句丽施行的是“开仓”予以“抚恤”。试想,此刻向饥民发放赈济这样的公债,饥民都已经开始相食,怎么可能用以生产,若以此方式救灾,无异于挑起饥民暴动。而除了上述列举的无偿赈济的记录外,高句丽还有更多的受灾记录,然而,并未记载政府有救济措施,但这并不表示高句丽统治者放任不管,任由人民自己寻求出路,否则近5个世纪里不可能未引发一次民变活动。恰恰是因为高句丽有赈贷法这样“恒式”的荒政法条,所以,有效解决了未产生大量“饥民”情况下的其他小型灾害的赈救和农业生产恢复活动。而因为此法为“恒式”,故无需再每每予以记述,这也符合了“赈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的记载。
灾害的类型是存在差异的,民众困苦和小的自然灾害时有发生,而大型天灾则是偶发性的,不时常出现。因此,就高句丽的荒政措施而言,赈贷法是常规性制度法条,而“发仓”“赈给(赈济)”“抚恤”则是变例。不仅在相对简约的海东文献中,就是在相对详尽的中原文献记载中,亦秉持“记殊而简常”的书写习惯,即习以为常的事情无需反复被罗列,更多的笔墨用来记述那些突发性和非日常事件。《三国史记》的记述方式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另外,关于高句丽赈贷法的利息问题。所谓“贷”,《玉篇》云:“假也,借盈也,以物与人更还其主也。”是指借出财物,待以时日再做归还。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借贷并非是无偿的,而是要根据还贷的时间和借贷的数额付以不等的利息。高句丽赈贷法只提及“每年自春三月至秋七月,出官谷,以百姓家口多少,赈贷有差,至冬十月还纳”,并未言明还纳的只是原本的借贷等额谷物,还是需再多纳利息。所以,关于高句丽“借贷法”有无息贷和有息贷两种认识。笔者更为认同无息贷的认识。
四、结 语
《三国史记》载,在故国川王颁布赈贷法后,“内外大悦”,所谓“内”乃高句丽,那么“外”显然是指高句丽政权周边饱受战乱和灾害困扰的民众。在获悉高句丽行此惠政后,不仅得到了本国国民的拥戴,更是开始吸引周边民众,纷纷移民高句丽,享受此法带来的福利。史载,在高句丽颁布赈贷法三年之后的汉献帝建安二年(197年),便出现了“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的情况。显然,就在故国川王颁布此法之后,饱受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之苦的汉地百姓,便纷纷“避乱来投”,而且人口数量“甚多”。这些数量庞大的人口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并且这些汉民还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高句丽社会的发展与壮大。因此,赈贷法的出台,助力了高句丽农业生产的快速进步,对于高句丽国力的发展和民间舆情的稳定意义重大。
赈贷法自在高句丽施行以来,不仅得到了高句丽民众的拥戴,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与赞颂。史载朝鲜时代的学者崔溥对赈贷法赞曰:
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赐之衣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庾。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是则有仁心而未知为政也。子产相郑国。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是则行小惠而不知为政也。故人君必欲人人而赐之。人人而济之。日亦不足。而惠之及于民者。反不周矣。今高句丽王。遣见穷民。给其衣食。因念一国之饥寒者。遂立赈贷之法。其知所谓恤民之政者乎。
该则文献再次说明高句丽之赈贷法源于中原,始于故国川王,并且后世赞其为“恤民之政”。正是这种仁政,造就了高句丽国力的壮大,使遭遇荒年和民贫状态下快速恢复农业,稳定民众情绪,巩固政治统治的延续。也正是因为高句丽有完备且“恒式”的赈贷法这样的良政,使得其在数次遭受外来势力讨伐几近亡国之际,仍可团结国人,再续崛起,并且更加强大,这是好太王碑中邹牟王顾命遗训“以道兴治”的具体表现。
注 释:
① 朴灿奎:《高句丽之“下户”性质考》,《东疆学刊》2003年第3期。
② 李爽:《试析高句丽食邑制度》,《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
③ 王旭:《高句丽与中原王朝财经制度比较研究》,《东北史地》2013年第5期。
④ 崔瑛琳:《高句丽社会救济情况初探》,《学问》2016年第5期。
⑤ 王旭:《高句丽土地所有制演变浅探》,《学问》2017年第1期。

⑩ 赈粜是宋代出现并形成的一种荒政,因出现时间较晚,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不再累述。参见李华瑞:《宋代救荒中的赈济、赈贷与赈粜》,《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