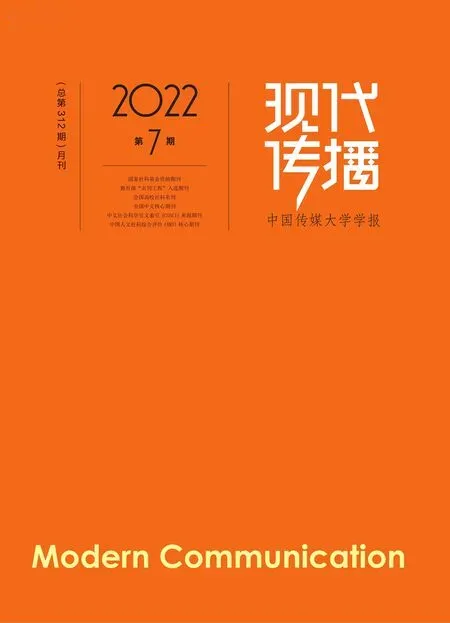电影与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
贾磊磊
我们之所以将国家历史作为集体记忆的前置词,是因为在文化意义上,国家与民族、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即“国家被视为静止状态的历史,历史被视为运动中的国家”①。尤其是在我们关于集体记忆的讨论中,民族、国家、历史经常是相互指涉、相互依存的概念。由于集体记忆的核心是指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指向其他,所以,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无论是作为集体记忆还是作为现实的话语体系并未得到充分整合,有时它们还处于分离与错位的状态。近年来在关于中国电影的诸多论争中,其焦点往往并不是关于艺术形式以及艺术风格的,而是关于历史意识以及历史观念的。人们建立在不同历史观念之上的电影判断,所争辩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电影的问题,而是电影中的历史涵义以及历史表述问题。在这样一个以视觉文化为传播主体的影像化时代,电影和电视没有理由不承担起镌刻国家历史集体记忆的文化使命。尤其是那些讲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片,在大众对于中国历史的心理认同以及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建构上,更是承担着不可忽视的文化责任。
一、集体记忆是点燃历史的“灵魂蜡烛”
对于人类来说,没有记忆的过去,无异于一片黑暗。我们的祖先曾经度过了一个没有记忆的漫漫长夜(史前史)。我们先辈的生命之火在荒野、莽原上驰骋、腾跃,在江河、湖海中畅游、漫舞。如今,这一切只能是我们的文化想象,而没有任何历史的记忆。因为只是在人类发明了图像和文字符号之后,文明之光才渐渐驱走了记忆的黑暗,文化的曙光才使人类的历史找到了记忆的载体。历史证明,人的记忆需要特定的符号载体才能够得以传承:从古代的图画、音符、文字,到现代的银幕、影像、视频。在大众传媒进入社会生活之后,记忆便具有了特定的群体属性,它开始在传承国家、民族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英语中“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一般都用“national memory”来表达。在社会心理领域“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一词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出版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作为与个人记忆(individual memory)相区分的概念,哈布瓦赫赋予了集体多重的涵义,他融合了柏格森与涂尔干二人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关于人的所有记忆都受到集体、社会框架的影响和形塑的观点②,为集体记忆确定了坚实的社会学与历史学方面的根基。英国学者弗兰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1966年出版了《记忆的艺术》一书。耶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场景”和“图像”对记忆的形成与储存的重要意义③,对于现在我们研究影像的集体记忆依然具有启示。丹麦奥尔堡大学传播与心理学系教授布雷迪·瓦格纳(Brady Wagoner)2017年出版了《文化与记忆手册》(HandbookofCultureandMemory)。作者在书中分析了记忆的概念、人类记忆的起源、记忆的种类以及记忆的文化语境。他还分别论述了记忆的文化建构和历史身份问题。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记忆的伦理》中曾经讲过:在历史上犹太人把罗马人毁灭神殿并将犹太人赶出埃及称为“毁灭”。这使犹太人永远也不会忘记“毁灭”这个词以及它背后所记述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碎片,它发挥了光荣的使命,而且形成了可称之为“灵魂蜡烛”的集体记忆。他们时时在点着蜡烛,去怀念逝去的亲人,去记住他们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灵魂的蜡烛”,它将照亮人们未来的征程,而那些没有灵魂之光照耀的路程,将是一片黑暗。
集体记忆有时还称为共同记忆。由于 “共同的记忆是集合性的概念,它集中了经历并记住某个事件的所有人的记忆,在特定社会中,如果记住事件的人的比例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如大多数人、压倒性多数、70%以上等等)人们就把对事件的记忆称为共同记忆”④。其实,世界各国都在用各种方式来建构各自的集体记忆,其中包括用影像和铭文来镌刻他们的历史,来强化人们对于历史的集体记忆。人们不仅仅是通过文字和影像,还包括建造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塔——这些与时间抗衡、与忘却作对的不同文化艺术形式。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对于战争的胜利应当庆祝、应当纪念,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电影中一次又一次地拍摄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呢?相对于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的伟大胜利,南京作为陷落的民国都城,不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肯定都不是值得被夸耀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对此不能忘怀呢?“为什么人类应当记住道德上的梦魇而不是胜利的精彩瞬间?”学者的提问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铭记历史不仅是汲取先辈的智慧,还经常意味着了解过去的思想的恶,无论它表现为何种形式。我们希望自己比前人更加明智,更加宽宏大量,或至少更加注重良知”⑤。对我们来说,需要甄别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记住什么,而不是说记住什么能够让我们高兴。这就是说,尽管痛苦的记忆不能使人得到什么喜悦,但是,它却能够使人通过对痛苦的回忆而自省。如果这些痛苦的历史能够点燃我们“心灵的蜡烛”,并且构成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我们将在警醒之光的照耀下不断前行。
记住我们的历史,这应当是明智之举。可是如何才能记住我们的历史呢?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个人必须要记住某个历史事件乃至某些历史人物,更不要说记住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了。法律是必须严格践行的行为规范,而我们所强调的关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更多的是属于思想乃至伦理范畴。我们希望国民能够以集体记忆的方式记住历史,是作为一种道德律令来设定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轻了道德,更不是忽视了法律。事实上,道德应当是最高的法律,因为它对人的约束不仅仅在行为范畴,而且还在思想范畴;而法律仅仅是最低的道德,它只限定了人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我们将集体记忆归之于伦理的范畴,是在强调国家历史的铭记要义,是通过唤起公民对于自己国家的心理认同——不论是采取艺术的方式还是新闻的方式乃至宣传的方式,在达成心理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共同的伦理取向来记住我们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讲,记忆的原则便是伦理的原则。因为如果需要记住的历史却被人们忘记,那么,这种忘却就是对历史的背离乃至背叛。阿维夏伊·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记忆伦理》中曾经提出,人类“有记忆的伦理吗?或者说有作为个人的微观记忆伦理和作为集体的宏观记忆伦理吗?”我们的回答是:有。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一系列关于集体记忆的伦理质问引入电影伦理的范畴,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将公民的集体记忆视为一种应当拥有的历史意识,那么,电影对于这种历史意识的建构又将通过什么方式来完成呢?
二、再现性电影建构的集体记忆
一部电影能够让观众记住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众心理学的问题。人们通常关心的是如何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即如何实现对观众预先设定的文化消费行为,进而使电影的商业利益得到兑现。至于观众走出电影院之后他们记住了什么,一般电影的市场研究觉得并不重要,因为制片方所期待的经济收益已经完成,至于观众走出电影院后记住什么之类的事情,也许根本就不在电影制片商的视野之内,即使在的话也就是围绕着明星效应、市场的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然而,作为一种以内容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电影中所涉及的集体记忆这样重要的内容,显然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的。集体记忆是人类历史词典中的活性索引,它能够给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与路径,使人们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这就是说,如果集体记忆是有伦理属性的,那么,不论是作为民族的还是国家的,其自身就有了特定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仅是要记住过去的人和事,记住这些人和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要记住它们的是非曲直,记住它们的善恶正邪。如果我们的电影不能有助于建构关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或是有碍于正确地建构关于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那么这种电影就应当被质疑、被否定。其实,我们有很多电影在关于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方面,都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我们过去的某些电影不能够正确地表达特定历史时代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好像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两军对垒,交战双方只是各为其主、各司其职,进而混淆了战争双方的政治归属和道德站位,让观众觉得历史不过是一场没有是非对错的暴力游戏。这样的表达极度地扭曲了观众对于中国历史的集体记忆。
对于电影而言,一般地讨论集体记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于集体记忆的讨论目前主要集中在特定的电影类型与题材上。我们可以把电影从总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想象性电影——这种电影的虚构成分占据着主要的部分,它与现实的世界没有“链接”的端口。像科幻电影、仙侠剧,这些都是没有确切的编年时间和空间地标的电影作品。《大圣归来》里有我们应当赞美的历史人物吗?《流浪地球》中有我们必须铭记的历史事件吗?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来自艺术家的想象,讲述的都是天马行空的虚拟故事,尽管这种电影与现实生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隐喻性关联,可是在经验事实上它们没有“现实的存根”。另一种是再现性电影——这种是在现实层面上有它的历史依据,与想象性电影相比它更像是一种非虚构的影片。其主导作品是历史巨制、灾难战争等史诗性作品。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来自真实历史,完成的是电影对于国家社会的历史再现。由于对于历史事实的依赖及其表现的故事内容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这些电影在讲述叙事过程之中难免会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重合,这样就对影片的创作提出了与虚构性电影不尽一致的创作要求。像《革命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人物的历史塑造,《长津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再现,这些电影最为核心的叙事焦点都设定在属于历史范畴的命题上。我们所讨论的电影与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的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类影片而言的。
不是说想象性电影不能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的文化使命,而是说再现性电影的历史承载功能可能更为直接。特别是对于在国家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时期的历史记述方面,再现性电影的记忆职能比纯虚构性的电影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同。不是人们刻意地要挽留历史,而是历史对它的集体记忆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意义与伦理色彩。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所经历的那些屈辱与创痛的历史,我们更是不能将其遗忘。
对于再现性电影建构的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而言,究竟哪些内容应当被我们记住呢?集体记忆所指向的历史应当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必须是真实的、确定的。我们不能将那些模棱两可的事情提升到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的高度来认识,凡是进入集体记忆的历史必定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无可非议的事件,这样才能够保证集体记忆的严肃性。其二,对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的判断必须是社会公认的、获得普遍认同的。没有获得整个社会一致认可的历史判断,没有得到公众普遍认同的历史形象,将不能上升到整个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范畴。而获得社会一致认可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彪炳千秋的革命英烈,绝不能够随意质疑、肆意诋毁。
三、电影的集体记忆与国家的“历史印章”
电影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多种功能、多样类型的文化工业及艺术形式。尽管世界各国的电影承载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职能设定却是一致的。在世界电影史上许多国家都在通过电影完成对历史的再现,进而建立国民对于国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具体认同。特别是通过讲述与国家政权的建立相联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形成公众对于国家意志的普遍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对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这类影片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种特有的类型及题材,横贯世界电影100年风云浩荡的历史。电影创作者始终都在电影中寻找着记住历史的各种路径。不论是辉煌的胜利还是惨痛的失败,历史本身所提供的事实都是电影认定的叙事对象。客观地讲,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用电影去记录夺取胜利、建立国家的伟大历史,进而利用电影达到铭记历史的目的。斯大林当年在苏联面临纳粹入侵的生死考验时,启动了源自沙皇俄国的伟大爱国者亚历山大·内夫斯基的民族记忆,因为他在13世纪击败了条顿骑士团;与此同时,他还唤起了人们对伊万的历史记忆,因为恐怖的伊万曾在16世纪在喀山打败了鞑靼人。⑥可见,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的提取有时要看具体的历史语境,而不是简单地根据它的时代归属来判断。当年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电影界也创作了《木兰从军》(1939)这样历史题材的故事片,虽然这部影片并没有直接表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但是,创作者却通过这些影片的叙事主题唤起国人关于抵御外敌的历史记忆,在“孤岛”放映时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⑦,激励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精神。
我们强调电影对于民族国家历史集体记忆的建构,不是说个人的历史记忆没有价值,也不是说自我的叙述不能进入历史。而是说作为共同的、集体的记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涉及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历史。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否定个人在电影中对于历史的个性描述,只是在强调:这种个人的描述怎样才能够与历史本质相互一致,或者说在深度心理上怎样与国家“历史的印章”相互重合。对电影而言,如何让那些铭刻着我们国家历史的影像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纪念碑,比电影的商业票房重要得多。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在主旋律电影的框架内讨论电影的思想导向,在商业电影的范畴里讨论影片的票房收入,在艺术电影的领域中分析作品的审美个性。其实,商业电影中的思想导向有时比主旋律电影更值得关注,因为它所传播、所影响的人群往往比主旋律电影更广泛、更深入;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指数时常又比商业电影的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通过商业渠道来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怎样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公众正确的价值取向;艺术电影思想表达的正确与否常常比主旋律电影的思想表达具有更为广泛的示范作用,因为它会影响到受众所认同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对于那些应当被人们所铭记的英雄、伟人,我们铭记他们的方式是将他们的事迹写在史书里,再现在舞台上,映现在银幕中。人们还用他们的姓名命名了街道、学校和城市,使他们的英名与人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是为了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还是为了用他们的崇高精神去引领后人前进的步伐。然而,与那些名垂千古的英雄相比,还有千千万万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牺牲的无名烈士,他们在铁血横流的战场上,一片一片地倒下。他们的尸骨堆积如山,他们的鲜血流淌成河。人们已经无法在一场接一场的血战中停下来去掩埋战友的尸体,去辨明他们的身份。无数的血肉之躯在战场上顷刻间就变成了累累的白骨。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世,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牺牲的消息。可是,他们正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推进者。他们有时仅仅是作为一个数字驻留在战场牺牲者的名录上,更多的时候他们默默地躺在九泉之下,仰望着星光闪烁的夜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这样连姓名都无人知晓的英雄长眠在中华大地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像一句历史界的箴言所云:“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⑧
在讨论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时,我们还要看到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所谓黑暗的时期。这些国家在电影艺术领域相应地产生了对这种历史的书写。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些特殊的历史时代是电影应当特别关注的,因为这种惨痛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不能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就可以将它一概忘却,或是将它锁入冷宫。正如我们应当尽情书写历史辉煌灿烂的篇章一样,我们同样应当书写历史曾经逆向运行的一刻。只是我们的这种书写不能以个人的笔触改写民族国家的记忆。比如说对于一种动乱、失序、停滞的历史,我们能不能用“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它?这就是说,一种对历史的记录一旦进入到大众媒介的文化语境中,进入到公共文化视野内,进入千千万万的家庭里,与你分享这种历史经验的人,便成为叙述者内心文本的对应性观众,如果对他们的讲述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一种历史认知的话,那么这种讲述本身就带着特定的历史记忆。
在叙事学的视野内,“故事永远都是一种话语模式。每次讲述故事的行为都包括某人(讲述者)给某人(听众)讲述关于某事物(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世界)的某事(一个故事)”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望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历史的故事,不被某种“刻板模式”所误导、被某种个人偏见所遮蔽。电影的历史叙述应当是一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叙事形态。过去,我们的有些电影之所以折戟沉沙,往往就是因为创作者对于历史的叙事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存在着某种偏差,也就是说这些影片的“历史印章”被盖歪了。
如果我们今天的孩子真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说的那样在过度影像化的生活中消解了童年的历史,而成为没有童年的一代人。那么,他们现在是不是又面临着历史感的淡忘而可能成为没有历史记忆的一代人呢?坦率地讲,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不知道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情况已较为常见。尽管记住与忘却的界限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少,可是,一个被许多人忘记的历史,就很难成为这个民族记忆的现实存在。就像中国香港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呈现的现实那样,国家、民族的历史几乎在课堂上、教材上听不见、看不着,怎么还能让这些学生去记住那段历史,去缅怀逝去的英烈呢?
四、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痛感记忆
电影,作为一种由现实影像构成的叙事文本,它独特的视觉形象,使其具有一种“指认性”,即它能够为观众提供一种类似于历史的真实风貌。这就使电影的叙事语境从直观的形态上与现实社会语境形成了“映现”的关系。电影景观(film landscape)——特别是那些不是在摄影棚和电脑中制造的真实场景,便具有与影片所表现的时代生活相指认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对一部影片的视觉表象与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它的叙事语境与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发生“断裂”“错位”,那么这部影片的意义就会产生相应的衰减。
如果我们必须要在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中确定它的情感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特征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属于悲情的心理范畴。这种历史的痛感记忆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历史心理,亚洲许多国家有着类似的心理印记。在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处于传统的农耕生活时代的亚洲国家,先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在社会历史上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我们的国土被侵占,主权被剥夺,人民被奴役,尊严被践踏。与我们同处在亚洲的诸多国家⑩都曾经饱受外敌的侵略,造成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的“黑暗的殖民时期”。有些国家至今还受到殖民主义统治遗留的分裂与苦难,使相互之间的深度合作面临着难以弥合的裂隙。这些都是亚洲国家的苦难历史造成的我们的集体记忆,我们的历史造成了我们国家历史的集体记忆普遍带有痛感的情绪特征。
不同的国家虽然没有共同的契约,可是在讲述本国历史上却表现出普遍的一致性。就像亚洲国家所经历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无形之中共同形成了这些国家特定的电影叙述主题。这些影片虽然生产在不同的电影制片体制之中,但是在叙事主旨与民族精神上却表现出同样的文化特质,尽管亚洲国家至今也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金融方面的统一体。我们没有军事的同盟,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相互开放的边界,没有共同信守的宗教。这些内在的差异加之其他列强的干涉使得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很难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可是在文化领域的亚洲电影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历史的一致性。
在亚洲电影史上,新世纪就创作了许多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电影。这些影片为亚洲人民铭记自己国家的历史,再现自己民族英勇不屈的奋斗历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铭记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社会制度而有所改变。就像在过去对于抗日战争中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我们中国电影就有民国时期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1938),有台湾地区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1975)和内地管虎导演的《八佰》(2020)。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但电影对于反抗外敌侵略仍有着共同的表达意愿。这至少表明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的电影艺术家不会忘记自己的国家被殖民的历史,我们在寻求民族自主与国家独立时所进行的舍生忘死的斗争,使我们的电影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反殖民主义的叙事主题,它是中国在电影艺术领域共同表现出的历史主题,同时也构成了我们亚洲国家在电影思想领域的文化的通约性。
与其他国家电影中的集体记忆不同的是,韩国影片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国愁”记忆——那是因为半个多世纪前朝鲜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分裂、对峙的国家。这种难以排遣的民族性的悲情几乎萦绕在整个当代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之中。无论是古装动作电影《武士》《无影剑》,还是现代战争电影《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我们看到韩国电影对于破碎家国的痛惜与对国家统一的乞望,这种“国愁”始终贯穿在韩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之中。我们知道中国的宝岛台湾地区自马关条约后被日本占领50年,做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后来又被美国驻军27年,前前后后被左右、摆布数十年。对于这种屈辱、奴役的历史,台湾地区的电影曾经多有涉及。特别是《赛德克巴莱》对于华夏儿女铭记我们的历史非常重要。这部影片除了再现了日本法西斯用枪炮、飞机、烈焰、毒气去剿灭那些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台湾原住民之外,特别强调了当年的日本想从历史上铲除台湾地区存在的文化根基,他们在台湾地区建学校、设法院、盖邮局,还强迫当地人穿日本的服装,说日本的语言,按照日本人的礼仪生活。应当说对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本质的揭示,《赛德克巴莱》达到了同类题材影片未曾达到的历史文化高度。
综上所述,为了使人们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那些被侵略、被奴役、被蹂躏的历史,同时铭记那些为国家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千千万万的民族英雄,电影可以在历史的集体记忆方面进行深入、广泛的艺术交流与文化对话。事实证明,英雄的丰碑经过历史的冲刷,依然能够闪亮如初。就像俄罗斯萨拉托夫市卫国战争牺牲者纪念碑上所镌刻的一行意境深邃的诗句:“在记忆面前,时间失去了意义”。这就是说人们对于那些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追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任何改变。人民对于那些牺牲者的崇敬与追忆之所以不会受到任何时间的阻碍,是因为这些英雄不仅属于某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
注释:
①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②③ 成祖明:《“集体记忆”理论的西方言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13日,第4版。
④⑥ [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⑤ [英]阿兰·瑞安:《论政治——2500年政治思想史》(下卷),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85页。
⑦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⑧ 樊树志:《我们的国家:历史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⑨ [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王广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⑩ 如印度、朝鲜、韩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蒙古、缅甸、新加坡、文莱、印尼、菲律宾、阿富汗,以及西亚的也门、巴林、塞浦路斯、黎巴嫩、阿联酋、阿曼、伊拉克、科威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