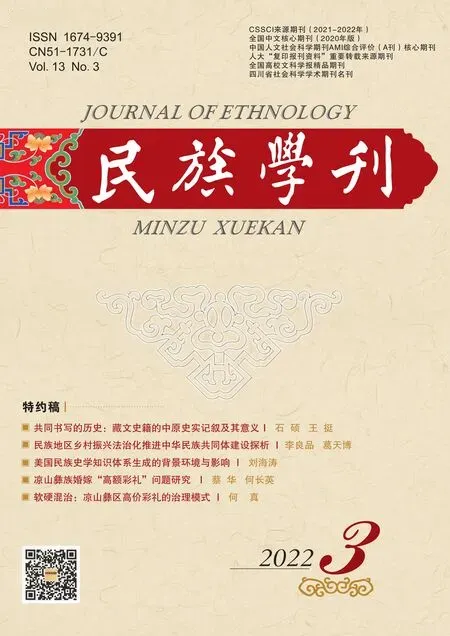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
袁智忠 杨 璟
文化人类学认为仪式是人类“各种思想、感情、行为的混合体”[1],它起源于人类原始宗教的伦理诉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维克多·特纳指出“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2]。坦姆比亚将仪式定性为“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3]尽管,学术界对仪式定义的解释存在差异,但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仪式具有伦理性,仪式通过象征符号体系来表达人类的伦理诉求。
电影也具有伦理性,“不论是在商业电影还是在艺术电影中,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电影中,伦理的问题都同样存在。”[4]仪式进入电影就形成了仪式化影像,在仪式与电影伦理性的双重作用下,仪式化影像也具备了伦理性。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仪式内在于影像而体现出的伦理性;二是电影创作者伦理观表达的仪式化倾向。前者如电影中的宗教仪式化影像、民俗仪式化影像和政治仪式化影像等所体现的伦理性;后者是指创作者为表达其伦理观,通过影像修辞手段所创造的仪式化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创作者凭借仪式化影像生成了电影的审美伦理意蕴。
一、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生成机制
无论是经典电影理论还是现代电影理论,都有一批热衷于讨论电影影像与现实关系的理论家。例如,马赛尔·马尔丹认为:“电影画面首先是现实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拥有现实的全部(或几乎是全部)的外在表现。”[5]安德烈·巴赞提出了“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这一著名命题。从这样的电影理论视角出发,仪式化影像的生成首先应该具有现实生活逻辑,它们是现实生活的复现。其次,正如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学派得出的“文化是被建构的”结论所示,各民族、国家在各个时代的伦理精神,创作者的伦理观及其伦理理想也必然暗含于电影仪式化影像之中。
(一)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产生
仪式产生于原始巫术活动,涂尔干·埃米尔认为,原始人借助仪式来满足自己的愿望,仪式将神圣生活与凡俗生活隔离,它通过宗教象征符号对道德精神产生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仪式逐渐脱离了纯宗教性,在各项重要活动中出现,如阅兵仪式、纪念仪式、节日庆典仪式、会议开闭幕式、结婚仪式等,这些仪式也可归属于人类社会的伦理文化。中国世俗社会历来重视仪式,孔子将礼仪制度看作国家政治伦理名分的重要内容,孟子也提出“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把是否讲究礼仪作为国家兴衰的标志。可见,从仪式的产生、仪式与伦理文化的关系,以及先贤对仪式的价值判断来看,人类社会中的仪式本身就蕴含着极强的伦理诉求。
在以安德烈·巴赞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为代表的电影纪实美学学派看来,电影发明的最初动因是记录生活。在这种电影“本能”的驱动下,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仪式”也很自然地被搬上了荧幕。如,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曾拍摄过《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法国,1896);电影故事片的先驱者乔治·梅里爱的著名电影《月球旅行记》(法国,1902)中有载歌载舞的“送行仪式”;据记载,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1913)中也展现了一段繁琐的结婚仪式。可见,电影影像很早就与仪式“联姻”了。
仪式化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种艺术形态之中。简·艾伦·哈里森在其著作《古代艺术与仪式》中提出“对艺术而言,其早期阶段,其相对简单的形式,就是仪式,仪式就是艺术的胚胎和初始状态。”[6]事实上,如生活中随时有各种仪式,艺术也一直与仪式伴生,例如,中国的政治仪式必然会奏国歌,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国政治仪式的标志,并且《义勇军进行曲》象征性地连接着个体与国家的伦理关系。又如,宗教信徒鉴赏宗教美术作品的过程“即是一个宗教仪式的经历,是一次宗教行为。”[7]电影是人类社会较晚出现的艺术形态,所以,早期电影理论家将电影称为“第七艺术”。尽管,早期电影理论家,如法国先锋派、巴拉兹·贝拉、鲁道夫·爱因汉姆等均从电影影像语言出发论证电影艺术的独特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电影艺术从萌芽、发展到成熟,也是向人类其他艺术形式及其生产经验借鉴、“挪用”和“取经”的过程。因而,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在吸纳其他艺术元素时,也将其他艺术的仪式化及其伦理性纳入到电影影像表达体系之中。
维维安·索布切克揭示了类型电影的仪式化问题,他认为“每一种影片类型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仪式,它自己的公式化、规范、符号表现的体系。”[8]厉震林认为电影的奇观段落“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多体现出写意的性质,时间、地点、服饰、化妆、表演和场面规模都有着非写实的倾向,在表演形态上体现出一种仪式化表演含义。”[9]实际上,不仅仅是类型电影,在电影史上,许多电影创作者为更好地表达其伦理观,在影像创造时就存在着仪式化的倾向。
前苏联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前苏联,1925)著名的“敖德萨阶梯”段落中,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使用了150多个镜头,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了沙皇军队屠杀人民群众的场面,制造了一场“屠杀”仪式,其中“阶梯”“奔逃”“母与子”“婴儿车”“军队整齐的步伐”“石狮子”都是革命伦理的仪式化表意符号。日本电影《罗生门》(日本,1950)中,瓢泼大雨冲刷着破烂不堪的寺庙、反复出现的黑压压的森林,仿佛是天神正在检视着人性的晦暗面,造成电影整体的仪式感。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美国,1970)的开端处,巴顿在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背景下长达6分多钟的演讲段落中,影像中的星条旗、巴顿行军礼的动作、巴顿身上的军装、勋章、戒指、马鞭、手枪都成为象征美国精神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仪式化符号。中国电影《天云山传奇》(中国,1981)冯晴岚去世的段落中,蜡烛熄灭、冯晴岚的旧衣服、菜板上的食材、风吹窗帘、破旧的房屋、远山、流水、满山遍野的红花以及哀婉的音乐等视听元素都构成了“葬礼”仪式,传达了创作者对冯晴岚高尚品德的道德评价。可以说,这些电影中的仪式化影像都含蓄地体现了创作者的伦理观。
可见,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仪式的伦理性、艺术仪式化所蕴含的伦理性以及电影创作者伦理观表达的需要共同决定了仪式化影像具有伦理内涵。
(二)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生成机制
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生成是电影创作者在整体叙事和主题表达的基础上,利用影像语言构筑仪式,通过上下文链接与观众进行伦理话题交流的过程。
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生成机制首先表现为象征(隐喻)化。电影中的伦理精神传达可以采用直接或间接的策略,而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呈现通常是采用象征(隐喻)化的间接性策略。厉震林将影像仪式段落称为“游离情节”,这种“游离情节”实质上是通过对叙事情节的简化来突出其仪式感。《公民凯恩》(美国,1941)中被戏称为“早餐蒙太奇”的经典段落中,凯恩的服装从正式的晚礼服转变为随意的睡衣,再变为工作时的西装,最后用一个广角镜头突出凯恩与艾米莉之间的空间距离。这场“早餐仪式”简化了凯恩的婚姻关系逐渐走向恶化的过程。“早餐仪式”与电影主人公凯恩追求“美国梦”的人生理想相呼应,再与象征“美国梦”破碎的“玫瑰花蕾”意象相链接,象征性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极端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婚恋危机。又如,《开国大典》(中国,1988)中国民党边防司令李襄南的仪式化死亡,导演在前半段运用第三代导演常用的正义英雄牺牲手法,后半段却让其倒在一个臭水凼,寓意其与人民和历史潮流为敌,遗臭万年,则又是创作者通过仪式化影像表达伦理观的经典桥段。
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生成机制还表现为审美化。仪式本身具有高度的表演性与形式性,电影以影像为媒介使仪式之美被进一步强化。例如,在《红高粱》(中国,1988)的“颠轿”“野合”“祭酒”等仪式化影像段落中,创作者利用造型、光影等镜语手段强化了仪式之美,这些“游离情节”实际上表达了其对中国文化中压抑人性的那些封建伦理的反叛,在改革开放的新语境下,讴歌人性本真的回归,拥抱新的时代伦理精神。又如《四月物语》(日本,1998)就是一部表现青年人追寻纯真爱情的伦理片,整部电影都具有仪式化倾向。影片开端处,榆野惜别远在北海道的家人,孤身前往陌生的东京,四月的东京樱花纷飞,和谐美丽的“景语”正是榆野获得接近自己暗恋的山崎机会的“情语”;榆野三次前往武藏野书屋是为了邂逅山崎,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爱情仪式;“雨中借伞”段落是爱情仪式的高潮,在舒缓、悠然的背景音乐中,导演利用了雨景、街道、红伞等元素,使榆野的苦闷得以宣泄,以含蓄、冲淡的韵味创造了一首纯洁初恋的赞歌,是创作者追求自由爱情纯粹性的伦理理想的影像化呈现。
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生成机制最为重要的表现是神圣化。仪式本身具有神圣性,电影影像通过动作、造型、摄影角度、景别、蒙太奇、表演和音乐等视听手段强化仪式神圣的“光晕”,以夸张性、震撼性表达创作者的伦理观。例如,《甘地传》(英国,1982)开场气势恢宏的葬礼仪式是对甘地为民族解放奋斗一生的高尚道德的肯定;又如《末代皇帝》(意大利,1987)的登基大典,将清政府虚假的荣耀植入到溥仪幼小脆弱的内心深处,成为溥仪人生中错误伦理选择的“童年阴影”。在《秋之白华》(中国,2011)瞿秋白就义段落中,瞿秋白身着妻子杨之华亲手给他缝制的衣裳,轻声哼唱着《国际歌》漫步着走向刑场,选择花团锦簇处作为自己的墓地,鲜花、绿竹、仰拍、慢镜头等影像元素和影像语言将屠杀转变为神圣的国葬典礼,将刑场上的国民党官兵从死刑执行者角色转换成典礼的参与者。
电影的仪式化影像是对人类社会各时代仪式文化的纪录、展现和想象,但是,纪录、展现和想象绝不是仪式化影像的终极目标,从语言学角度来观察,仪式化影像的所指更趋于表达创作者的伦理诉求,其创造出来的是含蓄蕴藉的伦理意蕴,引发观众对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性的伦理反思。
二、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基本表达范式
人类的仪式丰富多样,根据仪式所属的社会范畴,可将仪式化影像区分为宗教仪式化影像、民俗仪式化影像和政治仪式化影像,从中可考察仪式化影像伦理性的基本表达范式。
(一)宗教仪式化影像
宗教在人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涂尔干·埃米尔认为“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他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10]也就是宗教仪式具有显著的伦理诉求,而“正是在仪式中——就是使行为神圣化——认为‘宗教概念是真实的’和‘宗教指令是合理的’这类信念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11]也就是说,宗教仪式具有宗教伦理询唤作用。
电影很早就有宗教元素了。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考证出“最早拍摄《基督受难》(法国,1897)的是卢米埃尔公司。”[12]由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世界电影史上存在大量宗教元素、宗教故事电影。宗教元素也较早地出现在中国电影中,例如,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摄制的由梅兰芳主演的戏曲片《天女散花》(中国,1920)就是佛教故事戏曲电影;上海影戏公司但杜宇导演的《海誓》(中国,1922)也有天主教教堂结婚仪式的场景。从1928年到1931年由《火烧红莲寺》(中国,1928)引发的武侠神怪片浪潮开始,宗教也逐渐成为此类型电影影像中重要的视觉元素。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电影中也有一定的宗教元素,如《盗马贼》(中国,1985)、《静静的嘛呢石》(中国,2005)、《冈仁波齐》(中国,2017)等都将宗教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和视觉奇观。
宗教仪式化影像具有伦理性。《基督最后的诱惑》(美国,1988)和《耶稣受难记》(美国,2004)都是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宗教电影。在《基督最后的诱惑》(美国,1988)中有洗礼、圣餐礼等仪式,并将耶稣受难仪式化;而《耶稣受难记》(美国,2004)主要展现了耶稣被捕、受鞭刑、受难之路、骷髅山殉难的过程,同样将耶稣受难仪式化了。两部电影中的仪式化影像——特别是耶稣受难的仪式化影像——突出了基督教义中人对上帝信仰的宗教伦理命题。又如《春夏秋冬又一春》(韩国,2003)展现了一位僧人童年时期对动物所做的恶,其青年时期又经不起世俗诱惑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在影片的高潮处,刑满回寺的中年僧人拖着佛像上山顶供奉的苦行仪式化影像与前文链接,象征性地表达了人生悟道、赎罪艰难的宗教伦理观。《天下无贼》(中国,2004)的寺庙里信徒烧香拜佛仪式化影像段落,表现了王丽对过去犯罪生活的诚心悔悟,而在后续的叙事中,王薄也在王丽的感召下,以自我牺牲来成全傻根“天下无贼”的社会理想,实际上暗含了作者对佛教求善理想的伦理认同。《我的个神啊》(印度,2014)中外星人PK看到的各宗教派别的仪式成为对人类因信仰不同而导致冲突的反思性符号。
大量电影中的宗教仪式化影像的目的正是创作者希望通过这些影像实现宗教伦理询唤,或是借用宗教仪式中的宗教伦理实现世俗伦理询唤,宗教仪式化影像显著地突出了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
(二)民俗仪式化影像
“民俗是在民众中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是被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3]民俗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自古以来,各民族、各地区的岁时民俗,如宗教性节日、生产性节日、年节、文娱性节日,人生仪礼,如诞生、成年、婚姻、丧葬,以及信仰民俗,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都离不开仪式。
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美国,1922)开创了民俗电影的先河,但电影中的民俗影像决不仅仅满足于记录功能,“民俗电影要让观众反视自己的生活,从银幕上找到相似的地方——他们自己的过度礼仪、物质文化、饮食以及民族性如何对他们的生活起作用,又如何与所看到的影片记录相呼应。”[14]可以说,电影中的民俗仪式化影像往往伴随着对民俗文化的伦理性反思。
一方面,民俗仪式化影像是创作者反思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异化,呼吁回归“真”与“善”的伦理文化符号。例如,《教父》(美国,1972)开场,在维托·唐·科里昂的小女儿康妮意大利式盛大传统婚礼上,老科里昂等人在书房中筹划的阴谋,象征着这群意大利移民受到美国利益至上价值观影响后的卑劣与野蛮。《南京!南京!》(中国,2009)中日军的“召魂祭”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文化屠杀。《阿凡达》(美国,2009)的祭祀场面,利用原始巫术信仰仪式,表达创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性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利益至上等伦理问题,也促使电影创作者时常调用民俗仪式化影像来怀想对传统伦理关系的回归。如在《入殓师》(日本,2008)中,日本葬礼的传统仪式成为电影影像的“主角”。在该片的高潮处,电影影像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小林大悟为曾经抛妻弃子的父亲行入殓仪式的过程,表达了创作者对东方传统伦理的深切怀念。《入殓师》在全球范围的成功,正在于它民族化地融入了对西方当代社会家庭伦理问题的反思。
另一方面,一些民族和国家的部分电影创作者把民俗看作是阻碍该民族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异质性力量,因此,他们试图在电影中进行伦理文化的除旧迎新。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样的观念也被部分电影创作者所认同。例如,中国第五代导演就特别热衷于民俗仪式化影像的呈现。《黄土地》(中国,1984)中的“祈雨”仪式,利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语言造就震撼性的“游离情节”,并与之前解放区的“腰鼓阵”仪式化影像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批判隐喻意义直指中国农民传统观念中的天人关系的文化落后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1991)中的“捶腿”“挂灯”“封灯”等仪式化影像,象征着中国封建婚姻关系对女性的压迫。进入新时代,这种利用民俗仪式化影像进行伦理反思策略也得以传承,如,《气球》(中国,2020)的葬礼仪式化影像就象征着部分少数民族女性在父权、神权的双重压力下,对生育无从选择的伦理困境。
民俗仪式化影像时常是创作者从其所处时代的伦理精神出发对其民族和国家存在的伦理问题的反思,民俗仪式化影像凸显了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
(三)政治仪式化影像
在政治语境中,“仪式庆典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话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构对政治世界和身处其中的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的理解。”[15]王海洲认为,政治仪式是人们对政治权利的情感和认知的中介,他总结道:“政治仪式的心理机制在情感和认知的具有关联性的双重作用下,能够有效干预权力生产的实践原则和过程,从而达到合法性建构的终极旨趣。”[16]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合著的《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也早已指出“这部影片所投射的政治意义不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话语,而是一种道德话语。”[17]可以说,政治仪式进入电影后形成的政治仪式化影像可以通过引发观众的伦理情感,实现个体对某种政治观念和行为的伦理疏离或认同。
《大幻灭》(法国,1937)的战俘营中,德国军官向法国战俘宣读战俘营管理规定及对战俘营各种禁忌的介绍的仪式化影像,象征着战争毁灭了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广岛之恋》(法国,1959)中,电影摄制现场所再现的广岛百姓反核示威游行的仪式化影像,表现了战争对人造成的身心创伤的持久性。在《莉莉·玛莲》(德国,1981)中,600万纳粹士兵每天晚上在收音机前聆听维莉演唱的《莉莉·玛莲》,电影将维莉演出所受到的追捧与战场的残酷镜头并置,歌曲《莉莉·玛莲》成为抚慰前线士兵心灵的“战前仪式”,链接着在外作战的士兵的乡愁,也象征着维莉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在这些反战电影中,仪式化影像寄托着创作者对特定时期极端政治行为泯灭人性的伦理性反思。
然而,伦理认同模式始终是电影中政治仪式化影像的主流策略。好莱坞电影在对外输出美国价值观时,常常采用这一方法。例如,梅尔·吉布森电影《勇敢的心》(美国,1995)、《爱国者》(美国,2000)、《我们曾经是战士》(美国,2002)、《血战钢锯岭》(美国,2016)等,在历史叙事中通过政治演讲、战前动员、追悼仪式、战场上血染美国国旗等仪式化影像场面及影像元素将美式自由主义、美式个人主义、美式战斗精神和美国救世精神的价值观伦理化处理,潜移默化地塑造全球观众对美国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伦理认同。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中国电影,为引导人民对党的政治观念和行为的伦理认同,也常常娴熟地使用仪式化影像。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国,1949)结尾处的通车典礼中,红旗、工作服、列车、剪彩、人们的欢呼,高亢的歌声等仪式化影像以及侯占喜提出入党的对白,象征着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建立起一种新型政治伦理关系。又如,从《中华女儿》(中国,1949)、《董存瑞》(中国,1955)、《英雄儿女》(中国,1964)、《烈火中永生》(中国,1965)等“十七年”电影中发展而来的革命英雄“牺牲仪式化影像”或“就义仪式化影像”也象征着英雄与国家的政治伦理关系,这种仪式化影像至今依然在中国银幕上表现出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基于仪式化影像的基本范式的考察,我们认为,电影的仪式化影像是电影审美伦理表达的中介,它在电影中被造型化展示,其意图是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达创作者的伦理观,引发观众正/负两面的伦理情感,从而引导观众的伦理认同或伦理疏离。
三、仪式化影像在影像叙事中的价值与意义
艺术本身具有伦理性,以聂珍钊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派提出文艺起源于人类的伦理诉求,其核心动力是因为人类具有“斯芬克斯因子”,人类需通过文学克服“兽性因子”,拥抱“人性因子”。中国主流艺术观也认同艺术美和伦理善的统一性,“艺术美既包含有道德活动的积极成果——善,又包含有认识活动的积极成果——真。”[18]同时,仪式本身也是具有伦理性的活动,仪式进入影像后也就成为仪式化影像,仪式化影像也随之具备了伦理性,它在叙事和表现中会产生伦理道德判断,凸显伦理思想内涵。
(一)凭借视觉造型隐含伦理判断
仪式化影像可以产生和强化造型性功能,提升观赏性。视觉造型性是电影艺术的重要特征,电影用影像叙事,其中人物的服装、化妆、表演以及场面、道具、构图、光线、色彩共同构成电影造型语言元素。创作者的伦理观要通过仪式化影像来表达,他们常常会调用视觉造型手段实现具震撼力的审美效果,在提升电影的观赏性的基础上进行伦理道德意识的传达。
《鸦片战争》(中国,1997)的“虎门销烟”仪式,在暗黄的整体色调中,海上日出、旗帜飘扬,官员们一字排开,林则徐面朝大海祭天,工人们赤膊劳动,礼炮齐响,销烟池烟雾缭绕,特别是俯拍销烟池的全景和远景镜头,创造了油画感和视觉冲击力。从而,电影中壮美的“虎门销烟”仪式化影像被提升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赞歌。又如,《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美国,2016)中,在橄榄球场的授勋仪式上,灯光由暗变亮,烟花齐放,舞台干冰释放着滚滚烟雾,在聚光灯的照射下,军乐队和战士们在歌舞表演中齐步前行,授勋仪式与大型娱乐文艺演出的混搭既具观赏性,也构成了电影的反讽意义,这样的授勋仪式极大地贬损了以比利·林恩为代表的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战场上拼死战斗的价值,传达了华裔好莱坞导演对伊拉克战争的伦理判断。再如,《金刚川》(中国,2020)中的高炮排长张飞与美军轰炸机同归于尽,在炮台上壮烈牺牲后,创作者在造型上将张飞及其炮台雕塑化;同样的造型处理方法也应用于电影《长津湖》(中国,2021)中的“冰雕连”的场面中。两部电影中,这种仪式化影像中的特殊造型处理,体现了创作者对革命先烈为国家和平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的伦理价值判断。
(二)通过影像语言创新展现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
仪式化影像可以产生和创造象征(隐喻)意义,创新影像艺术语言来突出伦理性。象征(隐喻)是文艺作品的特征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艺术作品就具有象征性品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分析了隐喻的特征;康德提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重要命题;黑格尔深刻地分析了象征的内涵,并把象征型艺术划为最初的艺术类型;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象征是潜意识的机制,而文艺创作采用的正是这一机制;卡西尔直接将人类定性为“象征的动物”。在电影理论史上,俄国形式主义、苏联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符号学也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阐述了电影影像语言的象征(隐喻)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创作者对影像艺术语言象征(隐喻)代码的新发现,就意味着影视艺术语言的创新,因此,具有象征(隐喻)效果的仪式化影像,往往在影像艺术语言创新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前苏联蒙太奇学派在仪式化影像中就创造了示威游行工人与河流解冻画面联接的抒情蒙太奇(前苏联,《母亲》,1926),将屠杀工人的仪式与屠宰场宰牛剪辑在一起的杂耍蒙太奇(前苏联,《罢工》,1925),谢尔盖·爱森斯坦还在《战舰波将金号》(前苏联,1925)的“敖德萨阶梯”中创造了利用蒙太奇延长时间的手法。又如,中国第五代导演通过中国式仪式化影像,开创了新的电影风格,《一个和八个》(中国,1984)、《黄土地》(中国,1985)、《盗马贼》(中国,1986年)、《红高粱》(中国,1988)、《晚钟》(中国,1989)中的仪式化影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前中国主流电影,如《古田军号》(中国,2019)中贯穿全片吹军号的仪式化影像,《守岛人》(中国,2021)中的升旗台和升旗仪式化影像,《革命者》(中国,2021)中的牢房和就义仪式化影像,创作者都为能够更好地表达其伦理观而重视在其中创新影像艺术语言。
(三)以倾向性的所指凸显伦理思想内涵
仪式化影像可以丰富和提升影像的思想性,从而凸显其伦理内涵,催生经典影像文本。在艺术史上,凡是被奉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无不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一百多年电影历史中的那些经典电影也时常会超越时间的长河,感召着当代观众,而仪式化影像的伦理性指向正是这些经典电影思想内涵提升的有力手段。
《黄土地》(中国,1985)的“祈雨”仪式化影像很好地表现了大众的蒙昧和憨憨的觉悟,“婚礼”的仪式化影像则表现出大众麻木以及翠巧反抗封建伦理的悲剧性。又如《守岛人》(中国,2021)中不断重复的升旗仪式,把主人公护岛如家、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精神传达得形象真切,丰富和提升了电影影像的伦理内涵。在电影史上,从《淘金记》(美国,1924)中流浪汉查理吃皮鞋的“餐前”仪式化影像的阶层身份象征,到《2001太空漫游》(美国,1965)中象征人与工具的关系的猿人拿起武器的“进化”仪式化影像,再到《你的名字》(日本,2016)中怀念故土、企盼永恒爱情的丰穰祭;从《桃李劫》(中国,1934)中象征旧社会毁灭青年人生的毕业仪式,到《芙蓉镇》(中国,1987)中象征极端政治压抑人性的扫街仪式,都提升了电影的伦理思想内涵。
电影中的仪式化影像的首要功能是人类学价值,它纪录了人类的仪式,是人类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时代记忆。影视人类学认为,影像是“反映思想和感情的文化前提和文化模式,也可影响观众的行为”[19]。例如,中华民族历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中国,1988)、《建国大业》(中国,2009)、《我和我的祖国》(中国,2019)等主旋律电影中得以复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引导观众对新中国政治产生伦理认同。其次,仪式体现了一个民族伦理文化的独特性,同样,一个民族电影中的仪式化影像也是民族电影的标志。再次,电影中仪式化影像往往浓墨重彩、美轮美奂,从侧面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伦理意识及电影工业水准,可以说,仪式化影像是独特的审美伦理创造。最后,电影中的仪式化影像最重要的功能是伦理询唤。伦理道德是特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及其后理论,如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等都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文艺作品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载体,往往采用伦理道德询唤策略,而仪式化影像无疑是实现伦理道德询唤的表现性高潮。
在人类漫长的文化历程中,仪式是社会群体伦理诉求的体现,而电影将仪式作为其影像表达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时,其影像就具备了伦理性的内涵。电影通过宗教仪式化影像、民俗仪式化影像和政治仪式化影像的呈现,以极具视觉造型性的影像审美创造,审视时代伦理精神,表达创作群体的伦理理想,因而仪式化影像具有伦理性。就新时代中国电影来说,需要在继承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守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东方伦理意识,创造出更多极具民族性、时代性,含蓄蕴藉、意义丰富深刻的仪式化影像,助力中国影像文化以高品质美学境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