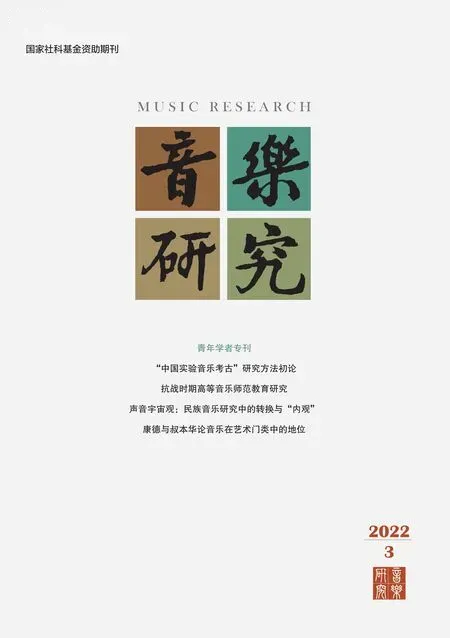“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研究方法初论
文◎朱国伟
中国音乐考古学若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发掘和研究为学科成立标志来算,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从刘半农清宫乐器测音的实践来算,则已将近百年。它在新时期涌现大量成果的同时,出现了一些研究瓶颈。比如,在研究对象上,古代音乐文物数量、种类虽然众多,但是目前已出的音乐考古学成果聚集性地呈现在编钟研究之上,而在编钟的研究方法上,目前的研究模式又趋于固化。
中国音乐考古研究所用方法,除常规历史学、文献学方法之外,就是考古类型学与测音及音列分析方法。(1)历史学、文献学方法基本没有“音乐学”特色,与早先金石学传统有关。(2)考古类型学方法通过李纯一、王子初、方建军等前辈的探索,已经摸索出许多与器物音乐性能息息相关的类型划分及形制分析方法,意味着在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音乐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应用,已在普通考古类型学基础上向着音乐学方向有了明显推进,但其仅适用于大批量存在的文物类型中,涉及音乐性的类型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编钟。(3)测音及音列分析,是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中逐步完善起来的一种最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已成为音乐考古学者区别于多数普通考古研究人员,使音乐考古学者有机会参与考古发掘单位乐器课题研究的一项重要技能,也是彰显中国音乐考古研究中“音乐性”的重要手段。然而,测音研究方法有着先天的条件局限,即只能施用于耐久性材料制作的不易损坏的乐器遗物。目前可用作测音的仅有骨笛、埙、钟、磬等少数几类,例如丝、竹、匏、木、革等类器物不适用。在适于测音的乐器中,骨笛易在测音时发生损坏,磬出土时多已破裂,故原件测音案例并不多见,仅针对有设置音高的编钟和未损坏的埙来进行。
这样看来,中国音乐考古学赖以独立存在的学科方法所能施展的范围比较有限。当然,目前音乐考古新材料不断涌现,利用传统历史学、考古学方法结合音乐学方面的测音与分析,研究工作仍可以不断展开,但方法支撑方面的短板仍然存在,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学科进步。近年来,学科方法的扩充,成为中国音乐考古学者在研究实践中努力突破的重要课题。在马王堆汉墓乐器、曾侯乙墓乐器和贾湖骨笛等重要考古发现的研究和复制工作中,复原实验的方法有了丰富的前期经验积累,①有关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前期积累,见另文《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研究:历史与展望》(待刊)。这种方法在方建军、王子初等学者其后的研究中不断得以提升和总结。方建军不仅对出土乐器演奏、图像表演姿态等复原相关的实践内容进行关注,还专门提出“复原和模拟实验”研究方法②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版。王子初最近的研究成果,也集中介绍了他本人几十年来的系列复制实验工作,首次提出了“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学”的建设问题。③王子初《碎金风华:音乐文物的复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2——452 页。2016 年,笔者开始关注以复原研究为基础的实验音乐考古方法,④在第8 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年会上的发言《实验音乐考古的探索及应用展望》。并对国外相关研究有过梳理。⑤参见朱国伟《从实验考古到实验音乐考古————概念、分类及国外研究综述》,《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4 期。相较国外,中国的实验音乐考古有着自身的特色和巨大的应用前景,成为中国音乐考古研究方法的有力补充。
一、定义与对象
实验音乐考古的名称,衍生于国外“实验考古”方法,其基本特征是以考古出土物为对象,以“复原”的手段探知音乐文物的历史信息和音乐功能。⑥本文在只用到“复原”一词时,一般将“复制”含义包括在内。有时为强调二者有所不同、或强调“复制”发挥特定作用时会使“复制”“复原”二词连用。有关其区别,本文主要采用王子初的观念(参见注③“绪论”,第4——6 页)。方建军对二词解释有所不同,其创造性地将复原分为可视性复原与可听性复原,亦颇有价值(参见注②,第255 页)。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述及研究实践,可将实验音乐考古研究定义为:根据考古资料及相关数据,通过对文物本身和制作过程的复原或模拟,来实现对音乐文物或相关事象的材料、结构、成形过程、功能,以及声音特性/音乐性能等方面的认知或检验,进而在古代音乐相关技术和音乐行为方面得到更深的实证性认知。⑦同注⑤。
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与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吻合,即为古代人类社会音乐生活遗留下来的,或是能反映古代人类社会音乐生活情况的实物史料,包括音乐遗物(如乐器、乐俑、音乐图像、音乐书谱等)和音乐遗迹(如乐器埋葬单位、音乐文物作坊及声音相关的古代景观和建筑构造等)。⑧关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本文在综合王子初、方建军所著学科概论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参见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25 页;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第23——64 页。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对象的时间范围可从人类产生开始至清代,空间范围为中国境内发现的实物史料,遗物方面的材料以考古出土为主,以传世文物为辅。当然,研究这些对象的同时,不必排斥其他相关材料的结合应用(如文献和民族学材料),但其核心对象应为音乐相关实物史料。
从郑觐文的古乐器仿制,到现代严格按原出土物翻模复制,再到带有音律研究目的的骨笛、琉璃磬等乐器的复原制作,⑨凌律《大同乐会民族乐器图片简释————兼谈大同乐会和创办人郑觐文》,《乐器》1982 年第1 期;陈正生、沈正国《国民大乐————大同乐会郑觐文主制乐器评介》,凤凰出版社2011 年版。胡家喜、陈中行、张宏礼《采用国产有机硅橡胶翻模复制曾侯乙墓编钟成功》,《江汉考古》1981 年第s1 期。童忠良《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中国音乐学》1992 年第3 期;孙毅《舞阳贾湖骨笛音响复原研究》,《中国音乐学》2006 年第4 期;王子初《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艺术百家》2016 年第2 期。针对古代音乐文物对象的复原实验,经历了长期的探索阶段,产生了一批相关成果。“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提炼及运用,对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拓展、深化有着重要意义,它契合了中国音乐考古学发展中亟需扩展应用型方法建设的现实需求,势必会为中国古乐复原研究和复原作品的产生,奠定良好的实证理论基础。
二、手段分类与实施要点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实验音乐考古是通过复原实验的手段,来实现对音乐文物制造历史信息和古乐器的“音乐性”等相关知识的揭露。
笔者曾对国外实验音乐考古实践进行过分类和综述,现将实验音乐考古分为外形复原实验、制造复原实验⑩笔者在《从实验考古到实验音乐考古》一文中,依照国外“full replicas”的称谓译为“全真复原”,因复原是基于研究的推测,仍有非历史本体性,而这一层次的核心特征实为制造过程的复原,故舍弃“全真”一词,而改用“制造复原”的表达。、功能复原实验(演奏法研究)和体验性复原实验(编创型古乐复原)四个层次。
(1)外形复原实验。主要是对乐器基本结构与外形、装饰的复原实验。这一类别重在外形的复现,而有关其制造方法、内部细节甚至材料方面,可因研究目的的不同分别采用替代手段来实现。①目的在于复原一套供大众参观或教学展示的古代音乐文物,制造方法上便可采用现代科技和手段达到快速完成器物成型的工作。②如果只是柜台方式的展示,可以完全不考虑能否发声的问题,那么材料亦不苛求原材料,用近似材料便可(此类缺乏“研究”的目的)。③如若研究目的为通过复原实验来实现对出土残损音乐文物原件的安全修复或完整外形复原,则实验所用复原件除了残损部分连接处外,其他部分可用简单材料粗略复原,对残损连接处和缺失部形状进行细节分析,研究修补和复原方案,最后择其合理者施用于原件(要补充的缺残部分却不一定用原材料补充,在文博人员考古修复工作中,就经常用石膏等材料塑造缺损部分的外形以示其并非出土时固有)。④如若研究目的为乐器的音响印象,那么内部结构和发声体材料都需要尽量符合原件数据,但在制造方式上仍可采用现代工具做成,在细节程序(如部件拼接方式)上也不必拘泥古法。曾侯乙墓发掘后,各方专家联合攻关,用科技手段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研究,最后成功复制,⑪湖北省博物馆《经多学科研究,曾侯乙编钟复制已基本成功》,《江汉考古》1981 年第S1 期。即可视为外形复原实验的典型案例。
(2)制造复原实验。重在制作过程的复原,是普通实验考古最为核心的方法手段。如果说外形复原实验重在对考古对象成品的复原,制造复原实验则是重在对制造行为的重建。其研究目的主要是对古人制作音乐文物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实验模拟,以对器物选材、结构功能以及制造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的探讨,进而对古物制作的难度和功能优劣进行评价。操作步骤通常为:①对原器物材料、结构进行检测,对制造工艺进行推测;②制定复原方案,包括选取符合时代特征的制作工具、方法和生产条件;③进行复原工作;④评价复原成果。严格按原材料、原手段复原出的乐器,也应当具备接近历史样貌的发声条件,可供音响情况的测量和评价研究。譬如,进行编磬复原实验,首先可以对古人制出一块磬坯、调出一块成品磬的难度进行认知;而在手工制磬过程中,还不可避免会因内部结构破坏出现发音不佳的磬体,通过实验计算古法制磬的成品率高低;得到的古人制磬难度评价,可能会让我们对编磬这种表面不珍贵的材料之所以能与青铜钟并列成为乐悬重器产生新的认知。
在手段上,其精髓在于研究古代音乐文物的材料性能、器物结构和制造技艺,并尽最大努力依原样进行实验制作。在实验过程中,制作的依据和制作过程须详实记录。有多种可能方案的应逐一实验,并进行评价。遗憾的是,国内已有的严格追求历史还原的音乐文物制造复原实验极少,公开发表的尚未见到(国外则有大量案例)。相近的尝试在贾湖骨笛复原制作中有所体现:尝试用骨质材料模拟复原贾湖骨笛的实验案例已有多例,⑫孙毅《舞阳贾湖骨笛音响复原研究》,《中国音乐学》2006 年第4 期。但钻孔法大多采用现代工具和技术;有尝试不用现代仪器钻孔的,但又在选材和技术选择上不做推敲。⑬李寄萍《骨笛仿古实验及分析推测》,《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 年第2 期。这些尝试都重结果音响,而轻复原过程记录,因此也都还未达到实验考古要求的“全真复制”(full replicas) 标准。为评价骨笛的制作工艺、成本,甚至是研究骨笛取音的过程,这一工作手段仍然有必要继续推进。
(3)功能复原实验。重在对乐器演奏功能进行探索的复原实验。其所依托的复原实验品,一般采用第一种外形复原便可实施。如仅为探求演奏姿势与手法,则仅需做到较好的外形重建;如需同时探讨演奏法对音响的影响,则需重建包括内部结构在内的整体造型;而如果制造过程对演奏效果可能产生影响的话,则最好采用上述第二种制造复原所得的乐器进行实验。演奏功能实验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古乐器的演奏姿势、演奏手法、演奏法与音响之间关系等方面。其操作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须制定复原方案和演奏实验方案,通过在复原乐器上进行有依据的或充分合理的实验(应基于历史文献描述和历史图像等资料进行研究判断),对乐器的演奏性能进行实证性的探讨。如方建军曾对先汉笛子工艺进行的研究,⑭方建军《先汉笛子的制造工艺和音阶构成》,《中国音乐》1988 年第3 期。以及后来他指导研究生吴桂华做中山寨骨笛、王丹彤继续做东周和汉代笛的实验。⑮吴桂华《贾湖与中山寨出土史前骨笛新探》,天津音乐学院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王丹彤《中国出土东周和汉代笛类乐器模拟实验与复原研究》,天津音乐学院2017 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些实验虽都没有按“制造复原实验”方法去做(因他们的实验目的在于探知乐器性能而非乐器制造),但都对汉笛的演奏方式和演奏能力进行了实验和探讨,可视为典型的功能复原实验音乐考古做法。王子初的玻璃磬复原实验,则扩展了这一研究维度,借助多学科力量,证实了汉代玻璃磬可投入实用演奏的可能性。⑯王子初《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出土仿玉玻璃编磬的复原研究》,《艺术百家》2016 年第2 期。
(4)体验性复原实验。是在上述复原和演奏探索之后,为了进一步探索音乐文物的音乐表现效果,进行的音乐整体性评价的复原实验。从音乐文物类型讲,乐器类文物重在探索某种乐器可达到的音乐表现力程度,或与古文献所描述的表现力效果进行实验比较;成批同出的乐器,则可通过实验探索合奏效果;立体造像或平面图像类的音乐文物,可实验其所描绘的场景性音乐效果。从实验应选用的音乐素材讲,实验音乐考古所用来实验的音乐素材,应追求古意,可参照以下寻找音乐素材的顺序:有同时代古谱者,用古谱用乐;无同时代古谱者,用后代标注为此时代的古谱用乐;无此时代古谱者,用后人创作此时代题材乐曲(清代以前);都无古曲者,用现代依古乐素材编创的音乐。但由于古代真实音响的不可得,这类复原实验总体上仍都可视为编创型古乐复原。其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古代音乐效果的积极探索与加深认知,另一方面也非常有助于古乐作品在当下的开发与应用。如曾侯乙墓发掘后,首先通过科技考古手段,对编钟及其他乐器进行了材质成分和铸造技术的研究,进而对大部分乐器进行了复制(这种复制是用现代乐器制造手段制成的,但对材质、尺寸等方面的还原度很高)⑰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多学科协作攻关的成果——曾侯乙编钟复制的研究与试制基本成功》,《江汉考古》1981 年第S1 期。;其后基于复原乐器,进行了曾侯乙墓乐器声音性能和音乐表现能力的探索,得到了很多曾侯乙墓“乐队”层面的音响效果认知,也产生了一批可供音乐史教学使用的音像作品。⑱邹衡、谭维四主编《曾侯乙编钟》,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5 年版,第475——518 页。纵使这种探索在当时来说只是现实需求驱动而非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引导促成,但它仍然为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的探求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三、方法优势及应用原则
对中国音乐考古研究来说,实验音乐考古方法,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①在研究过程上,依其实证的手段,有利于研究的步步推进;②在理论成果上,能广泛涉猎各类古代音乐文物,并使研究对象得到制造技术和音乐性能的多层面揭示;③在成果应用上,通过复原实验,能卓有成效地补充古代音乐史中的“有声”成分。
首先,实验音乐考古具有实验考古的一般属性,其性质决定了实验音乐考古研究,须是一种带有科学实验性质的研究。科学实验的重要特征,包括研究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比如,对制作过程要求最高的音乐文物制造复原实验,在研究过程中应对每一步工作进行科学记录,包括选用的方案、材料,使用的工具,操作的步骤,甚至是手法和耗时等,以供第三方或后继研究者检验、改正和推进。而对于演奏研究方面的功能复原实验和音乐表现力研究方面的体验性复原实验,实验过程记录也应成为必备要求,如果只是简单地罗列演奏和表演效果的结果,则会让研究失去证据支撑,对演奏法与表演效果研究的前提设置及合理性失去判断依据,也就大大减弱了研究的可信度。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一直提的“复原”,并不可能是历史的完全重复,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对于实验音乐考古,无论是外形、声音还是效果,“严格复原”都只是追求,“复原永远只是具有相对性”⑲李幼平《大晟钟的复原研究与仿(重)制试验》,《黄钟》2015 年第4 期。,但对于逼近历史真相的追求和研究永远是有价值的。实验音乐考古的实证方法,正有利于步步为营,逼近真相。
其次,在研究对象方面,实验音乐考古方法,虽然仍在古乐器研究上最有应用空间,但是也完全能运用到其他多种音乐考古对象中。如音乐图像提供的演奏姿态信息、背景声景信息、乐器组合信息,以及乐舞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合作信息,都可以成为实验音乐考古的实验对象。考古对象可总分为遗物与遗迹两大类,乐器与音乐图像都属于遗物类,而远古人类活动遗址、墓葬、戏台及建筑等对象都属于遗迹类。中国音乐考古界对音乐考古遗迹的关注一直较少,这与国外这一方向的大量研究成果形成较大反差。国外如石圈遗址的声学研究,史前遗址洞穴绘画与回声及音声仪式的关系,遗址中的塔建、墓室等建筑的声学分析,以及一些石骨器遗存的乐器可能性辨析等,都有大量研究成果。⑳〔英〕鲁珀特·蒂尔著,朱国伟译、李子晋校《跨学科视域下的声音考古》,《中国音乐》2021 年第4 期;王歌扬《国外史前音乐研究述评》,《音乐研究》2021 年第3 期。由于国内音乐考古学者现场参与考古调查较少,考古人员的工作中又较少关注声音现象,所以导致这种成果很少见到,目前有一些戏台建筑遗址的声学研究,则时代偏晚。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还大有可为,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特殊建筑,以及历史时期的祭祀遗址,还有与音乐密切相关的特殊地点(如华清宫梨园遗址)㉑㉑ 方建军《论华清宫梨园遗址及有关问题》,《交响》2013 年第4 期。,都可以介入声学手段,通过模拟手段来探究其在使用中的声音现象。而这种研究,正需要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支撑。在这一方面需要注意的原则是,忌过多想象或牵强的联系,针对遗址与声音的关系,还需有一定证据的支持;其次是祭坛、宗庙等可能包含音声仪式的遗址,其他则需要一些附加的史料证据来证明研究对象与音乐可能的关系。
可以想见,实验音乐考古的研究成果,是音乐考古学研究成果中最易于向社会进行应用、推广和宣传的成果类型。一件乐器或一幅音乐图像的出土,对于现代人(无论内行或外行)来说最想了解的,就是它所隐含的声音效果如何。而大多数实验音乐考古的目的,正是朝着“声音”前进的!近年来,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SGMA)已将实验音乐考古,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研究动向反复进行强调:2018 年该学会首次组织召开了“实验音乐考古专题研讨会”;2021 年末刚刚举行的第11 届年会,专设了实验音乐考古专题环节;2021 年3 月在意大利举办的(大致也是由该学会成员作为主要发言人的)“古代乐器:方法、结果、视角”(Ancient Musical Instruments: Methods,Results, Perspectives)网络研讨会,也与实验音乐考古息息相关。以上这三次会议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几乎每一个报告的最后都是复原的音乐效果展示,而且部分主讲人汇报的成果里面已经包含了出版的仿古音乐专辑或视频作品,部分则是在其开发的网页上进行长期运行推广,甚至还有基于音乐遗址的游戏软件开发。这些应用,无疑是对音乐考古和公众知识都有好处的双赢成果。国内目前在这方面的开发也早已起步。如曾侯乙墓出土后,其墓中大部分乐器都经复制或复原投入了演奏探索;其后河南博物院成立华夏古乐团,成功开发了一批基于古代乐器或图像而编创的古乐作品,时代从远古到宋代都有;近年武汉音乐学院的宋代怀古音乐,㉒㉒ 李幼平《怀古音乐:历史的真实音乐的善美》,《黄钟》2021 年第3 期。㉓ 李娇《〈唐宫夜宴〉为什么火了?》,中国作家网转载《文艺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329/c419389-32063129.html,2021 年3 月29 日。其中的部分也是基于古乐器与古乐谱的复原创作,带有实验音乐考古特征。上述很多作品,已然成为全国高校甚至中小学课堂中的教学短片,为原本无声的先秦音乐增添了炫丽的色彩。但这些复原尝试比较常见的现象是,音乐考古研究团队与音响呈现团队处于割裂的两张皮,各司其职,乐器研究成果就是理论成果,编创就是借助乐器形态进行创作或古谱配乐。这些成果无疑也是有正面社会效应的,但因“实验音乐考古”属性不够强,有时发生历史信息的错乱而不宜作为音乐史的教材使用。相信在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加持下,从“物”到“声”的音乐考古成果转化,会更加吸引人。因其更“有嚼头”,历史考古研究的呈现,能增加应用成果的知识普及维度;乐器功能探索的实验过程,能增加成果演示的互动趣味;编创中强调多元证据的融入,使作品编创更有文化数据的支撑。这些都能使编者不至无味,闻者更觉受益,特别在历史课堂中更经得起推敲和传播。
这种实验的原则,最好是专家学者与编创团队共同参与,在具体表演所涉音乐、乐器、道具、服装等最好都能得到学术论证。但是体验性复原实验在除硬性证据之外的部分,也可允许一定程度的“体验优化”操作,在特定场合的节目舞台转化时,也不是非要排斥现代声光电手段的结合。比如,将实验音乐考古的某个实践成果,做成类似于2021 年初火爆全网的《唐宫夜宴》的视觉形式,㉓㉒ 李幼平《怀古音乐:历史的真实音乐的善美》,《黄钟》2021 年第3 期。㉓ 李娇《〈唐宫夜宴〉为什么火了?》,中国作家网转载《文艺报》,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329/c419389-32063129.html,2021 年3 月29 日。也未必不可行,但在课堂上讲解时则需要有研究性的说明。当然,这属于实验音乐考古“研究”后的“扩展应用”部分了。
由上所述,实证性、普适性、应用性这三个特点,乃是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优势所在,并为其后续的推广应用、方法改进和成果转化提供了巨大潜力。
四、方法属性
“中国实验音乐考古”这一研究方法,脱胎于考古学的“实验考古”方法,隶属于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体系(以从事音乐学研究为主要任务),这是它的基本属性。
与“实验考古”这一名称相近,且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另一工作方法是“实验室考古”,二者因名称相近而有时被并列提及。“实验室考古”近年在中国被提出并迅速走热,指的是“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发掘清理,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㉔㉔ 杜金鹏《实验室考古入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 页。㉕ 同注㉔,第12、16 页。。
实验室考古与“科技考古”有较多的共通性,早期被视为科技考古的一部分,但杜金鹏等学者更倾向于将两者分离,认为实验室考古重在发掘清理阶段的手段运用,而科技考古重在考古研究阶段的手段方法应用,但共同点都是实验室科技手段的运用。㉕㉔ 杜金鹏《实验室考古入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 页。㉕ 同注㉔,第12、16 页。在国外尚未见到实验室考古的提法,但从大量国外实验考古案例不难发现,实验考古基本上不包含实验室考古的部分,实验考古重在复原与原生条件模拟,而实验室考古的本质是科学数据分析。在此环境下,国外称为实验音乐考古的研究,也基本上不纳入现代科技手段,而大量利用科学手段对出土乐器的研究,则不被视作实验考古。
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实验音乐考古工作有必要含盖部分科技考古的内容。这是在考虑实验音乐考古的性质、研究目的,再结合中国音乐考古实践探索历程所做出的建议。
首先,实验音乐考古与实验考古一样,核心及前提都是遗迹、遗物的复原和重建,但在实验音乐考古的复原中,很多对象离不开科技手段的介入。比如,各地出土的各类青铜钟,以及大云山琉璃编磬、丝竹乐器的弦质及漆料,这些文物的复原必然要先测定其材质,在复原过程和成品检验中,也需要用科学手段检测配方的吻合程度;且在不同层次的实验音乐考古研究中(见前文分类),对复原的手段要求不必一致,科技手段在某些实验中完全可以参与工作。
其次,从实验音乐考古内涵和目的看,它理应是通过复原实验,来实现对音乐文物制造和器物“音乐性”相关知识的揭露。如果一些音乐文物的制作本身就与古代科技息息相关(如编钟、琉璃磬),那科技的手段自然需要在复原实践中全程参与;如果通过科技的手段能更加精确地还原出土古物的形态,以供测定原形态的音乐功能,那么没有理由不去采纳。比如,竹木乐器的氧化和脱水会导致形态变异,可以通过实验数据进行尺寸和形态的还原。而实验音乐考古的演奏功能探索与表现力的体验,也可以鼓励人耳听觉体验结合科学仪器的测量进行描述,以促进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和量化描述,使已往难以客观表述的音乐体验,借助现代手段得以更具象地体现在研究成果之中。
最后,回顾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历程,借助科技手段的“复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并且或多或少地产出了一批实验音乐考古相关成果。与国外实验音乐考古一直是在实验考古的理论框架下发展出来的不同,历史上我们的复原与实验,并非在某种方法论指导下进行,而经常是在一些现实需要中进行,其中有的是为表演,有的是为展示,有的是为研究。但这并不排除部分内容很大程度上符合实验音乐考古的性质和目的,如前述曾侯乙墓乐器复制后的乐器演奏性能和表演空间探索。这样的历程证明,科技手段的介入只要运用得当,便仍有望做出符合历史研究需求的实验音乐考古成果。
实验音乐考古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的界定,在不违背实验考古精神的前提下,理当考虑中国已有的经验积累(编钟为重点),需要符合中国音乐考古的实际需求(多种类乐器的声音复现),更要考虑“音乐”这一对象的特殊性。这样一来,科技手段的适当介入无须排斥。事实上,笔者的上述定义也考虑了中国的实验音乐考古探索,即在界定上并没有排斥科技考古方法的应用。
当然,一门学科的方法,也必然有其施用范畴与固有规范:如将所有与音乐文物有关的“复原”都视为实验音乐考古的成果,这并不合理;同样,并非所有与音乐文物相关的“实验”都须归属于实验音乐考古范畴。实验音乐考古应具有实验考古的基础特征,㉖㉖ James R. Mathieu.“Experimental archaeology:Replicating past objects, behaviors, and processes.” BAR,2002; Christina Souyoudzoglou-Haywood, Aidan O’Sullivan.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Making, Understanding, Storytelling. Oxford: Archaeopress, 2019 ;John M. Coles.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1966:99, pp.1-20.即通过对考古材料或现象进行基于考古学证据的复原/重建,用以产生和检验假设,以提供或强化考古阐释的推理证据。
上述很多引证的早年音乐考古复原和演奏实验工作,要将其视作实验音乐考古时,其实需要我们人为进行“后期加工”,将原本分裂的多个环节组合起来,去提炼其对历史音乐情况的揭露作用。这中间必然缺乏实验环节的记录,如此便少了“实验”的科学性数据,也突显不出以“历史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针对性。同样一个工作,如基于古谱改编成先秦所见乐器的乐队作品,带有实验音乐考古性质的复原,会着力关注其历史信息的呈现效果;而商业性、娱乐性或政治任务性的复原,则须将潜在受众的感受排在第一位。这两种思路都有存在价值,也都对古乐知识传播有效果,但就音乐考古学术研究来讲,只能以前者为正。
另外一个有关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的属性问题是实验音乐考古与实验考古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牵涉到实验音乐考古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从实验考古中独立出来。西方基本都视实验音乐考古为实验考古的分支,中国实验考古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与音乐考古交集甚少。目前实验考古最重视的是全过程制造模拟实验,对遗迹、遗物的形成或制造过程研究起到较大作用,但它在音乐有关领域中基本只涉及乐器制造。基于以上中国实验音乐考古的发展历程及方法解读,笔者认为,实验音乐考古是实验考古与音乐考古(后者重考古对象的音乐学研究)的融合体,可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较之实验考古方法这个“母体”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尤其因“音乐”研究的特殊性强,故而针对这一方法有着后续的独立探索发展和讨论研究的必要。实验音乐考古的属性,是属于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脱胎于实验考古,但因具备较多特殊性而有了独立性。
结 语
方法只是手段,就音乐考古学或中国古代音乐史来说,一切能为音乐历史与文化的揭露提供帮助的手段都有价值。方法的理论研究及范畴限定,自然不是为了禁锢手段的多样化与创新,而是促进方法的规范化,以及通过研究和实践的积累使特定手段日趋成熟,使研究者有章可循并快速找到有效的操作路径。中国实验音乐考古方法,本身是为丰富和扩展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面向而提出的,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觉积累期后,已经获得了许多有益经验,于是便有了对其进行系统思考和学理定性的条件。
在本文写作期间,国际音乐考古学会(ISGMA)2021 年会在柏林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首日(柏林当地时间2021 年11 月1 日)便将实验音乐考古作为一个重要单元推出,中国学者方建军、王子初的主题发言,也都与实验音乐考古相关;其后会议的工作坊,也多与实验音乐考古相关。可以说,此次会议将这一研究方法又一次推向了关注中心。中国方面,笔者曾于2020 年12 月在中国矿业大学,组织召开“汉代乐舞研究与复原实践高端学术研讨会”,20 多位音乐考古研究与汉画像研究方面的专家齐聚讨论古乐复原问题,可视作实验音乐考古方法讨论的一次尝试;郑州大学中国音乐考古研究院预期举办第二届世界音乐考古大会,专列“实验音乐考古学研究”板块,惜因疫情延期。中外音乐考古界不断对实验音乐考古研究方法的关注与推进,有助于解决篇首所述“音乐考古材料不断增加”与“方法手段比较局限”之间的矛盾。
有了近现代中国已行的大量前期复原实验经验,以及国外实验音乐考古方法的探索经验,可以说,中国实验音乐考古方法建设的时机业已成熟。实验音乐考古因方法的实证性、对象的丰富性、成果的多元性等,在音乐文物制造、功能用途、舞台转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研究与开发前景。与传统音乐考古相比,实验音乐考古理念的引入,能大大扩展音乐考古的研究视角;与普通实验考古相比,又因其对声音、演奏法、音乐表现力的特有关注,而具有独立方法建设的必要。实验音乐考古研究的开展,能在做到学术深化的同时,也能为当代精神文化建设与艺术繁荣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