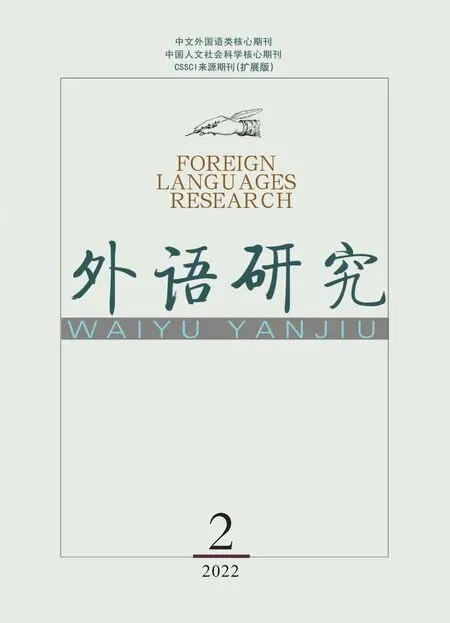鸠摩罗什之偈的译学史意义疏解
蔡新乐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0.引言
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343-413)生活在动乱年代,后秦(384-417)主姚兴(366-416)攻占后凉(386-403)之后,公元401年将其迎入长安并为之组织译场,他才有条件在人生的最后十数年安心致力于翻译。因而,他本人的著述不多。在他留下的两首偈中,其中一首是写给沙门法和(前秦僧人,生卒年月不详。其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卷五)的,本与其“嚼饭与人”之喻置于一处①。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理解,才可完整呈现什公的翻译思想。但是,此偈很多著作都不收录,学界鲜有关注或重视②。
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揭示,进而对此偈疏解的依据进行分析,试图探索其中的“心”和“明德”的意向以及此偈之于译学史研究的意义。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是学理探讨,无关信仰。
1.什公赠予法和的偈
什公赠予法和的偈③,《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2004:42)、《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朱志瑜,朱晓农2006:175)、《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朱志瑜等2020:48)以及《翻译论集》(罗新璋,陈应年2021:34)之中都未收录,尽管此偈与“嚼饭与人”出现在同一段话中。《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Cheung 2010:94),在这段话的译文之中把它删去。翻译思想史和理论史的专门著作,如《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王秉钦2004:11)和《中国译学史》(陈福康2011:13-15),对此偈也没有讨论。一般的研究,鲜有触及此偈。
此偈所在的段落,完整抄录如下:
初沙门僧叡,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什尝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④凡为十偈,辞喻皆尔。(释慧皎1992:53)
这段话既然收入什公的“嚼饭与人”比喻,又录此偈,理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将它删除,或不予理会,都是不应该的。
2.“心”和“明德”的意义疏证及其释解依据
“嚼饭与人”之喻要说的是,翻译不能不“改梵为秦”,但中文与梵文“辞体”毕竟不同,因而,汉译若是质直太过,所能起的传教作用有限,有时不免有“嚼饭与人”之嫌,毫无趣味可言,甚至是让人厌恶。
因很少有人关注,需要对此偈进行相应的疏解。此偈大致的意向是:只有用心体贴,才可促成沟通;人“心”本善,可以孕育“明德”,高升似“山”,因而能将佛教教义传遍寰宇。由此可见,此偈的核心意义是,有了这样的“明德之心”,佛教教义的传译才有基本的条件。
可以看出,“嚼饭与人”说的是“文体”,也就是语言表达的风格取向问题;“心德如山”之比讲的则是,人心之于佛经传译的作用。有此心,方有此译,也就能促成教义的有效、深入的传播。但问题是,佛教不是强调“四大皆空”吗?那么,它会认同“心”作为“实体”的存在及其之于交流的作用吗?这就需要对疏解的依据加以反思,进而才能确定,此偈的思想导向及其之于译学史研究的意义。
“由延”即“由寻”,是佛经中长度计量单位;“流熏万由延”一句强调,自性光明竖穷三际、横变十虚,无可阻碍。“哀鸾”是释迦牟尼(前565-前485,南传佛教或认为前623-前544,一说为前622-前543)语声的代称,也是佛法精神的体现,可谓佛祖功德成就的象征;“孤桐”指“古琴界”。这样,“哀鸾孤桐上”的意思便是,象征佛法的“哀鸾”之音,在琴瑟上演奏出来。
论者指出,此偈的意义是:“经过佛法的修行与培育,身心达到正道的功德。通过无碍的佛法在广阔的宇宙流转。佛法之声自琴瑟而起,妙法之音响彻于九霄苍穹”(霍旭初2016:104)。
论者的探索并不属于翻译研究,因而,其文其余观点本文不加援引。但应指出,其文并没有对“心”与“明德”进行专门的解释。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这两个关键词的意义进行疏解,进而才能对此偈之于译学史的意义做出分析和说明。
既然是什公所作的偈,他本人又是得道高僧,依照佛理来解释“心”和“明德”及其关系的意义,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让人纠结的是,这却不可行。首先,佛教本身坚持的就是,“万法皆空”。依此,“人心”和“人”都无所谓本身,无所谓有或无,因而无法按照一般佛理来加以理解。其次,什公本人的思想表明,依此而解,也是不可能的。任继愈(1916-2009)指出:“鸠摩罗什的哲学是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实体存在的,他的方法论又使他从不坚持任何肯定的意见,所以他始终不肯可否,但倾向则是否定的”(任继愈1985:471)。再次,“鸠摩罗什介绍的中观派般若思想,特点之一,是把空观贯彻到底”(同上:341),“它毫不含糊地表示:世界万有,实际上是由人随意创造出来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同上:376)。“万法皆空”,“心”也在其中,因而,依之作解自然是不可能的。最后,佛家坚持“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根本不相信人的理性思考、言说和推论等能力。《大智度论》云:“过一切语言道,心行处灭,遍无所依,不示诸法”(鸠摩罗什1991:168)。这意味着,即使承认“心”的存在,对之的疏解也一样是不可行。
佛家有“顿悟”之说,强调消除一切障碍,直达佛理,所谓当下现成,“立地成佛”。所以,从“空”到“空”,万物皆空,任何人类行为都很难产生意义。即使是“渐悟”也一样无法摆脱“万法皆空”的佛理。但是,跨文化翻译毕竟有其特定的导向、程序,要想使之成功必然要有出发点和归结处,而且也必采用一定的语言处理手段;最重要的是,人心必然发挥作用。因此,如上所述,不论是从佛教一般原理,什公本人的佛教观念,他主要传译的佛教典籍中的思想,还是佛家对语言和思维的否定,都可说明,他所说的“心”和“明德”无法依照佛理来解释。这样,要想对之进行有效的释解,就需另寻途径。
我们可能会以为,通过“不二法门”就可入乎佛理;“不二法门”大概是讲,佛家的“俗谛”(又称“世谛”或“世俗谛”)和“真谛”(又作“第一义谛”或“胜义谛”)同义。但是,“不二法门”,依什公所译的《维摩诘经》,并不是要突出“真俗一体”,而主要还是说一切皆空。如经中《入不二法门品》云:“妙臂菩萨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赖永海,高永旺2010:143);又曰:“识即是空,非识灭空,识性自空;于其中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同上:146)。“心空”“识空”,凡有“明德”之义。
这样,如果仍然坚持,以佛理为进路,便有可能造成“释解无谓”的结果;因为,“一切无谓”。如任继愈所指出的,“[佛教]‘中道’的基本精神在于,似乎是什么都可以否定,什么也可以肯定;而实际上什么也不予肯定,什么也不予否定。这种态度正是取消了人类正常的认识作用。罗什的译籍洋洋数百万字,其结果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实在有些令人吃惊”(任继愈1985:418-419)。
即令依照“心行处灭”之意来释解“心”,也一样难以成功。因为,如果这样,这句话便要理解为:心在发用之时,即行即灭;也就是,行到哪里在哪里灭;按照佛理,它当然是空。如上所述,这固然可视为“顿悟”的一种表现,但毕竟不适用于对被视为“宇宙进化中最为复杂的事件”⑤的跨文化翻译规律的揭示。
可以理解,什公随机应变,脱离了事物是“因缘和合而成”“无其自性”的佛理,承认“心”作为“实体”在跨文化翻译之中应该能发挥既定的作用。这一合理的取向,与《礼记》对翻译的界定,以及儒家对“心”的大用的凸显相一致;因而,可为我们重新认识翻译思想史,甚至是反思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基础性的素材或支撑性的要件。
3.为什么要从儒家角度解释“心”和“明德”:什公洞见的译学史意义
先说“明德”。它是儒家经典之中常见的重要用词。如,《诗经·大雅·皇矣》:“帝迁明德”(毛亨等2000:1199);《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郑玄,孔颖达1999:1592);《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司马迁1989:43)。在儒家看来,“明德”既为圣人之光明德性,亦即为常人所应求者。
其次说“心”。钱穆(1895-1990)在批判清时学者时,强调:“必欲避去一心字,則全部《论语》多成不可解”(钱穆2018:90)。孔子(前551-前479)删述“六经”,形成生命力强大的思想传统。他本人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如朱熹(1130-1200)引程子所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1983:44)。儒家非常重视“人心”的作用。将世界的创造视为人心的创造,这是儒家思想的一大创获。
最后是“心”与“明德”的关系。儒家教人,认为人要想在内在里生成创造的力量,就必须先行打造好自己。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中句,《论语·学而》子贡引)(何晏,邢昺1999:12);所谓“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同上:5);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同上:157)等等,都可见出其中消息。成就君子的品格,其导向是:以初始之善或曰仁人之心,趋向天道,化天德为人德,不断实现仁德。初心之善,可成“明德”。郑玄(127-200)将《礼记·大学》之中的“明明德”解为“显明其至德也”(郑玄,孔颖达1999:1592),朱熹解释:“明德者,人之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熹1983:3)。有此得于天的“德”,则人修养之、培育之、强大之,行走于“成人”(《论语·宪问》)(何晏,邢昺1999:188)之途中,不断成就完美人格。
因此,什公讲“心山育明德”⑥,将“心”比作“山”,并特地点出“明德”,显而易见,他可能是有意借用儒家的思路,来解释“心之明德”之于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他是在说,培植出“心之明德”,并且使之发用,也就能够促成这种交流。这样,他预设了人心本善和与人为善的前提,同时也暗含着交流也要“以善为目的”这个结果。
在儒家看来,“心之明德”之求,既是做人的根本取向,也就应是“交流”的趋向,跨文化翻译当然包含其中,需依此理而行。《礼记》之中对翻译的界定(详下),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可以说,依儒家,“心山育明德”意为,人心得养育、强化自身之德之资粮,光明如初,而见之如山。人生而善良,且有先贤作为榜样,可为人生指南。什公既以此为助缘,等于承认“人之初,性本善”:正是有了这样的“本善”,交流才有可能,传教也才可行。
如果这样解释还算有道理的话,什公便是在借用儒家思想来突出“心”和“明德”的作用;退一步说,他的思想观点也是与儒家相契合的。
事实上,不少情况下,佛家也不能不认可“心”乃“实在”,而不一定是空无所有。佛家敬称年长者为“高僧大德”。“德者,得也”,上得于天/佛,下得于人,先需打造自己,不断强大其精神力量。“心”之实在,无可厌弃。其高弟僧叡(东晋高僧,约351/355-418/422)称什公“慧心夙悟”⑦(释僧祐1995:292),描述他译经“西明启如来之心”(同上:293),说他在西明寺翻译佛经,尽心尽力要启发世人领悟“如来之心意”。他早慧之才之所具为“心”,佛教妙道亦可以“心”称之。人佛同趣,此心难违。故而,什公弥留之际遗言中有“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出世,恻怆何言”(释慧皎1992:54)之语。心未尽而人将去,万恨千难,不可一道;什公因“十不出一”(同上)而难免愧疚,留下永久遗憾。
如此,即以什公本人的生平行事来看,他“心慧”异乎常人,弘扬佛法对“人心入乎佛心”孜孜以求,临终则深感自己“未尽其心”。一切的一切,都关乎这颗善良而又赤诚的“心”。而且,不仅人有此“心”,“如来”也有此“心”;更何况,“人心”与“如来之心”彼此呼应,相互沟通,传译佛经的活动才有成功的可能。那么,又如何能否认它的“实在性”,而坚持“此心毕竟空”?
尽管可以承认,什公是将“心”作为“方便法门”,暂时运用,以求抵及其应达之境界;但是就思路来看,“启如来之心”无可置疑地突出的是“心心相印”。因而,应该再次强调,什公偈中之所论,依据的应该并不是佛理。此偈之中所突出的“人佛沟通”的观点,体现的正是“心”之大用,其倾向与儒家完全一致。
不过,在后者那里,天人之间的沟通却是最为重要的⑧。儒家认为,人需以圣贤为榜样,而以效天为志业。因而夫子有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何晏,邢昺1999:241)。他盛赞尧帝“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同上:106)。因此夫子自道,他是要“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同上:199)的。这里的“上”指向的就是“天”。尽管如此,就此而论,什公此偈之中的思路,仍可见其与儒家的一致之处:“与天通”是儒家之所求的最高境界;“与佛通”,应是佛家的最高境界;尽管目标不同,但二者都要突出“心心相通”之义。
具体到他的译经活动,也有一个显例,可以说明什公之所译也不可能脱离开“心”的大用。因什公“未备秦语”和“名实变故”,僧叡指出:“察其语意,会其名旨,当是‘持意’,非‘思益’也。直以未喻‘持’义,遂用‘益’耳。其言‘益’者,超绝殊异,妙拔之称也。思者,进业高盛,自强不息之名也。旧名‘持心’,最得其实”(释僧祐1995:308)。值得注意的是,僧叡所说的都关乎“心”。什公因汉语水平不够的缘故而不明“持意”之义,易为“思益”,而僧叡认为还是旧译“持心”更为合宜。这个讨论告诉我们,就其导向而论,佛典之传译,必关乎“人心”。“持意”是持“心之意”,“思益”之“思”乃是人的“心田”,而“持心”也一样是在说“心”。“心”之大用如此,的确是不可不加以正视的。
因此,什公运用“心”和“明德”,其目的是要说明,佛教在人世间的传播,需要依赖人心,期其与佛心相通,如此才可达到目的。如果完全否定“心之明德”,一般的交流不可能,佛教的传播也是不可行的。
此一洞见,其重要性表现在,它与儒家经文对“翻译”的界定,观点是一致的。
《礼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晓达五方之志,通传五方之欲,使相领解”(郑玄,孔颖达1999:399)。《说文》:“志,意也”;“意,志也”(许慎1981:502),二字互训;“愿,谨也,从心原声”(同上:503)。“志愿”乃是心以其意之所之,所要达到的目的。《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心之所之谓意”(董天工2017:218);《四书章句集注》三处将“志”解为“心之所之”(朱熹1983:54;70;94)。“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王先谦1988:428)。“五方之民”志意相互通达,诉求得到满足,进而形成彼此关爱之势。这便是“译”等词语的意向,亦即为有关人员的职志之所向。可见,在《礼记》此篇的作者看来,人们对翻译早就以之为“以心为主”“将心比心”的交往活动:翻译与人心息息相关,不可须臾离也。
这样,联系上“嚼饭与人”之喻,我们就会发现,什公从两个方面呈现他的翻译思想。一是在技艺方面,他主张“出实而见华”,如实再现佛典的“藻蔚”;另一方面,他提倡“依心而行,彰其明德”。后者是前者的保证,亦即为译文成功的条件。也可以认为,即使“秦梵”语言不同,文体殊异,译文无法保证“藻蔚”的再现,但译者有此心,读者有此心,他们便可通乎于佛之“心”。如此,佛教圣言流传于世,佛理广被人间,也就是“达其志,通其欲”的事情:心至其所之,情通之所通,即成翻译。而这不也正是陆九渊(1139-1193)所说的“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陆九渊1980:523)之意吗?
由此看来,不论什公是否有意以儒家思想为借缘,来宣讲他的“心山育明德”,要想在俗世使其说有其意义,促成佛典的翻译、流布和广被,他也便不能不采用另一套思想系统,以期其行远。毕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左丘明等1999:1024)⑨。言当然是“心言”,亦即为“德言”,进而才可成“文”。而严复(1854-1921)在解释“信达雅”之时,特地引之来释其“雅”(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罗新璋,陈应年2021:206),可见其基底也一样是以儒家所说的心和德,来作为其翻译最高追求的支撑。
还有必要指出,严复是以“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同上),来范围“信达雅”的。而这里的“文章”意即,君子修身,自我培养之内德的彰显过程(蔡新乐2016)。如此,“信达雅”是儒家做人的基本要求,因此,才可能成为跨文化翻译的“楷模”。严复译论当然是儒家思想在跨文化翻译之中的运用和发展(蔡新乐2021)。
总而言之,“心山育明德”的意思是,要求人以初心之善,培育、滋养其德性,使之高耸如“山”而立于天地之间,以为生存和交流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基本的条件。
如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从《礼记》到什公再到严复,因都在突出“心山育明德”,而见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史之中的一条线索,因而,有待我们继续思考,以为其正名,并最终依据可信的史料和理据,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4.结语
佛教在中土的流传,既有道家思想融入的助力,更有儒家思想的推动。人毕竟要立于尘世,展望未知和未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与基础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洪修平等2013:6)。孔子被称为Master of Communication(Hall and Ames 1987:296),“交流的大师”或“沟通大师”(郝大维,安乐哲1996:228;2020:353)。对于交流,儒家讲究的是“心言”与“德言”,即人与人将心比心的沟通,唯有“人心相沟通”交流才是有意义的。而本文所疏解的什公之偈“心山育明德”的寓意中亦含有同样的洞见,这与儒家对交流的认识及其对翻译的界定可谓“心心相印”了。此偈显示的佛心与儒家之心的“对话”中究竟还隐含着什么,这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或可为我们重新认识翻译思想史,甚至是反思翻译理论的建构提供素材和要件。
注释:
①另一首出现在他给慧远(334-416)的信中。其全文是:“既已舍染乐,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虚诳等无实,亦非挺心处。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释慧皎2015:217)。
②汪东萍(2018)对什公翻译思想的研究比较全面,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什公“为僧叡论西方辞体”:“不可译”,与僧叡改译《正法华经·受决品》:文派,临终与众僧告别辞:翻译“诚实誓”与简约等翻译思想,以及《思益经序》:摒弃格义是什公译文优于支谦译本的关键。但此文并未触及本文所论之偈。
③“偈”本是佛经中适于唱诵的文体,类似诗歌,数句一首。梵语作Geya,汉译为偈,又作偈颂,译为齐语,通常四句一首,也有六、八、十二句一首者。句式通常为四言,也有五、七言等。从本文下文(第2节)引的《高僧传》之中什公所说的“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来看,偈可被之弦乐,用来赞颂国王或佛门之德,适宜吟诵,便于记忆(张海鸥,李琼艳2017:107-108)。孙尚勇(2005)提出,偈的梵语对应词是Geya,巴利文为Geyya,而不是Gāthā,但仍可看到学界有人在用后者。
④在《出三藏记集》中,此偈作:“心山育德薰,流芳万由旬。哀鸾鸣孤桐,清响彻九天”(释僧祐1995:534)。
⑤理查兹(I.A.Richards)的原话是:the most complex type of event yet produc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smos(转引自Wilss 2001:111)。
⑥在给慧远大师的信的偈中,什公显而易见对“心”也一样重视。详见注释①。
⑦据《晋书·艺术传·鸠摩罗什》记载,“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房玄龄1974:2499)。他的“夙慧”可以“惊人”来形容。
⑧钱穆提出,天人合一说乃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最大]贡献”(钱穆1991)。儒家贡献良多。
⑨《孔子家语·正论》作“: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杨朝明200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