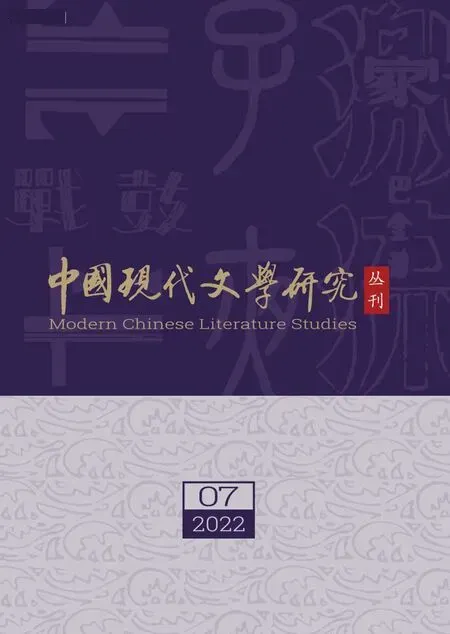第一座花园
林 棹
倘若我们赞同布罗代尔的见解——“文明在本质上是人类和历史在其中劳作的空间”①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观看的视角,用以观看我们生活的空间,观看我们朦胧的回忆情有独钟的空间:那些收容了我们童年的地方,那些我们在梦中一再重访的地方。
人们归纳古已有之的空间原型:道路(通道、十字路口),旷野,林地,集市,洞穴,海滨,农田……得出结论说,那些充当容器保守(或碾碎)我们童年的空间,将会沉淀为我们的“心灵风景”。我们毕生所为,要么是努力使它以任意方式重现,要么是尽力杜绝它重现的可能。在童年游历过地狱且放弃自救的人,则会在持续的坏预感和不间断的恐惧的笼罩下熬过一生。
不管你认同与否,这只是一种说法,一种“叙事”。正如福柯讲述监狱的故事,王尔德讲述花园的故事,我的妈妈讲述王尔德讲述的故事。“王尔德的花园故事”自然是指《自私的巨人》,一则关于奉献、自我牺牲和转变的童话,一个令人生疼的故事,它的悲剧性折磨我、诱惑我。我强迫妈妈一遍一遍重读这个故事,连同收录在《快乐王子故事集》里的另外两则——《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它们是我的“悲伤启蒙”,是我六岁之前读到过的最悲伤的故事,是三记连环打出的悲伤重锤,让我号啕大哭。三则故事的模式出奇的统一:脆弱之物,微小之物(燕子,夜莺,小孩);显性的、易于理解的创伤(失去的眼珠,刺破的心脏,手脚上的伤痕);与死亡相关(死去的燕子,死去的夜莺,死去的巨人);最后,所有这些让幼小的我无法承受的悲痛都施加在自然身上,或借助自然施加于我:冻死燕子的寒冬,刺穿夜莺心脏的玫瑰,花园的春冬以及覆盖巨人尸体的白花。
在《自私的巨人》中,王尔德用他的花园空间实现了多种意义的转变:自然的(春夏秋冬,花开花落,草木枯荣),生命阶段的(幼年,壮年,老年),时间的(等待,重逢),信仰的(皈依)。花园本身即已蕴含这些叙事的潜能,“巨人”和“孩子们”是让儿童更易接受的人格化形象。《自私的巨人》之后,更多花园接踵而来:弗朗西斯·H.伯内特的米瑟斯韦特庄园,碧雅翠丝·波特的美味蔬菜园,刘易斯·卡罗尔的仙境,《一千零一夜》的禁苑,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曼陀丽,斯蒂芬·金的树篱迷宫……相比希腊神话、格林童话当中野性的山林水泽、危机四伏的黑森林,花园是一种更温和亲切的文学空间,尽管儿童读物里的花园往往是温带植物的领地:橡树、欧石楠、蔷薇、欧丁香、毛地黄……我的童年过早地被远方植物的名字塞满,却难得有机会亲眼目睹它们的神采。我几乎从未读到过“荔枝”或“缅栀子”。市少年宫旁边倒是有一座“荔枝公园”。当我们走在公园里,妈妈把一株平平无奇的矮树指给我看并说“那就是荔枝树”时,我十分失望,因为它身上既没有荔枝,也没有“树”的挺拔。我也没有读到过“湿热”“台风”,没有读到过绿的秋天、绿的冬天或在冬天怒放的花簇。我只在阿拉伯、非洲童话里读到过干燥的酷热,在大洋洲神话里读到过漫长的雨季。
我们头脑中隐秘的细刷,难道从不曾偷偷地涂抹几笔,以增添“心灵风景”的戏剧性?难道从不曾以虚构的精美修饰真实的残缺破旧?将记忆比喻成曲径通幽的园林,或“迷宫般的花园”,是平凡又恰当的。幸好,书本与现实的错位及时被后者校正了——在我度过童年(0—9岁)的小区里,坐落着(或用一个更戏剧性的词,“隐藏着”)一座真实的花园,规模不大,五脏俱全:栅栏、园门、环形小径、被小径和植被环绕的三层小楼。如果你亲眼看到过那座小花园,一定会认为它是专为儿童建造的。栅栏是水泥材质,足够宽疏——我们可以把脸塞进栏缝间,向内探望;足够低矮——实在按捺不住,稍加努力即可独立翻越;足够坚固——大人远远看见,也并不阻拦,放心让我们攀爬。园门双开,光滑轻巧,难得上锁。
从我有记忆以来,园中植物就已浓密得恰到好处:隔挡了漫长夏日的毒日头(这里的夏天从四月开始,持续到十月),把简简单单的环形小径包裹成探险乐园;但又不至于过分浓密,野猫、儿童仍然可以毫发无损地匍匐其中,有余地供鸟筑巢,有余地供风嬉戏。整座花园就是一章——一节——活的岭南植物词典,供儿童拉扯、嗅闻甚至咀嚼——它既秀色可餐,又宽宏大量。单纯的游园快乐已经举世无双。我们幻想灌木丛中存在着秘径,通往仙境,像兔子洞,像《龙猫》里大大小小的隧道、入口;我们膝盖着地爬行,把私语埋进落叶堆。在草本、木本编织的紧凑天地间,我想要热烈地、紧紧地拥抱一种“被拥抱”的感觉,想要回抱那个紧紧拥抱着我的、巨大又温柔的事物,一种当时的我无法叫出名字的事物。后来,在谢默斯·希尼笔下,我读到了那种熟悉的热望,以一种无比精确、精美的面貌呈现:
所有的孩子都想窝在他们的秘密巢穴里。我喜欢我们小巷口一棵山毛榉的树杈,屋前一道黄杨树篱的茂密灌木丛,牛棚阴僻角落里柔软、塌下的干草堆;但我尤其喜欢待在晒谷场尽头一棵老柳树的喉部。那是一棵空心树,长满多瘤、蔓延的根须,一层柔软、快要脱落的树皮,以及多髓的内部。它的口部如同马轭上油滑而坚固的孔眼,当你缩着身挤进去后,你便进入一种不同生命的中心,眺望外面熟悉的院子,那院子仿佛突然间处于一道陌生的窗玻璃背后。在你头上,是这棵活生生的树在繁茂生长和呼吸,你用肩膀顶着微颤的树干,而如果你把额头靠在粗糙的木髓上,你便感到整个柔软和低语着的柳树冠在你上面的天空中晃动。在那个紧窄的豁口里,你感到光和树枝的拥抱,你是一个小阿特拉斯在用肩膀顶着它,一个小塞努诺斯在支撑着一个鹿角世界。①谢默斯·希尼:《摩斯巴恩》,《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尽情玩耍的儿童从不会忘记发问。花园的谜团就像园中植物一样茂密。持续困扰并诱惑着我们的问题首先是:花园的主人是谁?这是第一问题、问题中的问题,亦即,创世问题。是谁拥有花园,是谁设计并建造了花园,是谁掏的钱(当时的我们已经稍许建立起一点钱的概念),是谁决定种这些树而不是那些树,是谁真的出力、种下了那么多的树?
创世问题引发一连串新问题。花园主人现在在哪里?为什么造了花园却不住?为什么造完花园就离开了?为什么选择在此处,而不是在隔壁小区,或河对面,造这座花园?是先有小区,还是先有花园?……问题本可以是无尽的,接下来也许就要问到小区的建造者和深圳的建造者了。问题越积越多,我们只得到过一个答案——花园主人是个华侨。
“花园主人是个华侨。”这个答案合情合理,十分无趣,因为它不包含任何意外或魔法。而意外和魔法,是我们爱上花园和故事的原因。对我们的其他问题,大人们再也答不上来了,统一回答“不知道”,或“你自己去问婆婆”——这样一来,我们的婆婆就正式出场。婆婆一直在场。她看起来比我自己的婆婆还要年长许多,她是我见过的最年长的人。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是花园的“管理员”。大人很早就告诉过我们(“从前——”):婆婆受华侨之托,独自住在花园里,看管花园。
神秘花园里的神秘老婆婆。这正是童话故事的开场啊。
好天气的早晨、中午、傍晚,经过花园的人会见到婆婆坐在花园门前吃饭。短发全白,向后梳,被一支纤细的黑发箍固定;永远穿大襟衫,蓝色,雪青色,起风时候加一件冷衫。婆婆吃饭时,两把竹椅对摆,一把自坐,一把放菜。那种带靠背的矮竹椅,过去很常见的。遇上她吃饭,我们也不太讲礼貌,仍要跑去同她说话。我心里仍牢记着她常吃的一道菜——咸鱼段蒸肥猪肉,连同铺面的细姜丝,盛有一点汤汁的瓷碟。五六七八月,她耳后就多两朵白兰花。有时她叫我靠近去,交一串白兰花给我。她的手掌是很薄的,很凉的。她的手背是很皱的。
自然会有关于婆婆的问题:婆婆叫什么名字?她几岁了?她从哪里来?她有家人吗?她怎么就开始看管花园了呢?华侨和婆婆,谁更老些?我们想要听到关于婆婆的,以“从前”作为开头的故事。但既没有答案,也没有故事。
当我们,结伴探险的儿童,第一万次向花园进发,我们假装那是我们的第一次,或仍有一些角落未被我们涉足,仍有一些秘密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假装正在施肥或打扫落叶的婆婆并不存在。我们假装她是某位高龄仙灵(她的形象本就完美符合,无须做任何增减改动),正在敲打她的树精仆人。我们念念有词、手舞足蹈,被各种各样的童话角色附身,既不搭理别人,也不需要别人来搭理,因为在花园里,每个儿童为且只为自己的白日梦忙得晕头转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固定路线是通过一条(假想中的)密道溜到三层小楼背面,那里有紧贴地面的露台,半敞式结构对所有好奇心过剩的儿童来说无异于一张半开的邀请函。轻轻松松翻进露台,我把脸贴向茶色落地玻璃门,还要把拱成弓形的两手也贴上去,以挡住光线,这样,我能勉强望进幽暗的室内去,那里有幼年的我见到过的最奇异的景致——一排装有套色玻璃的长窗——“满洲窗”。
儿童不厌其烦地半弯下腰,快速穿过密道,翻露台,把脸和弓形手贴向茶色落地玻璃,就是为了将那排满洲窗一望再望。有时它的隔扇完全拉平,有时它很随意地折起。彩色玻璃的灵魂——那些色彩——被阳光打出来,落在地上、墙上,或和其他色彩重叠在一起,总之,一切取决于长窗折叠的角度、阳光的角度。儿童受到那种不确定性的蛊惑,着了道,中了魔:光斑的形状、色彩相加的结果,每一次都不同;那种不确定性被黑影子框定,那是普通事物的影子,最最常见的黑影子,它们变成了一种边框——罕见之物降临了,把边框反衬得那样平淡、坚固。统御那些彩色玻璃的美学是那个儿童前所未见的,她在书本、卡通片,或生活的别处哪儿哪儿都没遇到过那样的东西,她只能用那种不太礼貌的办法,不断重返露台,试图弄明白那种关在屋里的、不可触碰的奇异刺激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使得那些窗叶如此特别?彼时,儿童的词库里既没有“满洲窗”,也没有“美学”,甚至没有“奇异”。她发现她掌握的词语根本不足以表达她的疑问。她缺词,她的疑问像失控的烟雾一样在她体内膨胀。
在回忆和想象日复一日的作用下,花园早已虚实相交。对此,保罗·利科早有提醒:“在对想象进行批判的边缘地带,在记忆这个没落传统的逆流中,应该着手将想象和记忆拆分开来,尽可能将其进行得更彻底。指导思想是,在两种指向、两种意向性之间,存在着可以说是本质的差异:一方面,想象的意向性,它指向幻想、虚构、非现实、可能性、乌托邦;另一方面,记忆的意向性,它指向先前的现实,这种先前性尤其构成了‘被记得的事物’的、如其所是地‘被记得的东西’的时间标记。”①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第7页。那座真实存在过的花园也许是我的第一个虚构作品——基于现实,基于悬念,基于没有答案的问题,基于彻底变形的时间。在中空的现实里头,我用虚构的材料筑巢: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即可获得的快乐。那是我虚实相交的仙境。真实的蒲桃树会在夏日真实地绽放烟花般的花团,难以计数的长软的雄蕊真实地轻扫脸颊,虚构的微型仙子群居在雄蕊深处,使那些花团散发不存在的淡香。必须绕过芭蕉树,离它远点儿,因为有只女鬼住在芭蕉树上。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蒲桃树释放它中空的球果,每一颗球果一经摇晃便哐啷啷闷响,因为果中寄居着精灵。果中精灵总会在我“卜”一声压破果壁前一秒逃跑得无影无踪。花园作为我的“心灵风景”,它的分量是惊人的。它是与我为邻的魔力之源。我也总是隔着卧室窗玻璃观看它。那种时候我不在它之中了,我与它拉开距离,从外部感受它、想象它、记忆它。从我所在的高度(一楼),我只能采取平视的视角,那也许是一种幸运——我们知道,任何迷宫一经俯视,其魔力即刻灰飞烟灭。
花园的结局是那个扒着窗、贪婪张望的儿童所无法预知的——在她8岁那年,小区某户人家雇佣的小保姆突然辞工,住进花园。大人说,是被婆婆收了做干女儿。起初小保姆和婆婆一起忙进忙出,渐渐地人们不大看见婆婆了。人们发问:“婆婆呢?”——像其他关于花园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无人回答。
没有人再见过婆婆。植物慢慢凋敝。儿童不再跑进花园,因为花园日渐萎缩、狰狞。有一天,小保姆领一队人进去,开始锯树。他们在里头连干五天。他们撤离的时候,原地只剩三层小楼、空旷的水泥地坪和外围栅栏。那是一种触目惊心的光秃。那种光秃扎你的眼睛,扎你的心。
看起来,小保姆对凭空诞生的空旷十分满意。我们可以推测:小保姆的童年是在空旷之地度过的;空旷之地也许就是小保姆的心灵风景。不久,她在水泥地坪上养起鸡来,大肆养起来。她开始晒菜干。一排、一排地晒过去。菜干底下跑着她的鸡群。那之后不久,我们就举家搬迁了。
这就是完整的花园故事。开端的繁盛、结尾的凋零,都是这段叙事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空间,也是一种情感结构,或借用哈·麦金德的术语——一种枢纽,当它旋转起来,可以引发一系列智识及情感效应。20世纪的景观学者声称,“景观像一门语言”。今天我们更可以确信:空间,或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确然包含着语言,它持续地向我们低语,持续地影响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