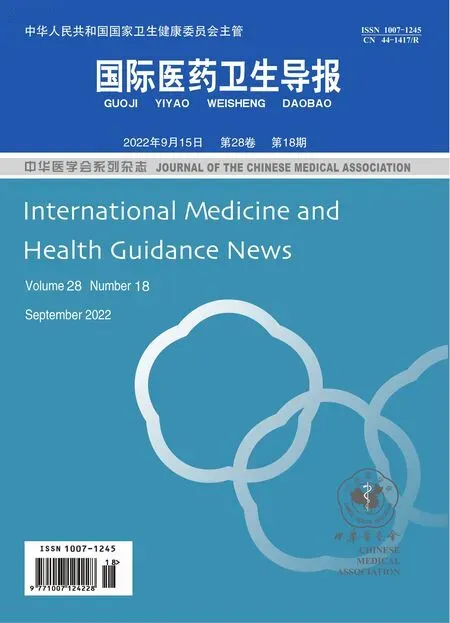浅述肺动脉栓塞栓子来源
周琪 张筱晨 孟晓菲 张清潭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滨州 256600
肺栓塞是以各种栓子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而引起肺循环和右心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1]。呼吸困难、胸痛及咯血是其典型症状。肺栓塞是继急性心肌梗死和中风之后,西方国家第3大常见的心血管病死亡原因[2]。我国关于肺栓塞的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较少,在美国,每年有50~60万人患有肺栓塞,其年发病率约1‰~2‰[3],每年至少有10万人死于肺栓塞[2]。对于急性肺栓塞患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病因并明确诊断,将严重影响患者生命健康,但肺栓塞作为一种常见的高病死率疾病,其病因复杂,病情进展迅速,尽早诊断和治疗对临床医师极具挑战性。本文综合近几年PubMed及知网上已发表文献,对肺栓塞的栓子来源及病理生理进行整合阐述。
血栓性栓塞
肺血栓栓塞是肺栓塞的主要类型,尸检结果显示,肺栓塞栓子类型中血栓性栓子占71.33%[4]。传统观念认为,肺血栓栓塞来源于静脉系统,近些年来,原位肺动脉血栓这一概念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5]。
1、静脉来源血栓
全身各个部位的静脉系统及右心腔的栓子都可导致肺栓塞,其中下肢深静脉为栓子主要来源,van Langevelde等[6]对428例肺栓塞患者进行统计,发现70.6%的患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其中51.3%的患者左下肢受累,39.4%的患者右下肢受累,9.3%的患者双下肢受累。杨鹤等[7]通过分析43例经尸体解剖确诊肺栓塞患者的病理及临床资料,发现33.3%的患者栓子来源于下肢深静脉,27.9%来源于盆腔静脉血栓,26.2%来源于腹腔静脉血栓,4.7%来源于右心血栓,2.3%来源于上肢深静脉血栓,4.7%未发现血栓来源,其中左右肺动脉干以上的栓塞66.7%来源于双下肢深静脉。
急性肺栓塞引起的右心室衰竭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当血栓栓塞引起肺血管床面积减少25%~30%时,肺动脉压开始升高,同时,血栓素A2、5-羟色胺等物质释放及缺氧引起血管收缩,这导致肺血管阻力(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PVR)增加,PVR的突然增加使右心室后负荷增加,通过Frank-Starling机制改变右心室心肌收缩性,从而增加肺动脉压,改善了阻塞肺血管床的血流,但机体这种适应能力有限,由于右心室室壁较薄,急性肺栓塞时右心室最大能维持40 mmHg(1 mmHg=0.133 kPa)的肺动脉压[1,8]。急性右心室扩张通过心室间相互依赖性使左心室舒张顺应性显著降低,左室充盈受阻,导致心输出量及动脉血压下降,这会快速引起心源性休克和死亡[9]。此外,全身性低血压及右心室压力增高会减少右冠状动脉血流,导致右心室缺血[10]。
肺栓塞最普遍的症状来自于气体交换的改变,栓子阻塞一个或多个肺动脉,血流再分配到非闭塞的血管,这导致通气/血流(V/Q)异常,包括栓塞区域V/Q值增高及非栓塞区V/Q值降低,从而引起气体交换受损、低碳酸血症及低氧血症[11]。低心输出量和高组织代谢需求增加了器官和组织的血氧摄取率,极度不饱和的血液通过低V/Q的非栓塞区时不能充分获得氧,这也导致了机体缺氧[12]。
2、原位肺动脉血栓
既往认为DVT脱落阻塞肺动脉是肺血栓栓塞症的主要发病机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没有DVT的肺动脉内也可能产生新生血栓,我们称之为原位肺动脉血栓。Brown等[13]通过建立小鼠钝性胸外伤模型,发现肺动脉新生血栓以纤维蛋白和CD41阳性嗜酸性蛋白物质偏心聚集的形式出现。Velmahos等[14]对46例患有肺栓塞的创伤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其中仅有15%的患者合并有DVT。Van Gent等[15]的研究与之相似,其回顾性分析了11 330例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2 881例患者接受了下肢彩超监测,31例肺栓塞患者被纳入研究,发现只有12例肺栓塞患者合并有DVT,有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DVT完全脱落引起,但12例肺栓塞+DVT患者中发现10例患者有下肢深静脉残余血栓,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血栓只是部分脱落阻塞肺动脉。有研究表明,原位肺动脉血栓常见于艾森曼格综合征患者,与高龄、双心室功能不全、肺动脉扩张及肺血流速度降低有关[16]。另有研究指出,在韩国,肺结核破坏、肺切除后的肺动脉残端及肿瘤的肿块效应是原位肺动脉血栓患者的基础疾病[5]。
对于结构及功能完整的血管内皮细胞,其具有抗凝血及促凝血的双重机制[17]。具体来说,内皮细胞生成和释放一氧化氮、前列环素I2等物质产生舒张血管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内皮细胞还能产生血栓调节蛋白并激活抗凝因子蛋白C以维持抗凝。此外,内皮细胞表达硫酸乙酰肝素和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TFPI),分别提高抗凝血酶Ⅲ和纤溶因子的活性[18]。当内皮细胞损伤时,其提供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和组织因子(tissue factor,TF),在胶原和成纤维细胞的内皮下区域表达,并在血管壁损伤时暴露于血液中,由vWF的受体结合诱导血小板聚集,TF与循环中凝血因子Ⅶ结合,从而启动外源性凝血途径,引起肺动脉局部血栓形成[19]。
炎症和缺氧可刺激血栓形成。炎症可激活内皮细胞,活化的内皮细胞分泌多种因子,在血管活性因子的分泌过程中,Rho激酶系统的过度和持续激活在活性氧的产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活性氧的过度产生(氧化应激)会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增强黏附分子的表达,并激活血小板和凝血系统,从而形成血栓[20]。缺氧可诱导促血栓形成因子(如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的表达,这一过程通过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调节靶基因的转录来实现;同时,缺氧也可以通过诱导促炎症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IL)-1间接调节血栓形成[21]。
非血栓性肺栓塞
非血栓性肺栓塞较血栓性肺栓塞少见,症状和体征(如呼吸困难、胸痛等)特异性低,影像表现常与血栓性肺栓塞难以鉴别,临床中常被忽视,其诊断也对临床医生提出了挑战。非血栓性肺栓塞栓子来源主要包括生物源性(羊水、脂肪、肿瘤、细菌、真菌等)和非生物源性(气体、骨水泥、硅胶等)。
1、羊水栓塞(amniotic fluid embolism,AFE)
AFE是指羊水中的有形物质和促凝物质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急性肺栓塞,AFE是产科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在各国差异较大,据估计,AFE的发病率1/8 000~1/80 000,其病死率27%~60%[22]。AFE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除了羊水引起的机械性梗阻外,可能与羊水引起的免疫风暴有关。当羊水进入母体循环时,免疫系统可由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触发。PAMPs或DAMPs可能通过模式识别受体信号通路、过敏反应或补体途径激活敏感个体的母体免疫反应,大量的炎症介质在短时间内释放,导致全身性血管痉挛、毛细血管渗漏、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甚至呼吸、循环系统衰竭[23]。
2、脂肪栓塞
脂肪栓塞是脂滴进入血液循环阻塞小血管所致,常见于外伤后[24]。关于脂肪栓塞的病理生理目前有2个理论。第1个理论是机械理论,脂滴是由骨折的骨骼或脂肪组织中的脂肪细胞被破坏而释放出来的。这些脂滴进入受伤部位附近的撕裂静脉,然后被输送到肺血管床,大的脂滴导致机械性阻塞,作为栓子被困在肺部毛细血管中。较小的脂滴(7~10µm)可能通过肺毛细血管进入体循环,导致栓塞到大脑、肾脏、皮肤或视网膜。大的脂滴也可能通过预先存在的肺部毛细血管前分流和病理性静脉-动脉通路(如卵圆孔)进入体循环[25]。第2个理论是生物化学理论,它与机械理论并不排斥,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部分患者症状的延迟出现。骨髓脂肪栓塞到肺部导致局部释放脂肪酶,将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和甘油,游离脂肪酸对内皮细胞有毒性,导致血管性水肿和出血。这些情况会释放促炎症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IL-1和IL-6,可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此外,骨髓脂肪有促凝作用,在血液循环中,它很快被血小板和纤维蛋白覆盖,启动凝血级联反应[26]。
3、肿瘤栓塞
肿瘤栓塞被分为3种类型,Ⅰ型肿瘤栓塞为“真”肿瘤栓塞,起源于通过血液传播的远处原发肿瘤,它与血源性转移不同,因为它通常不侵犯血管壁;Ⅱ型肿瘤栓塞是由于肿瘤生长到肺动脉(如肾细胞癌)。Ⅲ型肿瘤栓塞指局部肿瘤细胞浸润和阻塞肺血管,无论是原发性肺癌还是转移性肿瘤[27]。肿瘤栓塞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肿瘤细胞可诱导凝血级联反应,血管闭塞常是由于血栓和肿瘤细胞混合性栓塞导致[28]。由于影响血管生成、细胞凋亡和炎症的信号通路相互作用,恶性肿瘤细胞在肺部的最终结果是转移、淋巴管浸润、形成肺动脉高压或细胞清除[29]。
4、脓毒性肺栓塞(septic pulmonary embolism,SPE)
SPE是指含有病原体(细菌、真菌或寄生虫)的栓子栓塞到肺动脉,引起肺栓塞和局灶性肺脓肿。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最常见的病原体[30]。SPE常见原因有三尖瓣感染性心内膜炎、牙周脓肿、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化脓性血栓性静脉炎(包括Lemierre综合征)、静脉药物滥用以及皮肤和软组织感染[31]。肺外局部感染可导致微生物(通常是细菌)移位到静脉系统,毒素和炎症介质对内皮细胞的损害,以及微生物直接产生的致血栓毒素最终导致血栓形成[32]。纤维蛋白和血小板基质是微生物理想的增殖场所,当其内容物排入肺循环时,可导致远处转移性感染。特别应注意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以产生杀白细胞素和凝固酶,通过间接的炎症机制,表现出血栓形成效应,导致内皮细胞功能障碍,最终导致脓毒性肺栓塞[32]。
5、气体栓塞
气体栓塞是由于创伤、各种有创性诊疗活动或减压病而导致气体进入静脉系统,大量气体进入肺动脉导致肺动脉机械性阻塞、肺动脉高压、右心室阻力增加、静脉回流减弱、心输出量减少,严重时会导致心力衰竭[33]。气体进入的速度和量决定了症状的严重程度,估计其最低致死量300~500 ml[34]。此外,发生气体栓塞时肺部毛细血管床中被激活的中性粒细胞释放血栓素和白三烯,增加气道阻力和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导致肺水肿和肺泡塌陷[35]。如果患者存在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或肺内分流等情况,静脉系统内气体栓子可能会进入动脉系统导致反常栓塞,这可能会引起脑栓塞。动脉循环中的空气可以形成微气泡,破坏微血管循环,触发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的释放,并诱导血小板聚集[36]。这些变化可能触发细胞因子(如IL-1和肿瘤坏死因子)的释放,导致弥漫性血管内损伤、微血管血栓形成、器官缺血和多器官衰竭[37]。
6、异物栓塞
异物栓塞在临床工作中并不多见,在文献资料里常以病例报道的形式出现。骨水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常用于椎体成形术,Venmans等[38]对299例椎体压缩性骨折患者532次椎体成形术治疗进行统计,发现肺骨水泥栓塞的发生率约2.1%,其中发生骨水泥栓塞的患者并无明显症状。近些年来,液态硅胶越来越多被用于医疗美容,常见的注射部位包括乳房和臀部,其也可经静脉系统到达肺动脉引起机械性阻塞,硅胶栓塞的临床表现及病理生理与脂肪栓塞相似[39]。前列腺近距离治疗是前列腺癌患者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在影像引导下,放射性粒子被放置在前列腺及其周围组织中,这些放射性粒子可以通过前列腺周围的静脉丛迁移到下腔静脉和肺部,患者通常没有明显症状[40]。一些吸毒者将口服药物片剂碾碎溶于水中用于静脉注射,其中不溶性颗粒如滑石粉、淀粉、纤维素等会损伤肺毛细血管,除了引起机械性阻塞外,还会引起肺部异物肉芽肿[41]。
肺栓塞是常见且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疾病,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对临床医师来说,及早明确诊断依然存在难度。肺栓塞的栓子来源包括血栓性和非血栓性。本文通过描述肺栓塞的栓子来源及病理生理,以期为早期干预肺栓塞发生提供可能的线索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