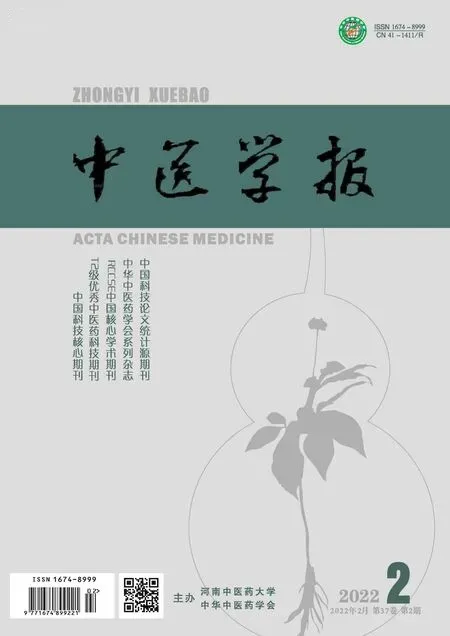五苓散加减治疗糖尿病肾病研究概况*
韦婷婷,黄雪霞,孟立锋,李丽容,张鹏
1.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200;2.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3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作为糖尿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患病率逐年攀升,其治疗难度大、预后差,目前已成为我国终末期肾病的首要病因[1]。DN起病隐匿,进展迅速[2],其高昂的医疗费用给个人和国家医疗体系带去沉重的经济负担[3]。关于DN的治疗,目前西医主要在运动营养干预的基础上通过控糖、调脂、降压及减少尿蛋白等对肾脏进行保护[4],药物方面主要选用具有降低尿蛋白和肾脏保护作用的降压、降糖药,尚无对DN精准的治疗靶点和治疗药物[5]。近年来,得益于中医药理论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在治疗DN方面取得成效显著,展示出中医药在该领域的广阔前景[6]。
中医认为,DN是消渴类病发展至中后期的变证之一,病久阴损及阳,脾肾阳(气)虚,气化失司,水湿内停,泛滥于肌肤。患者常见畏寒肢冷、腹胀纳呆、尿少、浮肿,舌淡胖嫩、苔薄白或白腻,脉沉等症状[7]。五苓散出自张仲景《伤寒论》一书,由泽泻、茯苓、猪苓、白术、桂枝5味药物组成,全方具有利水渗湿、温阳化气之功,不仅健脾以助气化,改善体内水液代谢,兼能解表,使蓄水留饮自除[8]。后世医家常根据患者不同的临床表现及自身经验对本方进行加减化裁。五苓散凭借其组方严谨精妙,疗效显著等优势在DN的治疗中取得满意成果。现做一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DN由消渴病失治误治发展而来,是多种病理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张宗礼认为,DN总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气血阴阳俱虚为其本,痰湿浊瘀为其标。湿、痰、浊同源异流,阻碍脾胃气机升降运化功能,“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故认为湿邪困脾是导致DN发生的重要因素[9]。梁晓春认为脾肾两虚是其病机关键,发病之本,病初以脾肾气虚为主,至疾病后期多见脾肾阳虚。长期高糖、高渗状态使微循环障碍,血行不畅,故瘀血、浊毒内生,瘀血和浊毒既为病理产物,又促使病情进展,贯穿疾病始终,为发病之标[10]。吕宏生则认为DN的发生与先天禀赋不足,情志不畅,饮食失节,劳逸过度或失治误治等相关。病久脾肾虚衰,气化无力,水湿内停,易成气血阴阳俱虚,水湿泛滥之虚实夹杂证候[11]。阎晓萍指出脾失运化,脾不升清导致DN患者精微下泄,形成蛋白尿,继而加重病情进展[12]。
DN根据其临床表现归属于中医学中“消渴”“水肿”“虚劳”“消瘅”等范畴。宋代赵佶《圣济总录》云:“消渴病久,肾气受伤,肾主水,肾气虚惫,气化失常,开阖不利,能为水肿”,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水病者,由脾肾俱虚故也”,当脾肾虚衰,脾失运化,肾失封藏而致精微物质外泄,水液输布失常,导致大量蛋白尿、顽固性水肿等表现,称为糖尿病肾病综合征[13]。水肿进一步发展可致高血压、胸水等严重并发症,患者免疫力低下,感染风险增加,肾功能进一步恶化。为此,减少尿蛋白、有效利尿是治疗本病中后期的主要目标[14]。五苓散通过恢复脾肾气化功能,使全身津液重新布散,水肿得消,脾气健而肾气充,二脏统摄之力增强,蛋白流失减轻,有利于残存肾功能的保护,延缓疾病的进展。
2 临床研究
仝小林等[15]认为应根据湿、浊、毒的不同对DN病程中出现的浊毒内蕴进行分治,故以五苓散加减治疗水湿内盛的脾肾(阳)气虚型DN水肿患者,效果良好。敬仁芝等[16]将68例气阴两虚型DN患者通过抽签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罗格列酮口服,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五苓散。治疗8周后,试验组有效率为94.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5%,且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餐后2小时血糖(2hPG)、三酰甘油、24 h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肾功能等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五苓散联合罗格列酮临床疗效优于单用罗格列酮。刘畅等[17]予五苓散合五皮饮治疗DN水肿患者60例,对照组采用呋塞米20~40 mg静注,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五苓散合五皮饮,3周后结果显示治疗组有效率90.0%。提示五苓散化裁可通过增加24 h尿量,显著缓解患者临床症状。辛奇遥[18]将60例以双下肢水肿为主要表现的阳虚水湿瘀阻型DN患者按双盲法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予呋塞米片口服,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真武汤五苓散加减进行干预。结果显示两组的FPG、2hPG、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24 h尿蛋白定量及中医证候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治疗组疗效更佳且无任何不良反应。提示真武汤合五苓散加减在降低蛋白尿,保护肾功能,改善临床症状方面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陈宁[19]按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将60例脾肾阳虚型DN水肿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先予托拉塞米注射液静注后改片剂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联合加味五苓散进行治疗。疗程结束后发现,观察组24 h尿蛋白定量、水肿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证实加味五苓散在辅助治疗脾肾阳虚型DN水肿方面疗效确切,且安全性高。
由此可见,基于临床症状辨证治疗,特别是对于脾肾阳(气)虚型DN水肿患者,五苓散加减通过降低血糖、血脂,增加尿量,减少尿蛋白和改善肾功能等方面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延缓病情进展,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3 机制研究
DN发病机制极为复杂,现代医学认为其主要与遗传易感、糖脂代谢紊乱、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细胞因子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过度活跃等多种因素相关[20-22]。近年来,依托新兴技术与平台,关于五苓散治疗DN的作用机制及药理研究日益增多。
3.1 调节水代谢平衡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水通道蛋白(aquaporins,AQPs)是一类能介导水分子跨膜转运的蛋白家族,对机体水代谢平衡的维持起到关键作用[23]。水通道蛋白-2(aquaporin-2,AQP2)主要分布于肾脏集合管并受血管加压素(arginin vasopression,AVP)调控,对多种肾系疾病进程中出现的水代谢失常具有重要调节作用[24]。于滢[25]在五苓散对肾阳虚水肿大鼠水液代谢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五苓散显著降低大鼠肾脏中AQP2的表达,抑制集合管的重吸收作用,增加尿量,改善水肿,同时有效减少尿蛋白,减轻肾脏病理损伤。提示五苓散对DN的疗效可能是通过下调AQP2 mRNA 及相关蛋白表达来实现的,这一发现也为DN的治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另外,国外有研究发现[26],五苓散给药后的大鼠血浆肾素活性和醛固酮浓度降低,而尿量、Na+排泄增加。提示其可能通过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醇系统诱导利尿,维持机体水代谢平衡。
3.2 纠正糖脂代谢紊乱糖脂代谢紊乱能够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DN的进展,因此,积极纠正糖脂代谢紊乱是治疗DN的重要手段[27-28]。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29-33]五苓散方中单药富含的各种萜类、多糖类、有机酸等有效成分,能显著降低血糖、血脂,纠正机体糖脂代谢紊乱状态。陈青梅[34]研究发现,五苓散通过降低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2hPG、FPG的水平发挥调节糖脂代谢,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郝晓博[35]探讨五苓散治疗气阴两虚兼血瘀型DN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两组TG、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2hPG、FPG、24hUpro、Scr均较治疗前下降,且五苓散组各项指标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五苓散加减通过纠正糖脂代谢紊乱,减少尿蛋白,保护肾功能,延缓DN进展。
3.3 抗氧化应激和抑制炎症反应高糖状态下,活性氧产生过多诱导肾脏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OS),OS发生的过程中释放大量炎症因子、生长因子等促使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导致肾小球硬化,最终发展为DN[36]。张倩霞等[37]运用五苓散、五苓散去桂枝、五苓散去桂枝加桂皮醛分别干预阿霉素诱导肾损伤大鼠模型,结果显示上述三组均能明显提高大鼠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在降低血浆丙二醛、谷胱甘肽、SCr方面效果显著,推测五苓散化裁方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减轻OS对肾脏的损伤。Yoon等[38]研究表明,五苓散通过下调DN大鼠模型肾组织中炎症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的表达、降低炎症因子细胞间黏附分子1的含量,抑制核因子κB信号通路活化以减轻肾脏炎症反应,改善肾脏病理。以上研究表明五苓散可能通过抗氧化应激和抑制炎症反应发挥保护肾脏作用。
3.4 网络药理学研究网络药理学基于系统药理学、生物学等层面,运用复杂网络与可视化技术以阐明五苓散治疗DN的作用机制、作用靶点和组方规律[39]。申鑫惠等[40]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分析平台(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s pharmacology database and analysis platform,TCMSP)、人类基因数据库对五苓散中单味中药活性成分靶点及DN相关靶点进行筛选,将双方匹配后得到五苓散-糖尿病肾病关键靶点,并构建疾病-药物-活性成分-关键靶点关系网络进行蛋白质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分析。为预测靶点,进行关键靶点基因本体(gene ontology,GO)富集分析和基因相互作用(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通路分析。结论提示五苓散减轻DN肾损伤和延缓病情进展的作用可能是通过调控凋亡蛋白酶家族蛋白、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蛋白家族等细胞凋亡相关蛋白来实现的。王诗怡等[41]运用TCMSP对五苓散中有效成分进行筛选及作用靶点预测,得到五苓散治疗DN关键靶点21个,主要包括DN结合转录激活活性RNA聚合酶II特异性、类固醇激素受体、类固醇结合、核受体活性等相关。对其进行KEGG通路富集分析后发现,AGE-RAGE信号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细胞凋亡、癌症相关通路等可能是本方发挥作用的主要信号通路。以上均体现了中药复方五苓散治疗DN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协同作用的特点。
4 结语
DN中后期阴损及阳,病机由阴虚内热向脾肾阳(气)虚演变。《素问·经脉别论》有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辨证录》曰:“夫消渴之症,皆脾坏而肾败”,皆表明该病系因脾失健运,肾失开阖,三焦气化失常,水液输布障碍所致,故DN的治疗应注重温阳化气行水。
五苓散方中泽泻为君,味甘性寒,其功达水脏,可增强肾与膀胱渗湿利水之力;猪苓利水效力较泽泻更强,茯苓兼能健脾,二苓淡渗,通利水道,共为臣药;《医方考》云“猪苓质枯,轻清之象也,能渗上焦之湿;茯苓味甘,中宫之性也,能渗中焦之湿;泽泻味咸,润下之性也,能渗下焦之湿”。三药配伍,分治三焦之湿。佐以白术燥脾逐湿,可彰培土制水之效,又可奏输津四布之功。《医学源流论·古方加减论》中指出:“五苓之要,全在桂枝”,桂枝妙用在于宣通阳气,蒸化三焦以行水,兼解太阳之表。诸药合用,可宣通三焦、气化水行,表里同治。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泽泻及其提取物可以降糖调脂、保护血管内皮[42];猪苓、茯苓能够利尿、抗氧化、抗肿瘤[43-44];白术具有抗炎症、调节免疫等作用[45];桂枝则能改善血液循环、抗血小板聚集[46]。整体组方能够提高DN临床治疗有效率,对疾病防治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DN是多种致病因素各自作用及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五苓散加减治疗DN具有安全性高,多靶点作用等优势,临床疗效值得肯定。随着对疾病机制更全面的认识及相关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更着重于从分子、细胞、基因等多个层次阐明中医药对DN的作用机制。但目前已有的临床报道多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全面性欠缺,未来亟待更多大样本、多中心和区域间紧密合作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将这些临床证据进一步发掘,以期能够达到循证级别,发挥中医药在肾病领域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