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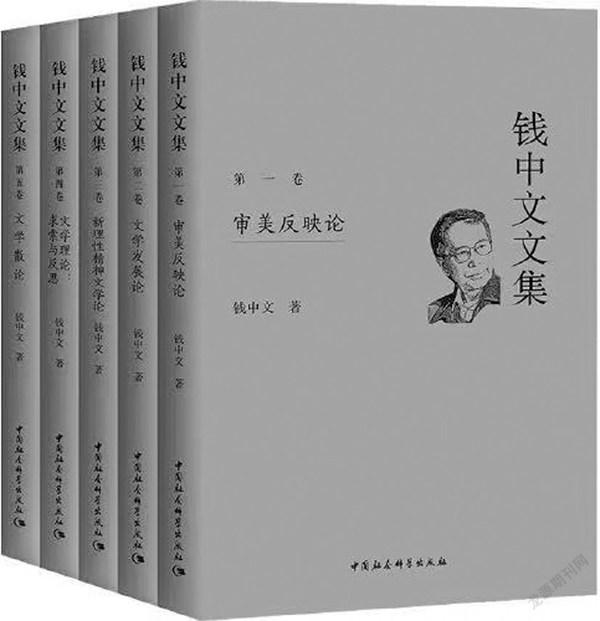
2018年5月,钱中文先生惠赠我大作两本,一是他的学术自传《文学的乡愁——钱中文自述》,二是《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读后者,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原来祁志祥在他二十三岁那年(1981年)就喊着“敬爱的钱伯伯”给钱老师写信了①,于是他得到了钱老师的回复和指教,并有了长达数年的通信,也有了志祥教授后来的成就与辉煌。我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知道钱老师大名的,但为什么我就不知道给他写信呢?
这就是差距!
不只是没有早早给钱老师写信,认识他也很晚。
应该是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我才在开会的场合见过钱老师,但那时他一般都坐在主席台上,是我仰视的对象。直到2004年5月16日,我与钱老师才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一天也是开会,却是我们自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那次会议规模不大,议题却不小——讨论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局外人瞅见这一题目或许会晕菜,但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关联着上个月首都师范大学的那次会议。4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联合《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一次“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童老师突然发飙了。他对在场的金元浦、陶东风嬉笑怒骂一番,从此揭开了他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序幕。而一个多月之后的这次会议虽主旨很学理,但在私下场合,我们都把它称作“批斗会”,因为会场上不仅有钱老师,还有钱老师的学生金元浦、陈晓明;童老师这边,则有他的弟子陶东风到场。虽然我并不清楚钱、童二老师事先是否有过沟通,但此会的用意却是清楚的——对文艺理论扩容者批而判之,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鼓吹者追而打之。而由于钱老师与童老师观点接近,思路相当,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与金、陶等人的争论也就成了师生之间的战争。
那天的会议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煞是好看。攻方是老师辈,他们高举高打,火力凶猛,横扫千军如卷席。但作为学生辈的守方却没有俯首帖耳,乖乖就范,而是不时地辩解、反驳乃至反唇相讥。童老师批陶东风时追根溯源,顺便把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拎出来清算,他说:“有人说我跟米勒的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上,怎么能不在一个层次上呢?明明是我们面对面对的话②,我听懂了他的话,他也听懂了我的话,怎么不在一个层次上呢?”大家伙儿顿时哄堂大笑。钱老师马上接话道:“你要是顺着他说,就在一个层次上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钱、童二老师并肩作战。虽然都是向自己的学生开火,但他们的战术风格却并不相同。童老师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他时而大弦嘈嘈,时而小弦切切,既疾言厉色,也适度调侃,直把气氛把控、渲染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钱老师则更理性,更节制,更儒雅,甚至更隐而不发,跃如也。童老师一旦情绪上来,就颇有一些和盘托出,不管不顾的架势;而钱老师却适当搂着:不放狠话,不用猛词,仿佛话到嘴边留半句。后来,我见钱老师专写童老师文章,其中有“我和童庆炳教授交往多年,在文学理论的重要观念上,各自有话直说,又十分一致,进而相互承认、互为补充、互相补台……相互买账,求大同而存小异”③之说,就觉得两位老师在性格上或许也是互补关系,否则,又如何解释他们“互相补台”时为什么总是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呢?
那天会后,我与钱老师坐在一起吃饭,听他讲起社科院钱锺书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的掌故,感慨不已。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钱老师是有立场有态度的;而因为这一讲述,也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在隆重的会议上,钱老师往往显得严肃、高冷、不苟言笑,但在私下场合,他却和蔼了许多。莫非是掌故八卦如同黏合劑,谁讲它谁就有了亲和力?
自从真正见过钱老师后,有关他的消息便如小河淌水,汩汩而来。因为童老师把他这位老朋友挂在嘴边,他那里一有什么动静,我们就春江水暖鸭先知了。比如,有人曾化名闰泉,写文章批评钱老师的“新理性精神”,并且也搂草打兔子,捎带上了童老师。有一阵子,“闰泉事件”就成了童老师的一个话题。又如,有了所谓的“马工程”之后,童老师开始担任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的首席专家,钱老师则是成员之一,但在2006年5月,童老师却给我讲了一件事情。童老师说:前几日教材编写组开会,先是钱老师说某教授发了许多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章,接着又开大会批判,这不是在搞运动嘛。某教授便回应道,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负法律责任!钱老师不高兴了,便拂袖而去,下午不来了。第二天总结发言时我说,学术讨论就是讨论,不要搞人身攻击。某教授立刻发难,说我是欺上瞒下。真是岂有此理,所以我就回敬他捏造。这时李衍柱老师站出来了,他说,你说童老师欺上瞒下,拿出证据来!结果就吵起来了。
童老师的口述自传出版后,我在里面看到了他对编写“马工程”教材的交代。据他言,当时他并不想揽这个事,便去找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想让袁放他一马。袁却做他工作,说他教材编得多,有经验,为人也随和,善于与人交往。童老师说:“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但你也只是说对一半。我跟多数人都是可以交往的,但是有那么一两个还是非常难交往的,经常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他们缺少文学知识,所以经常跟他们谈不通。”④如果与童老师口述自传的原始稿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他这里所谓的“一两个”是指过名、道过姓的,其中就有向钱老师发难的某教授,但成书时这些人名却被删掉了。而在童老师的讲述中,我能够感觉到编写组并非杨柳青青江水平,而是热风吹雨洒江天,仿佛随时都有人会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于是,对于童老师来说,钱老师能在这个专家组可谓意义重大,因为他不仅需要学术盟友,更需要思想战友。身边有钱老师,他心里可能会踏实一些。
这就不得不说到两位老人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早在2003年,童老师就对钱老师提出的“新理性精神”赞不绝口。而对此做过一番评析后,他又转向钱老师的“审美意识形态”,形成如下定论:“他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学界多数人对于文学本质特征的问题的共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立,应该说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的一大收获,它不是西方的‘审美无功利’论,也不是‘文艺从属政治’论,也不是别林斯基的片面的形象特征论,它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家寻找到的在诗意审美和社会功利之间、文学自律与他律之间取得某种平衡的现代文学理论。历史将证明,这一思想的确立是中国现代文论观念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⑤而后来我在钱老师的文章中则看到了如下说法:
1999年新年的一个晚上,童老师给我一个电话,一面表示迎岁祝贺,寒暄了几句,一面接着说,你提出的文学观念很有意义。他说他梳理了各种流派的文学思想与观念,又经过了反复的比较,认为我提的观念说,最能从总体上说明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历史地梳理了这一观念在我国流行的来龙去脉,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里使用了它。我听了很是震惊,我看到当时不少文章、著作都在使用这些名词,它们恐怕是不少人的共识,是共同完成的观念,不属于个人的了。于是一面向他表示感谢,一面建议他要谨慎,否则会引起“一些人”的烦恼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说不怕,只要我们说的有根有据,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听他这么一说,我想我在学术上遇到了真正的知音了。在学术界,相互承认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那种相互欣赏的“美美与共”的知音呢!但是我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果不其然,几年之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⑥
这里需要稍加解释。钱老师所谓的“我提的观念说”,实际上就是“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便是指某教授发起的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在“马工程”教材编写会上的那次发难。不过,这里最触动我的还是钱老师所说的这句:“在学术界,相互承认已经很不容易,何况是那种相互欣赏的‘美美与共’的知音呢!”而后来我在访谈钱老师时,他又进一步强调:“我跟童老师,可以说是知己、知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然,我有不少好朋友,但没有像童老师这样在心灵上非常契合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就我在学界厮混这些年的体会,学人之间的相轻甚至相侵,一点也不比文人差。钱老师与童老师能够相互承认、相互欣赏,高山流水、互为知音,既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也该是我们后生晚辈学习的榜样。
也需要说明的是,钱老师的这段文字出自他写童老师的怀念文章。童老师突然辞世后,钱老师泪如泉涌,悲痛不已,随后便写出两篇怀念文章。而那个时候,我已在编辑《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一书,钱老师的文章自然是要放在首要位置的。但在2015年初冬之际,我还是收到了钱老师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说:“赵勇老师:祝贺你‘新官上任’。有一事相扰。听程正民老师说,你们正在编辑一本关于童老师的回忆集。童老师去世后,我写了两篇悼文,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7月4日12版:《又见远山,又见远山》,后我寄了几份报纸给了中心。《文汇报》7月17日12版刊有我的另一篇悼念童老师的,原名为《理论是美丽的》,刊出时,孰料编辑给我的文章改了题目,成了《写小说要“轻轻地说”》,这自然出于实利目的,但这样一改,变成我去悼念莫言了!真是荒唐!如果你们收我一篇,就用前一篇,如果两篇都收,请将第二篇的标题改为原来的‘理论是美丽的’,这也有利于你们的中心。”
《轻轻地说》是莫言为童老师《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作序时使用的标题,钱老师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也就百十来个字,但编辑见此说法,却居然改了题目。媒体的势利由此可见一斑。
童老师去世后,我开始担任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这就是钱老师所说的“新官上任”。而“上任”之后,要举办学术会议,要迎接基地评估,还要筹划“十三五”课题等,诸事杂陈,常常忙得我焦头烂额。但想到钱老师与童老师的深厚友情,我却一直惦记着去向钱老师请益,既请他为中心的发展出谋划策,也听他讲一讲与童老师交往的故事。2017年底,我向钱老师提出请求,他说正忙于《巴赫金文集》七卷本与两本附录的修订,可缓一缓再说。后来我给钱老师寄送中心刊物,不久便收到他寄来的两本书(本文开头提及者)并一纸书信。钱老师写给祁志祥的信(部分图片印在书中),字是行书,清秀端庄,似有孤傲之气,让我想到了刘彦和的“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那是他正当盛年的“作品”。而他在86岁写给我的信,字却有些歪歪斜斜了,那应该是握管不稳所致。于是我很感慨,于是信也就越发显得珍贵,值得照录如下:
赵勇老师:
去年年底约谈一事未能进行,十分抱歉,这一年多来,我被巴赫金文集的审校一事缠住了身(准备出新版),对当前的文艺研究的了解几为空白,改革开放后的那些已不谈的问题,现在又翻了过来。我看《文化与诗学》,按原来的方针继续下去为好,多做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古今中西结合。最近两辑的思路很好,每辑各有主题而兼及其它(23、24辑),这是个好办法。要每辑有个专题,是有难度的,但值得探索与践行;要利用编委与学术委员会,请他们多出主意,特别是后者。他们知识丰富,积学深厚。
我有一个具体建议。在我国现代美学研究方面,金雅教授是很有成绩的,她的论著,拓展了现代美学研究的新思路,而且是我国本土化的思路。照她的愿望,她还想把现代美学研究提高到理论化的程度。还有上海的祁志祥先生,是位美学界的后起之秀,有大量著作与把握全局的能力。你可以先了解他们的著作,然后与他们联系一下,请他们提供讨论专题。在中青年中间,能人极多,多同他们交往。可惜我已赶不上了,老朽不堪了,极为无奈。
匆匆
即颂
教安!
钱中文
2018.5.25
信中提及的二人中,祁志祥教授我是熟悉的,我与他也多有合作,但金雅教授我却联系不多。一年之后的6月14日,她忽然微信于我:“今晨读到您发于朋友圈的纪念童庆炳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文章,感动于童门的师生深情,也重温了童先生的风采人格,触动了铭于心底的与童先生的一件往事。2007年10月19日上午,童先生应钱中文先生之邀,参加了我的博士后出站鉴定会,给予了我迄今难忘的勉勵和指点,对于刚步上学术之路的我,帮助启益良多。童先生娓娓道来,温婉清晰,临走前把他写在北师大便笺上的意见留给了我,我至今珍藏着。言不尽意,简止于此。”紧接着,她发过来童老师写的评阅意见及出站照片,让我感动。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曾进站社科院,钱老师是其合作导师。于是我便想着,以后也要与金雅教授联手,请她为我们的刊物等等出力添彩。但让我没想到是,我还没来得及向金雅老师发出邀请,就被“下课”了。
下课之后,我并没有淡忘拜访钱老师的念头,只是因为新冠疫情暴发,迟迟无法提上日程。而每每想到他与童老师的高情厚谊,就既让我好生羡慕,也让我心生困惑。比如,钱老师说过与童老师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⑦,这种“安全感”该做何解释,又有何深意?他们既然能相互承认或相互买账,那么买账的前提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打破学人相轻的陋习?有人记录钱老师说法,说当年他们与学生争论,他曾说过“子辈学者要‘弑父’,要剥夺父辈学者话语权”⑧。“弑父”是不是他与童老师的共识?有人合并同类项,把王元骧老师拉过来,称他们三人创建了“中国审美学派”⑨,钱老师能否认同这一命名?……
2021年8月7日下午3时,我带着两位帮忙的学生,终于走进了钱老师家客厅。在后来的两个多小时里,钱老师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他的嗓音略显嘶哑,却精神矍铄,并没显得如何老态。他反复说,是老天眷顾我,恩赐我,给了我这么长时间。我说,是仁者寿。
在钱老师的深情回忆中,他与童老师交往的细节渐渐丰满起来了。
2022年6月8日
写在钱中文先生九十华诞之际
【注释】
①钱中文、祁志祥:《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第9页。
②所谓“面对面”对话,是指在2001年8月5—7日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上,童老师与米勒先生曾就文学是否终结的问题当面对话。
③⑦钱中文:《有容乃大——记童庆炳先生》,载《桐荫梦痕:体验与感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52、48页。
④童庆炳口述、罗容海整理:《朴:童庆炳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第330页。
⑤童庆炳:《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特征》,《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⑥钱中文:《又见远山,又见远山!——悼念童庆炳先生》,载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编《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231页。
⑧张婷婷:《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
⑨吴子林:《“中国审美學派”:理论与实践——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2期。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