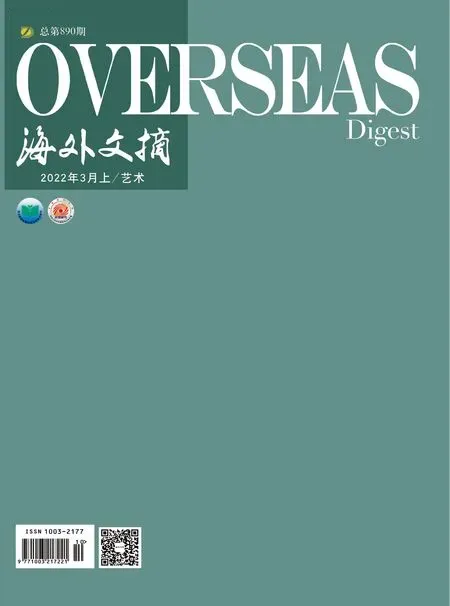新时代青年社会观中的冲突与对立
——以格雷马斯符号理论观《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启示
□欧阳兰/文
根据格雷马斯的象征理论,我们审视了人物在我们与邪恶之间的距离中的态度和关系。这部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反映了他自己对法律公正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在这部电影中,不同角色对李晓明案件的看法反映了法律与人情、正义与道德、善与恶、惩罚与宽恕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这些矛盾,电影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法律边界和价值的思考以及人类情感,以及实现平衡和正义的愿望。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我们需要找到符合公众意愿的标准。法律不一定冷酷,人伦关系也不会是罪犯的逃避,但掌握好他们之间的平衡,不仅能让罪犯家属安全地生活,还能让受害者家属减轻痛苦,过上好日子。当前,正确处理情感冲突,确立合理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9年,《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台湾播出,这部电影一上映,就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反响。这不仅是因为这部电影有着高质量的内容和主要创作者精湛的演技,也是因为它是一部反映社会规律和人类情感温暖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作品。镜头聚焦在李晓明剧院的谋杀案上。展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和人类情感之间的冲突。这部电影讲述了受害者家庭的故事:宋乔安的家庭,犯罪者的家庭:李晓明的父母和妹妹李大芝,辩护律师王赦及其家人,普通精神病患者吕思聪及其家人吕思月,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医院如何面对伤疤和重建他们的生活。这部作品主要通过善与恶的冲突引发人们对社会法律和道德框架的反思。《我们与恶的距离》作为一部反映现实社会价值主题的作品,从新闻报道开始,引出了整个故事。李晓明在剧院被谋杀后,受害者家属、肇事者家属、台湾媒体和精神病团体的生命受到了关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表明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和公众在被依法定罪后,也需要以宽容和人道的态度对待犯罪者的家庭成员和精神病群体。主要创作人物的“善”与“恶”的叠加,使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情节走向层级叠加,情节深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背景下角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对立关系,从而引发对这部作品和社会价值的进一步思考。
1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概念解读符号矩阵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概念解读“符号矩阵”是格雷马斯从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施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型发展到第四维度的符号分析模型。格雷马斯认为,所有的故事都基于一组对立的意义,但一组并不足以支撑整个故事,因此,将二元对立扩展为四元数,使得故事叙事和人物分析的实现更加完美。
2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中的应用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中的应用在深入分析我们与邪恶之间的距离之前,让我们先分析一下重要人物及其性格和态度。
第一个是宋乔安,受害者天彦的母亲。她不仅是受害者的家人,也是一名记者。在她的儿子被杀后,她对新闻业非常苛刻,对收视率有很高的要求。同时,丈夫刘兆国夫妻矛盾不断,与女儿的亲子距离越来越远。因此,宋乔安长期以来承受着不可抗拒的精神压力,嗜酒成眠。此外,杀人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在哥哥入狱后被父母改名为李大芝。她希望自己能以新的身份过上美好的生活,不要管她的哥哥和父母。但是,李大芝总是想着她的哥哥和父母,她希望自己能挣钱养活父母,她希望纠正舆论,要求获得杀人犯家庭的头衔,让自己和父母公开地生活在社会中。还有王赦,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他也许是关于我们与邪恶之间距离的故事中最理性的人。他身上溅满了粪便,受到妻子的辱骂和盘问。他的回答是“我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他乌托邦式的世界观中,囚犯在被定罪之前也享有人权。虽然他的律师身份代表了法律,但他的价值观中仍然充满了人性。他并不想为李晓明开脱。他只是想调查一下李晓明犯罪的原因,作为预警和反思,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案件了。最后,宋乔安的丈夫刘兆国是受害者的家人。虽然她没有宋乔安那么极端,但他只是想通过法律手段惩罚囚犯。《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主要人物有着独特的形象和态度。他们通过李晓明谋杀案相互联系,导致了善恶的矛盾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使影片的情节跌宕起伏,精彩且耐人寻味。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根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理论,首先我将加害者家属李大芝作为关键语义素X设定,她代表了“社会人情”,从想摆脱杀人犯妹妹的称谓开始,想让家人光明正大的生活在社会上,直到被宋乔安发现身份,离开新闻台,到奶茶店工作却被侮辱、被扔鸡蛋和垃圾。但最终,宋乔安对社会放下怨恨,与李大芝重新合作,开展愉快的工作。从李大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犯罪分子的冷漠,以及人们放下怨念之后的温暖。根据格雷马斯符号矩阵,与她对立的人物是受害者家属,即宋乔安,同时,李大志与宋乔安的冲突也是整个作品的高潮。从法律上讲,宋乔安希望李晓明受到法律的制裁,依法死刑没有什么错,然而,与此同时,当她得知下属李大芝是李晓明的妹妹时,她爆发了,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并将失去儿子的痛苦传给了李大芝和她的家人。她派电影摄制组跟拍李大芝的独家新闻,也希望李晓明的家属受到法制和舆论的制裁。因此宋乔安是与李大芝对立的反X。他们主要体现了人情与法制的对立。在这部影片中,王大赦律师和受害者家属刘兆国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对立。在社会案例中,人类的方方面面都值得讨论和思考。无论李晓明的家人渴望生存权,还是宋乔安和刘兆国希望坏人受到法律惩罚,他们都有可以理解的因素。所以,在作品的最后X李大芝和反X宋乔安、非X刘昭国和非反X王赦都达成了和解。整部作品形成了一个符号矩阵,善与恶、法律与人情的矩阵,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在法律和道德的合理存在下展现了各种矛盾的各种人物要素的对立。
3 符号矩阵下的人物关系
3.1 社会大背景下的道德较量,规则与人情的冲突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X迫害者家属李大芝与反X受害者家属宋乔安之间的矛盾。李大芝,原名李晓文,原是健康积极的新闻系大学生,虽然她的家境一般,但也活在父母和哥哥的关爱里,自从她哥哥李晓明在戏院犯下9死21伤的滔天罪行后,她变得颓废无助,把自己锁在家中不愿社交,在母亲强迫她改名外出工作后,她找回了一点生活的希望,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及其家人带回正常的生活,摆脱自责,然而,当她发现自己的上司是罹难者家属的时候,她开始惊慌失措,当被宋乔安发现自己是李晓明的妹妹时,在母亲强迫她改名外出工作后。李大芝认为即使他哥哥犯下了罪,但她和她的家人也有权利正常健康的活下去,而不应该一直遭受社会的谴责。
宋乔安,剧中是台湾品味新闻台主管。在此之前,宋乔安和刘昭国育有一儿一女,且夫妻二人都是媒体工作者,生活幸福,乔安对儿子天彦尤其喜爱。然而就在母亲节前一天,宋乔安带天彦去看电影时,在乔安出去接个电话买杯咖啡的那个时间段,李晓明闯进了电影院开枪扫射杀死了九个人,而天彦就是遇难者之一。这对宋乔安一家是巨大的打击。从此之后。在公司里,宋乔安成了一个冷酷的上司,对同事冷酷无情,大声责骂员工。在家里,她不愿意和老公、妹妹谈起天彦的事情,不去触碰天彦的东西,不进天彦的房间,对老公和女儿天晴冷淡,最终导致婚姻出现问题,她自己已经完全被打垮深以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甚至发出“希望自己当时没有出去接电话买咖啡而是和天彦一起死了。当宋乔安知道知道李大芝就是李晓明的妹妹时,她把矛头和怒火都指向李大芝,她派摄影组跟拍李大芝一家,深度挖掘李晓明的家庭,想探清是否是家庭教育影响了李晓明的身心健康。
宋乔安和李大芝的矛盾体现在加害人家属是否有权利重新正常生活下去。当李大芝质问宋乔安:她的哥哥是杀了人,但她和她的家人就没有权利活下去吗?这时宋乔安反问李大芝:难道她儿子天彦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这是整部作品最有见地的两则疑问,也是最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的确,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家属,他们都有权利活下去。在法律层面,情况的确如此。在道德层面,人们认为李晓明在戏剧中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因为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所以在一般民众认为李晓明的家属应该为此事负责,甚至有些偏激民众认为,李晓明的父母应该和李晓明一样被判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乔安与李大芝的争吵不仅反映了善与恶的矛盾,也反映了法律与人情的衡量。
于道德来说,李晓明的做法的确令人厌恶和恐惧,但是这和李晓明的父母有什么关系呢?对于道德责任,李晓明在这部影片中给出了答案: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花二十几年去培养一个杀人犯。在社会道德层面上,李晓明父母虽然没有犯下罪,但也引起了社会公愤。由于涉及到一亿台币的赔偿金,若其父母不受到处罚,案件将以李晓明死刑了结,巨额赔偿将从税款中支付。
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道德来惩治李晓明父母是符合平息社会公愤原则的,但大众的侮辱话语和举止又令人寒心,毕竟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杀人,他们自己也没有触犯法律,而他们也常常生活在自责中无法平息。
3.2 注重原因和注重结果的矛盾
律师王赦和受害者家属刘昭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注重原因还是注重结果。一方面律师王赦并不是想为李晓明辩护他的罪行,而是想探求出李晓明实施犯罪的愿意。由于他是李晓明的特辩律师,在不明所以的大众看来他就是为李晓明辩护,为他免罪。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他只是想探求李晓明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代表法律却远远不止步于法律。而刘昭国则是注重结果的代表。他希望李晓明越早执行死刑越好,不应拖延,他不希望李晓明的案件再次掀起社会风波,同样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他,他与宋乔安大不相同,他不希望新闻抓住道德标准来衡量李晓明的父母,推迟对李晓明的死刑判决。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法律惩罚李晓明。因此,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开始,刘昭国就以公务之便与律师王赦进行了会谈,他说明王赦想要探求实施的原因的为了帮助李晓明躲过死刑。的确,刘昭国承认那是一个律师的职责,但是,那真的对得起人们的良知吗,难道是要那纳税人的钱养他一辈子吗?王赦提出,探究原因的目的是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外,纳税人的钱一直在支持各种惩罚,因为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凶杀案在世界各地上演。王赦提出了新的疑问。杀人游戏和家庭教育只是这起案件的表面原因。刘昭国反驳说,他不是上帝。他只是想惩罚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人。
3.3 媒体人之间的道德感矛盾
在宋乔安发现李大芝就是李晓明的妹妹时,他派摄制组跟着李大芝,找到了李晓明父母的藏身地,拍摄到了李晓明的非公开葬礼独家画面。在这则新闻播出后,不出意外的大众找到李晓明父母家,扔垃圾、砸玻璃,来宣泄愤怒。而宋乔安的丈夫刘昭国,同为媒体人,却对宋乔安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不应该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并且认为宋乔安身为体制内的员工不应该放任无良媒体的作为,若不改变则为放任和犯罪,媒体不应该做出如此没有道德感、没有素质的事。更为重要的是李晓明在被捕的时候放言要扬名立万,而宋乔安这种做法更加助长了李晓明的嚣张气焰。刘兆国认为,作为媒体人,我们不仅要关注收视率,还要通过媒体理顺社会道德价值观。,尽管宋乔安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他的行为出于道德考虑也是极端的。因此,从宋乔安与刘昭国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人之间道德意识的冲突。
3.4 案件真因的探求和家庭温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
王赦是一名执法律师,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从事着法扶工作,收入不高。即使他的妻子家境优越,但也愿意为了他过上普通生活。而在王赦妻子发现王赦在给李晓明和其他精神病患者作特辩律师的时候,妻子由于害怕社会公愤对自己和孩子的影响,她劝王赦放弃为李晓明做辩护,去走父母铺好的路。因为她担心社会公众的愤怒会影响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妻子从支持丈夫的工作转变为反对丈夫的工作的根本原因是王赦因成为李晓明的律师而引起的担忧,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争吵。律师有责任在法律层面探索真正的原因,但追求和平也是妻子最简单、最起码的要求。在丈夫职业道路和职业道德的选择上,夫妻之间存在着对立和矛盾。
4 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分析《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情
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可以将影片剧情分为六大部分,即为主体与客体、帮助者与敌对这、发送者和接收者。这六个部分相互联系,连贯起来了整个剧情,可观六者之间的联系。
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中的主体一般是整部影片的主角,具有主观目的并想要达到目的,而客体与主体相对,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联贯穿于情节的重要部分。发送者就像整个情节的助推器,推动着整个情节的发展趋势。顾名思义,接收者接收发送者发送的消息,发送者可以是任何主要角色,甚至是主题。助手和对手都存在于主体周围。帮助者是帮助主体实现目标欲望的角色,对手是阻碍主体实现目标欲望的角色。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主要阐述了李晓明戏院杀人案和应思聪因精神分裂症冲入幼儿园引起恐慌两个故事。
4.1 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分析李晓明戏院杀人案
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得出宋乔安是整个故事的主体。在这个案件中,宋乔安面对着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压力和丧子之悲的冲突。在发现其下属李大芝就是凶手的妹妹时,矛盾爆发,其关于人性的恶展开了激烈讨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客体是人性的邪恶。案件中的宋乔安为了抒发丧子之痛,探求真相,给自己和其他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以缓解内心的悲痛,通过和李大芝的激烈质问探求什么是人性之恶。宋乔安认为向李晓明那样的疯狂行为是人性之恶,而李大芝在被拍到住处和私人画面的时候时也爆发了自己的愤怒:他们这些媒体杀的人不比她哥哥少。通过讨论人性中的邪恶是什么,促进剧情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刘兆国反对宋乔安的错误新闻观,提到宋乔安和刘兆国是对立的,所以刘昭国是对手。宋乔安的其他下属,如苗牛石,无疑成为了帮手,因为他们不敢违抗宋乔安的命令。
4.2 用格雷马斯行动元分析应思聪的精神分裂症冲入幼儿园引起恐慌事件
首先介绍一下这案件的主体应思聪。他既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疯子,天才在于他对于拍摄影片有着超高天赋,疯子在于他忍受着过大的压力易产生偏激行为,例如妈妈在他幼时遗弃了他、在服兵役期间女友自杀、有拍摄天分的他却在剧组遭受各种阻挠,这也是他得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在应思聪精神分裂症发作时,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他认识了宋乔平,她是一个贴心、温暖的护工。每次应思聪感觉心理不舒服时都会找宋乔平,而宋乔平也很耐下心的开导他、安慰他,因此,宋乔平在这个案件中是辅助者。回归到这个案件的关键,患有精神疾病的应思聪冲入到幼儿园进行拍摄引起了空慌,而他内心纠结的关键是: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的妈妈愿意无情的抛弃孩子离开,为什么是他的女朋友竟然在他服兵役期间自杀,为什么是他的上司逼着他、让他没有喘息的空隙。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他精神分裂症的原因,而他上司又在一次催着他交出作品,而无法控制情绪的他冲入幼儿园劫持人质。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为什么他是客体。在案件过程中,无论是幼儿园家长也好,还是应思聪的姐姐应思悦均为反对者,前者是因为幼儿园家长对此事的恐慌,后者则是姐姐对弟弟精神状态的担忧,希望弟弟的病可以治愈,回归正常生活。
从以上两个情节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整部电影在矛盾中发展,以和解告终,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贯穿于整部作品。李晓明和应思聪的过激行为均触犯了法律,按照法律他们应该受到严厉的制裁和处分。但同时,他们也有精神问题。法律通常容忍有精神障碍的罪犯,但这无疑对受害者家属不公平。他们所遭受到了痛苦不愿以一句精神失常而得以平息,因此体现了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其次,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最终都以和解的方式结束。宋乔安最终放弃了执念,与丈夫、女儿和解,打破台湾传统新闻业的枷锁,辞去原来的工作、做起了正义积极的新闻,李大芝也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重回新闻台。无独有偶,她的长官依旧是宋乔安,但这一次没有对抗,只有相互努力。这种和解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法律可以和人情以特定的比例共存,以促进社会生活和谐。应思聪也在姐姐的帮助下,获得了父亲和继母的帮助,也达成了和解。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关心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歧视现象逐渐减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善与恶之间的和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社会就会更好。
除此之外,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还有律师王赦对真相的追求、他作为罪犯辩护律师的工作和他妻子美媚希望丈夫回归正常简单生活之间存在矛盾。并且,律师王赦是经历了这两场案件的,在李晓明案中他是律师,而在幼儿园案中,他不仅是应思聪的律师,也是受害者的家人,为了探索真相,为精神病患者争取世界的温暖。也正是因为幼儿园案件,让王赦和其妻子的矛盾爆发,展开了对职业生涯的讨论。而在最后,妻子依旧选择支持丈夫的工作,而王赦在选择做法扶律师的同时,也做到了多多关注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危。所以两人达成和解,使工作和家庭得到平衡。
5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对立冲突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表现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从而引起人们思考。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我们可以发现多种冲突,如法律与人情、职业道德和人情道德、职业理想与家庭规划都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联。
5.1 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李晓明、应思聪因为过激行为触犯了法律,而同时他们都患有精神类疾病,在人情道德层面他们有可以躲过法律的制裁。这些角色均在法律层面均有大罪过,不可饶恕,但是社会不是只有法律,人情可以给予一定的庇护,而在大众看来,涉及到生命、关涉到儿童的罪行是不应该被原谅的。从而就体现出了法律与人情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并不是个例,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法大于情还是情大于法的争论也依旧争持不下。在影片中,导演用更加直接的手法呈现了这种冲突。在我国《刑法》中,对精神病人犯法的处罚也作出了详细规定,要依据神经状态定罪,不能以偏概全,要做到仔细鉴定,逐一鉴定。所以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对李晓明和应思聪的处罚完全不同,前者被执行死刑,后者却被送入医院治疗。而对于直接产生法与情冲突的主人公宋乔安、李大芝,在这部影片中,编剧使用了中庸之道缓解了冲突:宋乔安离开原来的单位,进入到新单位重新开始积极的工作。在这时,李大芝也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工作中,加入了新闻台。但编剧特意制造了一个巧合,李大芝和宋乔安加入了同一家新闻台,与其开头相呼应,暗示着从敌对的工作态度到积极合作的态度的转变,从而表达了法律与人情冲突的缓和。
5.2 职业道德与人情道德的冲突
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宋乔安和王赦身上。宋乔安是一位媒体人,同时也是李晓明案件的受害者。在知道李大芝是李晓明的妹妹后,宋乔安十分惊讶和愤怒,为了挖掘出李晓明家的状况,她派下属缪纽世跟拍其父母住处和李晓明非公开葬礼画面。所有做局部技术处理,但住在周遭的人依旧可以一眼看出地点,所以李晓明的父母家遭受民众扔垃圾、砸鸡蛋的泄愤,并且李大芝和她的爸爸妈妈的生活被严重扰乱,从这一点上看宋乔安的确是违背了职业道德。但作为受害者家属,想深入了解李晓明的家庭背景,探究李晓明的行为是否受灾家庭的影响又是人之常情。从这里可以得出宋乔安身上所存在的职业道德与人情道德的冲突。同样,编剧以宋乔安与自己和解,走上阳光正确的道路的中庸方式平衡了这种冲突。
同样有这种矛盾的是律师王赦,与职业道德来讲,王赦竟然做了李晓明的辩护律师自然要帮着李晓明减轻罪行,在对于人情道德方面,王赦作为法扶律师为罪犯辩护就是违逆大众心理的选择,虽然他是为了调查李晓明的心理,做好社会预警工作,但这种原因是不被大众理解接纳的,大众认为坏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通过法律的束缚才会减少这类案件再次上演,因此是违反人情道德的。在这个案件中,因李晓明被判死刑而结束了王赦的职业道德与人情道德冲突,这体现了外界因素也是缓解自我价值冲突的一剂良药。
5.3 职业理想和家庭规划的冲突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编剧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矛盾,即在自我职业理想与家庭规划之间的权衡。人生的道路究竟该如何选择?是追随自己的内心还是向家庭的安排妥协,编剧在这部作品中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答案。在这种矛盾下不急着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先试着追寻职业理想,但在这条路上,家人的感觉不容忽视。就像《与恶》中的王赦一家。王赦一心想要找出李晓明犯罪的深度原因,在这期间,他的妻女一直承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妻子所遭受的心理压力是难以舒缓的。当王赦成为李晓明的辩护律师期间,王赦的妻子美媚正值怀孕期间,而民众对王赦不断施压让美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她害怕民众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从而伤害到她和她的孩子,跟担心民众的愤恨会再次对王赦做出不公的事情。
然而王赦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律师,做着永远也打不赢官司的法律援助律师,收入低,还被群众辱骂说没人性,替死刑犯开脱,但是他很有理想和抱负,但生活情感中却愧对自己的妻子,没办法给她更好的条件,但他很爱这份受力不讨好的职业。妻子一开始是理解并赞许的但是经历了公众的愤恨之后,女生乞求平安的本能初展,劝王赦放弃。起初,王赦并不同意,但随着案件的发展,妻子的出走,他向家庭妥协欸。其实,那不是妥协,那是和解,是爱的和解,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正义合格的律师,并且他的这种和谐缓解了家庭矛盾,再次找回了家庭的温暖。显然,在职业理想和家庭规划的矛盾中王赦做出了一个双赢的选择。
6 个体基于认知矛盾的反思及价值观的形成
《我们与恶的距离》对真实案件的改编阐述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教育的思考。社会教育的主体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社会教育的内容关联于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等。而这种教育在现实生活中是缺失的。大众通过观看这部作品,可以加强对自身社会价值观的思考。而人的价值观是随着自身亲身参与而形成的,大众的目光追随着剧情发展,剧情激发思考,在潜移默化中,在剧情与个人情感和个体思考下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
6.1 真实案件下的情感抒发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作品所展现出的冲突主要是法律的公正与人情的温暖之间的对立关系,善与恶之间的度量,以及渴望社会少一些恶,多一些善的愿望。在每一个社会个体成长的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会对其社会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价值观会随着思考的加深、成熟而不断完善。在这部影片中,编剧对宋乔安的态度安排得十分精巧。从怨恨到原谅,在工作上如此,在生活上更加如此。这正是人们在处理烦心事的日常态度。从宋乔安的情感态度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变化,从而不断思考个体在处理事情时是否可以先冷静想一想,以达到跳过不成熟的过程。通过《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情感抒发从而思考自己的情感态度,设身处地地为主角考虑,代入式的情感思考在现实中更加容易促进自我的情感反思。无论是过于平静还是过于激动的情感所影响的社会价值观都容易受到冲击产生偏差,只有在繁乱的琐事中保持自己的节奏,有着正常的情感抒发,形成有活力的价值观才是健康的正常的。
6.2 同情心的价值观的判断与应用
说到同情心,《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被同情心安慰。宋乔安、刘昭国夫妻的丧子之痛需要同情心的宽慰;李大芝和她的父母因为是李晓明的亲属而遭到社会的怨恨泄愤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需要同情心的安抚;王赦和美媚也因为社会的压力需要同情心的疏导,应思聪因精神疾病和巨大精神压力而犯下的罪行也需要同情心的理解。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大众真的不会给予如此之多的同情心。同情心的给予与否和给予量的多少是基于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事件对个体进行冲突后,大众依旧可以给予案件参与者一定的同情心,并且通过认知判断出同情心究竟该给谁,这都是社会价值观所形成的。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得到了一个和美的结局时,社会道德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同情心该如何正确运用,这又是社会价值观的作用结果。通常来说,社会价值观影响着人们在社会场上的行为举止,通过加强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从而加强社会道德责任教育,达到更好的运用社会同情心的目的,是社会这个整体和美大同,个体幸福美满,这便是通过教育达到的。
6.3 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和和解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编剧和导演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无论是多么大的怨恨,或者多元的观点,在不断地发展和思考后都会走向和解。但他不同于其他影片的无理由和解,强制性欢喜结局。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争吵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矛盾一次一次的加重,案件一次又一次的升级,使人物关系不断交织,又通过不同案件,人物的不同反思,角色自己冲破牢笼,将多元的思想归于统一。由此看到,人类的社会价值观在不断发展进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不断进步,社会才会多一点爱与温暖,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会融化,冲突才会和解。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但是不需要多元的冲突,如果有,也需要慢慢缓和冲突,趋于大同。给当代社会价值观注入人文色彩,且在大背景下使冲突不断调和,将其留下的美好精华注入人的品质。这样社会道德社会法律会更加平衡,社会纷乱会更少。
7 《我们与恶的距离》启示意义深度剖析
在文学中有这样两种类型,单一价值观的独白小说和复调式小说,单一独白式小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读者,复调式小说就好比集中旋律和谐共存,而真正好的理解是不应该受到读者意志主导的,在这部剧中笔者看到了导演的一些想法,他并不是把人物的恶强制性地向我们灌输,而是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局引起我们的思考,这种方式在剧集中是这样,在舞台剧中更是如此。
在翻版的舞台剧中,黄志凯导演给观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立刻执行李晓明的死刑?选项为:A是;B否;C无法决定。
在选项中可以设计无法决定这个选项是让观众有时间有权利看清自己心里的犹豫。在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东西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当现场观众做出选择后会立刻将反馈投入现场的大屏幕上,并且决定了戏剧的后半场。在其中一场巡演中导演即兴问观众:你是否愿意继续观看现场直播?观众的选择竟是压倒性的“否”。
现场互动的投票、论坛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社会价值教育和凝聚共识的过程,也给了观众一个机会去反思。若投票后,“是”与“否”的票数没有过半,则代表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然而很多事情我们决定的往往不只是当下,而会决定很多人的命运。这让我们反思,是否能思考得更远一点。
很多观众反映做完选择看完自己选的结局后反而没有得到标准答案,反而更加疑惑了。但困惑是理解的开始,这样才能搅动我们的思绪去弄清楚问题的不同面貌。在身处案件中过多的情绪往往会让我们看不清这件事,而人有一定的情绪,当情绪来临的时候就请感受情绪,等情绪冷静后再思考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笔者认为在看完《我们与恶的距离》后我们应该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把人杀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2)王赦的正义会将宋乔安推向地狱吗?(3)宋乔安的愤愤不平是通过欺负李大芝来宣泄的吗?(4)如果在这个案件中,受害者将向谁讨回公道?(5)我们口中的正义和公道会不会是捅向别人的一把刀?在提出这些问题之后笔者愈发觉得:不是说在看完这部剧之后我们就要同情精神病人,只是希望再看到类似案例是大家多一点思考时间和角度,虽然我们不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即使是案件的涉及者或是当事人都不一定会知道所谓的事实,但至少我们要有同理心。因为我们所谓的正义,可能正把另一个人推向地狱。这部剧告诉我们,从辩证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善恶。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近在毫厘,在一言一行里,在推波助澜里。但我们与善同样相近,在谨言慎行里,在温柔宽容里,在坚守道义里。■
引用
[1] 杨杰.自我反省式的寓言故事_矩阵理论视野下的杀生[J].东南传播,2013(12):104-106.
[2] 冉恬羽.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废都》的女性世界[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8):59-61.
[3] 赵利利.试论格雷马斯叙事矩阵对新闻实践的启发[J].传播与版权,2015(5):5-6.
[4] 党丽霞.以符号矩阵理论浅析中韩穿越剧叙事:步步惊心和屋塔房王世子为例[J].视听,2016(7):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