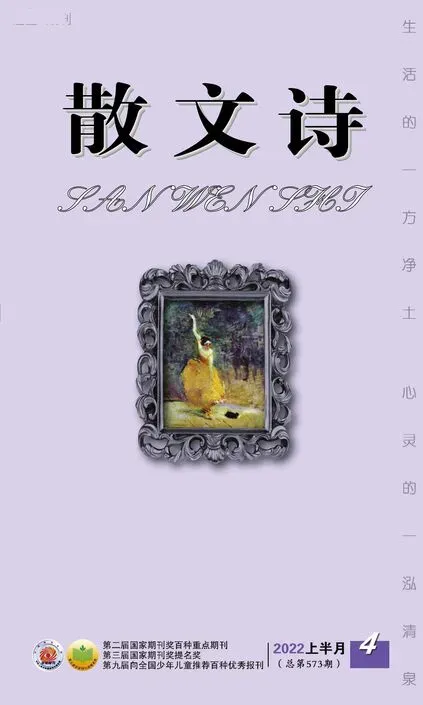在贺兰山下写诗
◎王跃英
再说沙湖
一汪水,一脉沙,资质与周围条件无异,却成了中国旅游排行榜的天之骄子。
几十年,一直风姿绰约。
几十年,这沙的名头与身边的毛乌素、腾格里、乌兰布及一众沙漠,响誉四方;这水的成分里,河水、雨水相映成趣,都是天赐的明镜。几十年来,这一角一直水波连天、鱼鸟翔集,生动在北中国干旱带边缘。
生死相依,不离不弃,倒是沙、水这对前世冤家唯一不变的信念。
简单的沙,简单的水,书写出来的,都是惊世文章。
通向这片人间秘境的大道,游人一直络绎不绝。
葫芦人家
院里,挂满大大小小的葫芦;院外,贺兰山淡蓝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葫芦高高低低地挂着,心事高高低低地荡着。一阵清风吹来,葫芦跟着点头致意;密密的叶子下,布满斑斓光影。
女主人姓陶,在葫芦上烫画,是她的看家本事。
端详女主人,看不出她的心事。只要圆润吉祥的葫芦在她的手中、怀里,就看到了春风拂柳,就有了乡思归途,就有了佛踪禅意,就有了儿女情长。
游人鱼贯而入。
Leech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语用能力是指对说话者的目的和用意的理解能力。他把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交语用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两部分。其中语用语言能力以语法能力为基础,涉及语言的使用规则,不仅包括正确使用语法规则遣词造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在一定的语境中正确使用语言形式以实施某一交际功能的能力。社交语用能力是指遵循语言使用的社会规则进行得体交际的能力,是更高层次的语用能力[2]。Kasper则把外语语用能力定义为外语学习者对外语语言行为的理解、产生和习得[3]。
一枚葫芦,被一双巧手衍化成一枚追求幸福的定海神针。
敬览家谱,方知女主人乃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一脉。
顿感满院的葫芦更生动起来。
远处的贺兰山脉也生动起来。
泥哇呜
泥巴也能卖钱?
透过低矮的并不显眼的手工作坊,一位回族艺人用他那自尊的双手,让我们在一团朴素的泥巴面前,没有失明。
就是我们脚下踩来踩去的泥巴,经过那双灵性的手掌打磨,再给以一团火焰,便造化神奇地成为一种能吹奏出呜呜哇哇妙音的乐器。
它的名字,自然也是“泥”字打头,配以象形的“呜呜哇哇”声韵。除此之外,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多余的配件,就能让你把这团泥土像粮食一样,亲近到嘴边。
那团泥巴被团成一盏通红的灯笼,照耀着我们,去做踏“泥”有印的事情。
只要踏实去做,就能在泥巴里回旋出荡气回肠的韵味。
我们踏实地踩在泥土上的脚印,是一行行人生之诗。
百年老藤
没有仅仅成为一种标签。
126年了。
如若不是主干盘曲的虬枝,如若不是铭牌上的注释,谁能想到这一丛丛葳蕤茂盛、硕果盈枝的葡萄藤,已届百岁高龄?
百年,一个世纪,其中任何一次呼啸而来的雪灾,都足以灭杀一切绿植,何况还有虫灾、旱灾、水灾……甚或那些不请自来的无妄之灾!
它们生长在这方天地,恐怕从来就没有过枉活百岁的野心。
一年,一年;一岁,一岁,就这么攀上高枝——周身光华灿烂。
美人迟暮,风华依旧。用在这一丛丛百年老藤上,绝非浪得虚名。
有它们在,周围新栽植的葡萄树苗,没有理由不欣欣向荣。
石嘴山密码
河流到达的地方,总是先于人迹。
黄河走进宁夏,量身定制397公里的身段。出于偏爱,离开时,透支其中108公里留在它的名下。贺兰山绵延220公里,过半的身子安卧在此,为它抵挡乌兰布和十万吨流沙。
从一个微缩版的民族自治区分娩出5310平方千米的城郭,版图娇小,丰饶的河流供养着最热的骨血,峻峭的山峦磨就一副最硬的嘴巴,打从名字出世,就天生一副大嗓门。
没法不让它牛气。
体量小巧,山中却藏着掖着世界上最值钱的乌金;大河奔流,站在石嘴子码头,名扬天下的河套平原就此分为前套后套。上包头,下兰州,钢碳,瓷器,金羊毛……白帆上舒展着的都是顺风顺水的希望,河套平原富庶的日子就等在岸边。
历史总是在最坚硬的地方不同凡响。
讲述传奇,得有天生一副好嗓子。
坐拥一方好山水,这里传出的声音,怎么听,都宛如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