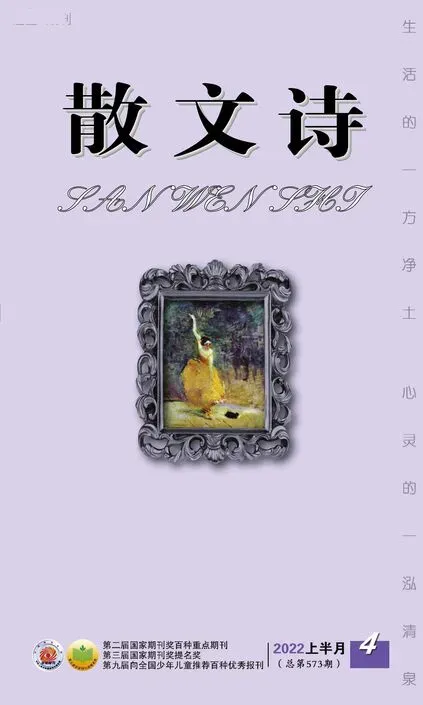窗 台
◎梁卫忠
孤烟般沉默的傍晚
关上窗户,昨天被抛向远方,秋天从云层里落下,孤鹜把头埋进万千树影,湖面鳞波中溅起沉醉的气泡。云在水中,心思浩渺,左岸青山分来了半面雨声,黄昏湿透的羊群,如同塔影里沉默的雪。
野菊花染上天空的蓝,骤雨般洒落在溪桥边。一定有一个人取风当马,山在动,也一定有另一个人手捧云岚,雨落下来。还有那么多人蹲下,像一块块石头,举起和晴天一样颜色的微光,把扬起的额头交给天空和雨。
他们应该与这一河毛腊草有着共同的境遇和命运——站稳脚跟,随风而动。又像一本书,任何单独的一页,都无法完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夜晚没有影子,用渔火织成的网构成此刻的傍晚,我喊你的名字,树叶落下来。
一个迟到的人,怀揣星空,衣袂间藏满风云和冗长的雨季。
窗 台
眼眶里暗暗的光,临近大地的胸口,时间的影子砸下来。把这一窗台鲜花,都抛入你的心里,彩虹跳动着细碎的水花。
我所有的心事都是你晾晒的谷物,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发酵,这种感觉唤起一种与生俱来的疼痛,却也散发着莫名的清香。雨落在窗台上,轻微的爆裂夹杂着兴奋。
九月是一只落水的麻雀,所有殷红都飞不过的栅栏,需要我把心抛进去,设下秋天的道场。
五谷为器,百草当歌,向阳花沉默,像一盏刚刚熄灭的油灯。
我们在窗台前对坐,写下彼此的名字,时间一粒粒变成僵硬的石子,我们曾拼命拾捡,把它们堆积在种植月季的花盆里,期待土壤和养料使它们变得柔软,期待月季的芬芳为它们赋予新的生命。
于是,就有一些时间趁着夜色爬上月季的枝干,又在某个早晨的阳光下,绽放成一束嫣红的花。
梦里溯源一条河流
风拍打着山崖,在更黑的夜晚,则会把自己挂在树枝上倾听——河流是岁月长长的划痕,还是大地俯仰的褶皱?此刻,它站起来,手捧黎明,向着黑色的断崖一跃而起。
水流的缓冲地带,一阵急风漫上麦田,惊雷般的晚夏击落一粒早熟的麦子,无人敢认领的果实,喂养着那些乌鸦、老鼠和雉鸡。
一条河流不需要江海,它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流着,有时干枯成一条冬日的树枝,有时也会丰盈成春天的草甸,但终究它会在更加遥远的平地上,渗入海绵一样的土壤。
它绕着一个个村庄,吞吐人间烟火;它绕过千万颗石头,横贯整个有梦的夜晚。
风依旧拍打着石碑一样的山崖,像在镌刻一条河流的生平,此刻,风又将所有嶙峋的事件擦去,重新思考着:怎样才能用更加简洁的文字去叙述一次次远去,又一次次生还的河流?
鸟叫在兰花坡
兰花坡铺满了珍珠般的鸟叫声,落下,又溅起。这声音竟然还活着,像兰花的魂魄,嵌着露水和风。
我蘸墨写下春天,二月兰偷偷捂嘴笑,一只乌鸦落在树梢上,看着另外两只乌鸦发呆,于是,整个春天都开始发呆。
太阳无形的牙齿,啃噬季节的芒刺,大地的唇印睡在鸟鸣里,心头缠绕的枯藤又在返青。
两棵槐树之间,是早春的通途,向着冬天、雪地和雪地上套着绳索的麻雀。
山岚千嶂,风仅能吹散半层,绵羊叫着,一个老人醒来,他望望窗外挂满春天的老楸树,再一次合上安详的双眼。
辛丑秋日刻印杂叙
磨平一块石头黄昏的海啸,我看见自己,倒映在三万年前的一场浩劫里。
云雾落在树梢上,清晨的拐点被一阵鸟鸣声击落,又被阳光平分成两半,未及撤退的恐慌,被称之为岁月的沉淀,或者年轮。
多少风雨才能成就一块石头的硬?多少霜雪才能冰封一块石头的岿然?此刻,我把名字刻进你的骨髓,就像刻进辛丑秋日的这场风雨里。
我要用带着刻度的眼睛,给你向北的星空和驭风的绳索;我要给你明天,让你抵达太阳的边缘,重新熔炼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要给你一面镜子,让你看见落日中向着树林深处散步的人;我要给你一片落叶,给你去年走失的整个秋天,让所有的悲伤都封存在镜子里,低下头,向世间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