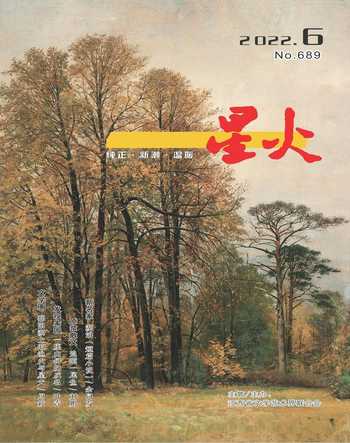在花朵中念与痛
马晓燕,回族。散文、诗歌作品见于《飞天》《星星》《中国国家旅游》等刊。出版散文集《如果,我在唐家河遇见你》。四川省作协会员。现居四川广元。
槐花幾时开
在青川小城生活久了,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有时候,会觉得小城很小,小到一抬头就能相互看见各家的烟火,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有时候,又觉得小城很大,大到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比如传说中芳华绝代的女神,精于卜筮的预言者,他们有如雷贯耳的名声,却潜游于小城深处,似乎一辈子就躲着你一个人。
村上春树说:“如果一直想见谁,迟早肯定见得到,所见之日,便是终结之时。”这么说来,我们一直盼着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逃不脱的某种命运。女人一生都在寻觅和等待那个最想去爱和最想去嫁的人,那个华发高贵,气质澄明如水晶的人。他可能无法给你最好的爱情,但他一定会给你最美的遇见。他是你年少轻狂时,唯一一个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的人。
少年时,一边读着爱情诗,一边幻想着爱情的样子。最初,只想长成《致橡树》中木棉一样的女人,遇见橡树一样的男人,他无怨地守着你,你无悔地陪着他,青梅竹马过完此生。可是长着长着,竟然长成了道旁的“一棵开花的树”,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为永远不会到来的那个假想中的人,一厢情愿、热烈而倔强地盛开着,孤芳自赏,空自零落。
所以,总会为道旁或窗前一棵开花的树而驻足,或叹息,或感动。但愿遇见它的人是温柔的、慈悲的,不会轻视默然站立的那棵树,它或许无趣,卑微,不聪明,不漂亮,但它不求回报,死心塌地地守护你,也是在经历它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可能是你前缘未尽之人,不然,怎会千山万水,偏偏跑到你的心门口安营扎寨呢。
所以,当树枝不小心触碰到你的时候,请不要残忍地斫断它,如果可以,请你温柔为它梳理下凌乱的枝条。当它怒放的时候,请不要鄙夷它浅薄无知,春天姹紫嫣红,唯有它用尽了一生的力量和妩媚,只为取悦你一个人,它的本相和内心,是庄严和慎重的啊!
就像去往青川的山野和道旁,长着许多的槐树,每当春天大踏步迈向夏天的时候,那些洁白如雪的槐花就优雅自若地打开了自己,那不早不晚、不徐不疾的仪态,像极了一个个信守誓约的女子,恪守着时间,也恪守着自我内心的品性与戒律。当它们释放出一生当中最热烈的芬芳的时候,整个春天,也都充满了甜蜜的味道。
这个季节,站在小城寓所的阳台望出去,翠色环绕之处,掩映着突然的白,有的连成一片,有的星星点点,即使漆黑的夜间,也是若隐若现。山风妖娆,吹进小城的香气,时而芳香喷薄,时而暗香四溢。山间的槐花,属于香艳却极为朴素的花朵,虽然站得高,看得远,但从不张扬,总是温婉地居高临下,自身芳香的同时,还不忘分享给周边的树木,就连山上的岩石和悬崖,也跟着“雨露均沾”。它们香甜,吸引着诸多的鸟儿和蜜蜂,也吸引着捋花做青团的妇人们。
我的旧居位于老城区,与木牍公园隔着一条宽敞的马路,所以,我爱着公园里的所有草木,却又不得不跟它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尤其是看到谁的窗下守着芊蕙葳蕤的梧桐,或是潇洒俊逸的银杏等嘉木,更是羡慕不已。
有一天猛地发现,隔壁体育小区里的那株大槐树,朝南的枝条竟然奇迹般地向我这边长了过来,已够着三楼,快要遮住楼梯口的大半个窗了。想到此后的夏天,也会有树枝吻着我四楼的窗棂,还有槐花伸手可摸,香味还会在房内流播,心里便窃喜不已。
年岁渐长,不觉有了惜物之心,经常会对着正在美好的事物报以会心的微笑,比如温暖的阳光,绚丽的彩虹,心动的名字,用英文朗读的叶芝的诗和莎士比亚戏剧。所以,每天上下楼梯,也自然会对着窗前的树枝微笑,我是真心地喜欢它们啊。
夏天的某些时候,我一连几天从楼下经过,发现地上有七零八落的树叶,心里有些埋怨环卫工近日的懒散。有一天回来得较晚,走到三楼,碰到一位老妇人,正在奋力拉扯伸到窗边的枝条,一只手麻利地摘花,身边的小竹篮里已塞满了白色的花,脚边还掉着一些被折断的细枝。那一瞬间,我陡然生出一种怒意。面对零落的花枝,我仿佛听到了它们被折断时的呻吟和叫喊。哎呀,这可是我每天对着微笑的小轩窗啊,居然就这样粗暴地被破坏了。
我终于忍不住了,对着她的背影吼道:你咋这么残忍,把这好端端的树枝折掉!可能是我的声音太冲了,唬得那个背影僵在那里。她转过身,面色涨红,小声辩解道:我就学他们捋些花儿,枝条是他们折断的,不关我的事。然后埋着头,转身逃走了。
望着地上的残花败枝,我忽地自责起来。这些年,或是忙于眼下的生计,或是沉迷于执念构建的虚无,似对周遭的一切失去了敏感,迷茫混沌中不知错失了多少美好。就眼前的槐花而言,我不就差点错过了它一季的深情吗,还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平白无故的伤害。我难过地走到楼下,我要对着这株日夜守护我的树,致以最深切的歉意。我相信万物皆有灵性,哪怕草木,所以,我要祈求它的宽恕。
待我抬头望去,眼前却是一树的繁华与明媚—旷达高远的枝头,白色的花朵洁净如玉,似成串含笑的风铃,又似一帘幽梦。柔软的微风拂过,花枝颤动,甜香缠绵,竟把我裹挟在漫天的香雪里,我知道,这是它以无限美好、大度包容、不计得失的姿态回应我与它难以尽言的缘分。
很早就听说过槐花。我什么都不太懂的年纪里,邻家姐姐偷偷爱上了素未谋面的男子,她说,隔着听筒,就嗅到了对方声音里幽幽的槐花香气。男子是一位缄默的学者,修养极好,任何违背秩序的言行,在他面前都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他像海岸上岿然不动的礁石,伟岸而坚定,或许只有尝试过无数次想要拥抱它的浪花,才对他理性背后的无情和冰凉有切肤之痛。
但姐姐还是义无反顾地抛下了小城安逸的生活,循着那缕渺然的香魂,只身去了男子所在的城市。如姐姐所愿,终于能和刻骨铭心的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呼吸,经历着同样的天气了。可他们终究没有见过面。或许世上最浪漫的事,就是没有后来的事。
那时特别为姐姐不值,也害怕成为姐姐那样的人。可等到我们不再年轻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个不常联系的人的消息或者照片,当你隔着手机屏幕也会颤抖,然后长久地陷入某种情绪里不能自拔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姐姐去的那个地方,是一座以槐盛名的古老都市。在槐花盛开的季节,街头巷尾,朝暮之间,全是槐花的香气。我们终究是怯懦的,在世俗面前溃不成军,唯姐姐是勇敢的,或许也是幸运的,她遇到了她命运的终结者,所以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即使是一棵开花的树,也要长在他必经的路旁,自顾自地欢喜着。
仓促的玉兰
玉兰是春天的蛊,而在晚春开放的花往往有些孤注一掷,收不住自己。小城滨河路一带是白玉兰,公园里是紫玉兰,小区里是广玉兰。丽日下,白玉兰仿佛一道光,把天空刺得格外蓝,像镶在心里的一面镜子,明净,博大,透彻。紫玉兰颜色瑰丽,但却透着一丝莫名的惆怅,像是一个待嫁的新娘,忐忑着,既害怕生活的苦,又期望着诸多的美好。广玉兰的叶片略显肥厚,碗状的花朵歇在树上,乍一看,以为卧着几只乖巧的白鸽。
这些玉兰,都是有色无香的,令人想起“天然去雕饰”的诗句,也多亏了不香啊,那么大的块头,要香起来,不就一盆一盆、一碗一碗地倾泻吗?若是重重地倒过来,或是狠狠掷过去,不把树下的人撞得趔趄才怪!对于花朵,我像一个埋伏在小城里的“盗美贼”,所遇见的美的花花草草都逃不脱我的“魔爪”。某日傍晚,我在滨河路散步,路旁洁白、丰腴的玉兰花在眼前依次招摇,诱惑着对美毫无定力的我,遂使我竟对花中的庞然大物也起了“歹心”。可惜每一朵花都高挂南枝,我也算身高臂长之人,但无论是使劲踮高了脚尖,还是铆足了劲儿跳起来,就是无法把它们揽入怀中。
天快黑了,我瞅着四下无人,一改平日的矜持,脱掉高跟鞋,躬身攀上矮树,终于够到了花枝。心里一阵窃喜,没想到用力过猛,竟然失手将整段枝条都掰了下来。正在此时,路边突然靠过来一辆轿车,我连人带花,暴露在了耀眼的汽车灯光里。那一刻,我进退两难,僵在那里,咬着嘴唇,尴尬地笑着,准备迎接一场劈头盖脸的训斥或者讥讽(因为我就是如此对待糟蹋花木的人)。
没想到那人狡黠一笑,锁上车门,点了支烟走开了。我在落荒而逃的途中,倒是想起了一句话:美丽的女人即使做了再坏的事,都容易被人原谅。现在,这句话是否可以改成:人们总会轻易饶恕一个做了美丽坏事的女人。
只是,万物都有自己的宿命,再好看的花在迟暮的时候,甚至颓败得令人胆战心惊,其中最不堪的,大致就是玉兰了。梨花或桃花落地,犹有泪痕满地的娇弱,令人怜爱惋惜。可凋落的玉蘭呢,又肥又腻的身子像一块脏兮兮的旧抹布,或者一团皱巴巴的餐巾纸。
玉兰也永远成不了养在花瓶里精致的插花,一离树很快就垮了,先是精神,接着是肉身。也不是整个儿的枯萎,而是一片一片地丧,一瓣一瓣地沦,像是心被凌迟着的人,被精妙的刀法割得痛不欲生,剩下的最后一口气,也只是用来承受不断袭来的、无以复加的疼痛。目睹了它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从此再也不敢攀折它的花枝了。
如此高傲的花朵,当真只适合远远地端详,被人仰望,或者被莫名地惦记。它清高,骄傲,其实也脆弱,还有些呆板。它们的花期很短,好像只有几天。长风一到,就迫不及待卸下浑身的沉重,纵身扑向大地,那种决绝当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匆促与悲凉。而在我看来,凋零的玉兰花是不屑任何哀怜的,既然美得惊心动魄,也要走得干净利落。
有时候我无端地想,这玉兰若是开在冬天的雪中,大致是最美艳与高冷的了,肯定还有一些居高向上的雄心与梦想。后来无意中读到清代诗人查慎行的《雪中玉兰花盛开》一诗,才忽然明白,在雪中盛开的玉兰,这世上也是有的。查慎行的诗说,“阆苑移根巧耐寒,此花端合雪中看。羽衣仙女纷纷下,齐戴华阳玉道冠。”
朝颜未央
它有一个端丽的名字,朝颜。大多数人看不见它的内心,随意给它取了个莫名其妙的名字—牵牛花,或是轻俗地叫它喇叭花。踏晨曦而来,伴午阳而凋,她风致嫣然,却又甘于清寂落寞。或许是因为极度的自恋,所以极度自尊。即使萎靡,姿态也是刚烈的,收放自如的。她将衰微的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无声谢幕,杳然而逝,不留下半点不堪,仿佛不经意来了世间一趟。
其实,很多时候,人并不比花高明多少,只不过,花不说出来罢了。比如朝颜,就把美好寄寓在人类那里。人们对于名字中的“颜”,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偏爱,仿佛其中有说不清的曼妙情致,抑或其他什么隐喻。
巧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城中有两位绝色佳人,名字中都带着“颜”,原以为她们会永远留在这里,却没想到,都在芳华绝代的年纪离开了小城。是啊,这样美丽的女子,又岂是这偏僻小城能藏得住的呢?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城里依旧流传着关于她们的种种传说和猜想,人们怀念她们,甚至不容置疑地说,她们的美,在青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小城的人们或许忽略了,美人都要迟暮,越是美的,越是惊心。只有那些看不到迟暮的美,才意外地活成人们心口的朱砂痣,或是窗前的白月光。
我的老家,有一位婆婆,姓氏从夫,名叫朝颜。新婚不久,她的丈夫参军打仗去了,二十年间杳无音讯。在人人自危的乱世里,娘家劝她改嫁,婆家嫌她多余,有人在谣传其夫的死讯。她却独守空房,发誓要一生等他。面对那些心生歹意的人的威逼利诱,和接踵而来的流言蜚语,她都安之若素,不闻不管。上天不负有心人,二十年后,丈夫载誉而归,以隆重的礼仪接走了她。丈夫流泪,问她是如何做到这般坚强的?她淡然,我心中有笃定的人,任何人都侮辱不到我!
或许是为了对应朝颜,日本人把黄昏时开的葫芦花称为“夕颜”。日本文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喜借花喻人。在名著《源氏物语》中,朝颜和夕颜,是性格和命运截然相反的两个女子。朝颜的性格坚韧,在黑暗中隐忍顽强,终于迎来了清晨的曙光。而夕颜,性格柔弱,逆来顺受,最后慢慢地消殒在黑暗之中。
诗人赞美朝颜说:“早上是种种颜色悄然显露的时刻,其中朝颜,伏地二期,在露水的压迫下,被太阳找见。”我至今记得,乔庄中学的路口有一拢翠竹,总是有一些皎洁的朝颜花朵,亭亭玉立于枝上,有的沉静,有的活泼,疏朗而细碎,一副清醒自知、不忧不惧的样子。却是每年都开,一律的素白,不掺一点杂念,像是应了某种承诺和期待。
之前我住在老城旧居,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经过那里,远远地看见那些细碎的白,我就远远地对它们微笑,那是我每天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微笑。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农村,随处可见野生的朝颜。瓦窑背老屋旁边用来堆肥的空地里长着一大片,如青瓷小酒盅般大的花,一色儿的素净,花蕊处藏着淡淡的一抹丽色,或紫或粉,淡雅清新,如小家碧玉般乖巧,可爱。一到夏天,就开得极其痴缠,一茬接着一茬。一朵花谢了,立刻在凋谢的地方结出一囊一囊黑色的籽,似在偿还阳光雨露的恩情,誓要为这一世的缘分,留下生生世世的纪念。只是越到深秋,花朵越小,花蕊越淡,可是籽实依旧是饱满的。
村里的老中医说,朝颜籽可入药治病,也是一味偏方,专治小儿夜啼。每年放暑假,我就跟村子里的小伙伴背个布袋,漫山遍野地找寻朝颜籽,开学后拿到乡卫生院中药房,卖个几毛钱揣在贴身衣袋里,随时翻将出来捋一捋,心里美滋滋的。
后来听说朝颜有众多的品相,之前不知道,忽有一日,在左邻右舍的花园里看到了艳丽、硕大的花朵,有粉红的,花朵攀在多刺的椒树上,真成了全副武装的大喇叭,应了人们眼里轻俗的景。也有玫红的,似一张画了重妆的大脸,风尘味极浓。居然有这样的一朵花穿过了栏杆,爬进了我的小花园,瞧见那步步紧逼、轻薄的模样,恶心得我赶紧用竹竿挑了出去。
我想,若是朝颜可以说话,若她有自我定位的权利,她一定不会认为这是她的同类,就是名字相同,对她也是一种诋毁。在我的潜意识里,总以为蓝色才是朝颜的灵魂底色,是无法取代的极品色。就像心目中倾城的女子,一定是穿蓝衣,透着神秘和冷艳,眉目间隐隐有淡淡忧伤。人们说,蓝和爱情是相通的,却又是孤寂的,无法触碰的。
可朝颜的蓝又是怎样一种蓝呢?是凡·高画笔下的星空蓝吗?迷幻,灵动,纯粹。还是海洋的蓝?博大,深邃,自由。或是蓝调音乐的蓝,婆婆纳的蓝,蓝宝石的蓝?后来无意中读到了日本著名俳句诗人与谢芜村书写蓝色朝颜的名句:“朝颜花啊,一朵深渊色。”心口瞬间袭过一阵凛冽的疼痛,熟悉又陌生。
我想,也许只有曾经一头栽进命运深渊的人,才更能理解深渊的颜色。像是茫茫大海上一艘失魂落魄的船,没有灯塔的召唤,只能在漫无目的漂泊和拼命的自救中,寻找生命出口和人生方向。但是,“我逃向哪里,你充满了世界”,这个世界的颜色,就是深渊色。
我一直未曾见过这深渊色的朝颜。直到去年冬天,在野地里偶然拾得了一些朝颜籽,悉数洒在了屋顶小花园里,任憑春阳夏雨,我由着它的野性,自顾自生。一日清晨,像往常一样,从鸟雀啼啭中醒来,我拉开窗帘,猛地发现小花园里蓝盈盈的一片。我惊了半晌,一时恍惚若梦。
深渊色,还有一个名字,天堂蓝……记得只告诉过一个人,一个眼前的人,一个如彩虹般绚丽的人,一个假想中的人,我最喜爱的颜色,是蓝色。
但是,唯有朝颜,以纯朴的草木之心,回应了我的表白。
梧桐树下
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愫。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是看到法国梧桐树,我都会无一例外地想起地震前的青川旧城,想起昔日满城的梧桐树,以及梧桐树下的那些人和事。
玛丽·格丽娜说过一句话:“那是可以回忆的时代,无数纯真藏在繁茂的枝叶里。”
曾经,整个老城到处是擎着巨大华盖的法桐树。尤其是老城的几条街道,任由夹道而生的法桐散云织锦。人在浓荫如盖、古朴肃穆的街道上穿行,总以为陷入了某种虚无的境界,或者误入了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森林隧道。
初中一年级时,我独自乘坐过路班车从乡下来到了小城,怯怯的心情可想而知。下车后,我紧张又忐忑地穿行在绿色隧道里,一路问到新华书店,买了英语学习资料;又问路到了国营百货商店,在那里买了双白帆布球鞋。全世界最想要的东西都被我紧紧地攥在手里了,我的眼里闪着兴奋的火苗,恨不得立刻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燃烧。我怕迷路走失,所以不敢多逛。中午刚过,就原路返回到了马家院巷子口阴凉的梧桐树下,忍住汹涌而来的饥饿感,快乐而满足地等待从隧道尽头驶来的、能最早返回乡下的客车。
多年以后,我在宫崎骏的动画片里找到了那时的童话世界,梧桐掩映的小城,汽车驶进了幽深的森林隧道,坐在路边小站上安静等车的女生,像极了那时的我。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进城,当时觉得可怜又可笑,现在却只觉得可爱。人生当中总有些许瞬间,某些细节,当时不以为然,多年之后回望,才发现其实暗含了诸多的滋味,甚至,带着某种宿命和预言的味道,比如,我和波的相识。
1998年夏天,我在乔庄镇小学参加中等师范招生面试,考场正好设在浓密的法桐树荫下。那天,我认识了一个扎高马尾,将白衬衫扎进黑长裤的瘦削高挑的女孩。她叫波,长得并不漂亮,但身上却有一种奇怪的能量,让我觉得她与众不同。后来,我知道了那是一种叫做气质或者气场的奇妙东西,拥有它的人,即使身处人海的晦暗之处,也可以随时闪耀出灼灼的光芒。和来自乡下戴帽中学,从没听说过素描,不会唱一首完整的歌,不会跳一支舞,更不懂得什么是即兴演讲的我不同,波在条件稍好的镇属中学读书,是复读生,有实战经验,还有一定的艺术基础。在等候考试的那几天,我们每天都相约在梧桐树下,由她倾尽所能,毫无保留地帮助一无所知的我“临阵磨枪”。出人意料的是,中考后,我如愿迈进了师范的校门,她却再度失利,无奈之下,只身去了广东打工。起初,我们俩还有书信往来,后来就断了联系。我看似顺利,实则过得异常艰辛。世上的很多事情,身在其外,心里多是猜测和向往;身在其中,则会觉得,人生的每一块场域,都有着不同的酸楚和磨难。
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次看到梧桐树,我都一定会想到她。当时,她年纪那么小,心却那么大,那么无私、真诚地帮助我,全然无视我们同处于没有硝烟的战场,甚至面前的我极有可能成为她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我至今都想不起我是怎么就抓住了波这株救命稻草的。但我一定是到了十万火急的紧要关头,我一定是被迫向很多人发出了求助的信号,而她是唯一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我的人;或者她在人群中闪闪发光,而我天生就是一个逐光者,我主动向她亲近和靠拢。她或许是因为性格中的羞涩客气和骨子里的善良厚道,不忍心拒绝我的坦率真诚,从而向我伸出了宝贵的援手。更有可能,是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刻,对着那些苍老的梧桐树默默祈祷,祈求它们能保佑我顺利过关,它们立刻有了回应,于是,就派她来帮助我渡过难关。
她是第一个在我生命中猛地出现,对我百般地好,却又突然消失的人。这样的人,在我此后的人生中,再次出现过。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极其强烈的预感,甚至初见时即有别离的隐痛。他们像夏日暴雨后的一道彩虹,绚丽,迷人,但总会很快消失在湛蓝无际的天空。
我一生都记得他们,祝福他们!
2008年“5·12”震后,青川小城进行了全面重建,在县城里长了几十年的梧桐树大多都被砍掉了。只有青川中学旧址旁,还有少许几株幸运地保留了下来,现在已经大到要两三人才能合抱得过来了。再后来,那里建了一座“木牍之光”公园。每逢天气晴朗的午后,梧桐树下常常围坐着一圈留守老人,他们大多随子女从农村迁居到小城,因为经历过相同的时代,又说着相似的方言,所以很快熟络起来,所以,树下总是热闹的。
梧桐树下的停车位上,不知何时放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一位患了白癜风的耄耋老人时常坐在那里。他戴着黑框眼镜,拄着拐杖,挺直腰板,端坐在婆娑的树影里,除了眼球,身体其他部位几乎纹丝不动。有一天我骇然发现,他患病的肌肤像极了身后斑驳的梧桐树皮,像是跟树合为一体了。
平日里,我喜欢把车泊在能遮阳挡雨的梧桐树下。一天晚上,我略微喝了一些酒,就托同事帮忙停车。第二天清晨去取车时,才发现一边的车窗打开着。我大惊失色,唯恐丢失了车厢里印着一对蓝色鹭鸟的白瓷茶杯。所幸知心的梧桐挡住了昨夜无意的“不设防”,我的茶杯还能安然无恙。我把冰冷的杯子紧紧地攥在手心,贴在我狂跳的心口,我用滚烫的脸颊温暖它,唤醒它,并且告诉它,我们要感恩眼前的这些树,是它们的成全,才让我们没有最终失去彼此之间最珍贵的东西。
法国梧桐在植物界又叫悬铃木,这是一个浪漫得近乎销魂的名字。如果把梧桐比作一个人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内心澄澈,庄重而又纯粹的人。但这样的人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像现在的青川小城里,已经很难看见如此俊美的“悬铃木”了,这不得不令人唏嘘遗憾。所幸,法桐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永久不灭的痕迹。就像上面这些文字,是怀想,是感喟,是一种树木之于一个人的恩赐与共携。
踏雪寻梅
昨夜有些寂静,清晨开窗,哦,下雪了,清冷的风吹来,带着冬天深处的某些消息。不一会儿,发小打来电话:“老同学,我要送你一盆花!”我吓了一跳,连忙一口回绝:“谢了,不要!”“别着急拒绝啊,我送你的,可是梅花!”他赶紧解释道,“是腊梅,腊梅你也不喜欢吗?盆栽好的,不用劳神养。”我愣了一下,可还是狠心拒绝了他的美意。
这个发小,其实人挺好的。只是,在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他给其他的男女同学都送了一张明信片,唯独没有我的。我很难过,气冲冲地跑去质问。他说,他考虑了好久送不送给我,最后还是没有胆量送,因为我是班里最难接近的女生,生怕他的热情反倒会招来我的一顿臭骂。看见我哭了,他就重新写了一张明信片送给我,却被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负气撕掉了。
从小到大,我从来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更介意异性送花之类的。在潜意识里,花是神圣的,任何一种花都寄托着一份特殊的情感,我怕自己担待不起,无法偿还。当然,如若世间真有我假想中的那个人,无论是他随手为我摘一朵路旁的野花,还是为我建造一座百花园,我都要。如若不是那个人,统统都不要。对于腊梅,我肯定是喜欢的,现在,他要送我,我知道他的好意,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收。个中情由,想必每个人都很明白。
有花开的季节里,家里那些大的、小的、瓷的、陶的、玻璃的花瓶,从来没有闲置的时候,总有绿枝垂抚,盆花相映。这些花草,都是我从郊外的野地里一朵一朵、一枝一枝、一束一束采摘回来的,全是我喜爱的颜色和长相:白的清心,黄的养眼,红的滋润。每天,我也会穿戴得整整齐齐,精神清爽地与它们相间,时常在一转身一回头的刹那,忍不住对它们莞尔一笑。
生活繁琐,但再平凡的日子,倘若有花相伴,生命也就突然地增添了色彩,即使有些不开心,也觉得前面充满指望。可冬天万物萧瑟,野外再难觅见花朵的踪影。无奈,只好违心地养着呆板的富贵竹,以敷衍自己。不过,多是草草地插在瓶里,懒得去浇水,似乎也不想多看一眼。春天一到,就毫不吝惜地拔了全部扔掉,像是甩掉一个厌恶已久的包袱。
依然记得第一次看见腊梅的情形,那是在山谷原舍民宿里,室中案几上的影青瓷瓶里,冷冷地斜插了几枝,忽就满室生香了,让人顿觉神清气爽,仿佛另一种天籁。腊梅啊,真像身边某些貌不惊人的女子,却有着独特迷人的气质,是的,正是那一缕香魂,让人一闻不忘。自此,我就被腊梅花勾住了魂魄。那一次,似乎是为了接待几位尊贵的客人,才有这样的奇遇,但在丰盛的佳肴之中,我的嗅觉里,都是腊梅的香味,满脑子也都是腊梅。
这才发现,我是多么地喜欢腊梅啊! 可又觉得,不能喜欢得太多。就像生命中突然出现的某个人,即使我们骨子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会同时目不转睛、暖暖地看着对方,却永远无法靠近。这种感觉,是疼痛的,就像一根刺,在心的某处隐藏。我素来是一个清醒而自知的小女人,我明白,像腊梅这样高贵的芬芳,亦如一些不可多得的情谊,是我不能奢望的。所以,虽然拒绝了发小,但我还是不自觉地兀自笑了起来。
几天后,小城又下了一场雪,虽然不大,但远近皆白。上午,和几个人坐在车里,气氛有些紧张,同行的一位男士似乎对我颇有成见,一路言语之间,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我们曾是故交,近些年,因为事业屡遭挫折,他变得偏激和乖戾。若不是有工作要做,更不想辜负这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我真想痛骂他一顿,早早结束无聊的对话,扬长而去。
好不容易到了城北的村子里,做完了手头的事情,又不想去和另一群人凑热闹,就一个人到雪地里转悠。冬天的旷野冷峻高远,天空一片幽藍,山际处飘游着几朵云。山谷里没有风,没有夏日的林鸟齐鸣,我在这自然的寂静里,以散适的姿态行走,而且越走越远。在没有人的山野之间,一个人,好像天地之间的一只孤影。远远地,瞥见了一树清淡的鹅黄,在白茫茫的天地间亭亭地站着,一缕清冽幽渺的芬芳,袅袅地钻进了鼻孔。
我猜那就是腊梅。走近一看,果真是她!那一树灿然,一树繁华啊!细碎的花朵,开得料峭清峻,开得傲骨铮铮,小心翼翼。小小的花瓣,黄得轻柔,细腻,干净,富有质感。清香附在那清瘦的枝干上,透着隐隐的沧桑与怅然,似要写尽一生的零落与孤高,像那终生不遇知音,却又不肯将就的人,把自知、自制、清冷、压抑、冷艳写到了极致。忽然间,我明白了这种花为何会选在冰天雪地里寂静绽放,原来这种品格的花,春天是揽不下的。天底下极致的色与香,只能与清寒相伴。
正在激动,忽地吹来一阵冷风,花瓣簌簌地落了几片。我心疼不已,却又无能为力。想起了张枣的那句诗:“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诗人笔下的梅花,或许还有一个名字:悔花。不过年岁渐长,从前以为最后悔的事,现在看来竟是最无悔的事,幸得当时攀缘强求的勇敢和莽撞,才使得封闭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有了些许光亮和惊喜。光阴一场,在小城,我还是愿意一直等待想象中的那个人,在腊梅飘香的冬天,骑马款款归来。
我小心折下几枝腊梅,一路拢在怀里,像是怀揣稀世珍宝。返程的车厢里弥漫着清雅的芬芳,那个怼我的男士突然安静了,看我的眼神里亦有了几分恭敬,几分羡慕,许是上帝方才给他打了招呼,让他不要为难一个怀抱鲜花的女人。此时,有微信提示。一段香彻心扉的文字也跟着跳了出来:“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业务也多生变故……为此很长时间也跟您疏于问候,实在是特别萦怀且过意不去的事。”看到这句话,我的眼泪无声地落在了花瓣上。我知道了,我不能更贪心,我已经拥有了花朵,不能再奢望神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