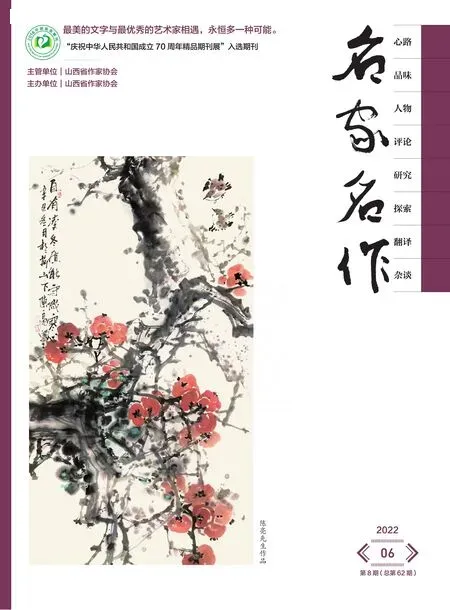李白《峨眉山月歌》辨释
欧 夏
唐开元十二年,即公元 724 年,24 岁的李白经水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途中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李白在短短二十八字中嵌入五个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与整诗无缝衔接,有机融合,了无痕迹,充分体现了李白的巧思和才华。只是诗中五个地名的具体所指或意义并不明确,宋以后一直争议不断。
在笔者看来,诸多争议中,最重要、最需要澄清的是围绕“三峡”和“渝州”的争议。“三峡”关乎诗人视野的大小、出行的目的及诗歌主题;“渝州”则是此诗巧思和诗意之所在,是此诗的“诗眼”。至于受关注较多的“清溪”和“平羌江”,笔者以为对所涉地方的旅游业影响较大,对整诗的理解反而影响不大。是故,本文不求面面俱到,只就“三峡”和“渝州”之用意略陈管见,乞教于方家。
一、关于“三峡”
由于在今日眉山市青神县与乐山市市中区接壤段的岷江之上,的确存在一个被称作“平羌三峡”的地方,还由于“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给人以“三峡”在“清溪”与“渝州”之间的“第一感觉”,近年来,不少人指出《峨眉山月歌》中的“三峡”并非指大家熟悉的“巴东三峡”,而是指岷江之上的“平羌三峡”。此说颇合常人解诗的习惯性思路,逐渐登堂入室,为学界主流接受并采纳。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注释《峨眉山月歌》时,先列“巴东三峡”说,再列“平羌三峡”说,并在“平羌三峡”说之后直言“按全诗地形,其说较妥”。
但在笔者看来,李白诗中的“三峡”就是指“巴东三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首先,这首诗是李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途中所作,如果“三峡”是指“平羌三峡”的话,则其最远的目的地便是“渝州”,严格讲还是在川内游历,并未“去国”,显然与“出川”的诗题不符。另外,“平羌三峡”与出发地“清溪”太近,刚一出发便“思君(峨眉山月)不见”,个中情感不是“依依不舍”,倒成了“扬长而去”了,这也不是离乡游子的正常心理。“三峡”若指“巴东三峡”的话,则“向三峡”三字便是“点题”,点明此行的目的——“出川”,因为“巴东三峡”是出川的门户,“思君不见”也有延展的空间,“依依不舍”之情才能得到充分表达。
但这并不是“三峡”指“巴东三峡”的最有力的证据。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李白生活的年代,其创作《峨眉山月歌》的时候,岷江之上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叫作“三峡”的地方。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一《剑南道·嘉州·平羌县》载:“熊耳峡,在县东北三十一里。”而当时的平羌县“南至州(即嘉州,今乐山)一十八里”。考察个中方位关系及古今地名变迁不难发现,唐代的“熊耳峡”就是今日所谓“小三峡”。换句话说,虽然当时峡谷本身是存在的,但人们却称其为“熊耳峡”,而不是什么“三峡”。
北宋欧阳悉《舆地广记》卷二十九《成都府·嘉州·龙游·县》载:“平羌镇,本汉南安县地,后周置平羌县及平羌郡……有熊耳峡,诸葛忠武凿山开道,盖今湖禳峡云。”南宋范成大《吴船录》上卷载:“放船过青衣,入湖瀼峡,由平羌旧县至嘉州,日未晡。”可见,两宋时期,人们改称“熊耳峡”为“湖瀼峡”,仍旧未以“三峡”名之。
唐宋有不少文人与嘉州有关。李白、杜甫、岑参、薛能、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都曾在嘉州游历、任职、学习或生活过。但遍查他们的诗文,找不出嘉州存在另一个“三峡”的丝毫证据。尤其是苏轼,生长于与嘉州山水相连的眉州,还曾在离“平羌三峡”不远的中岩一带学习多年。二十岁,苏轼追随乡贤李白的脚步,顺岷江舟行出川,在嘉州小作盘桓,并题有《初发嘉州》诗。后因父母去世,苏轼两次返乡。这条进出蜀地的千里水路,李白一生只走过一次,而苏轼却至少走过五次。其间所写诗文中曾提及峨眉山、中岩、玻璃江(岷江)、凌云山、龙泓口等地,而频繁路过、游过的所谓“平羌三峡”,苏轼竟只字未提。公元1090 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得知好友张伯温即将赴任嘉州太守,特赋诗一首《送张嘉州》。其中有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难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可见,苏轼对李白的《峨眉山月歌》颇为关注和欣赏,并指出在嘉州登楼望月可以更好地理解太白诗意。如果苏轼认为嘉州也有“三峡”且就是太白诗中“三峡”的话,他不可能不在诗中提及,好让大家对太白诗更好地“解道”。结论只能是,在苏轼看来,嘉州并不存在一个叫“三峡”的地方,李白诗中的三峡就是“巴东三峡”。
李白《登锦城散花楼》中有“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句,有人认为其中“三峡”即指“平羌三峡”,然通览全诗,此说根本不通。《登锦城散花楼》作于公元722年李白重游成都之时,当时的李白已有“辞亲远游”之志,登楼赋诗即为表明心迹。“春江绕双流”暗含对家乡的眷恋,而“暮雨向三峡”则寓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三峡”只有指长江大“三峡”,才与诗中“极目散我忧”“如上九天游”的意境相符,才与诗人登高望远、渴望出川的心志契合。若指去成都不远、无人知晓的岷江小“三峡”,则境界局促,诗意全无。岑参《初至犍为作》中的“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也应作如是观。“三峡”与“百蛮”相对,显然只有天下公认的长江大“三峡”才能对得上、对得起,拿“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岷江小“三峡”与“百蛮”相对,分量极不对等,也无法引人共鸣,乃行文之大忌。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杜甫《寄岑嘉州》中的“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向来被视为“平羌三峡”在唐代即已得到公认并被写入诗歌的铁证,但这其实不过缘于对杜诗的误解而已。通读全诗不难发现,虽说诗中“外江”确指嘉州境内的“岷江”,但“外江三峡”却并非指岷江之上的“小三峡”。公元 766 年春,身在云安的杜甫收到老朋友岑参从嘉州寄来的信件和诗稿。近十年未收到岑参音讯的杜甫,手捧信件和诗稿,感慨良多,提笔写下这首《寄岑嘉州》。为彰显喜出望外之情,杜甫多处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如接下来的两句“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说的是读岑参的诗稿,感觉岑参的诗像谢朓的诗一样值得反复吟诵,而诗人自己却像冯唐一样年老,只能听听他人恭维。同理,“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的意思就是,嘉州境内的岷江与云安附近的三峡一水相连,但能对着酒读老友的诗作却真是不易。此处“三峡”明显是指云安附近的长江大“三峡”,若指岷江小“三峡”,则诗不可解。
由上可知,至少唐宋之际,专业典籍和文人诗文中,找不出今日岷江之上的“平羌三峡”在当时被称作“三峡”的丝毫确证。这说明,对于岷江之上的峡谷,当时的人根本就没有形成“三峡”的概念和称谓。在此情况下,李白是断不可能以岷江之上的“三峡”入诗的。
退一步讲,即便当时的人对岷江之上的峡谷已形成“三峡”的概念和称谓,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三峡”也不可能指这个“平羌三峡”,因为那明显与李白诗意不符。
此诗是李白出川途中所作,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既如此,由诗中“夜发清溪向三峡”句可知,“清溪”必位于“三峡”的上游。而实际情况是,虽说关于“清溪”的争议非常多,但无一例外,皆位于“平羌三峡”的下游。就笔者所知,关于“清溪”大概有以下七种说法:乐山市市中区板桥溪说、犍为县孝姑镇太平村说、犍为县清溪镇说、汉源县清溪镇说、洪雅县止戈镇清溪渡说、内江市石子镇说以及泸州市纳溪区清溪河口说。其中,板桥溪位于“平羌三峡”南出口处;犍为县的太平村和清溪镇则位于“平羌三峡”下游百公里开外。汉源县和洪雅县的那两个“清溪”则均位于今天的青衣江上,至乐山才能汇入岷江,以水路算也当在“平羌三峡”的下游。至于内江和泸州的“清溪”,都出了岷江,靠近今天的重庆,位于“平羌三峡”下游更是显而易见。不管“清溪”是指以上七个中的哪一个,如果李白诗中的“三峡”是指“平羌三峡”的话,那“夜发清溪向三峡”便成了逆流北上,由“出川”变成“回家”了。
二、关于“渝州”
诗的最后一句为什么是“思君不见下渝州”?“清溪”与“三峡”之间还有不少地方,“三峡”以东更有名城无数,李白为什么要在第三句确定起点 (“清溪”) 和终点 (“三峡”) 之后,以两者之间的“渝州”收尾?
笔者认为, 这体现了李白的慧眼巧思。 不夸张地说,“渝州” 是本诗的“诗眼”,是其之所以“成诗”, 确切地说,之所以“成为李白诗”的关键所在。唐代的渝州属山南西道,治所在今天重庆市西南部九龙坡区一带。从距离远近上看,如果设定 “清溪”位于峨眉山附近,“三峡”即指 “巴东三峡”的话,“渝州”正好位于两者的正中间。 但从地形学上看,峨眉山是邛崃山的余脉,位于我国地势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横断山脉的东缘。“渝州”与“三峡”间虽有一定距离,但同属广义的巫山地区,而巫山是我国地势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重要分界线,“渝州”正位于这一分界线的西端。从峨眉山下的“清溪”出发,顺岷江南下,入长江折而向东,至“渝州”,恰好经过四川盆地的西南部和整个南部边缘,也恰好贯穿整个第二阶梯腹地。
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等都是现代地理学术语,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自然不得而知,但是,不知道术语不等于没有术语背后的概念。通过以下对《峨眉山月歌》等诗的解读就会发现,李白对峨眉山、四川盆地、渝州、巫山、三峡及江汉平原的地形地貌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清楚的,甚至对中国地势的阶梯状特征已有相当明确的感知和认识。
公元724 年的这次旅行,是24 岁的李白平生第一次出川远游,他当时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潜心学习和准备,终于可以去往外面的世界,实现自身的价值,内心自是按捺不住的憧憬、激动和兴奋。另一方面,即将告别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故乡和亲人,难免会心生眷恋和惆怅。
诗人初出蜀,乃人生一件大事。在老家江油,家人、亲戚、朋友肯定是千叮咛万嘱咐,依依惜别。在成都,想必也有不少朋友为其设宴饯行。甚至在夜发地清溪,可能也有朋友举杯相送。选取其中的感人场面和美好意象打磨成诗,是传统送别诗的常规套路。而诗人却将所有这些场面和意象通通忽略,把内涵极其丰富的“故乡”概念浓缩成一个至简的意象——“峨眉山月”。“峨眉山月”美丽、皎洁、温馨、祥和,囊括诗人对故乡青山绿水、一草一木、家人朋友的所有美好想象。而且,诗人敏感地捕捉到“月随人走”的视觉效应,借以抒发诗人与故乡互相依恋、互难割舍的情愫。更让人吃惊的是,诗人的老家是江油,蜀地的核心城市是成都,而诗人却弃此二城,选择距江油七百里开外的峨眉山作为“故乡”的代表性符号和远游的始发地,这充分说明诗人的视野之大,诗歌的地理跨度之长。没有足够的地理学知识,胸中没有一幅精准的千里江山图的话,是断然不敢下笔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张力满满,诗未就便知是大手笔。
“夜发清溪向三峡”,果然,诗人此次出行是要从峨眉山下的“清溪”出发,沿水路跨越整个四川盆地,再穿巫山,直抵“巴东三峡”。简言之,诗人要“出川”。
峨眉山头半轮秋月悬挂,月华皎洁泻入平羌江随波流照,夜深人静时分,诗人纵一叶扁舟,离开清溪,直奔三峡而去。诗的前三句,从意象的选取、情景的描绘,到人物的出场、事件的交代,可谓巧妙、唯美、飘逸、清晰,但在唐代,这还不能叫“诗”,更不能叫“绝句”,尤其是“太白绝句”。在唐代主流眼光看来,只是以优美的字句和韵律来抒情叙事,尚不足以称“诗”。诗贵含蓄,须有言外意、弦外音、味外味。绝句尤甚。太白绝句更是个中代表。太白的绝句名篇无不以含蓄隽永见称。《峨眉山月歌》的前三句,怎么看都像是铺垫,像是跳水比赛中“完美一跳”前的一系列准备动作。
“思君不见下渝州”便是这最后的“完美一跳”。以“峨眉山月”代指故乡,以“月送人”代替“人送人”,已经体现出诗人构思的巧妙,但更巧妙的是,诗人敏锐地察觉,“人送人”的物理时空比较受限,“月送人”的物理时空则可大大延展。人送人,虽有“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一说,但真正做到“送君千里”是不可能的,一般送人出村、出城、上马或上船就结束了,距离、时间都不会太长。但月随人走、月伴舟行的时空跨度可以很大,可以使不现实的“送君千里”变成现实。在李白诗中,送行的时空跨度往往预示着双方的感情深度。“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都是在尽力拉伸送行的时空跨度。但时空跨度可以无限拉伸吗? 并不是。比方说“峨眉山月”送诗人出川,就需要以峨眉山和月亮可以被同时看见为先决条件,只看到其中一个,便不能称之为“峨眉山月”。如前所述,从峨眉山经水路到渝州,舟正好沿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行驶,人在舟中西望峨眉,视线通透,毫无阻隔。“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在到达渝州之前,“峨眉山月”一直陪伴着诗人,“思而可见”。李白晚年曾有“归时还弄峨眉月”句,“峨眉山月”的这次千里相送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自己的“千里弄月”。“千里弄月”通过人与月的长时间、长距离互动,充分表现远游的诗人与故乡之间的缱绻深情。渝州再往东,进入巫山地区西缘,西望峨眉的视线受阻,当真是“思君不见”矣。而且,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不规则球体,李白从峨眉山下出发东行,行至一定距离,西望峨眉的视线必然会被地球本身遮住,李白最后看见峨眉山顶的视线就是地球的切线。峨眉山海拔3099 米,渝州大致位于今重庆市九龙坡区一带,九龙坡区平均海拔325 米。通过计算,在海拔325 米的地方看到一座海拔3099 米的高山的最远距离是 303.64 公里,而利用高德地图,测得峨眉山与重庆市九龙坡区的直线距离恰好是303 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李白在渝州西望峨眉山顶的视线正好是地球的切线;除去其他因素,仅从地球形态上考虑,渝州的的确确是李白一路上可以望见“峨眉山月”的终点,同时也是“思君不见”的起点。“思君不见下渝州”,一句一千多年前的古诗,竟然不仅与现代地理学高度吻合,也与现代几何学完美统一,令人摇头啧叹,无法相信。
《峨眉山月歌》是一首抒发乡愁的诗,无渝州则无乡愁,渝州出则乡愁出,渝州远则乡愁深,渝州之为“诗眼”正在于此。
要透彻、完整地理解《峨眉山月歌》,还需要把她的姊妹篇《渡荆门送别》拿来一并讨论。李白出三峡后继续东行,至荆门,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浮现眼前。诗人平生二十余载,一直生活在多山的巴蜀地区,从未见过如此广阔的天地,内心激动难掩,挥笔写下《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诗人乘舟东行,“山随平野尽”是向西回望,只有在山区与平野的交界地带才会出现“山随平野尽”的画面。“江入大荒流”是向东前瞻,诗人将像大江一样前行,平野虽广袤,但对诗人却显得陌生而遥远,一如诗人的前途,故曰“大荒”。地平自然江阔水静,所以,月映水中,犹如天镜落下,明亮而平静,与诗人故乡峨眉山下的“影入平羌江水流”明显不同。江面宽阔如海,云彩在其上升腾变幻,宛如海市蜃楼,故曰“云生结海楼”。低头往下看,深情的故乡水托举着孤舟,不远万里,默默相送。这首诗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一是“荆门”的选点。荆门位于今宜都市东北长江南岸,对岸即今枝江市。此处在今天被学界公认为江汉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西起点。李白的选点竟与今天地理学的科学界定出奇地一致。可见,李白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地形地貌,乃至地势三阶梯的特征是了然于胸的。自然,对于“渝州”在这幅千里江山图中位置的独特性,她与峨眉山、四川盆地、巫山及以东地区之间的关系,也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下”的是“渝州”?《渡荆门送别》可引以为旁证。二是“故乡水”意象的选取。诗人离乡东游,前来送行者实有二,一为“故乡月”(“峨眉山月”),一为“故乡水”。“故乡月”与“故乡水”虽非一物,但却有一共同特点:与人同行。“故乡月”送诗人至“渝州”,然后被山遮蔽,“思君不见”。而“故乡水”继续伴诗人东行,穿巫山,过三峡,直至“荆门”,“万里送行舟”。李白在“故乡月”和“故乡水”的陪伴下翩翩登上大唐诗坛,这是诗歌史上最浪漫的出场、最惊艳的亮相。
至于那些认为“思君不见”中的“君”为作者友人,《峨眉山月歌》是一首怀人之作的说法,笔者认为是望文生义,埋没、辜负李白对“峨眉山月”意象的巧取妙用。
关于《峨眉山月歌》的题诗处,最流行的说法是,李白题诗于今乐山境内顶高山(原锦江山)颠,后人在太白题诗处建有太白亭,黄庭坚书《峨眉山月歌》于石碑之上,以示纪念。现在看来,这一说法恐难成立,因为像“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样暗合物理、数理和情理的佳句,非亲身经历从峨眉山脚至渝州全部行程者,断然写不出。所以,笔者认为《峨眉山月歌》只能作于渝州以东,大概率就是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