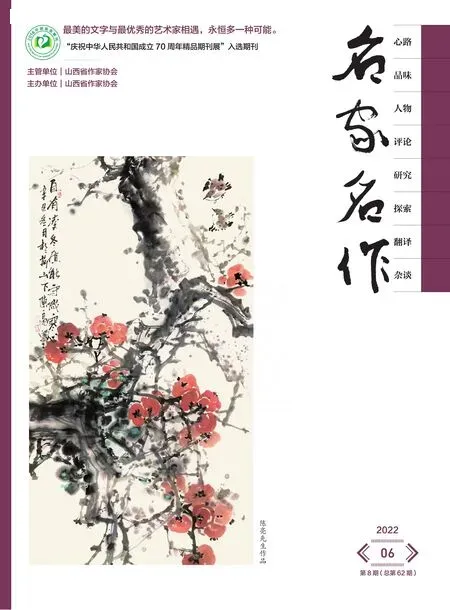知识者处世的两种姿态—《过客》与《春尽江南》之比较分析
陈晓曼
鲁迅是书写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开创者,在他的笔下存活着许多处于历史“中间物”的启蒙知识分子。在散文集《野草》中,《过客》主题上表现出知识分子探索精神荒原的悲剧意识,他与腐朽现实的决然反抗,与顽固民众的精神交锋,一意孤行走向荒原,都体现鲁迅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刻反思、批判。同样在《春尽江南》中,格非以谭端午为代表,展开对当下知识分子生存境遇和价值选择的书写,曾经自命不凡的诗人在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中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人”,尽管如此,他心中仍有文人坚守的乌托邦理想。两部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变革时代中的启蒙先行者,在跨越历史时空的现实背景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如何在怀疑中确立自我的存在价值,以及如何处理现实生存与精神理想之间的矛盾。鲁迅对格非的影响是深远的,格非曾说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就是鲁迅,他欣赏鲁迅对待虚无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创作的谭端午与鲁迅笔下的过客是对知识分子命运和精神不同代际间的共同书写。
一、孤独的精神
创作于1925 年的小诗剧《过客》,据说在鲁迅“脑筋中酝酿了将近十年”,篇幅仅有1500 字左右,却字字珠玑,让世人看见一位孤傲倔强的出走战士。他虽为匆匆过客,却是一位彷徨于精神文化荒原的先锋探索者,鲁迅将他的独立意志投射在过客身上,表现出他思想意识的超越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鲁迅精神里最宝贵的财富,但在这难能可贵的财富背后,却是一望无际的精神悲哀和虚无远方。“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过客可以被理解为鲁迅的精神分支,在过客有记忆时,即是鲁迅现代立人思想矗立之际,鲁迅在发觉历史写满荒唐、民众被虚伪的真理蒙蔽后,试图与迂腐的现行秩序做对抗,可是,不管他以狂人之口告诫真相,还是以阿Q 之貌绘制国民丑相,没有权力支撑的独自清醒都不被现实理睬;过客看似荒诞的流浪行为,是鲁迅思想的一条线索,这一思想线索既是鲁迅企图摧毁背离人性的铁屋子的愤然呐喊,也是在竭力嘶喊“救救孩子”后,只有暗夜奔波走向明天的彷徨。过客与老翁的对话暗含了他与社会、与庸众之间的隔膜,他尝试和老翁在精神上达成共识,却不想被老翁告知前方是坟!老翁劝诫过客还是回转的较好,料不定往前也走不完,这是过客与老翁之间的第一次精神对话断裂。老翁也曾尝试往前走,走到坟时,他畏惧前路的荒芜,归顺于从前熟悉的旧道,这里的老翁和狂人有过一样的使命、一样的命运,过客听后沉思后又说到他执意向前的缘由,他是为了能见到有皮面的笑容,心底的眼泪,因而他有必要向前走,在老翁提醒他可以休息休息时,过客又说道前方有个声音在呼唤,老翁也说自己曾经也听到,只是置之不理,声音便消失了,这里是过客与老翁之间第二次的精神断裂。两种声音相互抵抗的表现是鲁迅笔下众多人物心理的写照,如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走过一段进步思想的道路,最后消极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愤然鄙夷的东西最后都顺从了……老翁对呼唤的声音不予理会再次让过客陷于彷徨,这里过客表现得犹豫又坚定,同时也是鲁迅对于是否继续战斗于精神处的矛盾与反复怀疑。田建民在《〈过客〉的“荒原感”解读》中提道:“老翁表现出渗透着老庄哲学精神的顽固保守的虚无主义人生态度。”诚然,比起麻木无知的庸众,虚无主义的拥护者显然更难被启蒙,这也是鲁迅在老翁形象设置上关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阂的深刻思考。过客漂泊的生命形态和独自行走精神荒原的形象是鲁迅置身于风云暗涌时代的真实照应,在经历呐喊与彷徨之后,反复质疑和自我肯定,是鲁迅独自承受痛苦的精神悲哀。
因而过客作为鲁迅精神的自画像有着独具一格的悲剧性,其悲剧在于灵魂的孤独,在于知识分子不为世人理解的孤独。一个世纪的变迁似乎并没有让知识者找到可循的心灵归路,在格非的小说《春尽江南》中,诗人谭端午的精神裂变史也有着作者格非的影子,在格非以先锋作家脱颖而出时,跨入新世纪的格非却沉静十年之久,其间他对历史迷雾后的悲凉代入《春尽江南》中谭端午的身上,曾经志气方刚的诗人在人文精神的大乱变中沮丧颓废,格非在谭端午身上寄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灵魂的孤独感和20 世纪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显现出相似的悲剧意蕴。
在《春尽江南》中,谭端午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是个桀骜不驯、个性张扬的知识青年。他可以为诗人之死展开放逐自我的离奇游历,也可以与导师断绝关系放弃优渥的就职选择,在感情上果敢贸然地与一夜情追求者闪婚,他曾引以为傲的知识者资本,却因与导师失和在社会中到处碰壁,被迫到老家地方志办公室成为小职员。没有了“诗人”光环,甚至对这个称号有点难以启齿的他,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曾经诗人的光辉给他带来现实的名利、金钱与性,如今也骤然失效,曾经还是学生的李秀蓉对他崇拜至极甚至献身,而今改了名的妻子对他冷眼相待。孩子的教育问题,老人的赡养责任,家庭的未来规划都将他避之门外,家庭地位的失守,社会地位的变化,身边殆尽的真心,让他逐渐与现实产生无法弥合的鸿沟。世人不再去理解他们的孤独,因为他们在名目、地主、驱逐和牢笼中奋斗得不亦乐乎,没有人质疑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与现实达成和解,以为拥有更多建立在牺牲他人精神之上的快乐,是自己精神得以安放的寄存所,错把这样的寄托当作是更高的精神追求,这便是当今社会庸众的精神之相,而知识分子——最先的觉醒者“自觉地承受着那些不自觉地在受苦的群众的痛苦,这就使得他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包含着比他个人的不幸命运远为深广的历史内容”。
二、苦痛的行为
过客的生存状态始终与“走”无法断裂,“过”表示已经走了许多的路,“客”即是不会停留。他的行走与反抗是苦难的、悲壮的、深刻的,在路上他有过迟疑、沉思、颓唐,下意识中却保持着对劝返的惊醒和警觉,接着就是一次次竭力反抗。过客是鲁迅深层思想中反抗绝望的象征体,这种反抗绝望比起为希望战斗更彰显鲁迅思想的深刻和超越。在过客身上有着两次反抗绝望的生命体验,第一次是在过客悲愤诉说不愿回头的痛苦中体现,为了反抗如牢狱一般的世间,为了前方催促的声音,因而来到此处就是反抗的结果;而第二次反抗绝望则是在老翁告知前方是坟后的坚定,这里可以看作是反抗绝望的高潮,比起要摆脱肮脏的名目与驱逐,向着坟前进的反抗是鲁迅清醒意识到自我与庶民对立后的执着,是他挑战世界荒诞性和超越生命苦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用现代文明感化麻木庸众,达到立人思想的根植。有学者认为“鲁迅一生都在坚守,努力追求向前的东西,和乌托邦的实质精神具有一致性”。可见在鲁迅的灵魂深处是一场基于批判现实的乌托邦革命,用来启蒙民众的力量与现实老旧、顽固、软弱的势力相互博弈,过客奔赴坟地的姿态象征鲁迅立人思想在乌托邦里被永恒放逐,面临终究毁灭的远方,过客却没有停止向前,这是一个肩负时代责任的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也是对立人内在要旨的超越。对于前方有无路径的考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是万念俱灰的坟又或是万盏灯火的乌托邦,只有默默地忍受向前,就如他说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在《春尽江南》中,对乌托邦理想信念的追寻是始终贯穿小说的潜在的主题,面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主宰的时代,谭端午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所维系的乌托邦理想被欲望、名利宰割得支离破碎,他表现得像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对生活中的一切仿佛丧失了热情,在工作中混天度日,对待家庭敷衍躲闪,与朋友之间逢场作戏,看起来对一切事物感到无比麻木,实则是在获取精神中的“消极自由”,用形同虚设的自我存在来包装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希望让孩子有更自由的成长空间却对教育事务无法承担……看待妻子的利欲熏心,甚至出轨都只是听之任之,在妻子与好友等成功人士的追逐下,他显得更加失败,即便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城市即将成为没落、躁动不堪的精神荒地,但无法获得自我价值,很难找到出路,只能随着精神湮没而漂泊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时代里,成为零余者。如他自己所说:“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东西……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但正当死亡逼近时,谭端午这个“失败者”的意义却凸显出来,妻子在病魔的挟持下孤独离去时,谭端午以爱与温情回报,曾经在妻子眼里是个发烂的人却在此刻散发着亲人温馨的光芒。格非在上海做专题讲座时说:“我为什么要写《春尽江南》,我们怎么评价这个社会?我首先考虑的是现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些人究竟对这个现实是什么样一种反应?我们有没有必要对现在的生活进行反省?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的话,我希望读者在看《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看到自己的灵魂。”格非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同工业资本文明下的腐化社会搏斗表现得冷静又深刻,在一个以大众为主体的场域中,越来越世俗的文化价值和审美取向并不会因为坚守诗意的知识分子而扭转大方向,金钱名利在当今社会拥有一个庞大有劲的磁场,会吸引更多追溯者在其中旋转,而揣着乌托邦理想的书生难以周旋,对于这样的世界,格非并不想让谭端午回到社会中心,反而是让他退却边缘,在磁场外圈珍藏对世间的人文关怀,看似将他们的价值定位放置一种无根、迷茫的状态,实则却让其拥有更自由广阔的精神空间,在边缘化地位中重塑自我形象,冷静窥视着时代与人的生和死。
过客用身体力行反抗绝望,走向现代立人思想的风暴,谭端午则保持着内敛的怀疑,以自我疏离的方式进行诗意的坚守和自由的反抗。过客作为第一代孤独者,饱受着与庸众对立的重压,与周围的现实背道而驰,谭端午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边缘人”,他颓废的行为、退缩的态度潜藏着时代精神裂变的悲哀,鲁迅和格非写出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共同面临的悲剧。
三、迷乱的时代
从过客到谭端午,无论他们的处世姿态是反抗出走还是坚守停留,现实总会使他们的精神断裂甚至难以续弦,无法找准自我身份定位的难题,让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身份正在消解,仿佛他们才是需要被启蒙的人,这背后的黑手实则是一个迷乱的世道。鲁迅时代的精神悲哀是庸众的不自知,现代文明被封建意志紧紧包裹,那是民众世代的避难所,难以唤醒的愚昧只能让坚守启蒙的知识分子走向荒原。鲁迅的发声便像是重拳出击在软棉花上,民众大抵都感到无关痛痒,因此鲁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孤走图”,告诉世人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哀。而格非感受的时代悲哀是被政治化、经济场排挤的糜烂人文精神,一个剥掉文明外衣的物化时代,正因如此,格非带着对乌托邦理想的怀疑和困惑给予知识分子更多自我救赎的空间,用他们的眼睛观察正在错位和殆尽的文明,来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此在《春尽江南》中,我们看到的便是江南这个承载民族人文精神的圣地,被横暴染指,褪去理性和诗意的光环,被工业文明吹散得不见踪影。格非以谭端午的精神堕落来警醒:承载着人文价值观的江南文明正在被资本裹挟得式微,即将成为一片精神的不毛之地。
在时间的维度上,五四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转换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怀疑和批判,在两个迷乱的时代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现代思想。鲁迅在面对庸众一次次的反驳与否定中,选择在绝望中逢生希望,这是鲁迅的担当意识和反思精神,他彰显知识者的存在价值;这种精神延续到格非的书写中,他赋予当代知识分子不一样的身份职能——社会观察者,努力让他们伪装成失败者的模样,身处社会边缘,以他们的自甘堕落明示精神腐烂的真正意义,让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不再成为浮华时代的一种情怀,而是支撑其摆脱被异化的人生,抵达生命自由的期待,在这个程度上,格非也是在绝望中找寻希望的可能。从秉承着启蒙立人思想的过客到冷观时代、坚守自由的谭端午,我们都能看到清醒的知识分子是认清迷乱年代的重要力量,他们和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在精神的追求上都显示了诗意的超越,在个体和庶众的对立中找寻自我独特的存在价值,虽然无法涵盖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复杂性,却深刻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