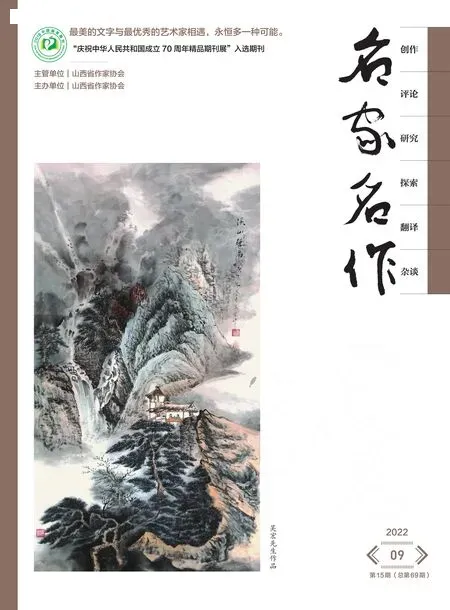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的城市空间
张若麟
一、第三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空间转向理论诞生于20世纪中叶,在西方现代文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理论先由米歇尔·福柯以及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理论雏形,随后美国的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在二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方面的学者,他在建筑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他对于空间转向的思考为这一理论的建立起到了原初性的意义。福柯为空间带来了独立价值,认为空间不仅跟我们所处的年代同样重要,而且在空间范畴中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甚至超越了人们对时间的客观感受,空间带来了新的思考维度。过去的思维方式以及文学创作基本采用的是以时间流为主导的线性叙事,承认世界是同质的,是乌托邦的,在艺术上推崇一种宏大叙事。而福柯恰恰觉得这种空间认知是僵死的、静止的、不运动的、刻板的,故而提出用“异质空间”的概念,认为空间的本质是多元的,是破碎的,不是同质的、统一的。福柯的异质空间论超越了真理探寻上的光明——黑暗二元说,包容二元而且超越了二元,用异质空间的手法解放了主流社会空间以外的特殊的边缘空间。
爱德华·索亚在解释第三空间时使用了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经典短篇小说《阿莱夫》的例子,阿莱夫是封锁于地窖中的空间,但它是无比开放的,一旦看到它,就等于探知整个世界了。这种边缘的神秘感正是第三空间,第三空间以其独特的象征意识,允许了超越种族、等级、阶层、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存在。创作主体在第三空间中感受到了“他者”,而非唯我论的创作模式。第三空间本质上瓦解了创作中心主义,变成后现代创作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多核心的创作模式。
第三空间提出的“他者化”在文学表达上消除了传统文学叙事中典型的以作者为核心的因果意识,作者捕捉到的因果关系可能仅仅是他看见的,是根据他既有经验感受到的。这种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于,文学不再被当成是一面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子,不仅仅对地理、人文进行复写和重现,不仅仅追求一种写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甚至参与到了空间性、社会性的进程里面,成为流动的生存意蕴的一部分。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城市空间
(一)“本土空间”与“异域空间”
1.上海
海派文化就是指上海一带的文化氛围,相较于京津文化,海派文化更加讲求的是多元撞击、价值并生。关于海派文化,海派名家程十发曾言“海派无派”,反映了海派文化之复杂性。从时代背景来看,海派地区的港湾是最早和世界接触的,因此商业文明也是最先在海派文化中生根,海派初期的一些小说因而就具有“现代性”“感觉派”的内涵,海派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是世界的窗口。从文化表现来看,海派的内容具有20世纪欧洲、美国、日本所具有的战时以及战后的虚无主义颓废之感。
造成海派多样性的原因非常有趣,即海派本身的形成基本上都是由外来省份的人才聚拢的,上海本地的艺术家反而不多,大多数海派艺术家来自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民国时期是海派艺术的鼎盛时期,当前市面上海派艺术的优质作品多是产自这个时代。民国时期的海派艺术是一种多元价值混杂的局面,其中西方的文化力量以及国内的改革思潮占据了主要成分,而能使海派坚守中国传统的大家们在比较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位置,激发出更多的创造活力。
张爱玲是20世纪重要的现代作家,其祖籍是河北省,但出生在上海,因而对上海的人文环境相当熟悉。张爱玲的出身跟曹雪芹很像,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因而更能洞察繁华凋落后的凄凉。《倾城之恋》是张爱玲闻名于世的小说之一,其中涉及多元命题的交织混合,是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时代战乱中的流离,把小人物的甘苦与大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张爱玲小说非常鲜明的模式。张爱玲的创作时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也恰是世界时局动荡最厉害的时期。国外兴起了各种启蒙后现代的思潮,如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各种宗教、制度、科技、文化都相应地涌入中国。中国早期的改革者也认识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墨守成规所带来的弊病,故相继抛弃中国之传统,而去接纳西学。
据王安忆说,张爱玲是有别于中国文学、有别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式的书写者,张爱玲不会嫌弃民间琐事,反而在对上海弄堂里面琐碎之物的描写中剖析了人性,找到了救赎。张爱玲在1943年8月左右创作了《到底是上海人》,对上海这一城市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张爱玲的批判是围绕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描述小人物在上海动乱中日常生活有何改变之处。
从侵略者到“一市之长”都大谈着上海的“可憎”,而张爱玲却不屑只是一味地从大概念上批评上海。上海的命运就是张爱玲的命运,它漂泊动荡,因为时局而不断改变着,上海的过于世故也早就浸入张爱玲的文字血液中,她很早就能够写出相当成熟的、辛辣的作品。
《倾城之恋》的故事主要围绕香港展开。上海白家的小姐白流苏在感情生活失意之后深受折磨,在上海寄居亲戚家时邂逅了外表潇洒的单身男子范柳原,便思考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借助范柳原来摆脱上海的环境。他们二人皆是情场高手,最后相约在浅水湾饭店开展爱情之前的博弈,这次博弈白流苏好像输了。后来随着战争的演进,战乱之中范柳原拼命地想要拯救白流苏。
在语言的创新上,张爱玲的语言更具生活化的关乎情爱的隽永。比如“ 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等,这种语言风格是非常感性化的,从逻辑上讲未必是真理,却绝对是创作主体由内散发的真实感受,因此读来有着眼前一亮的况味,非常具有个人魅力。
这种语言风格是海派文学的一种代表,比如鸳鸯蝴蝶派便是海派通俗文学界的代表,张爱玲尽管机灵,但也沾染了海派文学中对于媚俗的渴求。
张爱玲眼中的上海是新旧文化交替并且时刻面临现代社会高压的一座城市,里面存在着相当多的畸形产物,方便于小说书写,然而上海也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上海已经是个多元文化混杂的商业城市了,它虽然古朴拥挤,却也时刻充满着异域情怀,让张爱玲小说充满神秘韵味也跟她对上海租界的观察分不开,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萨黑妮公主、《创世纪》中经营药房的格林白格夫妇等就是异国的。
上海同时也是让张爱玲心碎的城市,《半生缘》里面记录的现代年轻人的故事,女人似乎跟男人一样“能够读大学,可以去咖啡馆,给别人当家教,能够自食其力”了。然而曼桢却依然没有走出封建大家族的苑囿和诅咒,被无情的姐姐迫害,最终只能成为家庭的生产工具。上海既像一个衰老的贵族,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它往哪个方向发展还很难说,常常会酝酿新的幻灭和新的伤痛。
2.香港
如果说上海是张爱玲的文学母乡,那么香港就是张爱玲的他城。张爱玲共有两次寓居于香港,第一次是1939年,当时欧洲正在发生战争,张爱玲因此无法去伦敦就读,只好来香港学习;两年后的1941年,张爱玲又因太平洋战争的牵连,被迫离开香港,回到上海。等到张爱玲再次去香港已经是十年后的1952年了。张爱玲两次去香港的目的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大时代的影响。香港这个《彼岸》况味的城市因而更有了动荡漂泊之感,乃至香港恰似上海的一个镜像,可香港毕竟还不是上海。香港和上海在张爱玲的笔下有“双城”之感,香港有时是另一个上海,上海也总是作为香港的“他者”。
张爱玲1939——1941年在香港留学期间,见到香港有许多仿欧式建筑设计,而另一边也有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那种怀念上海的旧式传统,把房屋打造成等级差异明显、富丽堂皇的宫廷。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又承接了上海的文化血统。海派文化中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学者以及艺术家其实都是从内陆其他省份逃难而来,等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又被迫流亡到香港,因而香港的文脉其实是跟上海颇有渊源的。从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来看,她的感受相当复杂,因为香港没有上海的“涵养”。
香港作为上海社会的“他者”,其实是对主流文化圈存在附庸的,比如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梁太太园会的时候,一切布局、模式其实还是上海的那一套,可梁太太却显得急了。从张爱玲对梁太太园会的描写来看,香港当时在模仿西方时,终究是太喧哗、太粗俗、太夸张,造就的也就是止于文化上的哗众取宠品。
比如《倾城之恋》中两个重要的空间白公馆和浅水湾饭店,前者是在上海,尽管包含了种种旧式家族禁锢的丑恶,可白流苏却把它当成家;浅水湾饭店尽管奢华、明媚、自由,可白流苏只会感到一种身是客的幻灭。这感觉就像获得成功的马丁·伊登,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心灵上的归属,反而更加压抑。当然,造成白流苏在浅水湾饭店拥有极度漂泊感的除了范柳原“不愿束缚”的婚恋伦理外,还有上海旧式家族的腐朽和亲情的背弃。白流苏前后无着,因此只剩下了孤独。
(二)隐喻性的第三空间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还包含许多具有隐喻性的第三空间,比如“公馆”就是一个。《辞海》解释:“公馆,公宫之舍也;公馆,君之舍也;按今谓官吏之寓所曰公馆。”公馆在日本文学里面经常可以见到,比如夏目漱石的许多文人小品就是发生在公馆以内。
而公馆之于上海来说,却代表了封建没落家族的存在,公馆是拥挤的,是等级分明的。香港一些遗老们为了维持生活上的奢华,也十分向往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因而公馆意识也融入香港文化里面。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是一位“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的丈夫死后,她把家庭完全改造成“古代的皇陵”,让人生畏。梁太太仿佛成了大家族中的西太后。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梁太太毕竟只是靠上流社会男人的支持才有体面的寡妇,梁公馆成了香港名流斡旋之地。梁太太尽管在情欲上会撩拨如乔琪乔和卢兆麟之类的小角色,然而生活的重点却还是搞好和上流人物的关系,为了维护公馆的虚荣,梁太太被迫要跟男性主流社会妥协,成为肮脏的、堕落的附庸。这是公馆空间腐朽性的体现。
相较于象征着阶级属性的公馆,公寓这个活动空间无疑成为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符号。女性生活在公寓中,不必考虑压迫性的问题,可以自由自在地表达各自的观点。用伍尔芙的话来说,女性能够在“自己的房间中切入观点”。女性主体精神性的思考也就更容易体现出来。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公寓这一意象的包括《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
三、结论
第三空间理论打破了文本叙事中唯时间——历史论的二元结构,让空间参与其中,使得作家对时代的观察更加深刻而敏感。第三空间为文学创作打开了异质结构的容器,作家也能通过对第三空间的描写更加深刻地探索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城市的本土化气质以及这一气质对故事中的人物有什么影响。
张爱玲擅长写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她的小说多以城市描写作为背景,空间意识十分浓厚。其小说以居住空间作为情绪和事件的凝结地,空间意识十分独特,这让她的小说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耐人寻味。从地点上来看,张爱玲的小说主要穿插于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彼此是对方的他者,一个是开始老化、新旧交替的上海,一个是蓬勃奋起但殖民地属性严重的香港。小说里的人物在两座城市之间流亡,默默承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伤害。借助于两个城市的描写,张爱玲将大时代下挣扎生存的小人物的悲喜与流亡写得精彩、饱满,人物刻画得十分生动。另外,小人物所处的空间,如公馆、公寓,看似平淡无奇,背后实则都充满了对社会意识形态、女性身份地位的隐喻,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