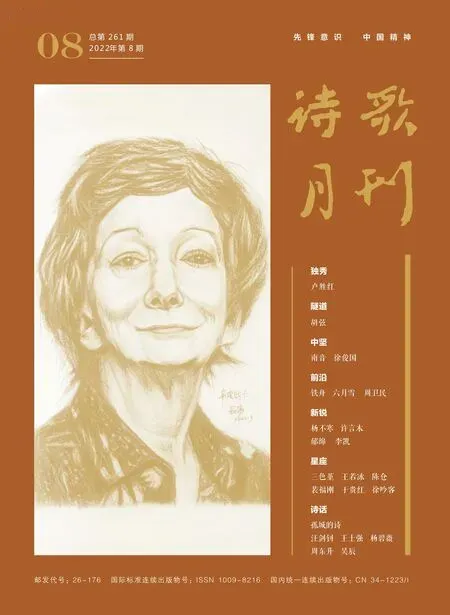一个唐朝剩下的诗人
周东升
读其诗,想见其为人。我读孤城诗虽不多,但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位有情怀的诗人,一位体察万物又不拘于物,对现代性有深入体验却追慕古典精神的诗人。在《花蕾一层层打开春天》中,孤城既谦逊又自信地写道“没有被形容词破坏过的细蕾,在稿纸上,/直接把我喊成——一个唐朝剩下的诗人”,显然,这是诗人的自我定位。“剩下”带有遗民的伤感,也有秉承唐人遗风的志趣。相对于那些高唱复兴传统的诗人,孤城的写作姿态显得审慎、节制、恰当。但不得不说,这样的自我定位也隐含着较大的封闭性,“剩下的诗人”就像前朝的遗民,拒绝顺应新朝,既有消极的对抗性,又有主动的排他性。正因此,它限制了诗人当代经验书写的广度和深度,也才有了这类与时代生存甚为隔膜的句子:“众云已扮成民间的布衣,逢单/赶集幽会,双日荷犁下田……”(《花蕾一层层打开春天》)
《读春天》写的也是一个乡村场景。起句格调不凡:“阳光一天天指出雪的肤浅”,抛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期待,但读到结尾才发现,这首诗不过是古人“喜柔条于芳春”和感春光之易逝的另一种精致化表达,似乎万物并没有随着人类进入残酷的现代社会。“雪的浮浅”“拔高春天的涵义”“劫持一头耕牛”等惊人之语也随之落入了惯性语境,止步于修辞层面,显得十分可惜,甚至,还有虚张声势之嫌。在孤城的笔下,不论“读懂”春天的阳光、青稞、羊群、庄稼、蜜蜂、冰、大海、耕牛,还是读不懂的雪和风,都成为诗人命名春天的诗性元素,但农耕文明行将消失的今天,如此多的农耕意象又如何能有效命名现代人的“春天”?
现代人的“春天”,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春天”,“唐朝剩下的诗人”当然清楚。但“剩下”的情怀使诗人甘心沉浸于唐人的视角,而拒绝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典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以及人赖以存在的文化和自然,都经历了一场沉痛又决绝的理性启蒙。日常生活的神性基础被瓦解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也遭到祛魅,自然万物被逼进各自的客观生命状态中。这事实昭示了现代人面临的巨大困境:即便古典的自然山水田园依然存在,人们戴着这双无法摘除的理性眼镜也难以看得见。更何况,自然确已消亡,无处不在的,只是经过精心算计、投其所好的风景;农耕文明也失去诗性根基。今天的农民和耕牛,像古典时代一样入诗,实则是非常残忍的。牛犁耕田的场景实已成为贫穷、落后和苦难的符号。身处现代性的困境中,人既无法返古也无法超越,这是残酷的又是真实的。因此,现代诗,不论西方还是东方,皆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偏于知性和批判性——就是要破除幻想,破除文人的伪浪漫,真诚地面对这一生存的实境。
孤城诗歌常有令人惊叹的造语,除前文所列,还可以举出许多:“那些被岁月动过手脚的人/像一株株老寒柳”(《中秋赋》)“秋风在草叶的/遮掩下,翻过山冈就不见了。”(《秋》)“与八百里弓背的波浪一起,练习恢复平静与/归隐”(《剩下来的时光,我打算这样度过》)“春天在窗外喊哑多少回嗓子了?/那把木椅/再没能回到山林”(《绝望》)等等。这样敏锐的感受力足以证明孤城的诗歌才华。然而,诗人的观念就像一个装置,始终框范诗人对生活的体验方式以及表达体验的可能。一旦观念固化,诗的偏见随之形成,优点将为缺点所累,缺点也将演化为致命的缺陷,这种情况即便当代名家中也不乏见。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孤城的写作也潜在着观念固化的危险。读他近些年的作品,风格越趋个性化,写作也日渐显出难以克服的模式化。古典主义的理想和趣味在限制着他的感受方式、写作路径和想象力,使他对现代人悖论式、失语化的生存困境,视若无睹或避之不及。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人心内在的巨大波澜和曲折隐忧,绝非单向度的古典情怀所能表达或命名的。这一点,我相信孤城也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