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古代黄河河神崇拜
□赵晓羽 夏厚杨
彩陶上的水波纹
原始水崇拜意识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实践活动。随着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的发展,华夏先民逐渐发展起了以农耕、畜牧为内容的生产经济。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壮大,水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彼时华夏先民开展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人们对黄河河神的崇拜,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先民对水的祈求与崇拜。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华夏先民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黄河洪水是生活在此流域的先民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

甘肃省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漩涡纹彩陶瓶
华夏先民面对洪水时,囿于认识所限,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便产生了“鬼”“神”的意识联想,将洪水视为“鬼魅般的存在”“上天的惩罚”。自此,水便成了原始宗教活动中的重要祭祀对象。
在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带有水波纹、漩涡纹等纹饰图案的彩陶,表明这一时期先民对水的原始崇拜已经出现,并成为原始河神崇拜的起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村落遗址的位置一般在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之上,距离水源很近。这些遗址出土了大量刻画着精美水波纹、漩涡纹等纹饰图案的陶盆、罐、瓶、钵等器物。
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黄河流域原始社会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陶技艺的提升,陶器上的水波纹等水形图案也逐渐由简洁具象的线条向复杂抽象的意象表达演化。水形图案的这一变化,表明水形图案不仅仅表达自然水流,还带着原始宗教色彩的烙印。
卜辞中的河神
“河”,在我国古代专指“黄河”。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先民向河神“求雨”“求年”“求禾”等祭祀活动的记载,显然黄河在他们心中已经具备神的魔力。“河”在殷墟卜辞中有4种用法,分别作人名、地名、水名、神名。作为祭祀对象的“河”,即为“河神”。河神在一、三、四期甲骨文卜辞中大量出现,祭祀待遇之高,祭物之丰盛,足以说明河神在殷代是极为重要的神灵。如《甲骨文合集》12853记载:“壬午卜,于河求雨,燎。”即为在河边用燎祭的方式祭河神。又如《甲骨文合集》33270记载:“甲子,求于河,受禾。”意思是在河边祈求五谷丰登。这说明,在殷商时期,人们对河神的祭祀已经成为国家祈求风调雨顺、战争胜利、占卜未来的重要宗教仪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关河神祭祀的不下500条。商周时期,河神祭祀被纳入国家祀典,官方和民间皆祀之。作为国家重大事项的河神祭祀,便从此时起逐渐走向仪式化、正规化。
需要指出的是,殷人所生活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现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其崇拜和祭祀的黄河河神,主要是与他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某一段黄河或大小支流,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整条黄河。此时的河神,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何经锋等人的研究表明,从一期甲骨文卜辞开始,河神就被认为与上甲、王亥一同拥有掌控自然的权能,这正是商部族早期首领借河神之力征服自然的重要原因。另外,河神还有佑助战争胜利的权能,表明河神还是商部族的保护神。此时,河神被赋予了更多人格化特征,不再是对一条河流的简单神化。这种从物到人的崇拜思想演变,契合了中国古人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转变的深层逻辑。
黄河河神的化身——河伯
人们普遍认为,人格化的河神,即为我们所熟知的“河伯”。关于河伯的来历,古籍中有诸多考证和解释。《文选》李善注以川后为河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以大禹为河伯。还有一种说法,河伯名冯夷、冰夷、无夷,其名始见于《庄子》《楚辞》《山海经》等书中。《龙鱼河图》记载:“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神异经·西荒经》记载:“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海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二七引《滑县志》:“河侯祠在县南一里。汉东郡河决,太守王尊以身填之,水乃却。及卒,民为立河侯祠祀之。”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河伯的来历并没有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此时的黄河河神,已经不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自然神,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故事的现实人。被神化了的河伯,成为河神的完美代言人,具有了管水治水的社会功能属性。这种身份转变的根源在于“神为我用”的中国传统实用主义逻辑。
最为人熟知的河伯故事,是西门豹治邺。战国时期魏文侯时,西门豹到邺担任县令。西门豹了解到,那里的官绅和巫婆利用河伯娶妇勾结在一起危害百姓,便设计破除迷信,并大力兴修水利,使邺地再次繁荣起来。西门豹治邺说明了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地区,祭祀河神在民间已经广泛存在。
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留下名篇《九歌·河伯》,描写了河伯与女神相恋的故事。《庄子·秋水》中讲述了河伯望洋兴叹的故事,描写了一个知错就改、有自知之明的河神形象。《尚书·周官》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史记·殷本纪》记载:“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对黄河河神的祭祀,承载着万众对国泰民安、福泽万民的期许。同时,河神祭祀也成为周王室和各诸侯必不可少的政治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河神经历了复杂的人格化、社会化演变过程,已经变成了承担黄河治理使命的社会人,成为古代黄河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历代黄河河神祭祀
《史记·封禅书》中的“(秦始皇时期)水曰河,祠临晋(今陕西大荔)”是关于河神祠的最早记载。临晋是秦朝最早的文化地域,临晋河神祠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祭祀黄河河神的场所,自此,黄河河神有了自己的庙祠。秦始皇重视黄河祭祀。“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河渎”,并把黄河祭祀纳入国家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中,使江、河、淮、济的四渎祭祀在国家文化意识层面得到了确认和统一。这个时期的黄河河神,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河渎神”,并成为全国四大河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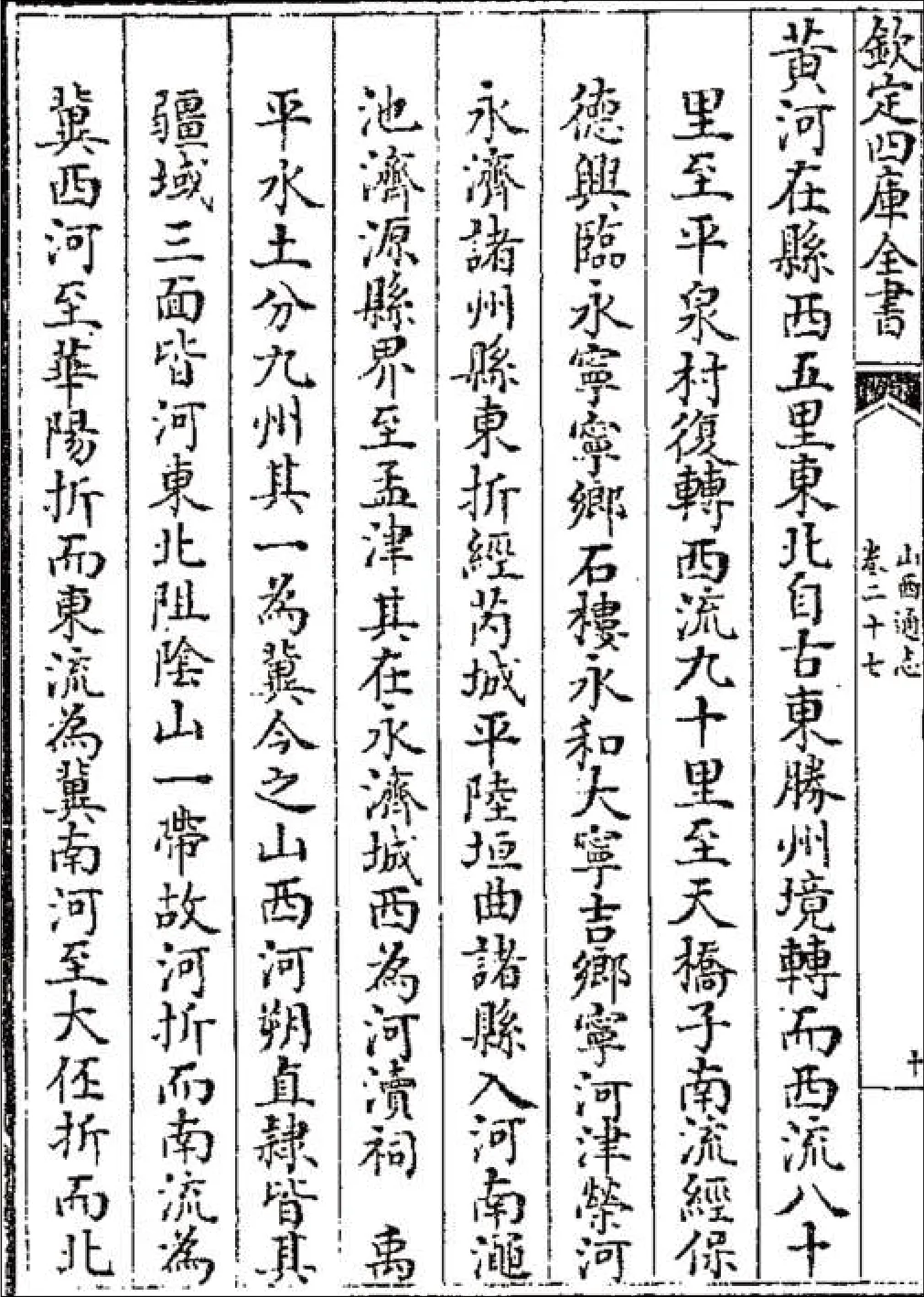
四库全书中关于河渎祠记载
汉承秦制,延续了秦朝祭祀黄河河神的传统。《史记》载,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天下平定,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其河巫祠河于临晋”,即让河巫在临晋祭祀黄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临晋,故大荔,秦获之,更名。有河水祠。”汉朝祭祀黄河河神仍旧在临晋。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修河渎祠,又规定祭河“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修河渎祠。汉武帝参加瓠子堵口时,还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黄河河神,并在《瓠子歌》(其一)中写道:“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诏岁祀河于临晋”,“令祠官以礼为岁事,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祀”,以此确定了五岳四渎的祭祀时间、地点和祭品等,使五岳四渎祭祀制度正规化。从此,五岳四渎成为朝廷山川祭祀的首要对象,为后世所沿袭。《汉书·郊祀志》载:“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祈为天下丰年焉。”同时突出了泰山、黄河作为其中的重点祭祀对象,每年派使者到临晋河水祠祭祀5次,祈祷天下丰收。记载汉代典制文献的著作《汉官旧仪》中记载,祭祀四渎,用三正牲(即猪牛羊)、玉璧、车马等沉于河中。
三国时期,曹魏承汉制祭祀黄河,《三国志校笺》载:黄初二年(221年)“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以五岳四渎的祭祀为代表,重新建立起整个国家祭祀的秩序。
北周非常重视黄河祭祀,由于北周当时的疆域没有达到其他三渎,无法在三渎原来的神祠进行祭祀,于是朝廷在北周的朝邑县汉代黄河祠的基础上建立了四渎祠,用以祭祀四渎。《太平寰宇记》载:“四渎大河祠,汉郊祀志云,祀河于临晋。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547年),于汉祠更加营造,因立四渎祠于庙庭。”到了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北周的疆域达到了其他三渎,于是就在长江、淮河、济水原来的神祠进行祭祀,唯有黄河祠依旧不改,每年派遣使者,用更多的玉璧和牲畜进行祭祀。
至隋代,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发布诏书,加强河渎祠的管理,专设一名负责人进行日常管理,并要求在河渎祠多移植松树和柏树。隋代确立了以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为首的祈雨制度,《隋书》记载的祈雨顺序是先祈祷岳镇海渎及诸山川,7天后再祈祷社稷,7天后再祈祷宗庙。这一祈雨模式被后世所继承。
唐代时,“岁祭河于同州”。唐以前,黄河河神的爵位,一直为“伯”,并不在王侯之列。但自唐起,黄河河神开始接受世俗化的等级尊封,并不断被加封晋爵,开始逐渐抽象化、概念化、官僚化。《唐会要·封诸岳渎》记载,唐天宝六年(747年),当时“其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答灵心”,于是“其河渎宜封为灵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奏使告祭”。河神由“伯”加爵成了“公”。
宋代时,黄河洪水频发,河神祭祀也达到了高潮。“自京师至州县,皆有其祀”,并“岳镇海渎之祀”,明确规定祭祀礼仪规格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决口,“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诣白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其后,立秋日祀西海、河渎并于河中府。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定河渎祭日及祭所,立秋日祀西海河渎,并在河中府河渎庙对西海进行望祭。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以汴口复通,祭河渎之神。“十二月己卯,诏澶州于河南,置河渎庙。初,帝幸澶州,大河不冰,虏若见阴兵助战,故立祠。”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次河中府,幸舜庙,赐舜井名广孝泉。度河桥,观铁牛。又幸河渎庙,登后亭”。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又诏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河神由“公”上升为了“王”。康定二年(1041年)三月,以黄河水势甚浅,致分流入汴未能通济,遣祭河渎及灵津庙。
金元时期,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年),诏以立秋祭河渎于河中府。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元世祖下诏,于立秋之日“遥祭大河于河中府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对中书省官员说:“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二月,给岳镇海渎加号封爵,四渎为“王”号,封黄河河神为“灵源弘济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一月,黄河自平陆三门碛下至孟津五百余里皆清,凡七日。顺帝“命秘书少监程徐祀之”,并下诏加封河渎为“灵源神祐弘济王”。
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于是下诏令“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黄河河神则被称为“西渎大河之神”。至此,黄河河神,由“王”上升为“神”。“洪武七年(1374年),令河渎山西蒲州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八月,以洪水为患,穆宗命总督河道都御史翁大立祭大河之神。
清代,清顺治三年(1646年),特封黄河河神为“显祐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加封黄河神“昭灵效顺”四字;清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下旨加“江海大神”封号,敕封黄河为“西渎润毓大河之神”。其河祠地点仍在山西蒲州。始建于1723年的嘉应观(位于河南武陟县)是雍正为了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建造的淮黄诸河龙王庙,是中国最大的河神庙,其内供奉10位河神,享受国家层面的中祀。
宋代以前,祭祀河神的处所称为河渎祠,宋以后,改称为河渎庙。清代时,河渎被封为四大王之神后,黄河两岸又建有多所大王庙。关于河渎庙,陈凯华的研究表明,河渎庙共进行了三次迁徙,分别是秦至唐代的临晋县(朝邑县)三河口、唐宋河西县、宋以后的河中府城(蒲州城、永济县城)。河渎庙在黄河以西的时间是秦汉至宋代天禧五年(1021年)约1200年,位于河东约900年。其迁徙的主要原因是黄河在小北干流左右两岸的洪灾。
除了官方对黄河河神的加封和祭祀外,民间黄河河神祭祀更加广泛且影响深远。以清代为例,祭祀黄河河神的大王庙,不仅在黄河中下游沿河地区广泛存在,而且在江苏徐州黄河故道沿河地区的8个州县建有47座。
民间对黄河河神的祭祀规格也相当之高。以河南孟津地区为例,在旧时的传统中,每年除夕都要牵羊担酒,到大王庙献羊敬酒。烧香磕头之后,把热酒洒在羊身上,如果羊身抖动,就表示神王已经领走了;如果没有,就再次磕头敬酒,把热酒洒在羊身上,直到羊身抖动为止。之后将羊宰杀,大年初一五更到庙里上贡。
综上来看,古人对黄河河神的崇拜与祭祀,自殷商开始,历经几千年,河神的形象由最初的自然神,发展成一个具有人格化、社会化、世俗化的社会神,到明清时期又演变成为人类英雄式的河神。无论是黄河河神崇拜祭祀的发轫演进,还是黄河河神崇拜的对外延展,无不反映出古人改造黄河、利用黄河的精神内核。
黄河滔滔,万里浩荡。河神祭祀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千百年来,河神祭祀作为国家重要礼仪大典,全国瞩目,国家和人民对黄河的期望都在河神祭祀中得以体现,这是中华民族对黄河的精神寄托。今天,我们通过遍布于黄河两岸的各类河神庙,依旧可以感受到历史悠久、承载民族感情的黄河治理精神!

河南滑县大王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