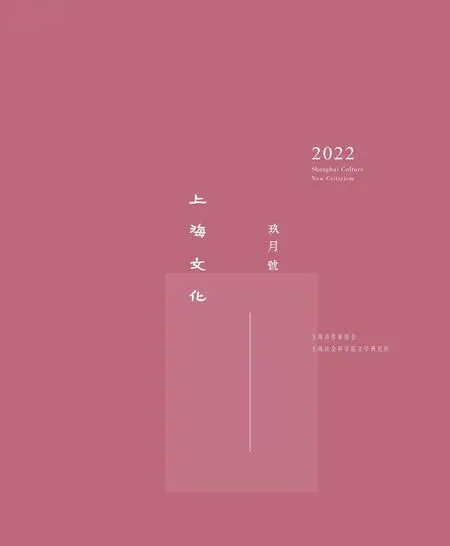而迷途于万物者,将追求光源里尔克诗歌中的“爱”
朱玲玲
一
痛苦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会,
而远离我们的死亡之谜
尚未揭开。
1926年12月21日,里尔克生命的最后时日,他给朋友的信中写:“可怜的瓦罐碎片还想得起自己来自泥土。”在与死亡之眼对视时,遥远的生命起源变得如此切近,以至于步入死亡对他而言,就是步入“敞开之境”,以及浩大的生命循环。这是他在诗中反复吟唱过的重大时刻。对于回归起源,进入生命整全之境的渴望,从来就隐伏在里尔克的诗中,“矿石有思乡病,它渴望/逃离铸造的命运。铸造/使生命变得贫乏。/从金库,从铸造车间/它渴望沿着像血管似的矿脉,/回到崇山峻岭中。它正是来自那里,现在,埋藏又一次使它安然无恙”。人的生命也如瓦罐与矿石,向着本原回溯,是生命本身秉有的一种超自然之力。在面临死亡时,朝着起源的归回与向生命终结的行进,最终重合,从何处来与往何处去叠合为同一个问题,共同指向一个本源的敞开之域。里尔克明白,这个敞开之域,对人而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入口,就是痛苦与爱。
这个敞开之域,对人而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入口,就是痛苦与爱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这篇长文中,置身于“世界暗夜”来观测里尔克复杂深邃的精神星空,将他称为“贫困时代的诗人”。时代何以贫困?海德格尔如此解说:“时代之所以贫困不是因为上帝之死……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时代之贫困与上帝之死无关,也并非由上帝之死引起的次生灾难。而是因为人误解和滥用了生命中最切近本质、强度最高、振幅最大的体验——痛苦、死亡与爱,以至于那个广远的本源之境被彻底遮蔽,造成了世界暗夜。
痛苦、死亡与爱,是人的生命至深的奥秘,也是超自然领域在属世之人中设置的三个突入口、三种强劲的召唤,当然,也是人走出洞穴接受光照的三次机会。然而,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失去了倾听和接收这强烈信号的能力,也几乎没有可能回应这凛冽强劲的呼唤,并据此调整生命的航向,而最终错失了这种启示。因此,敞开之境自行隐匿,造成封闭世界的形成,这是时代贫困的一个重要征兆。在里尔克的诗里,爱、死亡和苦难,始终是一再重现的重要主题,是通向无限宏大之存在的艰难启示。倾听这种启示,让陷于穷乏的灵魂得以瞥见来自生命本源的光亮,让生命朝向那自我之外的光源而调试自身、重新定位——这是里尔克笔下爱、死亡与痛苦的奥义所在。
其中,爱因为错乱丛生而尤为艰难。里尔克甚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作出非常严峻的判断:“我们这一代的巨大厄运不是在社会或经济领域,而是在此,在于爱的行动被逐至边缘。”在个人存在层面,辜负爱的最初馈赠和启示,一种向光明的敞开最终沦为封闭世界中两个坚硬个体的剧烈冲撞,这在世俗生活中已是常态;而在时代的精神状况层面,由宗教的爱者或者圣徒灵魂中熔岩般沸腾的爱之体验浇铸而成的宗教已经冷却、熄灭于表层的教条拼接,人最内在的神圣之火终归无法嫁接到已经变冷的道德基础之上,而被长久地遗忘,由欲望所定义的封闭个体轻易就能冲决道德的脆弱薄冰,整个世界就是各种级别各种程度的对抗力场。
这一切,在里尔克的判断之下,与人错失了爱的教诲,将爱逐至生命和时代的边缘不无关系。就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柏拉图主义者斐奇诺所言:“我们大多都爱错了……在幽暗的爱之森林中迷失道路比在任何旅程中迷失都更严重。”个人的迷途与时代的厄运都与此相关,所以,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断言:“谁严肃地看,谁就感到,同对于艰难的‘死’一样,对于这艰难的‘爱’还没有启蒙。”事实上里尔克的诗,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柏拉图之后,在基督教之后,对现代人重新进行爱的启蒙。因为毕竟,即便在世界整体的意义上,爱的行动被逐至边缘,但它并没有离人而去,如同散落的、跳动的火花,它始终在爱的狂热灵魂中存在,在爱人、哲人、诗人以及圣徒的灵魂中燃烧,任何时代这都珍稀有如圣火,任何时代这都是照亮世界暗夜的奇迹星火。
事实上里尔克的诗,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柏拉图之后,在基督教之后,对现代人重新进行爱的启蒙
二
看吧,我们爱,不是像花儿一样
发自唯一的一年;当我们爱的时候,
太古的汁液升上我们的胳膊
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向爱人发问:“你们恋人……我向你们/询问我们。”诗人所问的,是关于人之存在的谜底。时间的剥蚀,感觉和思维的似真非真,以及死亡的悬临,会让人产生对于生命的怀疑和不确定感。而爱人们在里尔克那里,显然是存在之谜底不自觉的知情者,他们的存在更为丰盈:“你们在对方的狂喜中增长,/……相互愈加丰满,好像葡萄丰收年;/你们有时晕厥,只因对方过于充盈;/……因为你们在手掌下感觉到/纯粹的延续。”被纯粹、强烈的爱所点燃的人,犹如满蓄的离弦之箭,急速飞离日常维度,在无限的光亮和无名的广阔之中,达到自身最高程度的存在,犹如进入一种迷狂之境。
更重要的是在爱中,关于人之存在的永恒维度在刹那间闪现出来。里尔克在《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里如此描绘恋人的相遇:“没有昨日,没有明日,因为时间已经塌毁了,他们从它的废墟里开花。”从遥远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传统来说,人是身体与灵魂的综合,因此也是时间性与永恒性的综合,但是作为身体性的存在被锁闭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的时间之流中,永恒的维度始终是被遮蔽的。而爱人在极其稀有的瞬间,直接体验到时间与永恒之间的极大张力,“时间塌毁了”,爱在有死之人的时空内开辟出一道非时间的,闪电状的路径,在时间断裂处出现了一个非时间的广域。在时间坍塌的废墟中,恋人的生命中开出转瞬即逝的灿烂之花,暗藏着生命的密码,即灵魂的永恒之维。
因此很自然的,与柏拉图《斐德罗篇》里的爱欲一样,里尔克笔下的爱同样有着超验的起源。柏拉图的天界叙事以神话的形式指明了爱情的形而上起因:灵魂来自天外世界,人人均有瞥见过真实的灵魂,而自肉体的诞生阻隔了对于神性起源的记忆,爱作为一种最为神秘的触发力量,使得灵魂受到天外记忆的召唤,萌发出翅膀,挣脱深不可测的遗忘深渊而向天界回归。
在里尔克诗中,同样否定了爱是源自此生此世的:“你像晨风拂来,你真的以为,/你轻轻的出场就让他心旌摇曳?/纵然你惊动他的心;可是更古老的惊惧/一触击他,他已深心震撼。”初相遇的震撼并非源自此时此地此人,而是因为“在恋人体内/诱发远古”。这里所谓的“远古”,毋宁说是在个体生命的经验性时间之外的某种绝对存在。

以诞生为开端的生命是无神论世界的现代人所知晓和承认的唯一一种生命形式,而在里尔克的诗歌中,这只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狭小循环。现代人因为失去了对神秘事体的感知能力,奇象、幽灵世界、死亡,都被日常的理性严密戒备、防御,并挤出生活之外,甚至人连接收它们的感官都已枯萎,这使得人的生命无异于脱离了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宽广河床,而被丢置在荒芜不毛的岸上,因为失去了与本源的深层联结而不可避免地显出枯竭的一面。里尔克以恢复人的整全的存在之域为自己纯粹的使命,他先知般地召唤一种纯全之境,在其中,死生共属一体。
爱是一种生命中最自然而又超自然的现象,作为一种异常强烈的触发机制,爱像洪水汹涌冲决开以诞生所划定的个体生命之开端的阻隔,使人获得与“本源的浪潮”汇合的可能。这与柏拉图笔下的爱何其相似,爱欲的狂热是一种最高程度的心灵活力,爱是一次经验和超验的激烈碰撞,燃烧的火光引起人对于此生之前本原生命的汹涌回忆。爱所带来的颤栗与骇人之感,预示着一种启明,一种灵魂的转向,灵魂因此突破遗忘深渊的封锁而朝向神性本原复归。里尔克的思想中虽然不再突出人的神性起源,但是爱所产生的剧烈的能量释放,依然是挣脱狭小生命循环的禁锢而进入扩展整体的契机,与死亡一样,爱是生存的切口,使得永恒的气息和光照能够进入生命之中。

他的爱欲没有足够的力量穿行过人世间,而是以直接超越世间的诗性方式抵达永恒。因为,人世之爱是如此艰难
三
合二为一的恋人,
曾相互允诺旷远,追猎和故乡,
不是也常常濒临绝境。
由爱的壮丽所敞开的宏大景象须臾而逝,从这种几乎非时间的澄明之境回到日常状态是一定会发生的坠落。里尔克曾经耐心地指引那些陷入爱的绝境中的年轻人:“你们使对方受到那种伟大情感的最强烈的照耀,……以至于刚才还带来增长和丰盈的照耀现在已经显得太多并开始摧毁对方;你们现在势必不自觉地为此报怨。”幸福可以说就是这种完满状态的无限延续,但事实却是,每个人都只能于寥寥几个瞬息被纯粹的本原之光照彻,在爱中亦如此。彼此允诺永恒,因为当时已在永恒中,但是从时间的裂隙即永恒之中再次坠入时间,从爱的癫狂状态重回理性的轨道,从彼此向无限的敞开到重新封闭,退守到坚固的自我之中,这是必定会发生的。


智慧在作为人的这一端,只能是对智慧生气勃勃且永不疲倦的爱欲企求

因为,即便所有人都具备感应爱的灵魂中枢,即便爱是人人秉有的自然天赋,即便爱的发生如同一种神秘的赐予一样自然而然,但是之后,爱在跌落回日常处境之后,在承荷着肉身生命的重负时,在穿行复杂崎岖的世间之路时,必然伴随着巨大的苦楚和艰难,以至于互相允诺永恒的恋人会“濒临绝境”。
或者,对于最初那稀有瞬间的记忆却形成一种近乎残酷的对照,使得重新坠入凡俗状态中的生存显得灰暗不堪,这种失衡也许会衍变成一种弥散性的失望情绪,笼罩之后的整个人生。或者,在剧烈燃烧中融合为一的恋人回到理性状态之后,也会重新冷凝成坚硬的个体,彼此的完全敞开变成两个个体之间的长期对峙和角力,超越之爱沦为专横的“僭主之爱”,个体自我的扩张必然导致狭隘,以及彼此之间的剧烈冲突,婚姻成为了支离破碎的聚合,是一种窒闷、颠倒和紊乱状态的长期延续。或者,如唐璜一样一再地重新开始。但是,即便对“伟大的、陶醉的瞬间”始终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欲望,一千零三个情人却无论如何意味着形而下的败坏。这些闪耀的瞬间无法在现实人生中着陆,它们最多组成在夜空中相继绽放、旋即消隐的烟花,却无力抵达大地,生长出现世的根系,始终不能附着在大地之上,开出有根有叶的花来。

爱在世间有无数种蜕化变质的形式。所以,里尔克对现世之爱的艰难和沉重心怀惕惧


四
他是水:你只需做成纯净的碗盏
用两只情愿伸出的手掌,
然后你跪下:他便源源不断,
超过你的最大容量。



“它巨大的搏动在我们心中分成/细小的搏动。它巨大的悲伤,如它巨大的喜乐,对我们而言/实在太大……但就在一瞬间,那巨大的心跳悄悄把我们突破,/令我们哭喊”——这才是诗,不是单独的、细小的搏动,而是巨大的搏动,像洪流一般冲开自我的封锁,而诗人成为一个火山口,诗从这里喷薄而出。
因此,最后的一刻一定是臣服,诗生成的瞬间一定也是诗人“自我弃绝”的时刻,唯有清空自己,才能做成那个最为纯净的碗盏,才能承纳无限者自上而下的满盈。“每个放弃的坠落皆落入本原之中并痊愈”(《哀歌——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要是我们像万物一样/屈服于伟大的风暴脚下——/我们也将变得宽广、无名”(《观看者》) 。“我们占有即损失。失去愈大胆,愈纯粹,/占有愈丰实”(《骨灰坛,罂粟果实的结节……》)——里尔克在诗中反复地吟唱这些伟大的臣服瞬间,他熟悉这些瞬间。
最后的一刻一定是臣服,诗生成的瞬间一定也是诗人“自我弃绝”的时刻,唯有清空自己,才能做成那个最为纯净的碗盏,才能承纳无限者自上而下的满盈


五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六
没有谁
更崇高地献出它,更完好地
归还给整一,更丰裕。你也这样
神圣地游戏,穿过不再指望幸福的岁月。






盗火者即是履险者,他们是伟大的信使,跨越界限带来未知的、不可测度的消息,拓宽了人类的生存疆界。然而他们也是最高意义上触犯尘世规则的人,将“绝对”置于生活之外,以绝对之名否定和侮辱生活,就是在拒绝接受人类处境,摧毁一切物质和精神均衡的存在形式。对绝对和无限的信仰如果以背叛混杂、有限的人世为代价,就是一种幻想和疾病。绝对的消息如何如春风拂过大地,洞穴之外的光亮如何渗透进洞穴之中,这使得“无限”文明化、风俗化的重任,诗人孱弱的身躯毕竟难以背负。
将无限的光亮引入贫困世间,这是诗人的使命。而让这光亮化为文明与风俗,在大地传布,重新培植健全、深稳的人世土壤,这已超出诗人所能。但是唯有如此,尘世之爱与无限之爱,水平结构的爱和垂直结构的爱,才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互斥选项,而是共存互渗的。无限之爱潜入尘世之爱,而尘世之爱承托无限之爱;尘世之爱因为有了无限的维度而不至僵化坏死,无限之爱着陆于尘世之爱,向下扎根,如此则人的生活,在地亦如在天。
❶ 里尔克:《谁此时孤独——里尔克晚期书信选》,林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页。
❷ 里尔克:《慕佐书简》,林克、袁洪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❸ 斐奇诺:《论柏拉图式的爱——柏拉图〈会饮〉义疏》,梁中和、李暘译,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版,第4-5页。
❹ 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❺ 刘小枫选编:《〈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林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❻ 刘小枫选编:《〈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林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❼ 里尔克:《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❽ 刘小枫选编:《〈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林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❾ 里尔克:《里尔克诗选》,林克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