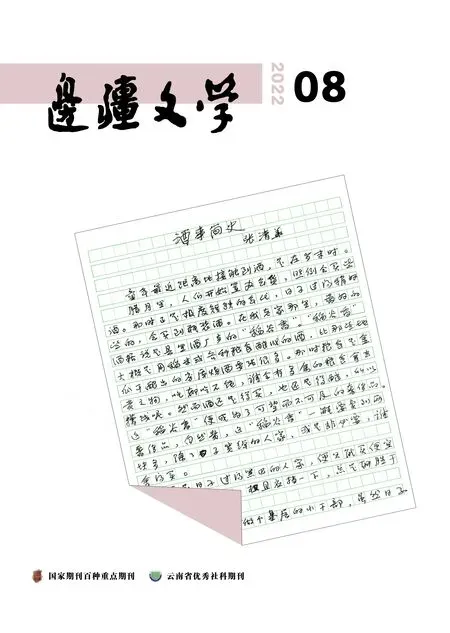众神的雪花 组诗
芒 原
腾格里沙漠
此刻,我一败涂地
正坐在腾格里沙漠,十万黄沙
让我悲欣交集,臣服于
广袤瀚海和每一粒沙子,也臣服于
触手可及。有种不真实的美
它们为什么聚集于此?从哪儿来
到哪里去?诸多疑问偏执地解构了生命
可我们还是不管不顾,面对这苍茫
有人奔跑有人嘶吼有人打滚……
每个人都瞬间饶恕了自己,试图与沙子和解
可风一吹,每个人都又裹紧衣服,不停
拍打身上的沙子,向后撤退
撤退,哪有什么真正的
和解?那只是一句虚构伟大的口号
把沙子多么了不起的善举
写成了一副标语
更伟大
更透彻人心
众神的雪花
天空是我用旧的电影院
雪花从灰色的荧幕里飘了出来
落在每个主人公的
头上。我们尝试着抖落
却又从身体里飘了出来,带着铁锈红
带着废墟的哭声,朝着彼此额头上,肩膀上
胸口上……纷纷剥落而下
姿势让人产生风车的幻觉:“请不要
轻看鸿毛所产生的重量。”
这个声音明显来自另一片飘出来的雪花
那年去观斗山顶,被人斩首的神像,
像署衙门前
张着血盆大口的石狮子,代替人说话:
“你不过是画皮里的一件皮囊。”
像堂吉诃德的铁剑 ——
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可我还在自己的出生地昭通,看雪落下来
看那千百万年来的巨大雪花
住在天空的宫殿里
是不是贪婪的放映机,用雪花点
惹怒了
众神的雪花
辛丑晚秋
从袁家山俯冲而下的晚霞
照亮洒渔河的水面
光影在水底燃烧,像绝望的灰烬
我知道,那是自己的幻象
此刻,派出所已被高楼不断挤压包围
但,霞光仍在暮色中扭亮身体
仿佛所有发光的事物都有落潮之时
而我看到的塔吊在反光玻璃上,像只小白鼠
它们都是这透明世界的试验品
蔓延的速度惊人,一边向前推进,另一边
又向后不停撕扯,像咬断尾巴的壁虎,来不及
给自己收尸
这就是辛丑的晚秋,它已经收走我的影子
当我回头走向食堂,喇叭里正在宣讲
一座城的注意事项
可指缝间的山和水,又亮了
雨的讲述
—— 雨还是落下来
在辛丑春日,它们像除夕
没有落完的鞭炮,又落一遍
像元宵没有落完的灯笼,又落一遍
落得让人心慌,落得满腹空空
落得像一场病,几千年都不曾落完过
落得像一出悲剧……落得
现在我才明白:雨和神明一样
是永远落不完的,也不可能轻易落完
“你必须相信。”它或早或晚
都会来的,它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它在我们头顶,也在我们
脚下 —— 你必须相信!
它就在万物中间,可它并不唯一
它数量庞大,它像蕴藏的
一个个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编制,法外,入刑,恩典……
它已瞄准大地,讲述
才刚刚开始
—— “夜来风雨声,花落
知多少。”孟浩然在空中,“雨水”
并非是他的隐喻,也非他修辞的集中营
一滴雨,或者两滴雨,甚至
众多的雨;小到和风细雨,毛毛小雨
大到倾盆大雨,狂风暴雨
雨就是雨,它透明之身有巨大愈合的神力
同时,雨也不是雨,“雨,不会构成
神圣,伟大,荣誉,羞耻
与谎言……怯懦却是自我的毁坏。”
雨覆盖着雨,它的外延,内核,对立与统一
它们的美,趣味,走向;过去,现在
及未来,是不是统统都从自身流淌一遍
把崇高与卑贱,咬合在
疲软的雨体与不断失窃的暗疾
其实,雨并没有
怯懦
—— 讲述仍在持续。雨再次
回到它自己的日常,肉眼可触
透明、流动:它敲打着车顶,像一场吊环
它从电线上,团身、旋转至360度
然后一跃,在落地那一刻
都是一个加速燃烧的过程:“而雨本身
是不会烧毁的。”它的奋不顾身
那些以粉碎为代价的举动,不论在玻璃上
还是在公园的湖心里
甚至在每一个伞顶……都以
它细密的针脚,像在
缝补春日古老的伤口:草与木
花与叶,泥与尘
一次次孕育,一次次
分娩
—— 那个在公园里冒雨打拳的人
那个在凤凰山顶拼命吊嗓子的人,还有
那些从雨中传来的枯枝
在落下那一刻,雨被短暂地挡在外面
这短暂如同体内的鸟鸣、煦风
泉水,以及闪电,这一瞬
怎能挡住身体衰老的铁锈与时间之盐
其中有我们的祖辈、父辈,也有我们的身体
这一瞬,又足以毁灭……
雨仍在下,它不偏不倚,不急不缓
早已从内部下得倾盆如注。而妄图掌握命运
的人也在雨中:有时滑倒,酿出悲剧
有时站稳了,得接受更大的风雨
只有雨抱着雨到来时
才会更具有
穿透力
—— 停止思考时,雨
欢呼:“是时候啦!是时候啦……”
可我还想再努力一次
是不是能真正进入雨的物理构造,释疑
心中那么多:怀抱雨水的人,捕捞雨水的人
炸毁雨水的人,截留雨水的人
盗窃雨水的人,扣押雨水的人
接纳雨水的人,抛弃雨水的人
弹劾雨水的人,共勉雨水的人
教育雨水的人,顺应雨水的人
监视雨水的人,审判雨水的人
敬畏雨水的人,藐视雨水的人
弹奏雨水的人,谋皮雨水的人
整顿雨水的人,弄脏雨水的人
除此之外,我也想看看雨的“落”与“不落”
落,是一根白骨,还是
一缕亡魂;与此同时,把雨
换作了另一种讲述
—— “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
尽头
第一次,在黑夜中看到新立小学
就被黑压压的乌蒙群山
陈旧的村居,以及
生在夹缝里的阴郁、灰暗怔住
而那一刻,我正从农用车上跳下来
手提一袋沉重的行李
秋风忽起,像个一脚踏空的孤儿
故意吹起满心呛人的灰尘
让人哆嗦——
当十年后,又一次
站在她的门前时,她已经废弃了
我远远地看见曾住过的宿舍
玻璃破碎,像一双空洞无物的眼睛
枯草悬在房顶,豁口的门开着
风一吹,那黑洞洞的咯吱
恍若散落的提问
与回答。我再一次怔住
二十年三十年呢?我不忍再往下想
仿佛自己心中剥落的尘埃
有一天
会把所有的埋葬
无他
反转的时空里,我做着
一件与命运相同的事
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替人间过客
捡烟头,拾纸屑,挑塑料
如同捡一张死去的脸,拾一个破碎的人生
挑天空下失散多年的风筝
时间久了,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荒诞的扫帚,像乌鸫的翅膀,扫你扫我也扫他
某日,丧乱的石狮子,从滚滚的流水涌来
铁桶撞击着木桶,竹篮打响水的空腹
月光兮丁丁,伐木者当当
——无他。但我
还是发了微信,亲自送上自己的半截身体
一位好友说:“这不是飞机的发动机
安装在牛车上,本末倒置。”
我突然觉得自己
还活在人间
“我饿,我太饿了……”
“我的米!我的米!”
把他从沟里提上来
满身酒气,像一摊烂泥
当刺骨的寒风吹得人哆嗦,他已半醒
像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
有人说,“给你找回来了,就在你身旁。”
那一刻,他慌乱的手像一只黑暗中的白飞蛾
扑向了烛火,令所有的事物一瞬间
填满温暖的渡口。他一把抓过来抱在胸前
痛哭流涕,紧紧地抱住,宛如抱住
一个失散多年的爱人
“你们都是好人啊!昨天,我一天都没有吃饭
我饿,我太饿了……”
“真的,我饿,我太饿了……”
突然,又一阵寒风吹过,一些人
已悄然离去
他还在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