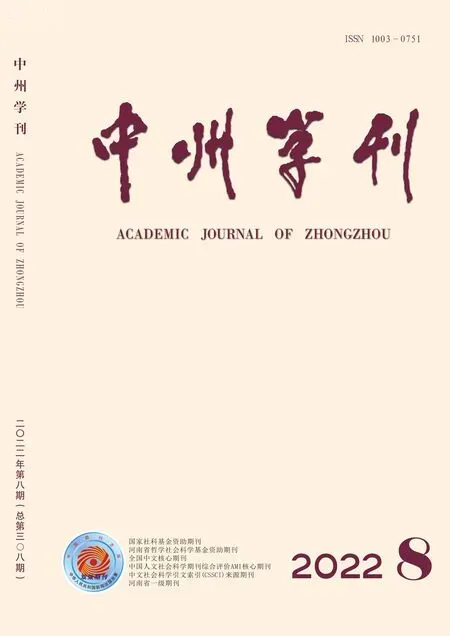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历史价值主脉辨寻*
程 亚 旭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流域以钟磬之乐为代表的礼乐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钟磬之乐“作为雅乐,由金石乐悬领衔,八音汇聚,其中有乐言、乐语之歌唱,有相应的乐舞,整体以多声形态一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多声音乐的先导”。学界关于钟磬之乐的研究多集中在乐器考古、音乐创作、乐器分类、乐器主人、乐律理论等领域,而很少有人从地域、水域或地理角度深层次地发掘其蕴含的潜在价值。本文以黄河流域为历史坐标,试图从多个角度揭示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价值内核,以期对当下黄河文化之价值观塑造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历史坐标
钟磬之乐中的磬由石头磨制而成,“磬,乐石也”。新石器时代的石磬为单件特磬,均发现于黄河流域地区,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山西闻喜县出土的特磬、河南禹州阎砦墓葬出土的石磬,均体现了龙山文化时期高超的乐器制作水平。河南偃师二里头第三期文化层出土的夏代特磬,由成组编磬代替单件特磬,打磨技艺更进一步。河南安阳殷墟一坑出土的3件一组编磬以及殷墟西区93号墓出土的5件一组编磬,磬的制作水平、形制和音乐性能都发生了重大改进。至周代,编磬在形制、工艺、数量、规格等方面日臻成熟,如陕西扶风县出土的西周中晚期15件一组编磬、山西曲沃县曲村晋侯八号墓出土的东周时期10件一组编磬、洛阳市解放路北段东周陪葬坑出土的23件一组编磬、山东济南长清区仙人台5号墓出土的春秋早期14件一组编磬等。“从大量的出土实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在制作上已经完全成熟,造型规范合理,编列完整,音阶齐全,音色、音准和制作工艺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成为当时重要的旋律乐器。”
编钟之出现可追溯至商代晚期的编铙,黄河流域出土的编铙多为大、中、小三件为一组。西周初年,出现了三件一组的编甬钟,随后扩展到3至16枚为一组,如春秋时期的晋侯苏编钟(16枚)。西周后期开始出现三件一组的编镈钟,如河南新郑市李家楼墓出土的春秋中期4件一组编镈钟、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的春秋时期19件编镈钟等。纽钟出现于西周晚期,如山西闻喜县上郭村210墓出土的9枚一组编纽钟,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如山东济南长清区仙人台6号墓出土的春秋早期9件一组编纽钟。西周时期,编钟编磬已经由节奏乐器演化为旋律乐器,钟也由植鸣演变成为悬鸣。在周代的礼乐制度中,乐悬之制中的编钟主要包括纽钟、甬钟和镈钟,编钟数量的增多使其音域不断扩展,基本涵盖高、中、低音区,尤其是甬钟的“一钟双音”技术大大促进了乐音的丰富多样性,为演奏复杂的旋律创造了坚实条件。
从考古发现来看,黄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以钟磬组合为主体的乐器群。如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了9套编钟共计206枚,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有编钟、编镈、钲、编磬,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有编钟、编镈、编磬等。钟磬在宫廷礼乐体系当中被视为乐队之首,音色浑厚悠长,极具立体空间感,“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
春秋战国时期,钟磬之乐由仪式功能为主转为娱乐功能为主,编制越来越庞大,数量越来越多,如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王孙诰编钟(26枚)、河南叶县旧县4号墓编钟(37枚)、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编钟(65枚)等。秦汉时期,“钟磬之乐”逐渐衰落,但在魏晋时期的“清商乐”中仍然极具代表性。即使到了隋唐时期,钟磬之乐在隋唐“九部乐”“十部乐”中依然保留,“钟磬”组合存在于其中的“国伎”和“清商伎”中,但已由“主奏乐器”演变成为“色彩乐器”。至宋代,宫廷雅乐基本因循以编钟编磬为核心的乐队编制,但逐渐处于伴奏地位,如北宋景德三年的一次郊禋祭礼活动:“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鼓、埙、篪、琴、阮、笙、箫、笛等各两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之乐。”明清时期,戏曲、说唱音乐广泛流行,钟磬只在宫廷雅乐表演中作为主要乐器,延续着其作为礼器、祭器、重器之身份等级标签。
纵观钟磬之乐的历史演变,基本是以黄河流域为时空依托,经历了原始社会与夏商的滥觞,西周的繁盛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顶峰,秦汉魏晋唐宋明清的延续,一脉相承。钟磬之乐蕴含的“形而上”的历史文化价值超越了“形而下”之乐器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反映了彼时主流社会的政治理想、文化观念和美学思想的更迭。
二、黄河流域钟磬之乐价值辨析
以黄河流域为地理标识的钟磬之乐,在“乐”之范畴经历了从宫廷之乐到世俗之乐的角色转变,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其价值内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被不断解读。
首先是以巨为美的审美价值。先秦时期,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审美价值在于“以巨为美”,《吕氏春秋》记载:“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钟磬之乐最大特色在于乐音稀疏、节奏简洁、速度舒缓,并且拥有辉煌丰满的金石之声,这种基于金石之声的音乐风格构建起华夏民族初步的音乐话语体系,奠定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基本审美品格和评价标准。春秋战国时期,审美风尚发生改变,正统的宫廷雅乐受到“郑声”的冲击,源自中原大地的郑卫之音带给人们新的审美认知,促使钟磬之乐受到民间音乐影响,“以巨为美”的审美观念更加突出娱乐功能和审美色彩。期间涌现的“美”与“善”“雅乐”与“郑乐”“礼乐”“中和”等美学范畴及“乐而不淫、哀而不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大音希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等审美主张,均是这一观念不断深化、持续发酵的结果。
其次是差序化的政治价值。礼乐制度严格规定了不同阶层在礼乐配享、乐悬、舞队、场合等方面的使用内容,“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用于区分各阶层的身份地位,不得僭越享用。钟磬之乐的政治价值在于“差序化”,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贵族,拥有的乐器数量就越多,如《左传·隐公五年》中有“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的记载。这种差序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古代皇权政治宣传和道德教化的重要选择,客观上起到了强化钟磬之乐政治功能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具有突出的政治伦理意义。
再次是致中和的文化价值。中和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原生智慧,它既是一种政治准则和道德伦理,也沉淀为一种文化精神贯穿于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致中和”,源出《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历代统治者大多强调“中和”的礼乐规范,钟磬之乐在规制、组合、曲目、演奏、风格等方面无不体现出这种思想,因此相继出现了“乐教”“诗教”“淡”“节”“度”等音乐观,凭借其典雅内敛的文化品格营造“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的境界,增进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同感,达到统治有序、天下大治的效果。
最后是伦理化的社会价值。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核心社会价值在于“伦理化”,《礼记·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钟磬之乐通过民间祭祀神灵或先祖、典礼与仪式等场合,配合地方性礼制规仪的程序特点与要求,对民众产生定向性教化影响。秦汉以后,“礼”和“乐”的思想在大众生活中日渐普及,作为感化、引导手段对人们的行为和内心情感进行规范和调节,达至“和人心、厚风俗”的状态,与统治者“政”“刑”等统治工具一起并用,促进文化大系统与文化小系统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协同一致,共同实现国家治理和天下太平。
三、乐以向德:黄河流域钟磬之乐的价值主脉
如前所述,以黄河流域为坐标,钟磬之乐经历了原始社会萌芽、夏商周时期发展、春秋战国走向巅峰、秦汉以后延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价值和使命,但其核心都是围绕“德”这一主流价值展开。周代“以德治国”,“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关于“乐”与“德”之关系,《乐记》强调“乐者,所以象德”,将“德”置于作品艺术性、创编技巧性、乐伎表演性的前位,同时强调“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将审美与尚德统一在具体作品中,这是对儒家“尽善尽美”艺术观的回应和总结。具体到黄河流域钟磬之乐,其价值主脉概以言之就是乐以向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始社会钟磬乐之德——天德。钟磬之声在上古时期已经萌芽,《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时期的祭祀乐舞“葛天氏之乐”,共分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表明以钟磬之乐来表现对“天常”“帝功”的歌颂和崇拜非常盛行。《黄帝内传》载:“玄女请帝铸钲铙,以拟雹击之声,今铜锣其遗事也。”上古时期的器乐已经有了鼓、铙、钲、磬、角等,金石类乐器占据重要地位。钟磬之乐配合乐章、乐舞表演,表达了上古时期人们对“天德”或“帝德”的赞颂。
第二,夏商周钟磬乐之德——祖德。夏禹之后,人们对自然之神的膜拜逐渐转为对祖先的崇拜,“德”的内涵发生了转变,人们把贤良圣君作为推崇对象。禹治水成功之后命皋陶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乃成乐舞《大夏》;殷汤平定夏桀之后,命伊尹作乐“以见其善”,乃成《大濩》;周文王尊于天下,周公旦作歌诗“以绳文王之德”,武王继位复命周公作《大武》以纪念之。成王平定殷民叛乱之后,“乃为《三象》,以嘉其德”。不难看出,自禹之后或者说世袭制兴起之后,“乐德”之内涵逐渐由“天德”转化为“君德”“祖德”,甚至是“己德”,意在彰显先祖的无限功德、丰功伟绩,“乐”由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上之乐下移为更具现实色彩的世俗之乐。
第三,春秋战国钟磬乐之德——君子之德。春秋战国时期,“乐”所颂扬的对象由祖德向人德转变,即褒扬“君子之德”。无论是晋国大夫魏绛的“乐以安德”,还是晋平公时师旷的乐以“耀德”“风德”,都开始探索“乐”对人的品性塑造和品德养成的作用。金石之乐因有助于“人德”之修为而得到重视,“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因此,钟磬之乐承担着“道”之以“德”的重任,君子在钟鼓磬管的洋洋乐奏中,领悟到“乐德”之真谛,“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铿锵有力的钟磬鼓鼙之音散播的是礼乐德音。
第四,秦汉以后钟磬乐之德——社会礼治道德。秦汉时国家实现大一统,儒家礼乐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乐”的基本内涵围绕儒家思想展开,礼即是德,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秦汉之后,随着礼制下移,“乐”的德行功能由上层集团延伸至整个社会阶层,孔子所谓的“成于乐”侧重人性培养和健全,在这一时期益发彰显了“礼乐一体”的社会属性。随之,钟磬之乐由宫廷扩展至乡俗礼仪(“吉礼、嘉礼、凶礼”的庶民化,冠婚丧祭等)、文庙祭孔、民间祭祀、节日盛典等地方性典礼场合。例如,祭孔乐器中,编钟编磬占据核心地位,多为16枚一套,再配以鼓、琴、柷、敔等乐器。祭孔歌乐与乐队伴奏的配合方式是:“凡每章八句,凡每句之先,击编钟一声,以开一句之始。凡一句将末,按谱击编磬一声,以收一句之韵。”“凡唱每曲之终,按谱击特磬,按谱击特磬一声,以收一曲之韵。”钟磬之乐的影响方式是潜移默化的,“诗、舞、乐”三位一体的表演方式营造着肃穆庄重的气场,对于地方各阶层来说极易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应和情感共鸣,形成极强的现场参与感,达到天人相谐、上下融通的效果。礼治思想通过钟磬之乐加以感性呈现,从社会顶层的士族阶层流传至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在耳濡目染、口口相传中将枯燥的礼转化为悦耳的乐,为人们所接受、认同、践行。
四、黄河流域钟磬之乐价值主脉对后世的影响
以黄河流域为历史坐标,围绕“德”这一价值内核,钟磬之乐塑造了中国人敬天畏神、认祖归宗、平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仁者爱人、谦恭礼让、以和为贵的道德标准,修身克己、慎独自律、为人君子的个人之道,深刻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1.
作为中国原生性乐器,以钟磬之乐为代表的中国古乐伴随着传统文化发展壮大最终走向辉煌,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源头活水,无论后世音乐文化如何变化,都是围绕“乐以向德”的价值主脉展开和延续,为后世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秦汉时期的乐府,通过采风观风俗、知得失、治天下,“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钟磬之乐充分发挥其优势,通过仪式性表演强化君主治国的神圣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钟磬之乐在相和大曲、清商乐等宫廷礼乐中焕发新的生机,以德抚人心,以德安百姓。至唐朝,钟磬之乐是整个宫廷音乐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雅乐作品如《上元乐》《大定乐》《龙池乐》《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等,无不采用钟磬之声彰显帝王功德。宋代,礼仪音乐既强调外部的礼仪规范,又注重其内在的审美以及情感的抒发,钟磬之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乐以向德”的社会属性得以彰显和推广。明清时期,民间音乐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民间歌舞、小曲、说唱音乐和戏曲等音乐种类丰富,源源不断地为钟磬之乐提供素材和灵感,二者相辅相成,一起强化着华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世音乐沿袭着钟磬之乐的价值主脉蜿蜒前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音乐发展脉络和路径,造就了中国人所独有的音乐品味,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灵与魂,延绵至今。
2.
从钟磬之乐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钟磬之乐之兴起与先秦文明的形成发展脉络高度吻合。先秦时期,以黄河流域为脉络、以夏商周为标志,形成了中华民族崇礼尚德、刚健有为的精神信仰,确立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从秦汉至明清,随着钟磬之乐的发展,这一价值主脉不断延伸,内涵不断丰富。钟磬之乐主要在祭祀、朝会或新帝登基等重大场合出现,以其宏大的演奏效果昭告于天,引发先民处理人与天、神灵关系时的价值观思考,诞生了敬畏自然、和谐统一的文化思想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由此,钟磬之乐成为后世子孙隔世传音、昭告祖先的桥梁和纽带,形成了中华民族以血脉为纽带认祖归宗的民族意识和价值认同。钟磬之乐承载的精神价值,奠定了中国人修身为本的修养理念,“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钟磬之乐所彰显的君子之德完善自身,塑造君子人格,形成了人人渴望成君子做圣贤的社会风气。随着钟磬之乐的普及,社会礼仪道德得到了最高限度的传播和彰显,千百年来如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内化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独特文化秉性。
结 语
钟磬之乐在数千年之前于黄河流域形成,“乐以向德”思想形成于黄河流域,历代宫廷雅乐一直遵循着“礼乐,德之则也”的用乐传统,强调“礼”和“乐”是修炼提升德性的核心准则,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核心基因之一。时至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沿黄各地出土的编钟编磬,领略到古代宫廷钟磬之乐的朔声遗韵。而从历代文献记载的雅颂之辞中,可以回想古代钟磬之乐的宏大场景及其带给时人的心灵震撼。
①本文所指的钟磬之乐,是指以编钟、编磬为核心,包含了鼓、竽、琴、瑟、笛等丝竹管弦打击乐器的金石之声,在先秦、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制度中,钟磬之乐占有核心地位。黄翔鹏在《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较之琴瑟丝竹之乐,钟磬之乐被统治者赋予了更多的仪式规范和宣教祭祀等功效,在乐悬制度中被固化为象征等级身份的国之礼器、祭器、重器,在此后历代宫廷用乐中一直作为标准配置使用。参见黄鹤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3期。②如黄鹤鹏:《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音乐研究》1981年第3期;王子初:《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钟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之二》,《中国音乐学》(季刊)2007年第1期;方建军:《商周乐器地理分布与音乐文化分区探讨》,《中国音乐》(季刊)2006年第2期;项阳:《礼乐制度滥觞阶段之孕育与成型分期探研》,《中国音乐学》(季刊)2021年第3期;曹贞华:《西周至唐宫廷雅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9年。③本文所谓的“金石之声”侧重于从音响音色的视角进行审视,钟磬之乐突出编钟编磬在礼乐活动中的文化意义,二者在礼乐范畴内的内涵与外延基本等同,只在叙述时因角度、立场、方法等不同而有不同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