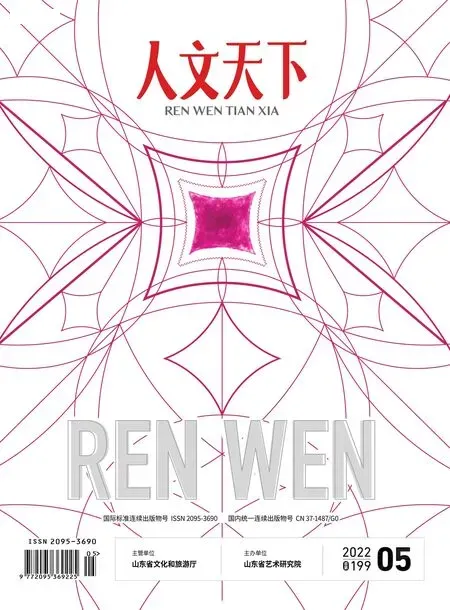老子“常变”思想发微
郝二伟
“常”与“变”作为中国哲学中一对重要的对偶范畴,很早就出现在各种典籍中。春秋战国之际,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都处于剧烈变革中,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一方面,三代以来一直传承的等级传统、天命观念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现实的变革真实且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日益动摇着传统的观念。于是,代表着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的思想家们试图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日益严峻的各种社会问题加以解释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而常变观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老子关于常变的讨论由于其逻辑缜密、内涵丰富、范围广博,尤其值得后人反复推敲、借鉴。本文将以《老子》为底本,试图从宇宙观、人性论、治国思想等几个向度展开论述老子的常变观。
一、《老子》中的“常变”观及研究概况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老子以史官的视角提出“常”与“变”的概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下,原有的宗族势力、传承千年的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逐渐失去效用,而人们仍以之为处世准则,自然不免与现实发生抵触。于是,人们希望在变革中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以此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而老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矛盾和社会需要。
在《老子》中,“常”总是与道、德、有、无之类的核心概念紧密联系,如常道、常德、常无、常有等。另外,通行本《老子》八十一章中共有十八章、二十九次提到“常”,尽管这些“常”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老子》中虽未明确出现“变”字,却几乎通篇在言“变”与“常”之对照关系。老子认为万物无一不在变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无一不在言“变”。另有多处亦明确表现出常变思想,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强调世间万物流变不息,万物皆无“常”,因之以见观“变”之意。面对随处可见的变动,老子并未一味守旧、躲避,而是不断对当时现象界的各种变化进行反思,敏锐地把握住“变”这一万物之基本规律,继而发现“在现象界无一不变,无一可以长久,亦即无一是安全之道”,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从现象界中不断向上追溯至宇宙界,发现在万物初始之处有一个“变中之不变”者,最终将之总结为“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可见,虽未直接出现“变”字,但老子显然意识并总结出了关于“常”与“变”的内涵和基本定义。
关于“常变”这对哲学范畴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常变范畴主要以天、道、理、气等各种独立实体概念的中介形式出现,其本身虽非独立的实体,但正是“由于这些中介,才构成整体结构系统”;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老子思想的起源正是对“常变”这对概念的关照;也有学者从知识体系的角度认为老子思想的来源之一是老子作为文化贵族对世道崩坏的反思;张岱年则指出“常即变中之不变之义,而变自身也是一常”,并认为常的观念始由老子而发。
综合来看,前人对于老子常变思想的研究还不全面,因此,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将这一对范畴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其宇宙观、人性论和政治观等几个方面。
二、老子宇宙观中的“常”与“变”
(一)道体之“常”与“变”
关于道体,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生”,故而道并非万物之一。万物处于永不止息的变化过程中,而惟有道不生不灭,“周行而不殆”。即惟道为“常”而万物皆处于“变”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老子构建的“道”虽然是“恒常”之道,但这里的“恒常”并非一成不变、僵硬死板之意,而是“常有常无”“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之常;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变者在之“常”,因此才既说“独立不改”,又说“周行而不殆”。“道”作为一种形而上之实存者,具有对立统一的两面性:一方面,永恒存在(不像万物一样有生有灭);另一方面,这种“常”(永恒存在)并非完全僵死不变,而是处于不断运动过程中。
(二)道物关系之“常”与“变”
关于道与万物之关系,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变”之万物皆由“常”道而生,于是常与变就为道与万物(包括人)建立起一层逻辑关系,使之成为二者间能够相互沟通的纽带——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常)以显示道(常住性),万物不断变动(变)以反映道(变动性)。为了进一步说明道物之常变关系,老子进一步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道就是万物之所以生成、发展的根据、总规律。劳思光指出,“万物万象皆变逝无常,唯道超万物而为常”,这也就解释了道为何能生万物但不属于万物之一。因为万物作为有形之实体始终处于变化当中,而道则由于无形无象因而能够“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即道本身是永恒的实存,不会随着万物的生灭变化而随之变化,而是在“独立”地“周行”,否则,舍此“常道”,万物将何以由生?
为了强调“常”与“变”乃沟通、联系各种实体性概念的桥梁,《老子》反复提及道与万物二者的关系。《庄子·天下》篇讲“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正是为了说明老子的道物关系,即庄子认为老子的贡献在于其揭示出世间普遍存在的“常无”与“常有”的道理,并将恒常不变的“太一”作为根本和宗旨。成玄英认为这里的“太一”正是指大道。万物皆变化不息,若我们承认万物皆来源于一个共同的源头,那么这个源头必然不能是一个具体的“物”,因为若万物之源为一个具体存在的“物”,既为“此物”,则必不能为“彼物”,且“该物”必不能随万物而生灭。然则世间万物皆源于此者,因此这个源头势必不能是一个具体的“物”,且此源头必为“恒常”之存在,这样就建立起了道(常)与万物(变)之间“母”与“子”的逻辑关系。
至此,老子宇宙观中关于“常变”的内涵与关系也就逐渐明晰了:“常”于《老子》中最基本的含义就是道恒常、永久的存在;而“变”则是“非常”,是对“常”的“反动”。老子通过一系列普遍存在、相互作用的抽象概念说明了世间万有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动当中,但决定其变动的根本法则却是恒常的。此外,“常”与“变”二者间的相互关系则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常变交错。对于“常”与“变”二者的先后关系,老子认为,“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在老子思想中,“常”往往与“道”同一,二者似乎须臾不得分离,常就是道,道就是常,“常道”“常德”“常心”“牝常”等语屡屡出现,甚至谓“知常曰明”。依此逻辑,老子虽未明确指出常变之本末,其意已不言自明。王弼本《老子注》也指出,“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将常与无、本结合起来,而将变与有、末结合起来,可谓老子关于常变关系之关键所在。
三、老子人性论中的“常”与“变”
老子关于常变的思想也体现在其人性论方面。由于老子最基本的动机在于为当时剧烈的社会变革找到一个不变的“常”,从而使得个人与社会从混乱、纷杂的情形中重归安宁、和谐。因此,在其建构了一整套以“常道”为核心的宇宙观后,势必要将此推至人生乃至社会。老子在天人时空中深切体验过兼“常”“变”的宇宙之“道”后,再把这个“道”推衍到人生和社会,这种理路是道者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因此,老子才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指万物皆由道而生,同时以“道”之结构、法则、规律发展运行,于是在构建起“道”的一整套知识系统后,向人生、社会推衍成为逻辑之必然。而在人性层面上,“常”与“变”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在“道”与“德”之关系层面。
(一)常道与常德
上述宇宙生成论层面,老子认为道与万物的关系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与“道”并非同一程度之范畴,然而二者之所以产生关系,则是由于有“德”这一中介,之所以称“德”为“道”与万物之中介,是因为老子认为“道”创生宇宙万物的过程,是由无形无相的道向着有形有相的万物下落的过程。形上层面的道下落至万物、作用于人生,便称其为德,即落向经验界的道就是德。《老子》中,万物的形成过程是“道生之,德畜之”,因而“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王弼认为,道与德的关系是“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即德为道之分化。道乃全者、一者,而万物各有其性,皆因万物仅各得道之一部分,老子称之为“德”,他认为“道”与“德”属于同一程度范畴。因此,万物、人经过德这一中介而与道相统一。或许是因当时其他诸家也流行讲德,老子为与之区别,称之为“玄德”或“常德”。老子之所以强调“玄德”或“常德”,皆为回归其理想世界之人性。也就是说,老子直接提到道,是表现其天道自然观,而一旦提到德,则是由道下落至人生界,即德才是与人生直接相关者。
(二)常德与人性
在老子生活的时代,天下纷乱,人心竞逐于智巧,而他所依仗者,乃常道下落于万物、人生界之常德。老子强调的常德与道同一,乃是混沌未分时的德,是最先活动时分而尚未成形时的德,因此他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与之对应,仁义、智慧、孝慈、礼法等皆为已分化、成形之德,而非他所强调的常德。老子所强调的常德与道同一,都具有混沌、虚无、不随万物、人生灭而恒常存在的特性,但道一旦经德而下落至万物、人生之有形质之物,则此有形质之物就与无形无象之道、德有所不同了,这里恰恰体现了道、德之常与万物之变。比如,道、德的特征是朴,人之本体道、德具体的表现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然而由道经德下落至万物、人生,“朴散则为器”,作为“器”的万物有形质,人有口、鼻、耳、目,各有其性,于是产生了色、音、味等欲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体现了作为本体的“道”“德”与作为“器”的人、万物之间常与变的辩证统一关系。
1.人性之“反常”(变)
对于口、鼻、耳、目等人性欲望,老子专门进行了区别。一方面,老子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一些不符合道、德之常的因素,即“反常”因素,比如由于口鼻耳目而生出的五色、五音、五味等欲望;比如形质之心所生出的贪婪、贪心、贪念等“知”。而这些对道、德之“反常”会让人陷入无穷无尽的追逐中,从而越来越远离原来的德。老子的解决办法是希望人们能够“各归其根”,即由德之“反常”重新回归到德之“正常”状态。“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就像婴儿那样既具有人之灵性却又处于善恶美丑尚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然而老子也看到现实中的人性离德之常终究太远,究竟如何才能使与“常德”渐行渐远的人性回归,老子给出了具体的措施:首先是“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不争”“使民不为盗”“使民心不乱”;其次,还需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将“圣智”“仁义”“巧利”这些为常人趋之若鹜者统统去除,如此才能“民利百倍”“民复孝慈”“盗贼无有”。在老子看来,只有如此才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无知无欲”,“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2.人性之“正常”
老子认为,即便在道之常经德下落至万物后,人性中依然存在许多与道、德之常相“玄同”、契合者。例如腹、骨等基本需要,老子认为就是与德之常相契合者,因此他在“虚其心”“弱其志”的同时还要强调“实其腹”“强其骨”。每个人的生存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资料,只有这两方面都得到满足,人才能生存下去。然而一旦超出生存的度,就落到“心”“知”“欲”这些“反常”的窠臼中,“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就是说,要人们去掉“心”“知”“欲”这些德之“反常”者而取其常。由此可见,老子认为“腹”“骨”这些人性之“常”与“心”“知”“欲”等人性之“变”间存在一股内在张力。
老子认为,人的本性中这种“反常”使得人们在获得了自己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以后却仍想占有更多,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这恰是人性中“反常”的结果。“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这里,老子似乎也无奈地承认并非人人都能抑制贪念,或许只有复归“常道”的圣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还给出具体的做法,即知足,他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知足之足,常足矣”,否则“必大费”“必厚亡”,甚至“不得其死”。
四、老子政治观中的“常”与“变”
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在宇宙论、人生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如陈鼓应所言,老子学说的整套系统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事实上,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在于建立一套形上学以迎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既然自然界万事万物皆处于常中有变、变中有常之中,那么同样受道支配的人类社会、侯王政治自然也居常变范围之中。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傅奕、范应元等人皆认为这句话说明老子思想中王(人)与道、天、地是并列的,事实上,老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体虚无之道,以为人君之道”,由君主(王)向德(常)的复归来引导民众向德的复归,即由“变”向“常”的复归。这些角度都反映出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常变因素。
(一)侯王政治之“常”与“变”
老子认为,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侯王,其自身必须首先复归于道、与道玄同。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灵,神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里的“一”正是指恒常之道。天、地得道(执常)而清澈明净、厚重安宁,万物凭借道得以生成,侯王也正是凭借此常道才能让天下宁定祥和,执一以驭众,以恒常之道驭不断变化之万物。此外,老子唯恐侯王“化而欲作”,因此还要“镇之以无名之朴”。他明确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希望侯王能够“守之”,这样“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正”。然而对于侯王远离常道、常德的“欲作”倾向,老子显然并不放心,于是再次规劝:“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侯王要想治理天下,自身首先需要从远离常道、常德之“变”(欲作)复归至道、德之“常”(清、静、朴)。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老子强调“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即老子认为无为、贵静、守常则天下自正。
(二)“常”“变”之平衡
老子立说的动机在于缓和人类社会中各种剧烈的冲突,而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统治者任意妄为。因此,老子认为侯王在修身方面保持一种常住性与变动性的平衡非常关键,他尤其重视知足,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唯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才可以长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只有认识到道的常住性与治国理政中人事的变动性之“和”才算“知常”,只有认识到常道的人才算得上“明”。如果不顾二者的平衡关系肆意妄为,则会“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即不合乎常变平衡之道之事会早早灭亡。老子举例说,为满足统治者一己之私而加征的苛捐杂税导致民之饥,对于这种远离道、德的“反常”,老子犀利警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三)“常”“变”之对立统一
老子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常”与“变”既对立又统一。他意识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立转化现象,万物变动不息,“万物并作”“众人熙熙”。世间万物虽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即变不失常、变中有常,这一“常”即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过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由此,老子将这种普遍存在的常变对立统一关系体现至治国理政中,提醒侯王必须认识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认为事物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在提醒侯王要防微杜渐,在百姓的不满、祸患尚处于萌芽阶段时就及时处理,“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而且要慎终如始,不然就会“常于几成而败之”。
(四)“愚民”与“常”“变”
在治理民众过程中,老子的具体做法是“愚民”,这也是千百年来老子思想中争议极大的部分,许多人认为老子是要实行愚民政策。通行本《老子》中共有三章出现“愚”字,然而结合上下文可知,其中两处“愚”皆是在说道、德本源混沌之朴、之常。例如,第二十章中“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此处之“愚”,早在王弼时就被认为绝非是“愚蠢”之“愚”,而是“绝愚之人,心无所别析,意无所美恶”之意。现代学者陈鼓应认为,这里的“‘愚’是一种淳朴、真质的状态。老子自己以‘愚人’为最高修养的生活境界”。事实上,老子自己将“愚人”作为理想的生活境界,也以此作为百姓的理想境界。老子的“愚民”是把修之于自身之德推之于百姓,而这也正表明老子视百姓如自己,绝无轻视、愚弄百姓之意。《老子》第六十五章提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王弼、河上公都认为此处的“愚”是指质朴不伪诈,陈鼓应也认为这里的“愚”指的是淳朴、朴质之意。事实上,这里的“将以愚之”并非要实行愚民政策,而是因为老子看见当时社会中智伪巧诈这些远离道、德之常的风气风行一时,君主、民众都迷失在诈伪之变中而不可自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使得远离道德之“常”的“变”复归于“常”,这才倡导“愚”。不仅侯王要复归于“愚”,百姓也要复归于“愚”。其实这正是老子以常变对立统一思维解决社会、政治中层出不穷的各种纷争、冲突的具体方式,而非要求君主对民众实行愚民政策。
老子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其政治学说和主张,其中围绕道、德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常变关系无疑是其核心内容,而“常”与“变”这一对概念也成为沟通老子最高范畴“道”与现实人生、政治之间的中介和桥梁。
结语
综上,可以看到老子思想的脉络正是以常变对待统一观念为核心,为迎合人生、社会之“变”而追溯至宇宙自然之“常”,进而下落至人生及社会治理等各个层面。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变动无常,民不聊生,他之所以立足于寻找宇宙最本质的道,其目的仍在于政治与人生,而贯穿其间的正是《老子》中随处可见的“常”与“变”。也正是依循此脉络,老子展开了其由人生至天道、社会政治,最终回归至人生的思想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