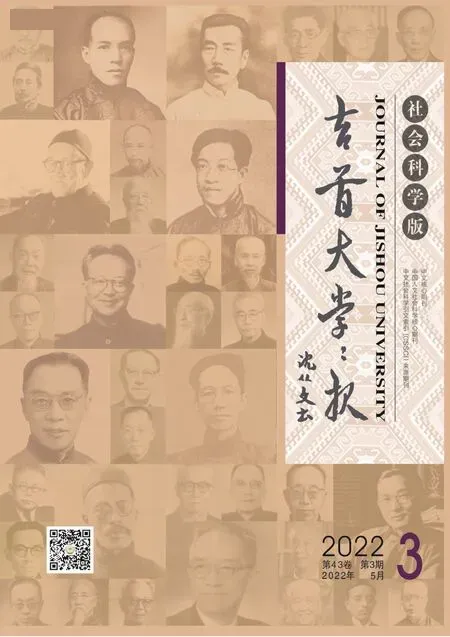从“在场”到“悬置”:鲁迅图像的发生及演变*
任 杰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图像创作受到了政治上的空前重视,被纳入国家政治文化工程,在意识形态建构和民众宣传教育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作为政治认同之媒介的革命领袖肖像画极为流行,而值得注意的是,身为文人的鲁迅,生前并未直接投身革命,自然更非真正的革命家,竟也有了数量众多的“造像”,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鲁迅图式”[1],以至于渗透进了彼时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显然,将这些鲁迅图像视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一面镜子”[2]是远远不够的,在《“鲁迅图式”的生成机制与表意逻辑——对20世纪40~70年代鲁迅图像的一种考察》[1]一文中,笔者已经讨论了“图像呈现什么样的鲁迅,鲁迅要如何呈现”的问题,但更为本质的问题则是,鲁迅何以被图像化?鲁迅图像又怎样成为一种文化政治?
实际上,鲁迅在世时,就已经有不少美术家为其创作过肖像画。与之相比,鲁迅身后涌现出的大量鲁迅图像体现出了诸多新质素,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作为图像主角的鲁迅从“在场”变为了“悬置”。通过整体性的历史考察,能够发现鲁迅图像创作经历了一个从私人情感的表达到政治话语之建构的过程,鲁迅图像也由此演变为一种“图像政治”。
一、“在场”的体认:1936年前的鲁迅图像
鲁迅的图像化不是突然出现的现象,而是有着较为深厚的图像传统和并不短暂的观念准备。从宏观层面来说,人物造像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帝王权贵、儒道先贤们的造像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文人也常以造像的形式留影于历史长河之中。事实上,人物肖像画本就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题材。及至晚清,在欧风美雨的激荡和洗礼中,中国文化场域呈现出了迥异于前的样态,以图像为核心的视觉文化开始流行于整个社会。摄影技术的盛行、专门画报的纷纷出现、书籍装帧图画的空前繁荣、油画的大力引进、国画的不断改良等,无不显示着图像正以新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渗透。如论者所言:“(语言)可以指涉一个客体,描写它,联想它的意义,但却不能像图像那样把客体的视觉面貌呈现给我们。词语可以‘引用’,但决不能‘看见’客体。”[3]可以认为,观看图像在晚清以降已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迈向“现代”的主要方式。
作为新文化界的关键人物,鲁迅自己就相当看重图像的功能,认为美术图像“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住”[4],而且图画具有的现实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5]。鲁迅还搜集汉画像,设计书籍封面,出版外国画选,招聚青年画家,宣扬木刻艺术,可以说身体力行地引领、参与了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发生、发展。因之,图像与鲁迅本身就有言说不尽的空间,这也是鲁迅被图像化的重要基础。
鲁迅在世时,留存、收藏了不同美术家创作的七幅鲁迅肖像。这一行为可视为鲁迅体认自我、“自塑”形象的一种方式。其中创作时间最早的鲁迅肖像是1926年应鲁迅本人之请,画家陶元庆根据照片为鲁迅绘制的一幅炭笔素描(图1)。画面中的鲁迅身体微侧,目光柔和而不乏冷峻。整幅画笔触粗粝轻松,明暗对比过渡自然,构图客观冷静,没有运用特别的绘画修辞,描绘出了一个平实朴素、普通平凡,完全没有伟人光环的鲁迅,但却让观者感受到了鲁迅独特的内在气质和精神力量。这幅画像深得鲁迅赞赏:“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6]后来,此画一直悬挂在西三条寓所客厅,足见鲁迅对其喜爱。能获得艺术鉴赏力极高的鲁迅的称许,与陶元庆对鲁迅的无比尊敬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有着莫大的关系。据许钦文的回忆:“元庆画这肖像是用了功夫的:他左手捏着鲁迅先生的照相,右手握着削尖了的木炭,在画架面前站了好几天……”他画肖像,“不只是求片面的象,而是要神似,把鲁迅先生精神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这画面上;而且要表现出大调子的风格来”[7]。鲁迅对这张肖像画相当看重,1927年他到达中山大学任职时,还复印此幅肖像寄赠友人,并在《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副刊上登出此作[8]210-211。

图1 鲁迅半身像 陶元庆 1926年
1932年,年仅17岁的陈光宗为表达对鲁迅的敬仰,创作了一幅鲁迅肖像木刻(图2)。这幅木刻用刀细碎朴拙,构图简洁大方。画中鲁迅微眯双眼,嘴角略浮笑意,面部轮廓柔和轻松,虽然从锯齿般的头发上依然可以窥见他的犀利和冷峻,但画面整体展现出的是他的幽默、和蔼与慈爱。这幅肖像生动感人、朴素真实,是鲁迅生前收藏的七幅木刻肖像之一。

图2 鲁迅造像 陈光宗 1932年
曹白创作于1935年的《鲁迅像》(图3)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幅木刻同样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鲁迅的崇敬。在画面元素设置方面,曹白选取了诸多极具特色的“鲁迅标识”,比如暗夜、吠犬、《呐喊》书影、阿Q、《故乡》月景、军阀等。横亘于整个画面的一支如椽巨笔,则提示画面上的“鲁迅标识”都来自于鲁迅的文学。居于画面中心的鲁迅瘦削憔悴,略显愁容,深邃的眼光直视前方,流露着不屈的意志和悲悯的情怀。画面整体气氛紧张而充满斗争气息,仿佛让观者进入到了那一动荡不安的时代中。1935年举办于上海的全国木刻联合会的流动展览会上,这幅作品在开幕前被国民党当局禁展。次年3月,曹白将此木刻像寄赠鲁迅,鲁迅因被禁事在像旁题字曰:“曹白刻。1935年夏天,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老爷’就指着这张木刻说:‘这不行!’剔去了。”[9]之后鲁迅在致曹白的信中表述了他保存此作的缘由:“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10]由此番通信,曹白开始了与鲁迅亲密的书信往来,受到了鲁迅直接的指导和鼓励。鲁迅还根据曹白自述的他因创作木刻来进行革命斗争而坐牢的材料,在1936年写出了《写于深夜里》。

图3 鲁迅像 曹白 1935年
罗清桢创作于1933年的《鲁迅先生象》(图4)和力群在1936年所刻的《鲁迅像》(图5),皆为鲁迅生前之珍藏,亦颇有代表性。罗作中的鲁迅面部深沉阴暗,与空白背景对比强烈,给人以阴沉冷酷之感。而在力群的刻刀下,鲁迅的面部则为画面高亮处,其相貌光明醒目、正气逼人,冷峻而刚毅。然细察这两幅木刻像,不难发现二者在整体构图、背景设计、刀法运用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了刻画的都是鲁迅正面肖像之外,二者都在背景中设置了书架,只是罗作中的背景书架简洁而不显眼,力群作品的背景设计则丰富了很多,除了书架之外,还添设了镰刀、手握钢笔直刺“叭儿狗”等元素,图像的象征意味更为明显、厚重。而在刀法形式上,两人“多用三角刀,细密阴线和阳线的并用,力求造型准确工整,……是典型的苏联风格”[11]。于此亦可见出,鲁迅1930年代对苏联木刻的译介和宣传,实实在在地对彼时的木刻艺术产生了影响。

图4 鲁迅先生象 罗清桢 1933年

图5 鲁迅像 力群 1936年
实际上,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肖像画创作在文化传统中本身就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到了19世纪照相技术出现之后,肖像画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但其艺术价值仍是照片所难以取代的。“肖像画之所以受到社会的需要,主要的是由于肖像画所负载的人文内涵,而非其笔墨技法所具有的独立的审美价值。”[12]并且,作为一种更有创作自由的艺术形式,肖像画所表达的意涵远较照片丰富,也更具意义的指向性。在鲁迅生前,由于他特殊而崇高的地位,美术家们创作鲁迅图像更多是为了表达对鲁迅的尊敬和仰慕,尽管如曹白的《鲁迅像》这样的鲁迅图像也显示出了一定的政治诉求,但毕竟只是一种私人情感的图像表达,所以颇见创作者的个人风格。总体来看,1936年前的鲁迅图像的表现形式和图像内涵比较多样、自由。原因或许在于,鲁迅本体的“在场”,使得鲁迅图像的创作无法脱离“在场”鲁迅的形象能指与思想内涵。何况这些鲁迅图像基本是鲁迅的友人或学生所创作,这就使其具有了一种“及物”性与“在场”性,而成为“在场”鲁迅的形象侧证而非唯一能指。历时地看来,这些1936年之前的鲁迅图像又事实上为此后的鲁迅图像创作奠定了基础,形诸其上的很多艺术修辞方式也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之后的创作,但显而易见的是,前后所体现的意味迥然有别。
二、视觉的魅惑:被“悬置”的鲁迅与意识形态建构
鲁迅逝世之后,在文化思想战线占据优势的中共逐渐把握住了鲁迅的阐释权,让人们认识、认可“鲁迅”并由此统合民众也成为文化工作的必要任务。早在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就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有的地位。”[13]那么,怎样“认识鲁迅先生”?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和阐释当然是首要方式,但是,其时“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14],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由书籍文字构建的文化空间是封闭的,鲁迅是谁、站在哪边,并不是他们能够轻易理解的问题。
面对着人数众多的“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构建意识形态,实现革命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是延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长段时间内领导人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42年前后,为了改造新文艺,更好地深入和统合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延安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开始了。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5]863文艺在毛泽东看来,本身就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5]848。彼时一个毋须讳辩的事实是,即使经过了大众化运动以及后来持续不断的教育普及活动,具备文字阅读能力的民众仍然相当之少。因此在具体的文艺类型中,图像艺术备受重视,因为“‘革命’是需要特定‘形象’的,‘革命’必须被视觉化才能造成广泛的影响,以达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掌握群众的目的。”[16]在这样的境况下,图像的认知和宣教功能得以不断凸显,而视觉鲁迅就由此被政治力量所召唤出来,成为承担革命任务的具体而又特别的载体。
“就人类的心智而言,人们总觉得视觉再现往往比任何对等的文字阐述更生动、更直接地表达意义。”[17]也就是说,图像实际上比文字更具魅惑性,更易直抵人心。进言之,鲁迅的视觉再现是政治权力再造和利用鲁迅的重要方式,图像化的鲁迅能够以更为直观、形象的方式呈现和表达政治的意涵,更容易在社会中被传播和接受,也就能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如果说,鲁迅在1936年去世之时被赋予了“民族魂”的内涵,那么在后来经由毛泽东等人的论述,鲁迅不仅成为了革命斗士和思想导师,而且也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典范和党的“一个小兵”,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率先锋。这在美术家们创作的鲁迅图像中都有着极为突出的体现。
陈烟桥所作的木刻《善射者鲁迅》(图6)就十分生动地展示了“以笔为箭”的斗士鲁迅,这一颇具艺术巧思的造型,使鲁迅的斗士形象让人过目不忘。赵延年的木刻(图7)中,则以情景再现的方式,运用黑白对比、聚中包围等艺术表现形式,突显了鲁迅的革命性、战斗性,以及在文化界的导师地位。蒋兆和的国画《我做一个小兵》(图8)的题款为:“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展现的则是鲁迅在经过“自我改造”之后成为党的“小兵”的形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的鲁迅图像相当常见,几乎成为了彼时社会文化中的基本部分。自然地,鲁迅图像中充满政治意味的历史表达和情感内涵就随之渗透进社会观念之中。

图6 善射者鲁迅 陈烟桥 1947年

图7 与宋庆龄等至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赵延年 1956年

图8 我做一个小兵 蒋兆和 1956年
说到底,1936年以后,鲁迅图像化的基础还是经由各种论述“重塑”的鲁迅形象。而讨论鲁迅形象的重塑过程,就不能不提到瞿秋白在1933年4月所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应该说,日后对鲁迅不断趋于极端化的政治性论述,其言说策略和立论方式都可以追溯至此。在此篇序言中,被鲁迅引为知己的瞿秋白第一次鲜明而清晰地指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鲁迅是在目睹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象后,“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18]106。更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出发,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18]110作为鲁迅研究史上的经典篇目,这篇序言把鲁迅思想的转变与现实历史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了一起,鲁迅思想的发展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就具有了一种同步性。瞿秋白的鲁迅论奠定了后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对鲁迅的论述基调。经过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党外布尔什维克身份的指认,鲁迅在政治层面上被迅速权威化,而他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更是得到了有力的强调和突显。
新中国成立后,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成为核心政治任务。因为思想“转变”的成功,鲁迅自然地被视作自我改造的榜样。比如,在冯雪峰看来,鲁迅在《野草》中表现出的“作者所感到的空虚和失望,从思想上说,是由个人主义的思想而来的”[19]300。而且《野草》中作者之所以表现出了痛苦和矛盾,是因为他在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个人主义在这里,成为了造成鲁迅思想上痛苦不堪的根源。然而,鲁迅“一贯的人民立场和革命意志,都决定了他非前进一步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可。这就是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为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19]300。如此一来,处于矛盾中的鲁迅正是在“前进一步”,“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投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之后,才顺利克服了自身思想的障碍与局限,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成熟的文艺战士。
与鲁迅研究者的文字阐释不同,美术家们则通过描摹鲁迅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场景,极为直观、显明地表现了鲁迅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转变”。李以泰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图9),图中鲁迅一手执烟,一手按书,静默地站立着,显然,刚刚所读的内容让他既满足又激动,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陷入了深远的思索中。而桌上另一本合着的书的封面则提示鲁迅所读之书正是马克思著作。相比于文字论述,图像的魅惑性更使得观者对画面内容确信不疑,通过此种图像呈现方式,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和他的无产阶级属性不言自明。

图9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 李以泰 1974年
三、政治的诉求:作为纪念形式的鲁迅图像
鲁迅逝世之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鲁迅纪念活动的频繁举办,尤其在逢五、逢十的鲁迅逝世日,纪念活动则更为隆重而盛大。这些纪念活动很多都是以文化界为中心,进而扩展到政治和社会等方面。鲁迅纪念活动经常被此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借用和融合,被赋予了远超“纪念”的意涵,其中,发挥直接效用的是鲁迅图像。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可以说“文化以权力为本位,权力并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介入文化活动,因此文化‘场’或艺术‘场’是他律的存在,受到政治‘场’的直接制约。”[20]鲁迅图像就是“受到政治‘场’直接制约”的一种文化生产。1942年,在鲁迅逝世纪念日这天,《解放日报》刊载了张望所作鲁迅木刻像(图10)。画面整体分为三个部分,居于最醒目位置的是鲁迅肖像:鲁迅侧脸而视,目光深沉,若有所思;嘴唇微启,似要言语;唇髭浓密,发型平顺,展现了他慈祥、冷静的导师风范。画面左边是受过鲁迅支持帮助、与鲁迅有直接联系的艺术社团,分别为一八艺社、野穗木刻社、木铃木刻社、MK木刻研究社、野风画会等。画面下方则是颇具政治意味的三幅小图:其一是无产阶级举旗呐喊向前,显示出不屈的战斗精神;其二是左翼美联诸同志被捕,揭露了时局的黑暗;其三是民

图10 纪念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导师鲁迅先生和左翼美联殉难诸同志 张望 1942年
众欢呼太阳的升起,寓意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虽然此画要表现的是鲁迅在美术上的贡献以及和左翼美联的联系,但画面构图的设置,实际上显示出鲁迅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1949年之后,新生政权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重构和统合,具体策略之一,是把在延安时期就已成为政治符号的鲁迅抬升成为国家符号。“‘在野革命’的鲁迅逐渐变成了‘在朝政治’的鲁迅”[21],相应地,鲁迅纪念活动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同年10月1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稿《京、宁筹备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为鲁迅纪念活动进行了定位:“本月十九日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了筹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鲁迅先生的忌日,十三日下午特邀请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联、全国青联和中共北京市委会等共同商讨纪念办法……会上决定由全国文联邀请各有关单位联合发起成立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筹备会,除将在首都举行盛大纪念会外,并由各学校、工厂自行组织纪念活动……”[22]此外,《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国家级刊物也纷纷刊登与鲁迅相关的纪念文章。
正是1949年10月的鲁迅纪念活动,规定了鲁迅在新中国应该被如何纪念、怎样形象。1951年彭宗岐创作的鲁迅像(图11)就可视为新中国成立伊始鲁迅“合法”的视觉呈现。这幅木刻像中,背景是摆满书籍的书架,提示着鲁迅的文学家身份。画面中的鲁迅表情平静严肃,仿佛在凝神静思,没有严厉冷峻之气,流露着柔和、朴实,以及一丝憨厚。不难看出,如此的构图和意蕴与1930年代的罗清桢、力群的鲁迅木刻像有一脉相承之处。

图11 鲁迅像 彭宗岐 1951年
1956年,中共中央出于对政治形势、经济状况以及知识分子改造等方面的“乐观估计”,在当年5月初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3]。文艺界迎来了“解冻”,呈现出一派“早春天气”。同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鲁迅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隆重的纪念。大会还邀请了亚、欧、美、非、大洋洲的18个国家的作家、学者出席,这“不仅反映出鲁迅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世界文化伟人,而且也是政府借助鲁迅来进行文化外交的一个鲜明体现,充分反映出政府借助鲁迅来联合世界上的左翼文化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文化战线,突破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中国封锁的目的”[24]。这一年的鲁迅纪念活动与其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又加上正值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因此不论是纪念鲁迅也好,政治表态也罢,美术家们纷纷拿起笔来创作鲁迅图像。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这一年的鲁迅图像从主题到形式都各有特点。
譬如彦涵的《鲁迅像》(图12),此画构图简单,色调低沉。图中鲁迅一手支烟,一手拿报,坐在藤椅上目视前方,若有所思,悲悯、慈祥之色尽显。汪刃锋的鲁迅像(图13)则在场景设计方面复杂了许多,画面中墙上挂着的珂勒惠支的著名版画《牺牲》就十分引人注目。这幅版画由鲁迅于1931年为纪念“左联五烈士”介绍进国内,之后广为传播。画中鲁迅手握《申报》,双眸刚从报纸上移开,斜视前方,目光冷峻而严厉,满含愤怒。画面流露出鲁迅的战斗气息,也隐喻了鲁迅在上海时社会形势的动荡多变。

图12 鲁迅像 彦涵 1956年

图13 鲁迅在上海 汪刃锋 1956年
1966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这篇社论充满了相当强烈的战斗气息和革命色彩。社论强调,不仅要发扬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还要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破旧立新。在这篇社论中,鲁迅变成了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25]。由此,鲁迅不但是文化先锋,更可谓其时的政治先锋。有了鲁迅“加持”,十年动荡时期更在文化、思想层面有了相当的合法性。与此同时,鲁迅的文章著作也成为了生产政治口号的资源库。
在波谲云诡、纷乱异常的特殊年代,鲁迅在不断变动的形势下被一次次当作政治运动的“指挥棒”,创作鲁迅图像是其时征用鲁迅的一种绝佳方式。1967年,中央美术学院红大刀集体创作的木刻《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图14)就相当鲜明地展现了鲁迅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这幅木刻中,鲁迅紧锁的眉头和严肃的表情,都体现着他的愤怒和不屈。更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右下方:一支锋利的巨笔无情地刺向了三个洋人,洋人惊恐而怯懦,完全无法招架。毫无疑问,这是对其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极端仇视”[25]的绝命回击,又加上是集体创作,其蕴含的政治意味可想而知。

图14 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红大刀集体创作 1967年
黄新波创作的《心事浩茫连广宇》(图15)亦颇见匠心。此作中鲁迅占据了画面空间的大部分,他形貌伟岸,面容刚毅,精神之父般地朝向前方。左上角大放光芒的五角星明示了鲁迅的立场归属;幻化为枪的毛笔则牵引着胜利的旗帜,带领鲁迅身后无数的革命志士向前冲锋,寓意要把鲁迅的战斗精神发扬在当下的革命中。这幅木刻将鲁迅的导师地位、战斗性以及无产阶级属性都融合在了一起,堪称彼时视觉鲁迅的经典表达。

图15 心事浩茫连广宇 黄新波 1972年
1976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此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人民日报》特发了《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的社论,这无疑具有特别意义。文章指出“革命无止境”,要在斗争中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鲁迅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去战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26]这一主旨在陈伯坚创作的《奋然前行——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图16)有着清晰的表达。陈作以高悬于天空的巨大人影,点明鲁迅以及他身后青年们是在受着象征共产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的指引下“奋然前行”。与此前众多鲁迅图像相比,这一画作对鲁迅的权威地位的展现一如既往,但不同的是,陈作并没有着力刻画鲁迅的战斗性、革命性,而是呈现了一个手持马列著作的儒雅、稳重而坚定的鲁迅形象,由此特别突出了鲁迅的“前行”,新的政治诉求于此一览无遗。

图16 奋然前行——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陈伯坚 1976年

图17 鲁迅 酆中铁 1937年
从1937年鲁迅被毛泽东正式“引用”开始[27],美术家们创作的鲁迅图像,很多都以纪念鲁迅的名义出现,而与其时的政治运动有着呼应配合的关系。当然,一开始美术家们可能未必会形成此种意识,并且也因为战争环境的紧迫与残酷,政治层面的表达尚未显示出急迫性,因此像酆中铁1937年所作的《鲁迅》就只是以鲁迅编印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为主体内容,仅以作为背景的虚化的珂勒惠支作品表达出一种左翼立场,并无更多的政治意涵。此外,这也与酆中铁当时在重庆而非延安有关。而在1949年之后,在愈发强烈的政治诉求之下,美术家们不断调整表现主题和艺术方式,描摹出形态不同、内涵相近的鲁迅图像。由此,“鲁迅”逐渐游离于历史本体,成为某种政治表征和时代印记。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的被符号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建构,但不能不认识到,鲁迅之所以能够被建构,也有他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的原因。1920年代中后期,由于鲁迅在文化政治上的坚持与实践,比如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事件中激烈的政治批评,让他的影响就远远超出了思想文艺界,[28]他开始被视作“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8]210。此时,他的政治形象就已颇有显现。并且,他留存于世的创作也仍旧在后来发挥着巨大作用,十年动乱期间类似于“毛泽东语录”的“鲁迅语录”即为明证。更进一步可以说,尽管鲁迅的言说在他逝世之后被不断扭曲,但被悬置为肖像的鲁迅,仍然以他的诸多言说而“在场”。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后来在视觉再现中重塑鲁迅的基本要素。
四、结语
“图像的意义不仅在图像本身,而更在于图像的制造者和观照者,以及二者在相关语境中的互动关系”[29],鲁迅图像的发生与演变就是如此。鲁迅“在场”时,鲁迅图像的创作当然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虑,但更多是一种私人间的交谊象征。在后来革命政治主导一切的语境中,美术家们制造的“鲁迅”则颇有现实适用性的考量,堪称一种图像政治。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即使在征用鲁迅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1960—1970年代,鲁迅图像仍然具有“藉形式使接收者从庸常达到超脱的符号文本品格”[30]的艺术性,也就是说,鲁迅图像首先是一种“画”。正因如此,美术家们才能对鲁迅进行一次次的呈现、改写和重塑。毫无疑问,经由这种艺术性的呈现,鲁迅图像在突显和强化鲁迅的某种属性的同时,实际上忽视和遮蔽了鲁迅更为丰富的其他面相。并且由于这种遮蔽,以及与此相伴的对鲁迅的政治性阐释,这一单一而片面的鲁迅,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特定观念上的存在。新时期王富仁等人之所以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所针对的就是这一被固化的鲁迅形象。
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的,记忆本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形式,通过心灵的回忆的“唤起”而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31]。可以说,在“一些记忆”的基础上,美术家们在图像中重建了“另一些记忆”,经由持续地“合法化”和“认同”,形成并固化为广泛的社会记忆[32]。1936年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鲁迅图像的不断生成和调适过程中,鲁迅与革命、政治的关系被有意重新勾连,并进一步深化乃至重建了某种历史联系。本质上,这是政治引导下的集体“想象”,想象当有了具体的依据和指向时,便从抽象层面落实为广泛的社会认识,并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也因此,这样重现的历史与记忆影响深远。而在祛魅和解构早已成常态的当下,曾经是“三家五最”的鲁迅被拉下“神坛”的同时,却又被推向另一个极端。譬如,1949年后出现的某些经典鲁迅图像在网络世界的戏谑和“恶搞”中,竟于无意间成为了“鲁迅还在”[33]的反向表达,其间所体现的张力与矛盾,在说明时代观念变化之巨大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关于鲁迅本身之丰富与复杂的即时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