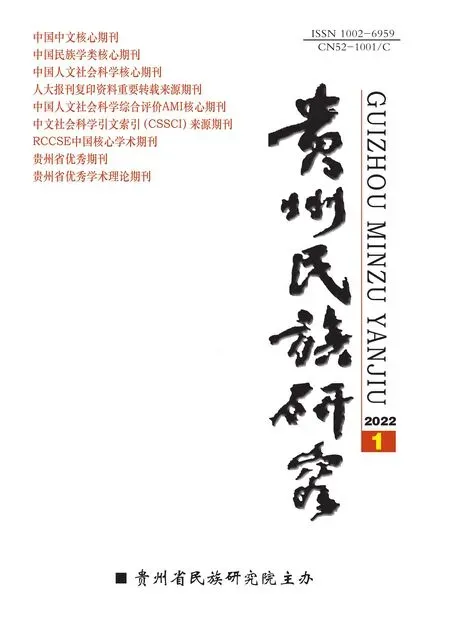乡村社会转型中仪式的展演与社会记忆的建构
——基于对大理萂村“接天子”仪式的调查
董继梅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昆明650031;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学院,云南·昆明650504)
一、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乡村社会
记忆的社会性研究肇始于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有其社会建构性,是由社会和道德维持的,既立足现在,又重构过去。保罗·康纳顿不仅看到了记忆的当下性,还强调了记忆的连续性,并阐释了社会记忆的运行机制。人们通过仪式的操演和身体的实践,传播和保持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基于历史的社会记忆体验现在。然而,社会记忆具有重构性,记忆不断地经历着重构,不仅重构过去,还组织当下和未来的经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路径,其理论在21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
近20年来,国内有关社会记忆个案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记忆的客观性,一定程度忽略了记忆的主体性。而个案考察则重在将仪式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身体实践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西北、闽南、广西、贵州等地,云南的个案研究较少。
对于云南这一少数民族众多的边疆省份来说,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探讨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承机制,研究仪式操演的实践记忆对凝聚乡村社会群体和社会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间的信仰和仪式常常相当稳定地保存着在其演变过程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内容,更深刻地反映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仪式的展演与实践记忆是过去与现在的承接和碰撞,村民们在仪式的操演中,不断地调整社会记忆,以寻求自身存在的真实感。笔者曾于2017—2019年间多次长时段到云南大理萂(wō)村进行调查。萂村位于洱海东岸区域,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白族传统村落。作为行政村的萂村下辖8个自然村,有居民1722户,总人口6174人,其中90%为白族人口。
在调查过程中,村民们常常提及“接佛”活动,尤其是春节期间,更是将“接佛”活动作为家庭安排及亲友交往活动中最重要的事情来对待。“接佛”活动事实上是白族本主崇拜的仪式实践。本主崇拜是白族人民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起始于南诏时期。大理地区在本主节、春节、神诞等节日庆典中,有将本主神、天子神、老太神等神祇接到村中巡游,并在村中的庙宇里过节的习俗,通称为“接佛”。“接佛”意即“接神”,抬神到村中巡游。这里的“佛”并非单指佛教神灵,而是所有宗教神灵的通称。
萂村有着历史悠久的“接佛”传统,萂村人同样把所有迎送神的活动统称为“接佛”。在萂村,最重要的“接佛”活动便是每年正月初十至十五日天子节期间举行的“接天子”仪式活动,被村民称作“过大年”。天子节期间,各村轮流迎送赵善政神像、杨干贞神像、老太神像、本主神像到村中庙宇和村民一起过年,场面盛大,参与人数多达四五千人。这一仪式活动的空间边界覆盖了萂村行政村的主体村落,由几个村之间进行轮值,各村之间既有合作亦有分工。在对这一仪式活动观察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接天子”仪式的展演不仅呈现了萂村的现在,还承接了过去,并不断地重构村落的历史。“接天子”仪式的展演,是村落社会记忆的实践,组织着当下的村落秩序,塑造了村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激发了村民的群体认同感,对村落群体起到凝聚的作用,并指向村落的未来。
二、作为本土知识的仪式展演
大理萂村“接天子”仪式是对萂村人心目中的一个历史事件的操演,是一个天子在家乡巡游的仪式展演活动,呈现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内容。“接天子”仪式主要迎送的天子神赵善政和杨干贞是南诏时期最后两任国王。杨干贞是萂村人,曾辅佐赵善政当上南诏时期大天兴国国王,后废赵自立为大义宁国国王,给萂村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荣耀。
据传说,两位南诏国国王在位期间给予萂村人特权,为萂村人谋利益。杨干贞在位期间,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至十五回故里过春节,分别在萂头、邑尾、萂中、萂尾、黑家邑等村体察民情,与民同乐。他了解到父老乡亲的生活十分艰难,过完节,回到羊苴咩城数日后,就颁布了一道圣旨:免除萂村徭役和赋税,乘船过洱海免交船费。后人为缅怀和感恩杨干贞的功德,在村中建盖寺庙,雕塑金身,把他回村过节的日期——正月十一至十五作为萂村人民永久性的历史传统节日,举行隆重而独特的“接天子”仪式活动。
“接天子”仪式的展演作为萂村的本土知识,使得萂村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帝王文化,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接天子”仪式活动中,这种村落中的帝王文化通过龙车、万民伞、肃静回避牌、侍卫、卫伍队、表演队所形成的象征体系进行表达。在萂村的庙宇楹联、牌匾以及文献记载中,“庙统垂千古,威灵镇四方”“永镇山川”“南诏宰府”等同样传递着一种家国情怀。并且,在萂村民间流传着大量有关杨干贞、赵善政的神话传说、大本曲等,这些神话传说与仪式都是一种人们借以表达对权利和地位要求的象征语言,使讲述者或参与主体的具体立场正当化。神话和仪式都在回忆历史,重复过去,强化群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聚合性,保证认同知识的再生产。萂村村民在选择、组织和重述神话和操演仪式,也是在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萂村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萂村的历史和维系萂村村落社会。
“接天子”仪式的起源并没有具体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萂村人的口述资料中,“接天子”仪式有着一套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复杂程序,具有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犹如在几个村庄中轮流展演一出规模宏大的戏剧。在萂村,“接天子”仪式活动是全民参与的。每年的正月十一“天子”出门至正月十五“天子”回坛,由邑尾、萂尾、萂中、萂头四村轮流组织迎送。
作为本土知识的“接天子”仪式活动深深影响了萂村人的日常生活,与萂村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交织。在仪式活动中,所体现的民间信仰文化杂糅了佛教、道教、本主信仰的宗教文化,呈现了村民对村落历史的认知,对村落历史人物的敬奉,对权力的崇拜与向往,以及村落社会轮值制度、互助制度以及休闲娱乐文化等社会再生产机制。“接天子”仪式强化了萂村的社会记忆,建构并明确了萂村各群体的社会空间界限。各自然村在迎送天子神时,绕村境巡游的过程,再一次明确了各村之间的边界,强化了村民们对群体的认同,构建了萂村的社会秩序,实现了资源配置的竞争与合作。
三、村落社会记忆的建构
萂村“接天子”仪式讲述两位南诏时期的国王回到萂村过春节并巡游村庄的故事,是村民们追溯村落过去的叙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建构了萂村的社会记忆。仪式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让村民们通过参与仪式活动,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国王回乡过年的事件、场景和荣耀这一传说的神圣化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在萂村的“接天子”仪式中,村民们始终会以他们所理解的天子在春节期间回乡过年的场景,迎送天子巡境。仪式中的龙车、万民伞、肃静回避牌、侍卫、卫伍队、表演队,这些象征符号形成了一个象征体系。这一象征体系表述了村民基于现在的生活,而对过去历史记忆的理解。“接天子”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仪式,其展演特征对于塑造萂村村民的群体社会记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年一度的“接天子”仪式操演中,村民通过身体实践,叠加关于萂村与赵善政、杨干贞等“天子”的社会记忆。
当人们在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展演,以此回忆或重述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是在重构这个故事,建构社会认同,强化村民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经验与记忆。仪式的重复性和象征性,表现出社会区分与阶序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述,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现实。仪式中呈现的秩序规则,进一步巩固了在现实生活中资源分配的秩序规则。在萂村,“接天子”仪式被村民们公认为具有千年的历史,但凡具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怀疑这一说法的科学性、严谨性。然而,萂村村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接天子”的仪式活动,在村民心中的象征意义早已超越了真实时间的维度,以致村民们并不怀疑“接天子”仪式的“千年历史”。如果追问村中老人关于“接天子”仪式的来历和变革,他们都会说,这个仪式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并没有任何改变。村民的这种表述说明这一仪式传统在萂村长期存在着,并在村民一年一度的仪式操演中延续下来,得到村民们的普遍认同。“接天子”仪式的重复,意味着延续仪式活动的过去,同时也是延续萂村的过去。
在“接天子”仪式的实践记忆中,实践主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萂村的文化空间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实现参与动机,举行仪式的展演。村民们用语言、文字、物象、仪式行为等,将一幕幕片段的事件与赵善政、杨干贞等历史人物,循着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组织起来,表述关于萂村的社会记忆。村民们将这些象征符号依时间、空间及社会生活逻辑安排到场域之内,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象征符号和文化模式,传递乡村精英们想象和建构的社会记忆,通过人们的言行从而生产、传递和改变着社会记忆。
萂村人常常讲述着关于赵善政、杨干贞与萂村的关系。他们要么说杨干贞和赵善政都是萂村人,要么说赵善政虽然不是萂村人,但与萂村人杨干贞有着姻亲关系,是两老表。萂村人关于赵善政和杨干贞的社会记忆,借由文献、口述、仪式、塑像等媒介,将赵善政、杨干贞作为联系唐代大理古城与萂村这个洱海东岸的小山村的纽带,根据时空与因果关系,讲述神话传说,在萂村坝子保存和流传。在保存和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相关的社会记忆在不断地经历着创造和选择的过程,体现出当代萂村人出于当代的经验,建构有关萂村的过去、神话、传说等过程,也体现出“接天子”仪式中迎送的主神赵善政和杨干贞在萂村人的社会记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萂村的天子庙所供奉的主神是南诏大天兴国国王赵善政。在仪式空间中,赵善政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比供奉在萂尾财神庙中的主神杨干贞高,得到村民更多地认可和崇奉。天子庙的右墙角镶嵌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赵善政天子庙传序》。2012 年,村民们在修缮天子庙时,根据《南诏野史》及相关的传说故事篆刻了碑文,重构了萂村人关于赵善政的社会记忆。据此碑文所记,赵善政与萂村的关系变成了萂村是赵善政的出生地。赵善政的母亲未婚先孕,流落到庙址所在地,生下赵善政。赵善政母子具有善良、诚实的优良品质,后又贵为大天兴国国王。于是,村民为纪念他而在此建庙,并将每年的八月十五定为赵善政的寿诞日,作为会期,并且萂头、邑尾、萂中(含萂尾)等几个村民小组在天子节期间都迎送天子神赵善政。再则,赵善政及其母亲善良、温和的本性也较为符合村民崇奉孝道的价值观,得到村民的颂扬与供奉。事实上,历史上赵善政并不是萂村人,然而,在日常信仰空间中,这一历史事实并不影响村民们对赵善政天子神的敬拜。村民凡碰到大事小事都要祈求赵善政天子神的保佑,尤其是生子、求学、事业等,村民们都要到天子庙烧香磕头,求神保佑,以致供奉赵善政的天子庙香火也较为旺盛。在天子节期间,迎送天子神赵善政的村落和村民数量远远多过迎送天子神杨干贞的村落和村民。
萂村有关杨干贞的神话传说及口述史料是非常丰富的。传说,杨干贞在位时期,在洱海区域给予萂村人很高的地位,为萂村人谋得利益,比如免除一切税收、免除过洱海的船费等福利。免除船费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据82岁的杨大妈回忆,她原本从喜洲嫁到萂村,以前她们去喜洲访亲,都是坐船过洱海,确实免交船费,直到1956年参加合作社时才终止。杨干贞对萂村的功绩也得到了所有村民及外界的认可。在文献与传说的交织和互构中,有关杨干贞的社会历史记忆,借着口述、文字、纪念物等媒介在萂村人中间广泛流传,成为了萂村人的集体记忆。由此,萂村人对建构出来的过去和历史也深信不疑。萂村是杨干贞的故乡这一事实,同样得到了村民和学界的肯定。近代以来,萂村人最集中地建构有关杨干贞的社会记忆有两次,分别在民国末年和2006 年前后。
1947 年,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萂村曾试图修建杨干贞纪念广场和纪念碑,后因新中国成立,政权的更迭,杨干贞纪念广场的修建工作停滞,最终也并未完工。然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云南省监察院简任秘书的丁怀谨作为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的官员和有名的文人,他争取经费责令时任乡长段凤鸣修建杨干贞纪念广场和纪念碑,并撰写碑文《南诏大义宁国杨干贞故里碑记》。这一举动将杨干贞与萂村的联系上升到政治层面,在政治和文化上确认了杨干贞作为萂村历史名人的地位。虽然,杨干贞纪念碑于1956年被拆去修大坝,纪念广场如今只留有断壁残垣,但在村民中间始终没有中断过关于杨干贞的社会记忆,并在后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中,得以扩大和延伸。
萂村在大理洱海区域的白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人们称之为“萂村王者地,白乡古遗风”。自2005年开始申请众多项目和称号的过程中,村民们在镇政府的带动下,或被动或主动地在建构关于杨干贞、关于萂村的社会记忆。2006 年,萂村申报云南省历史文化名村时,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村民们兴建陈列室,书写楹联,创作经文、大本曲、词曲,撰写碑文,编写并出版图书,在新闻媒体上大规模报道和宣传萂村的历史、文化等,通过多种方式建构了关于杨干贞的社会记忆,以此来作为申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旅游扶贫试点村等项目的基础。这一过程又一次大规模重构萂村的社会记忆。而萂村于2006年5 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文化传统保护区,获得大量建设资金的支持。这让村民们感受到萂村传统文化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极大地增强了村民的荣耀感和自信心,刺激了村民对社会记忆的建构欲望,激发了村民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内驱力。
在2006年左右,时任萂村村委会主任的D组织人请剑川的雕刻师傅雕刻了杨干贞的雕像。据说,他们根据专家考证的结果,最终将雕像安放在萂尾村的财神殿侧殿中。因为在萂尾村一直流传着关于杨干贞后花园在萂尾村的传说,也成为当时选择将杨干贞雕像供到萂尾的原因之一。人为造像的物象是传递社会记忆的媒介之一,雕像的存在与我们对过去的记忆相联结,物的“存在”及其“可见性”,不仅唤起了相关记忆,更使得“过去”更加真实,从而进一步强化民众的集体记忆。杨干贞雕像的供奉,一定程度上传递并强化了村民们关于杨干贞的社会记忆,使得传说中杨干贞的形象通过物象的存在变得更加可视化,也使得有关杨干贞的“过去”更加真实。
此后,2007年1月,萂村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4年,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5年,被确定为国家旅游扶贫试点村。萂村先后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文化传统保护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旅游扶贫试点村。这些名头的评选过程,事实上也是社会群体在面对社会生活资源的分享和竞争,对村落历史的集体进行再选择、创造和诠释的过程,从而建构了村落的社会记忆。
萂村陈列室于2013年建立,使得萂村的历史、文化等各种物件得以展出。陈列室中的很多物件都是从村民中间免费收取而来,有刺绣、衣物、农具、字画等。物件的陈列是对萂村白族传统文化的展示,同样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宾川县文管局指导萂村村委会对陈列物件进行选择、安排、展示,这样的行为向村民们传递了国家政权通过政府机构向乡村代理生产的想象和建构的社会记忆。
关于赵善政、杨干贞及“天子节”的社会记忆,在萂村乡村精英们一代又一代持续不断地实践下,不间断地建构着,又再通过仪式活动的展演和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及文章书籍的传播,得以一遍遍地强化。萂村人将杨干贞、赵善政与萂村的时空逻辑相结合,通过仪式、大本曲、天子经、诗词歌赋、楹联、碑文等方式,演绎着关于天子的传说,流传和保存并选择与建构关于天子的社会记忆。通过仪式的展演、碑文、经文、对联、雕像以及纪念广场等方式,将历史记忆和现实理解融合,从而形成相关的社会记忆。村民们甚至会将村中的一些古树、庙宇、房屋、古墓,甚至断壁残垣,都与赵善政、杨干贞等历史人物的一些神话、故事、往事联系在一起。当人们看到这些事物,就会唤起村民们对帝王神话传说与往事的记忆,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相关的神话传说,进一步强化关于帝王的社会记忆,并一代一代地传承这样的社会记忆。帝王文化以及对权力的崇奉也已深深地印入村民心中,成为萂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萂村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凝聚点。
在萂村,无论是“接天子”仪式这一行为,还是在民间流传的各种关于赵善政、杨干贞两位天子的传说故事,事实上都是在言说“王者的荣耀”,以及村民们由此享有的特权。村民们通过一年一度的仪式展演和身体实践,重复着他们所熟悉的传说故事,并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创作”与“再创作”,通过这样的过程,表达自身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体验和理解。记忆是过去与现实沟通、祖先与后人共聚的生活方式。萂村的社会记忆,沟通了这个村落的过去与现实,成为萂村的历史人物与当代村民精神层面交流的生活方式。村民们通过仪式的展演、神话传说的讲述、物象的建造等来承载社会记忆。在仪式的实践中,村民将关于赵善政、杨干贞的社会记忆和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都加诸到“接天子”仪式的具体活动中,用象征的符号表达。村民们通过“接天子”仪式操演的身体实践,借助一系列的象征符号体系,以高度的象征化操演记忆,从而成为群体成员的共同记忆。萂村的“接天子”仪式正是通过规范性程序的操演、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将历史的价值和帝王的文化意义赋予到村民们的全部生活,以致萂村村民们通过身体的记忆习惯性地操演历史,以此表达和保持社会记忆。
四、结语
仪式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仪式的展演也是社会记忆的建构,并在仪式展演和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强化群体认同。大理萂村“接天子”仪式的展演过程体现了浓厚的佛教元素、道教元素和民间信仰元素,以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些象征符号都将一个遥远的白族村落拉到了历史文化的叙事中。人们通过回忆村落的历史,来凝聚和强化本村落的集体记忆,由此来建构村落群体。村民们在仪式的操演过程中,共同完成一项任务,从而巩固了群体认同。社会记忆也得以在仪式的操演过程和实践者的社会互动中得以传递。一年又一年重复的仪式,使得萂村白族乡村社会群体相互关联。
村民们通过“接天子”仪式中共同的象征体系表述社会记忆,建构村民的群体认同。村落的社会记忆塑造了乡村共同体,并通过制度媒介保障其秩序体系的再生产。村落的社会记忆整合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通过记忆与周围的社会环境产生联系,展示了乡村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展望了乡村社会的未来,从而将乡村群体凝聚到一起。社会记忆强化村民的群体认同,村民们通过仪式、神话传说与身体的实践,诠释与重构村落的社会记忆,从而形塑乡村社会秩序,维系乡村社会结构的持续性。仪式激发群体成员的内化集体性与认同感,通过象征符号,激发个体的内生性群体意识,塑造群体的心态,建构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传统社会记忆的活化有利于促进良性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仪式展演与神话叙事的重构,通过身体实践,促进村落群体的认同,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社会记忆在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乡村振兴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良性运作,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的认同。
然而,在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村落的社会记忆有消失的风险,乡村社会秩序面临着新的问题。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正日益遭受严重的破坏,传统村落数量锐减、损毁情况严重,其保护与发展存在诸多困境。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充分,使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出现了乡村社会伦理道德缺失、法治缺失、社会秩序混乱、缺乏监督等乱象,其保护和发展存在不少问题。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中越来越多的青年村民到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务工以谋求发展,使得社会秩序发生了较大转变,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空心化、老龄化以及乡村传统文化和社区认同的弱化等乡村衰落的现象日趋严重。面对这一新的社会转型,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就面临严峻挑战。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是一条艰巨的道路。要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重新认识和发现乡村社会,需要活化乡村社会的记忆,以促进社会秩序的进一切步整合和有序发展。其次,实践主体对社会记忆和仪式展演进行主动调整和革新,进行适应性选择,有利于凝聚乡村社会群体和形塑乡村社会秩序,有利于社会记忆的活化,以实现乡村社会记忆反思性的保存与传承。国家权力通过选择性地积极对待和利用乡村社会记忆,在仪式操演者操演仪式的过程中,引导操演者革新和实践适应新时代的社会记忆。通过有效利用仪式对社会记忆的承载作用,以便有利于更好地保存和延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凝聚村落群体,强化村落群体意识,从而有利于发挥乡村社会记忆形塑社会秩序和维系乡村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以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良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