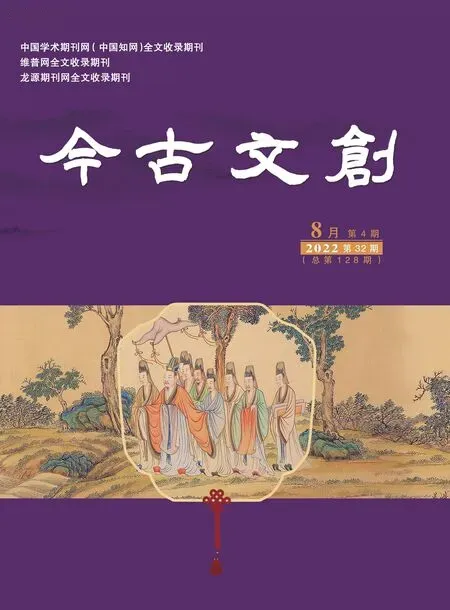龙山县洛塔乡楠竹村丧葬仪式调查研究
◎刘世发 张双秀 黎晓雯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丧葬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没有文字的土家族而言,丧葬仪式便是展现其独特文化精神和底蕴的重要载体。通过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土家族丧葬仪式的特性,从而挖掘其中的教育和文化价值。楠竹村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洛塔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龙山县洛塔乡政府西部12公里处,距县城58公里,共有4个村民小组,总计266户,17800余人。该村海拔1400多米,是一个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落,且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土家族的传统丧葬习俗,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方便。
一、丧葬形式
据史料记载,在改土归流前,土家族先民以火葬为其主要丧葬形式。“改土归流”后,受汉文化影响,除婴孩早夭采用火葬外,均改为土葬。从笔者的调查来看,楠竹村年代较早的墓葬均采用土葬。随着殡葬改革逐渐深入民族地区,龙山县就这一情况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殡葬改革措施,但由于土家族土葬观念历经数百年的沿袭,当地民众入土为安观念早已根深蒂固,除在县城居住的居民和少数因故在城中过世的村民施行火葬外,农村地区的大多数村民仍然延续了土葬这一习俗,但在仪式的主持者、丧葬仪式的时间、花费等方面较以往而言则有了较大的改变。
从仪式的主持者来看,改土归流前,仪式主持人多为僧道,由僧、道负责“讽经”,进行绕棺、做道场等仪式的主持;改土归流后,仪式主持人多为道士,由其负责整个丧葬仪式的主持工作。经过走访调查得知,当地原有的道士已经过世,且没有传承人,因而每次村中有丧事时,都需从邻村中寻找道士主持仪式。
从丧葬活动的持续时间上来看,在改土归流前,仪式持续的时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贫者三日毕,富者数月不等。而当下,村中有人过世时,丧葬活动的持续时间多为两到三日,寻找到合适的日子和时间后即将逝者入葬。当然,也有例外。由于土家族人崇信风水之说,逝者入葬的时间必须与生辰八字相吻合,因而,如若在近期未能找到合适的日子,当地人会将逝者及其棺木停放至家中,直至选到良辰吉日,才将逝者下葬,其中的时间跨度可达半年甚至数年之久。
在丧葬仪式花费上,改土归流前,逝者家属会:命形家择吉穴,费钜值不惜,前二三日,开堂设奠,至亲往奠,以羊豕、肴馔暨挽帐联,余祗香烛,丧家部以帛衣,各有差。即为逝者选定好穴位,在下葬前两三天开设灵堂,亲属前往祭奠,用羊猪作为祭品。现如今,仪式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简化,但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在吉穴的选定,寿衣和棺木的置办以及宴请宾客等方面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而在祭祀所用的牲品、逝者所穿的殓服等方面的要求已较为宽松,经济上的负担较之前也相比更小。
二、丧葬仪式的基本过程
英国学者维克多·特纳曾有一段解释仪式内涵的中肯言辞:“仪式能够在最深的层次揭示价值之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感动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在丧葬文化方面,土家族人“尚鬼”“敬畏鬼神”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已熔铸于丧葬和祭祀仪式之中,后来与巴蜀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最终铸就了土家族特有的丧葬文化习俗。当下,楠竹村土家族丧葬仪式的基本过程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入殓”“停丧”“上山”。下面,笔者将从这三个部分进行梳理和讲述:
(一)“入殓”。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走访调查和资料整理可以得知:在当地有人过世后,均会请道士到家中主持所有的丧葬仪式事物,参与做法的道士一般为五至六人。这与《龙山县志》所记载的:饭僧道供佛,或三日、五日,至葬乃止,曰:“做道场”相一致。
在到达逝者家中后,道士需立即进行灵堂的布置:灵堂前需放置两张桌子,第一张桌子名为:“师台”。用于“请菩萨与天师”。每次施法时,都需烧香和烧纸。第二张桌子名为:“祭台。”台上需放置猪头、酒、水、茶、一升竹筒装的米(用于插香)。在道士布置灵堂之时,老人亲属需跪于床前,将逝者床上蚊帐推开,以“使死者不致在阴间走错路,误入‘枉死城’受罪”。与旧时不同的是,古时在老人除丧后需:焚寓钱送之,或焚纸桥、纸人、纸马,“盖痛死者,虑其徒行也”。即要烧纸钱、纸桥、纸马等物,害怕逝者走不动路。
在逝者过世时,其家属需立即为其擦拭身体并穿好寿衣。穿好寿衣后由道士用白布将老人全身裹住,由众道士一同发力,将逝者移到一张实现准备好的门板之上,这称之为“提尸下柳床”。提尸布为六尺,取六一逢生之意。
完成好“提尸下柳床”这一仪式后,掌坛师傅(即道士)将在逝者的遗体旁边进行做法,当地人称之为:“请神”。在做法时,道士各有分工又相互配合:掌坛的道士负责打鼓和念词,其余道士负责敲锣、吹小号、吹喇叭以及打钹等工作。做法完成后,再由其将逝者放入棺木。放入棺木时需要对棺木进行清尘,在棺木底部放入干净、且用筛子筛好的干灰,用碗盖上一个个的圆形图案。除此之外还需要经过放纸、放灯草、放被子、盖被子等环节,待所有仪式完成后才能真正将逝者放入到棺木之中。
(二)“停丧”。在停丧这一环节主要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盖灯,即在将逝者放入棺木后,道士需进行做法,唱五方科,并为死者盖灯。灯一般为红色与白色,死者若为男性则盖十王灯和苦难灯,为白色,以此纪念死者在生前养育子女的艰辛与困苦;若为女性则盖血湖灯,灯为红色。这象征着女性十月怀胎,生孩不易。
第二个环节是封棺,盖棺的时间多为逝者去世的一天后。在未盖棺前,其子女需为其守灵,为逝者尽孝道,然后由道士作法将棺木上的影子扫去,“将生人的灵魂放还至生者体内,而将死者的灵魂留在棺木内”。封棺时,需家族中的长辈在场,逝者的家属需一一向长辈磕头跪拜,方可用大米和糨糊将棺盖合上,防止抬棺时棺盖脱落以及因天气炎热而散发出臭味。
第三个步骤是择地,择地的时间多为老人过世后的第二天。看风水时,需要根据死者的生辰八字以及山势进行判断和选择。选穴位时也有禁忌,例如不能对着山包,不能对着白岩,不能对着洞等。定好位后,由逝者的子女在坟上锄三锄,然后再由负责挖井的人进行挖掘。挖掘时需要上香、烧纸、置酒、放炮仗,以此“告诉山神,此地已有逝者入住”。
此外,当地人还会请三棒鼓艺人进行表演,表演时常一般为一到两天。演出的曲目多为《启鼓词》《劝慰歌》《恭颂词》,其内容多为恭颂、劝慰。以此怀念逝者生前的事迹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逝者子女则需要在道士的带领下进行磕头跪拜,为逝者敬茶敬酒。在此期间,香火不能中断,在土家人看来黑色代表着死亡,而香火的延续代表着人丁兴旺、延绵不绝。(即古时之绕棺)
(三)“上山”。上文也曾提及,逝者一般在停棺两到三日后即需要上山。上山的主要环节可分为三个部分:即上山前,上山时以及上山后。
首先是上山前。在上山的前期,需要将逝者的棺木移出灵堂,放置在大厅外,棺木的外层需要用黑布或者百布进行避亮。此外还需滴三滴鸡血入水碗中,第一滴是敬道士先生的,第二滴是敬东道主的,第三滴是敬天地的。三滴血如若凝结在一起则视为此次将平安无事,如若不能凝结则需格外小心,一切需谨慎行事。
山上时,道士会将水碗打破。在出殡队伍中,孝子位于最前面。长子一只手捧着灵位牌和遗像,一只手拿着引魂幡。抬棺木的人群居于其中。送葬和乐队位于其后。送葬之时:族戚皆送,视窆,毕而返。一路上需要撒买地钱且需要放声大哭。抬棺木的队伍在途中不能将棺木放下。
到达地点后,众孝子需跪于坟地之前。逝者的棺木需用孝帕垫住四角。道士先生选定好棺木的朝向后往墓地中洒富贵米。一番做法后,由抬棺的众人将老人的棺木放置入坟地内并将墓地封好。其余人则可返回家中。回到家中后,众人需要用淘米水和桃叶水进行洗手驱邪。逝者家人会将老人的衣物全部焚烧,最后再由道士先生进行做法,并亲自为逝者家中贴上符咒,以求主人家的一切顺遂。由此,道士先生的工作基本完成。丧葬仪式的流程也进行完毕。
纵观土家族丧葬仪式的整个过程,其仪式的本身是“死”,但仪式的主题和条件则是“生”。这其中融汇了土家族人对生命的珍惜与敬畏,也折射出了土家族人对死亡认识的乐观态度: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新生。
三、丧葬仪式所反映的土家族丧葬文化的内涵
仪式是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民族文化中最核心与最深沉的内容。在仪式的中,无论是对逝者生前的守护还是对逝者去世后的歌颂与怀念,生命始终是土家族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新生与死亡对于土家族人而言是一个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这种观念也蕴含于丧葬仪式之中。通过观察当地土家族的丧葬仪式,笔者认为这其中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文化内涵:
(一)灵魂不死的思想观。土家族人认为生命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点又是生命的起点。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的也映射于土家族的丧葬仪式之中。在当地人看来,老人的过世只是肉体上的消亡,而灵魂将会永存。因此,在老人过世后,会有比起年长家族长辈或其子孙来为其“喊魂”,以便其灵魂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在“扫影子”时道士会“将生者的灵魂归还给生者,而将逝者的灵魂留在棺木之中”;在逝者入葬后的一两天内,由家族中年长的前往墓地,寻找到一只墓地上的小生物并用纸制的盒子装住,放于家中的神龛之上。这些都无一不包含着土家族人灵魂不死的观念。
(二)乐观豁达的死生观。土家族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淡然,认为人的过世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开始新的生活,是一种解脱。一方面是老人摆脱了疾病困扰,另一方面则是子女不用再花精力照料老人,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事业和工作。所以,土家族人会在老人去之前会将其最后一口气用盆子装住,并将其称之为“福气”;在老人过世后还会请乐队唱丧歌,为原本生离死别的悲痛场景增添了一丝热闹与欢乐。这种乐观豁达的死生观既减轻了亲人逝世所带来的苦痛,也给在世的人继续生活的力量。
(三)朴素原始的孝道观。“行孝”是丧葬活动所表达的核心。子女为了表现自己对长辈的孝敬,通常会不惜花高昂的费用将葬礼办得隆重、热闹。而请乐队唱丧歌正是朴素原始的孝道观的重要体现。即通过唱词和仪式形成一种道德准则和一种行为规范,用以指导和调整社会中家族与家族、家族成员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给人们树立了一个衡量孝的标准。在老人去世前,子女需要守在一旁,聆听老人的教诲;在老人去世后,子女为其净身和穿寿服;在老人入殓后,子女还需哭丧,根据道士的要求进行跪拜等。这些习俗都体现了逝者的爱戴与敬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土家人对孝道的重视。
除了上述丧葬文化中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思想文化,在整个仪式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一,操办的时间过长。前文也曾说到,当地操办丧事的时间一般为三天两夜,但是由于下葬时间需要根据逝者的生辰八字进行选定,因此如若时间与八字不合,丧事的时间也会无限期的进行延长,这也导致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再者在众多的丧葬仪式过程中不乏封建迷信之处,例如在老人刚去世时不能哭,要为老人洗净身子穿好衣服才能哭,不然“逝者在阴间就会走不动道”等传统观念,与今日所提倡的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些种种都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四、小结
生与死是人生必经的两大命题,是自然发展的必然规律,丧葬仪式便是对逝者最后的礼遇。在土家族的丧葬仪式中,其通过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以及自身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民族的丧葬文化仪式和丧葬文化内涵,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不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在土家族丧葬文化内涵中,其乐观豁达的死生观、朴素原始的孝道观值得我们进行学习,但也需发现其中的不足与糟粕,从而做到对文化批判继承与学以致用。尤其是对于土家族丧葬仪式和丧葬文化的探究,对当前殡葬改革在民族地区的顺利推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①形家,即今世之风水先生。负责堪穴选地,今土家族堪穴选地之事多由道士进行,仪式主持亦然。具体可参考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②黄桂秋:《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73-82页。
③《龙山县志》卷二,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版,第411-413页。
④田荆贵主编:《土家族习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⑤据调查,所唱三棒鼓因其仪式性质不同分为喜词与哀词,其曲调较为固定,多口耳相传。演唱方式为打三棒鼓、唱山歌、耍刀三者相结合。具体可参考秦可国、李小平等编著:《土家族三棒鼓》,《湘西民族传统体育》2009年,第121页。
⑥湖南省保靖县县志编撰委员会:《保靖县志》卷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⑦李岑:《湘西土家族丧葬文化及其伦理研究》,中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78-579页。
⑧王钟霆:《简论土家族丧葬习俗的功能及特点》,《赤子》2017年1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