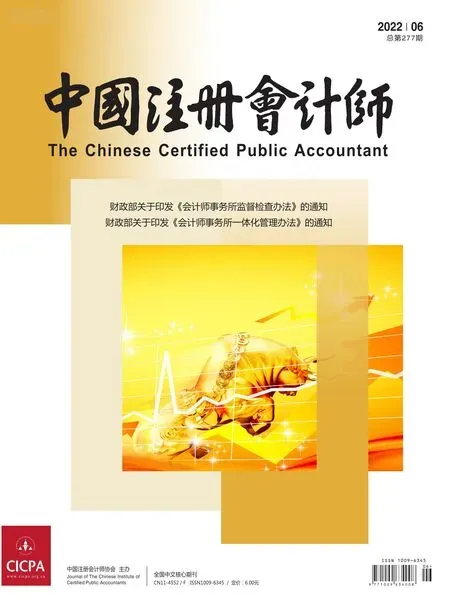辨析“其他权益工具”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确认与计量规则
| 马永义
“其他权益工具”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分别是《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应用指南(2018)(以下简称37号准则或37号指南)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2018)(以下简称22号准则或22号指南)下新增设的会计科目,两者名称中的“其他”分别是与什么相对称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否就是针对“其他权益工具”而进行的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终止确认时究竟是否应确认处置损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确认和计量规则对留存收益勾稽关系的研判是否产生了连带性影响?即便对资深业内人士而言,要准确回答出上述所有问题也绝非易事。
一、“其他权益工具”科目名称由来的概述
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会计科目的名称及使用说明一直由财政部来加以规定或调整。伴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基本确立,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概念开始进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话语体系,但时至今日,言及金融工具类准则时,广大实务工作者仍“谈虎色变”。
为便于准确理解金融工具的概念,笔者建议首先将其分拆成“金融”和“工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金融”分拆成“金”和“融”。具体而言,所谓的“金”指的就是资金,所谓的“融”指的是融通,所谓的资金融通,通常就被称为“金融”。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环境下,为了确保融资活动的顺畅运行,就需要通过合同或协议对融资双方的权益和义务加以约定,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语境下,通常就将与融资活动相关联的合同称为金融工具。简言之,金融工具就是与融资活动相关的合同。
从会计确认的角度而言,对融出资金的一方而言,就形成了金融资产,对融入资金的一方而言,根据其融入资金后所承担义务的不同,就分别形成了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在我国企业会计准体系框架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与计量是由22号准则来加以规范的,权益工具的确认和计量是由37号准则来加以规范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2006年我国初步建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时,在金融工具的分类层面,只存在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可简记为金融工具三分类。
在金融全球化和创新驱动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市场出现了以永续债为代表的新金融产品,新金融产品的出现对金融工具三分类的惯例带来了严峻挑战。以永续债为例,“永续债”的落脚点为债,发行人无法避免无条件加以偿还的义务,因此就具有了金融负债的本质,但“永续”二字却意味着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发行人无需履行偿还义务,这就与负债具有按期还本付息的特有属性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新金融产品的问世,迫切需要确立公认的确认与计量规则。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率先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新金融产品采取了应对之策,在应对实务工作无所适从以及实施持续趋同战略的合力推动下,我国在2014年度对37号准则(以下简称14版37号准则)进行了修订。
14版37号准则第三章的标题为“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该章对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且同时满足特定条件的可回收工具以及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笔者认为,特殊金融工具在本质上属于金融负债,因为发行方不能无条件避免其偿还义务,然而在发行方持续经营的状态下却无需履行偿还义务,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特殊的金融负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14版37号准则承认了特殊金融工具的存在,但对金融工具仍坚持三分类模式,最终将特殊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
将符合特定条件的特殊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其根本目的是解决特殊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类别的归属问题,但这并非就意味着符合特定条件的特殊金融工具等同于权益工具。为了进一步解决实务中特殊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问题,14版37号准则指南(以下简称14版指南)中特别设置了“其他权益工具”科目。
“其他权益工具”科目核算的内容为: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的归类为权益工具的各种金融工具。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其他权益工具”中的“其他”是针对普通股而言的。由于普通股通常是纳入“股本”或“实收资本”科目予以核算的,由此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判定,“其他权益工具”科目,是与“股本”或“实收资本”相对称的,类属于所有者权益项下的会计科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尽管14版指南设置了“其他权益工具”科目,尽管我国在2014年度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应用指南(以下简称30号准则或30号指南),但30号指南给出的资产负债表格式中,在所有者权益项下并未包括“其他权益工具”项目,这就意味相关具体会计准则之间出现了未同步呼应的现象。尽管30号准则和37号准则同属报告类准则,且两者同时在2014年度加以修订并发布,然而,受制于具体会计准则制定(修订)固有流程及时间周期所限,30号指南给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中并未出现“其他权益工具”项目倒也“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不能明示“其他权益工具”科目如何填入资产负债表的官方意志,就意味着14版指南针对特殊金融工具而设置的“其他权益工具”科目并未真正落地。
顺便指出,《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给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中,“其他权益工具”正式成为所有者权益项下的单列项目,至此,我国对特殊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与列报规则才暂且“尘埃落定”。伴随2017年度以来一系列非报告类具体准则的陆续修订、发布与实施,30号准则的再度修订早已“箭在弦上”,可以预见的是,在下一轮30号准则修订时,“其他权益工具”必将作为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单列项目而“登堂入室”。
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内容的深度剖析
在持续趋同战略驱动下,我国于2017年度对《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新22号准则)进行了修订,并在2018年度发布了修订的新22号准则应用指南(以下简称新22号指南)。新22号准则在金融资产分类层面,首先依据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将金融资产区分成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两大阵营,其次再依据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业务管理模式,分别对债权类投资和股权类投资进行具体分类。就股权类投资而言,纳入新22号准则予以规范的,只能是对被投资单位影响程度属于重大影响以下的股权投资。依照新22号准则的规定,股权投资通常应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新22号指南设置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来予以核算。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痼疾”仍存,资金使用效益仍有待提高,监管任务依然艰巨。本文简要阐述了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广西抓好扶贫资金监管问题整改的做法,并提出下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需要指出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的内容包括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两大类别。对于债权投资而言,只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债权投资才能够“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予以核算。对于股权投资而言,通常应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予以核算,但是,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可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依照新22号指南将其纳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予以核算。可简记为,股权投资通常应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但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也可以纳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予以可算。
需要指出的是,从供给侧角度而言,也许准则制定机构认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核算内容是具体而明确的,但会计准则作为事实上的公共产品,处于需求端的广大实务工作者,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核算内容的理解或判断恐怕就难以“整齐划一”了。
由于“其他权益工具”科目的客观存在,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意涵的理解就难免存在分歧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究竟应分拆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还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或者“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笔者的理解和解读如下:
1.首先需要将“投资”二字单独分拆出来,且意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属于金融资产类科目,因而只适用于该金融工具的投资方,而不适用于其发行方。
2.“权益工具”需要单独分拆出来,且其含义仅由37号准则来加以界定,即能够证明该金融工具的持有方拥有某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剩余权益,结合14版指南关于“其他权益工具”科目的使用说明,也可以将“权益工具”理解为实务中的普通股。
3.将“权益工具”与“投资”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权益工具投资”,就是指对普通股的投资。
4.对于重大影响以下的股权投资而言,依据新22号准则关于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通常应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新22号指南规定应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予以核算。
5.新22号准则第十九条规定,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中“非交易性”意指企业进行该权益工具投资的目的并非是出于交易,新22号指南规定,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应纳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予以核算。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非是针对“其他权益工具”的投资,换言之,不能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分拆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是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相对称的。对于重大影响以下的股权投资,通常应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予以核算,但对于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的股权投资,应纳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予以核算。
顺便指出,既然已经将“其他权益工具”设定为一个独立的会计科目,为了有效避免不同会计科目之间产生不必要的交叉干扰,如果用“其他股权投资”科目取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也不失为一种更理想的顶层设计,更何况新22号指南已经分别设置了“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科目。既然,我国的会计科目一直由财政部统一设置,从供给侧角度而言,仍需进一步加大准则制定过程中的相关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统筹协调力度,尽可能减少理解上极易出现分歧的现象。
事实上,在证监会发布的《2019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将不满足权益工具定义的投资指定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被作为“金融资产分类不正确”的问题之一加以明确指出。无独有偶,在《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也旗帜鲜明地指出:“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特殊金融工具本身并不符合权益工具定义,从投资方角度也就不符合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条件。”
由此不难推断,上市公司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核算内容的理解出现了分歧,有的上市公司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核算内容理解为就是针对“其他权益工具”的投资。笔者认为,如果不是“其他权益工具”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两个科目并存,上述现象就能够有效避免。
三、“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后续计量及终止确认核算规则剖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源于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指定,需要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如果所投资的权益工具没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究竟该如何进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的初始和后续计量呢?
梳理新22号准则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可以按照如下要领来加以操作:如果用以确定公允价值的近期信息不足,或者公允价值的可能估计金额分布范围较广,而成本代表了该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在初始计量时可以将该成本认定为公允价值;在后续计量阶段,如果被投资方的业绩和经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动(详见新22号准则第四十四条列举的七种具体情形),致使成本不能恰当代表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时,就应当通过评估(估值)来确定其公允价值。简言之,当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可以将成本认定为初始计量时的公允价值,但在后续计量阶段,如果被投资单位的业绩和经营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应当通过估值来确定其公允价值。顺便指出,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初始和后续计量阶段依据活跃市场来确定其公允价值即可。
依据新22号准则第六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笔者注:实务中应计入“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下同)。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22号准则并未明确规定终止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时,转让所得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究竟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但在实务中此情形是必须面对和应对的。笔者注意到,新22号指南的【例22】中将处置所得价款980万元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账面价值1000万元(成本1001万元,公允价值变动1万元)之间的差额20万元分别借记“盈余公积”科目2万元,和借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18万元。这就意味着,终止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时,转让所得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并未纳入损益核算系统。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账务处理代表的就是官方意志。笔者认为,一项金融资产“从生到死”均未纳入损益核算系统的做法,从理论层面是说不通的,然而,对于供给侧的“难言之隐”倒也不必“深入探究”。
四、“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终止确认计量规则对留存收益勾稽关系判断方法所带来的影响剖析
识别四张财务报表之间是否维系固有的勾稽关系,是业界进行财务报表分析约定俗成的“惯例”,也是识别财务报表是否存在低级错误的有效“利器”。毋容回避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终止确认计量规则的确立,对判断留存收益是否维系勾稽关系的方法论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正面干扰”,如果不从“顶层设计”角度来加以妥善引导和应对,必将对会计理论教学和会计实务应用产生严重冲击。
既然,“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后续计量过程中公允价值的累计变动以及终止确认时的差额均计入留存收益,就意味着“盈余公积”并非仅仅源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而计提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因此,在判定期初和期末“盈余公积”是否维系勾稽关系的方法上就需要做出相应变更。
依据新22号准则的相关规定,“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下称“情形1”);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如果将由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该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变动金额计入了其他综合收益,该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下称”情形2”)。依据新22号指南【例22】的账务处理,终止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时,应将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得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留存收益(下称“情形3”)。
既然新22号准则及新22号准则在“情形1”、“情形2”和“情形3”中均涉及到留存收益,在判定留存收益的勾稽关系时,自然就需要考虑各企业本会计期间是否涉及上述3种情形,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来判定留存收益是否维系了勾稽关系。笔者将其分解并描述为如下六个次序:(1)应聚焦企业是否启用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交易性金融负债”科目;(2)应了解或判定本会计期间是否发生了这两个会计科目的终止确认业务,并进一步判定企业具体账务处理的适当性;(3)在前两步基础上,判定新22号准则是否对判定留存收益的勾稽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4)如果上述3种情形对本会计期间的留存收益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对留存收益的具体影响金额;(5)在充分考量了新22号准则对本会计期间留存收益影响金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来最终确定本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的应有金额(下称“应有勾稽金额”);(6)通过观察企业本会计期末资产负债表“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的实际列示金额与“应有勾稽金额”的一致性,来最终判定该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是否维系了勾稽关系。
总而言之,判断“其他权益工具”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中的“其他”二字的含义就并非易事,“其他权益工具”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之间又极易形成顾名思义的关联映像,“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从生到死”均不得进入损益核算系统的账务处理规则又不可避免地对留存收益勾稽关系判定的方法论产生连带性影响,要理清这些关系着实存在不小的难度,期望本文能够向广大实务工作者传输一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