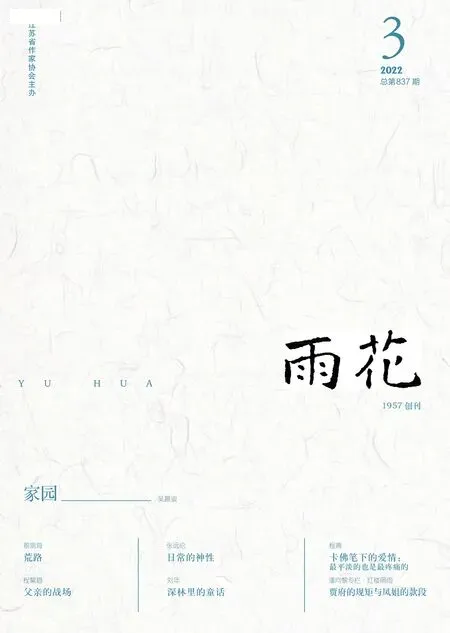悬崖之上
张洛嘉
我在长沙高铁站接到了从深圳来的姑妈。姑妈已经七十三岁了,清清瘦瘦,腰不弯背不驼,五官仍旧轮廓分明,大眼睛,高鼻梁,年轻时准是个大美人。姑妈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治疗干燥综合症。深圳的医疗资源不比长沙差,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对长沙更熟悉。事先,她让我替她联系湘雅医院的一位专家,挂上了门诊号。我陪姑妈排队验血做检查,等候结果,然后去看病、交费、拿药……跑了好些个窗口,每个窗口前都是人挤人。我和姑妈都感到很疲惫,但是能看出她的精神状态不错。坐下休息时,她说:医生讲不治疗只能活两三年,我知道那是要引起我高度重视,治疗不能再拖延了,我当然会积极治疗的,那就不止活几年,是不是?我马上说:这是肯定的!我握起拳头对她晃动,治疗,积极治疗!她也握了拳头晃了晃说,治疗,积极治疗!我们都笑了。
十个月前,我去深圳送表姐最后一程,姑妈曾向我流露出自己想死的心思,说自己年轻时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可找了个没出息的老公,这么多年来,就靠她辛辛苦苦地撑起整个家,女儿是她的全部希望,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没什么意义了(姑夫也在多年前去世),只求能早点死,就是有什么病也不想治了。想不到仅过了几个月,姑妈的心态来了个大转弯,我非常高兴她的悄然变化。
女儿出生后,越长越像她,聪明、漂亮,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处于婚姻压抑状态中的她,心情开始变好。她终于找到了精神寄托点。
结婚以来,她的心一直是冰冷的,有一种麻木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常常对镜顾影自怜、暗自神伤。
丈夫是个喋喋不休的人,为一点小事也要大吵。有时候她拿东西放错了地方,他会唠叨个没完。有次刷牙时,她忽然记起有件事要告诉丈夫,就跑到卧室,牙膏泡沫流到地板上。他勃然大怒,居然把牙刷抢过去,丢进了垃圾桶。
丈夫喜欢喝酒,有时候会找三两好友来家小聚。有一次喝酒时,饭桌旁煤炉上烧的水开了,而她正在厨房里忙碌,就叫他把开水灌到暖瓶里去。谁知他火冒三丈,起身提起开水壶,把开水浇到了煤火上。他的脸上写着一行字:我和朋友喝酒,你竟然还要我做事!
经常地,丈夫可以把一粒小小火星扇成熊熊大火,把家庭生活烧个昏天暗地。隔三岔五地,还跑到她母亲那里控诉她的罪状。她并不把这种“告状”当回事,自己怎么可能像他讲的那样懒惰、蛮横?冷漠倒是有一点。可没想到母亲居然相信了他的话,总是责怪她,要她认认真真地做个好妻子。
她辛苦工作一天,推开家门,迎来的往往是丈夫潮水一般漫过来的骂声,说她下班老是磨磨唧唧,等他把饭菜做好,自己吃“现成”的,只知道享受;说家里最劳累的事情都被他包了。她心里烦,懒得回答,难道背燃气罐这样的事情也要女人去做?自然,她也没个好脸色。吃饭时,他鼓眼暴嘴的,“吧唧吧唧”发出很大声响,气呼呼地把掉在桌上的菜又甩回到盘子里。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他对自己疑神疑鬼。有次单位组织活动,她准备和一个男同事同台演唱一首歌,他知道后,说同台唱歌,眉来眼去的,“哥呀妹呀”的一定是有什么“关系”,便在家里大闹,她怕他到时真去“搅台”,只好退出了这个节目。有两三次,她同他外出,在路上遇到男性熟人,便停步打个招呼,简单聊几句,这时,他就眼神怪怪地瞪他们一眼,一把拉着她就走,让她尽失脸面。
年轻时的她,长相漂亮,人又聪慧,追求她的男孩子自然不少。而那时,作为一个家庭背景“有问题”的女孩子,找个“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家庭,似乎是最好的归宿。当介绍人登门,巧言巧语推介姑夫时,她的母亲欣然同意——他的出身就是“响当当的”,这正是母亲所需要的。她想抗拒,然而,面对母亲哀求的眼神和话语,她心软了,虽然他大她近十岁,但她还是含泪点了头。后来,她只能感叹这是命运的安排,个人的力量无法抗拒。
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后来有了女儿,她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看见了光亮,她觉得自己必须努力,给女儿,给家庭,当然包括女儿的父亲,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且,她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她是下乡知青,从农村返城后,在街道居委会创办的自助小厂工作。工作之余,她捡起放弃多年的书本,考取了市里的一个财会培训班,结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做会计工作。她深知,自己必须有过硬的业务本领,才能在单位立足。那时计算用的还是算盘,她就苦练算盘技能,整天算盘不离手,在路上行走时,她也抬起手臂,两手在胸前不停地拨拉挑动,行人用古怪的眼神瞅她,以为她脑子出了问题。后来,在系统组织的算盘技能比赛中,她获得了第一名。她天生对数字敏感,读书时,数学成绩非常好,老师夸她是“数学天才”,现在做会计,她的账目清清楚楚,年年的财务检查,从没发现过一点差错与纰漏。她的业务能力全系统闻名,常常被上级抽调去参与财务大检查。她不仅业务过硬,而且也会做人,上下左右、内外关系的处理,拿捏准确。有时工厂与其他单位,甚或主管部门发生了“麻纱”事,厂长就说:让小张会计去办吧。分内分外的工作,她从不推辞,并努力尽善尽美地完成。很快她就升职了,成为厂里的财务科长。
回想那些年,上班的每个清晨,她从“社员广播”中猛然醒来,匆匆洗漱一番,然后叫醒上小学的赖床的女儿,就咬着丈夫刚买来的馒头或油条,冲出房门,几乎是小跑似的穿过路边乱糟糟的菜摊,穿过路上洪水般漫过的自行车流,奔向公交车站。上班的工厂在河对岸,要转趟车才能到达。一位常遇见的邻居曾笑话她,说张会计,你每天上班简直是“冲锋陷阵”!她淡淡一笑。是的,那时真是太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下班回到家天也快黑了。后来她也反省过,那时自己对家里的事情确实缺少关心,也没有顾及丈夫的感受。然而,自己的忙碌,不也是为了女儿,为了这个家吗?
一天下来,她感到身体很劳累,但心里踏实,那是因为有个小人儿在支撑着她。有一年,她被评为市里的先进个人,有记者来采访,问她瘦弱的身子里怎么积蓄着这么大的能量,她说了几句上得台面的话,但有句话却藏着没说出来:是女儿给予的力量!
在高铁站见到姑妈,尽管坐了好几个小时火车,她却没显出疲惫的样子。眉弓骨上开阔的额头,仿佛蓄着阳光,有些发亮;脸上也出奇地风轻云淡,没有呈现经历丧女之痛后的悲戚愁颜。
然而我发现,她原来那鹅蛋型的、即使人老了也还较饱满的脸庞,颧骨高高隆起了,皮肤也出现了明显松弛,脸形更为瘦削。也许,生命中那不可承受之重,曾残酷地碾压、吸取着她的血与肉。不过,她此时站在高铁站前的广场上,腰杆挺得笔直,神态安详。初春的阳光和煦而温暖地照着她。
我说,姑妈,你的精神很好哦!姑妈笑了笑,亲切地拉着我说,是吗?她告诉我,现在,她已从家里走了出来,参加了社区好多活动,还加入了一个失独老人组织。那些同样失去独生子女的老人,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她受到感染,得到鼓舞。她说,一个人待在家里,那种痛苦、悲伤,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她,太可怕了。姑妈拿出旅行茶杯,大口大口地喝了水,接着说,楼下的李婶得了癌症,每天都在练气功,红光满面的,精神状态好得不得了,李婶说人都是向天争命,多活一天都是胜利。姑妈抬起头望着天,感叹道:是啊,人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不努力与天争命呢?
表姐在世时也多次提起过,她的这位母亲真不容易,当年为了她上大学和攻读研究生学位,已经退休的姑妈毅然决然南下打工,钱的事情从来不让女儿过问,一个人默默解决。后来女儿买房,她又东拼西凑交了房子的首付。为此,她卖掉了家乡的大房子,租住着一间破旧的小房。
表姐说,妈妈总是不停地折腾自己,我知道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她的一生都十分尽力,为的是对抗命运的安排。妈妈在人生路途上拼命往前赶,也带着我小跑着跟随她……我很害怕妈妈会忽然间承受不住。
姑妈不停地咳嗽,整个人喘不过来气,呼吸有点困难,间质性肺炎已经到了中晚期,而干燥症让她整个口腔没有一滴唾液,只能不停地喝水。
那盏微弱的生命灯火忽明忽暗,闭上眼睛,无边的黑暗就漫了过来。她感到了内心的恐惧,不停地燃起记忆的篝火,烘烤着自己发冷的身子。在“哔剥”作响的火光中,她仿佛又听见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哭叫,听见女儿对着自己第一次喊出“妈妈”时有些含混的声音;仿佛又看见自己送女儿去外省读书时的情景——那是女儿第一次远离她,在火车站台上,已跨上车厢踏板的女儿猛地转身扑来,紧紧拥抱自己……
女儿走后,外孙女初升高,到学校住宿去了,女婿也早出晚归。独自在家时,她时常端详着女儿的照片默不出声,让回忆之轮碾碎寂寞孤单的时光。
也许回忆才是抚慰心灵的最好方式,而不是遗忘;生命中所有的遗忘,都不过是飘然易逝的浮云,而唯有如刻如镂的记忆,因每笔每划都粘连着血肉,那是一个人意识中无法抹平的痕迹,将不绝回响,尤其是人到晚年。
此时,当脑海里不断涌现那些逝去的难忘图景,尽管心痛如焚,她发现自己竟然掉不出一滴眼泪来了……
女儿走后不久,女婿回家吃晚饭少了,有时深夜才回,或者一夜不归。开始女婿还发微信,告知不回来吃晚饭,后来干脆微信也不发了。有天晚上,女婿拉着她坐到沙发上,吞吞吐吐地说:妈,我想和你说个事情,有人……给我介绍了女朋友,碍于情面,我还是,还是去见了一面……我觉得她身上,有种特殊气质,我,我不想错过这机会……坐在那儿,她觉得自己听进去了,又觉得什么也没听见,只感到一阵晕眩,手上剥着的大蒜也掉落到地上,好像有一波海潮突兀而至,将自己冲倒,淹没。她低下头去,她不想让女婿看到自己慌乱的神色。
过了一会儿,她缓缓说:遇到中意的,当然,你应该……
一直以来,她觉得女婿是个好女婿,对女儿很好,尤其女儿生病治疗期间,他细心照看,劳累奔波,从无怨言;虽然平时与她话语不多,却很尊重她这位岳母,不时有暖心的关照。在女儿走后最难受的日子里,他买来笔墨、宣纸,让她练习书法,排解悲痛。她能理解他去找对象,但女儿才走几个月,是不是太急了?自然,她没有说出口,却有如一个疙瘩梗在心里,她难受,也替女儿难受。
女婿有时候会拿走她做的几瓶调味菜,或其他好吃的,她会在心里想:肯定是拿去给那个女的了。有个周末,女婿带回一块腊肉,她猜想应该是那女人给的,就试探着问:这是哪个地方的腊肉?与我们湖南的不同。
她没有觉得自己失态了,那个疙瘩还结在心头。
女儿走后,她决定留在深圳不回老家,是因为害怕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会更加伤悲,而这里,至少还有外孙女每周能陪伴她两天;她更害怕回老家后,别人关心的询问,会使她的心更痛。当然,这也是女婿挽留的结果。如今,女婿心里已经装着一个河南女人了,不久也会离开的。面对现实的逼视,她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很快又定下心来,还是留在外孙女身边,这样,自己还能不时看见女儿的影子,感觉到女儿生命的延续,而且,外孙女是她从小带大的,外孙女也离不开她。
她看见自己脸上布满无数条皱纹,皮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就是一个明显的凹陷,而年迈的身体内,五脏六腑正渐渐下垂,她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要是还有年轻时那种生机与朝气,即便十分之一,就好了。
当得知患有干燥症后,她更是深深地陷入了惶惑、困顿的泥沼中。因为口渴得厉害,她经常泡上一大杯绿茶,坐于阳台上,看着小区里的树木荣枯,老枝新叶;或者斜躺于沙发,默默盯着前面电视机的黑屏,人便不自主地开始思索既往与未来。她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问自己:我是否已然面临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人到晚年,疾病降临,我是否会变得浑浑噩噩,苟延时日,在极度的悲时伤怀中,哭泣着走向死亡?或者,面对不幸的命运,我还能像以前那样不甘屈服,怀着青春期般的希冀,作最后的抗争,如那枯树新枝,以衰微的生命重新燃起绿色之火,然后,在火焰中高蹈着最后的欢愉,慨然赴死?……
她知道,人到晚年,最可怕的就是这两个字:等死。她了解自己,让她顶着一副痴呆木然的面孔,颤抖于生命的暮期,那是决然不可接受的。她觉得,必须改变遭遇不幸之后的生活与精神状态,重新萌生绿叶。
于是,她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与老年同伴玩乐时一如孩童。在家里,也不老是呆呆坐着出神,她临帖练字,于一笔一画中,结构晚年生活新的字形。她也开始读文学作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让她的心久久难以平静。雨果笔下的丑八怪卡西莫多,身体是残损的,却拥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灵,他像一只粗糙、普通的陶罐,能够盛着满满的水;而那个具有漂亮外表的骑士,内心肮脏,有如一只开裂的水晶瓶,已装不下一丁点儿水了。她觉得,自己也是残缺的,她害怕与别人的完整家庭、畅达命运去比较,但是,不幸与缺陷是能够拓展内心空间的,正如雨果所说:“凭借病弱而得以彰显。”少女艾丝梅拉达在遭受一连串致命打击后,发现只有一样东西依然在自己心中屹立不动,那就是——爱。
于是,她去搜索自己的“爱”。她发现,存留于心中的爱依然是那般丰满和浓烈,她爱已远走的女儿,爱外孙女,爱即将成为别人女婿的女婿,爱亲人,爱朋友,爱老年组织里的伙伴,爱所有善良的人,也爱自己……打开回忆之窗,她看见,是爱支撑她走过了生活中的坎坷和磨难,而爱所赋予的使命感,让自己成为了一名还算优秀的母亲。那么,现在必须找回自信,重铸冀望,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晚上,她独自在小区里散步。路灯下,蓁蓁树叶泛着光泽,茵茵草地像一张阔大的、给人温和的毛毯,而那一栋栋林立的高楼,灯火明亮。这时,她眼前似乎出现了雨果描绘的那座巴黎大教堂,它庄严的线条,它每块石头缝隙所渗透出的纯粹与安静,使纠缠着她的痛苦、惶惑也悄然消散。
安放在草地上的一只喇叭正播送着轻柔的歌曲。她觉得,如果人生像一首歌,那么,晚年的旋律应该是别具情韵的。
姑妈在长沙看完病后,回家乡在我家小住,她感受到我们一家人对她的盛情和关爱,因而卸下许多思想负担,轻松地与我们聊天。她说,现在朋友越来越多了,每天社区的活动都忙不完,与失独老人组织的朋友交心确实改善了心境,他们以自身过往的经验帮她走出阴霾。他们一起下棋,学做美食,组织旅游,去参加各种老年健康学习班等。她由衷地说,因为有亲人和朋友们对她的爱,她觉得自己更应该好好活着,好好爱自己。
我知道,丧女之痛和对晚年生活的焦虑担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的病情,并残酷地把她推向了生命的悬崖边缘,但我明显感觉到,她已经在用力地活着,以她一以贯之的意志和抗争,将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姑妈急着要回去,说社区有好多活动等她参与,那是不能耽误的。我送她去火车站,她转身挥手向我告别,夕阳下,她瘦削的身影显得那样挺拔,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她走得十分轻快有力。
站在广场上,我抬头望向天空,看见有一只孤单的鸟儿正往南边飞,是不是燕子?是什么原因让它离群了?它要飞向哪里?在我印象中,燕子总是不停地飞翔,它们辛勤地衔泥筑窝,不断地为孩子觅来食物。它们会有飞不动的时候吗?就像一个人终有不能动弹的那一刻。
那只鸟儿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了,很快消失在茫茫暮色中。我想象着,它已经飞临一条大河之上了,一艘大船正驶过河面,船后激起白色浪花,火红的晚霞把河面映照出一片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