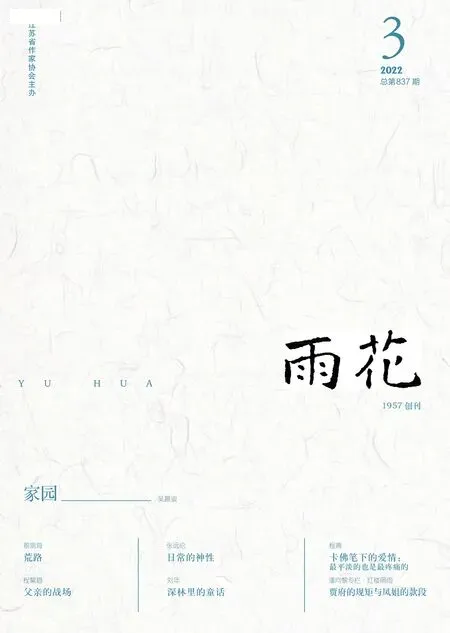治疗术
王 爱
那天早上,哈包幺幺一觉醒来,声称自己得到神谕。洞山菩萨以人的形象首次出现在他梦中,并亲口许诺,只要哈包幺幺初心不改,他将会如愿以偿,得到他朝思暮想的治疗术。
传说治疗术是一种有别于现代医学的民间秘术,专治疑难杂症。在古道溪,你也许听说过隐藏在普通人群中的治疗师,画符、念咒语,逢凶化吉,祛病消灾,百试百灵。那些遭恶疾缠身的古道溪人,拒绝去医院又不堪烦扰时,为解除痛苦,通常愿意穷尽心血去寻求治疗术。医院并非治不好那些古怪的毛病,可古道溪人不到生死关头,绝不会把脚主动抬进医院的大门。他们相信治疗术,只要足够虔诚,就能活得很好。古道溪人常说,菩萨心慈,借人的手搭救受苦受难者。但治疗师神龙见首不见尾,不是随便能找到的。等待施救的人若是没有一点缘法,便会求告无门。因为那个人今天是治疗师,也许明天就不是了。
我奶奶也是个迫切需要治疗术的人。她身上的恶疾是在香儿姑姑夭折后染上的。奶奶总说她嘴里面藏着一句话,像是含着一块尖锐沉重的石头,吐不出来,咽不下去。一直哽在那里,噎得她呼吸紧促、痛苦难当。她想说时常常忘记,不知从何说起;不想说时,又一直朝外翻滚,时刻显示它的存在。只要奶奶一转动心思,这句话就像长满锋利倒刺的野兽,用利齿划开皮肉;又似一锅翻滚的热油,在嘴巴里倾倒漫灌,燎来烫去。每到这时,奶奶便会口舌生疮,整个喉腔酸胀麻痒、疼痛难忍。奶奶被这个怪病反复折磨,心神不宁,寝食难安。她多次烧香拜佛寻求良方,然均无效。最后迫不得已去了医院,医生拿着电筒照来照去,检查无果。既没有解除奶奶的痛苦,也没发现她嘴巴里的古怪。多年来,奶奶那个想说却说不出口的秘密,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古道溪人总是将治疗术渲染得神乎其神。一个古道溪人能够无病无灾地过完一生,多半仰仗这种古老秘术的护佑。刚出生的婴儿,他的祖父母必定找遍整个寨子,去寻找初次鸣啼的童子鸡屙的嫩鸡屎,收集起来抹在幼儿的鼻尖上。每个新生儿的房间里,婴儿清甜的体香和淡淡的鸡屎味混杂一团,氤氲其间。仪式感能带来一种令人心安的魔力,代表父母长辈的寄托和祝福。给婴儿此生签订契约,在疏于看顾之际,寄希望于畜生的气味能掩盖生人的气味,蒙蔽鬼神之眼。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却被年长的古道溪人视为圭臬,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
一个新生儿,连续三个早晨涂抹嫩鸡屎后,方能放下心来。此时婴儿眼神明净,哭声嘹亮。成长一生的力气自此萌生迸发,足以保他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小孩长腮腺炎了,点上香,对着小孩的脸画几道符。完毕,小孩跳上屋前的梅李子树,蹲在树上摇几下树枝,唱着歌谣:猴儿包,上树摇,下树消。小孩嬉笑着回到地上,他腮边的肿包已随之消散。那些夜哭的孩子,通常会在他额头上画几道符点几次水,再跟鬼神唠叨几句,从此便能安睡到天明。不吃饭,日益饥瘦、黄皮寡脸的孩子,也有办法治疗,无外乎脸颊上拍几下,肚皮上揉一揉。一个走夜路受到惊吓的人,便有人替他将桐油和酒喷在烧红的铁铧上,制造出熊熊火焰以驱邪祟。
类似的民间小法子不胜枚举,这些伎俩不足为道,你要是跟年老有见识的古道溪人谈论这些,他们多半会哂笑不屑,回头再给你讲一讲真正的治疗术。
古道溪张母沟太太无儿无女,又聋又瞎,夜里就算被鬼附身,自己也不会知道。她独居深山,靠嗅觉行之于世,安安稳稳地过了一辈子。张母沟太太有个好鼻子,能觉察到危险,亦可闻出食物的好坏。然有一天,张母沟太太失去了她的依仗。
有个行事莽撞的年轻人上张母沟找兰草。山高目眩,困累交加。内急时无暇多想,蹲在一颗枫香树下解决了问题。轻松过后,便倚着树干一阵酣睡。暮日西沉,夜月东升。那个人幡然梦醒,才发觉自己冒失唐突。羞愧之下,他用干土盖住那堆腌臜物后,惶急下山。可以肯定,那个傻瓜掩土时经验不足,自作聪明用了一些小咒语。可他还是没能成功遏制住那股奇特的气息。一种在密闭环境中混合了草木、土壤、人粪、月光和巫气的不明物,发出了世上最刺鼻难闻的味道。张母沟太太紧掩柴扉,那个臭味搭着冷硬的山风仍源源不断地卷进她的屋子。张母沟太太忍受到第二天,实在挨不下去了,只好拄着拐杖,屋前屋后地摸索寻找。她足足找了三天,终于找到了那棵枫香树。张母沟太太扔掉拐杖,匍匐在地,用双手挖开土堆。结果,一股强大的气味随着掀开的土壤,猛地冲向鼻端,她的嗅觉就被夺走了。
张母沟太太失去嗅觉这事,没有人知道。大太阳天里,她在家里煮肉熬汤。那些腊肉没有熏干水分,埋在仓里的谷糠里存放,早已骨坏肉烂,奇臭无比。可是张母沟太太浑然不觉,照旧吃得心满意足。腐臭三里,盘旋不去,整个张母沟的生灵都恨不得没长鼻子。甚至来张母沟盗树的人,也不得不掉头离开。张母沟太太的遭遇当然也引起治疗师的怜悯之心。在大家对张母沟躲避不及时,他偏偏来到此处。治疗师费尽心力,从深山洞穴中诱骗了一只专吃臭味的虫子,用草茎捆绑后,倒吊在张母沟太太的肉锅上。臭味源源不断,虫子挣扎一下,治疗师就念一句咒语。持续五六下之后,虫子终于不再动弹,乖顺地张开了嘴巴。这时候,治疗师双目紧闭,双唇翕动,念念有词。虫子受到驱使,陡地奋力向前,鼻翼抽搐,甘之如饴,贪婪吞咽。腹胀如鼓后,身躯一阵扭动,草茎断裂,竟喷出一股淡黄色的烟雾。那是一种比锅里的肉汤还要臭的味道,张母沟太太随即痛苦大叫,好臭啊,好臭啊。她终于恢复了嗅觉,“呜啦呜啦”地呕出一大摊恶臭之物。治疗师将虫子小心翼翼地收入袖中,转身离去。张母沟太太每隔一个时辰就呕吐一次,整整呕吐了一天一夜,直到污秽的肠胃洁净如初。
老山沟有个老猎人,他的身上寄宿了一只跳蚤。老猎人一辈子痴迷打猎,手中不知折损了多少飞禽走兽的雄心烈胆。跳蚤也许就是某只受伤的动物故意过给他的。但老猎人除了打猎,其余诸事不碰。日子过得浑浑噩噩、邋里邋遢。跳蚤究竟是哪种猛兽濒死前的复仇一瞥,他浑然不觉。跳蚤不吭不响地藏在老猎人的身体毛发中,来无影去无踪,就像魔鬼,既机敏又放肆。它终日侵犯吸血,养得膘肥体壮。惘然不知的老猎人又痒又痛,坐立难安。这只跳蚤灵性十足,很快觉察出宿主其实软弱无能,只能对付高大凶猛的野物,对小小的它却束手无策。跳蚤在老猎人身上安家定居,整日在他耳边窃窃私语,以威胁恐吓为乐事。老猎人再也无心打猎,他每天至少脱去衣服十遍,全身上下翻找,可惜徒劳无功。
半载有余,跳蚤滋扰不息、昼夜不宁。老猎人疲惫消瘦、痛苦不堪。人人都说,老猎人打了一辈子猎,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居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跳蚤,每日被折磨到惊恐躁狂、笑怒无常。人们替他求到治疗师门下。那个人对着已然溃败的老猎人燃香静坐,两个时辰过去,屋内寂然无声,老猎人终于沉沉睡去。治疗师方才起身,径直走向老猎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很快就凭着微不可寻的迹象找到了跳蚤的老巢。治疗师拨开老猎人厚实浓密的白发,顺着发根一路梳理。黑白分明,醒目耀眼,那精灵一般的小虫赫然显现。此时它乖巧可爱,正恬然酣眠。治疗师念念有词,手指曲起合拢,迅疾如电,直入老猎人的耳朵后窝。犹如探囊取物,准确无误地擒住小兽。不待众人惊呼感叹,他手指略微使劲,已在作法之际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它的性命。人们只听到“啪嗒”一声脆响,跳蚤滚圆的肚皮随之破裂,老猎人被盗走的鲜艳血汁顿时溅满了治疗师的双手。放下猎枪和利刃,就此歇息吧。治疗师对懵懂醒来的老猎人留下这句话后,轻飘飘地走了。
不久前,刚搬来明溪镇的一家三口,到处跟人打听治疗术。刚满十岁的女儿坚称身后多出一道模糊的影子。她走到哪里,那道身影就跟到哪里。那道旁人看不见的影子使小女孩神情恍惚,被噩梦追赶,茶饭不思。她被带去医院,也没查出任何问题。
那家人被迫无奈之下,因人指点,来到明溪镇找到那个会治疗术的人。治疗师跟小女孩单独待在一起,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对父母守口如瓶的孩子相信了他。尔后,治疗师来到河边,让小女孩赤足立于河中,冰凉沁骨的古道溪水从洞山深府而来,又潺潺流淌而去。余辉点点,光芒灿烂,河水绕过膝下,如泣如诉,缠绵徘徊。小女孩牙关“嘚嘚”响动,浑身颤抖。终于一败而溃,放声大悲。微波荡漾,一团只有小女孩才能看见的墨影自水底冉冉升起。水面一阵嘈乱之后,黑影趔趄了一下,慢慢固定成清晰的形状。那是隐藏在小女孩心底最深处的秘密,也是她的病痛。她双手掩面,声嘶力竭后慢慢平复下来。河水让她自愈,她得到安慰,委屈和悲伤便顺着河流消解了。
小女孩终于告诉父母,那是一条狗的影子,虽然他们什么也没看到。治疗师颇费一番周折,知道了事情的来由。小女孩流着眼泪向父母承认,家中那条相伴十年的狗,不是意外丢失,而是她故意驱赶出去的。那条狗无家可归,四处流浪,最后被人残忍地吊杀了。小女孩目睹了这个可怕的过程,因而自我谴责,愧疚悔恨。狗的惨死,在小女孩心中留下浓重的阴影。她由此噩梦连连,茶饭不思。而河边,就是那条狗的临终之地。一家人依言行事,买上香纸烛火到河边的桂花树下洒扫悼念了一番。返程时,小女孩露出久违的笑颜,声称再也看不见那道影子了。
治疗师说,人人都有甩不掉的狗尾巴,那是作恶留下的影子。
这样的故事多不胜举,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哈包幺幺更是沉入其中,难以自拔。就连一向斥之为无稽之谈的奶奶偶尔也会动容点头。不过治疗术再神奇,也只能听听而已。如今想想,治疗师们也许是高明的心理学家,他们碰巧治愈了一些人的心理疾患,才会被不明缘由、心怀崇敬的乡民口口相传、添油加醋,逐渐渲染演变成某种外人难以窥探的神术。我们没想到,哈包幺幺竟信以为真。他把当一名治疗师视为毕生所愿,并多次建议我奶奶试试治疗术。哈包幺幺信誓旦旦地说,他曾亲眼见过许多人因为治疗术而重获新生。
为了寻找治疗术,哈包幺幺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甚至多次离家出走,做下不少荒唐可笑的事情。外出寻找未果,他干脆把自己关在家里,废寝忘食,冥思苦想,按照那些传说依样画葫芦,研习治疗术。可他私自琢磨出来的治疗术不但没有治病救人,反而给我家惹下许多麻烦和烦恼。每当有人找上门来讨要说法时,爷爷就得替哈包幺幺赔礼道歉甚至补偿损失。多年来,奶奶费尽心力,不停地平息事端,早已怨忿不堪。她哪怕被恶疾折磨得痛苦不堪,也拒绝喝下哈包幺幺煞费苦心制作的符水。
哈包幺幺生来不大聪明,跟我奶奶的关系一直十分恶劣。他没有多大挣钱的本事,也不愿意耕田种地、踏踏实实找点事做。在奶奶眼里,哈包幺幺就是个啃老的人,借着治疗术的由头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我奶奶忍无可忍,虽然一个锅里夹菜吃饭,但对他从没有过好脸色。哈包幺幺我行我素,根本不管那么多,我认为他即使再蠢,对奶奶的嫌弃还是看得懂的,可他装作不懂。
哈包幺幺原本也是有学名的。但是他哈里哈气,从小就被人叫做哈包。时间一长,他的学名也无人记得了。他是我奶奶最小的儿子,是她躲在娘家,千辛万苦生下来的孩子。据说奶奶当初怀他的时候,差点没保住,多亏娘家嫂嫂帮忙,才顺利生下哈包幺幺。都说幺儿最让父母疼爱,可奶奶并不喜欢哈包幺幺,时常对他横眉冷眼。那时候,香儿姑姑还在,她只比哈包幺幺大四岁,两人从小相处,从不相让,争吵打闹不休。香儿姑姑争强好胜,处处挑事,哈包幺幺人小力弱,却也不甘屈服。家中天天鸡飞狗跳,哭喊不断。等到爷爷奶奶干活回家时,香儿姑姑口齿伶俐,总是恶人先告状。哈包幺幺就又会遭到一顿训斥,甚至是责罚。他生性笨拙,不善辩白,即使受到委屈也只能忍受下来。
香儿姑姑自小挑食,常常不吃这个不吃那个。那时候家里穷困,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可哪怕是烧一个红薯,奶奶也会挑一个最大最好看的给香儿姑姑。哈包幺幺没有这种待遇,他也从不挑嘴,有什么吃什么。大概因为这样,偶尔家里煮点肉汤,香儿姑姑挑剩下后,爷爷也会顺便问一下哈包幺幺:“你不要吧?”“既然知道我不要,你还问?”哈包幺幺朝爷爷吼道,蓄积已久的眼泪哗哗直流。爷爷性格温厚,哈包幺幺只敢朝爷爷发火。他很委屈,虽然他从不挑食,但也渴望得到同姐姐一样的关注和照顾。他吃很少的饭,甚至不去夹菜。可惜没人注意过他。
哈包幺幺不懂像一个正常的小孩那样,向父母倾诉和示弱,他只会暗自发脾气、闹别扭。香儿姑姑一直很娇弱,不光挑食还老生病,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痛。大人重心转移,对香儿姑姑嘘寒问暖、百依百顺。哈包幺幺疑心姐姐为了得到更多疼爱装病,但到他偶尔感冒发烧时,却不敢像姐姐那样正大光明地告诉父母,反而害怕家人说他娇气,竭力表现得若无其事,努力隐藏自己的病痛。那时候,哈包幺幺的忍辱负重,实在可堪佩服。
跟香儿姑姑在一起,哈包幺幺通常是那个被忽略的孩子。然而,他这种不被偏爱的人生却因一场事故戛然而止。有一次,大人都不在家,哈包幺幺和香儿姑姑在山里游玩,无意中摘食了一种有毒的野果。等到奶奶回家发现时,两个孩子已倒在地上,呕吐抽搐,大喊腹痛。爷爷是个生意客,外出贩牛未归。寨子里人烟稀少,离得最近的那户人家也有一个山头。事情紧急,奶奶连滚带爬过去,那家人大门紧闭,不知道在哪里干活。奶奶喉咙喊破、嗓音喊哑,也没听见一点回声。奶奶只好又跑回来,眼看着两个孩子都快不行了,她心急如焚,捶地大哭。两个孩子加起来一百斤出头,对一个做惯农活的人来说,这重量也许不足为惧。但奶奶是个女子,她在年轻时为了躲避土匪追赶,跳进后山的苕洞里跌断了右腿,自此走路跛脚,使不上力气。她拖着一条残腿,就是背一个孩子走十几里山路都很艰难,更何况还是两个孩子。
奶奶全身失去力气,腿脚全软了。可哈包幺幺的眼睛慢慢闭上了,香儿姑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奶奶流着眼泪,在姐姐和弟弟的身上来回望着。香儿姑姑无声地看着奶奶,那双逐渐失去光芒的眼睛里满是乞求和哀怜。似乎在说:娘,救我啊,救我。不,还是救他、救他,救弟弟吧。那种眼神,把奶奶的心碾得稀碎。奶奶一会儿爬到哈包幺幺身边,一会儿爬到香儿姑姑那头。当她想救香儿姑姑时,娘家嫂嫂就出现在她面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一言不发,冷漠、刻薄。好像在说,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救这个儿子。“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救哈包,我就要救我的女儿。”奶奶一边大哭,一边大骂。她把心一横,背起香儿姑姑就走。可只走了几步,她就把香儿姑姑放下了。她转身跪在地上,朝堂屋的神龛磕了一下头,不敢看女儿一眼,背着哈包幺幺一步一挪地走出了家门。
情势危急,奶奶背着哈包幺幺跌跌撞撞地下山,不知摔倒过多少次,可她一次次爬了起来。她凭着本能在跑,一路在荒无人迹的荒野哭喊:“有人吗?老天爷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啊!”她凄厉的求救声惊飞了不少山鸟,一些动物在山涧饮水,闻声转头,疑惑地看着这个悲伤绝望的女人。那一天,乡民信仰的山神菩萨始终没有出现。
奶奶跑了十多里山路才碰见几个种地的山民。等到旁人接过哈包幺幺,她再返回救香儿姑姑时,错过时辰,香儿姑姑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先救儿子再救女儿,这样的选择,在当时的乡村天经地义、正确无比。没有任何质疑,众人佩服奶奶不是一个只知道哭哭啼啼、手足无措的无用妇人。否则,她只要稍一犹疑,就会连一个孩子都救不回来。
后来,奶奶便时常哭泣。似乎为了得到冥冥之中香儿姑姑的谅解,她反复诉说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不得不救哈包幺幺。她说她不是怕娘家嫂嫂的冤魂,更不是怕她的婆婆。奶奶的婆婆那时已死去两年。但那个眼里只有孙子没有孙女的老人,仍然给家人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古怪而冷酷,对儿媳妇严厉苛责,打骂随心。奶奶自从嫁给爷爷后,因为腿脚不便,干不了重活,一直受到婆婆的嫌弃和欺压。老太婆重男轻女,把孙子视为命肝心,孙女则可有可无。她虽然去世了,余威还在,地位还在,她的坟墓就在后山上,她的眼睛还在死死地盯着奶奶。奶奶虽说不是怕她,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扔下亲生女儿。
香儿姑姑殁了以后,奶奶长久地陷入自责和抑郁中。她对哈包幺幺愈加冷淡,甚至到了不理不睬的地步。毕竟,她把目光落到哈包幺幺身上时,看着这个身体强壮、逐日长大的孩子,难免会想到那个被她残忍舍弃的女儿。她对香儿姑姑的愧疚与悔恨,无一日不在蚕食着她的心。她便日日捂着嘴巴,痛得眼泪汪汪。我一直不解,奶奶为什么讨厌哈包幺幺。整个事件中,哈包幺幺其实是无辜的。更何况,在香儿姑姑死之前,奶奶就不喜欢哈包幺幺。
哈包幺幺迷上治疗术后,跟奶奶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难以共存。但我明白,哈包幺幺为何如此痴迷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治疗术。奶奶罹患怪病后,深受折磨。哈包幺幺又何尝不痛苦,他自小承受着奶奶的无名之火,时常处于惶恐不安中,便将这一切归咎于奶奶的恶疾,归咎于命运的恶意。当他一事无成,突然找到一条母子相处的捷径时,不由得眼睛发亮,神采飞扬,整个脸上像有一层光芒笼罩。哈包幺幺也许没有身为治疗师的资质和天赋,然而用治疗术解除母亲的痛苦,让她接纳自己,是他最终的目的和心愿。他发誓治好奶奶的恶疾,自此对治疗术向往景仰,孜孜求之。
哈包幺幺自认为得到菩萨的点化,一早起来欣喜若狂,忍不住当众说出他的计划。他要朝着洞山菩萨指点的方向一直走,他将到达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里会有失传已久的治疗术。哈包幺幺宣布,找到治疗术,治好奶奶的恶疾,他才会停止追寻的脚步。其实没有人关心哈包幺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哈包幺幺虚头巴脑,多年来鬼话连篇,关于治疗术的梦境没人相信。他年岁虽不小,在家中却人微言轻,几无地位可言。
爷爷不以为然地听着,拿起炭火上烤熟的糍粑,夹上满满一筷子大头酸菜丝,蘸着古道溪霉豆腐,准备大快朵颐。奶奶的涵养功夫可没爷爷的好。说实在的,作为当娘的,她早已受够这个打了几十年光棍的小儿子了。不管哈包幺幺说什么,她都将其视为混账话。听了哈包幺幺这番话,奶奶不但没领情,反而怒火腾升,顺手抄起火钳就扔了过去。哈包幺幺训练有素,身子朝我这边一偏,照常躲过一劫。哈包幺幺撞翻了我碗中的洋芋汤,我甚是遗憾。虽然洋芋汤每餐都喝,可汤里漂浮着两片花椒叶子,还是很香的。
汤洒了,花椒叶沾在哈包幺幺的鞋面上,那是奶奶今冬刚做的新棉鞋。奶奶气得拿筷子直戳哈包幺幺,她的脾气年轻时就很不好,在她有了顽疾后,更是暴躁易怒。奶奶认为,哈包幺幺的心愿至少应该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治疗术。
那天早上,哈包幺幺一番豪言壮语,全无悔改之意,于是遭到奶奶的辱骂驱逐。他狼狈出门,鞋面上带着花椒叶,也顾不上跟我告别。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他,那个在梦中出现的菩萨究竟是男是女。厨房里久久残留着饭和汤泼洒后的味道,再无人惹奶奶生气,她依旧怒容满面,咒骂不停。爷爷享用他的一日三餐,对哈包幺幺的出走莫可奈何。他只劝过我奶奶一回:“哈包是你那年躲土匪,吃了多少苦头才生下的,你怎么就容不下他啊?”爷爷刚说完,奶奶的恶疾突然就犯了。她捧着嘴巴呻吟起来,眼泪直流,看着我爷爷,痛得说不出话来。爷爷长声叹息,再也不敢在奶奶面前提从前的旧事。
哈包幺幺离开后,跟我们从无联系。倒是关于治疗术的传言与日俱增,哪怕奶奶充耳不闻,人家也会把这些信息从口袋里掏出来源源不断地塞给她。最初两年,偶尔有人找上门来,要哈包幺幺承担治疗失败的责任。奶奶无动于衷,对哈包幺幺生死不问。爷爷每次赔着笑脸将来人打发走之后,劳心耗力,都会累病一场。然而,没有人就此事怪罪来人,反而让我们心安,至少我们还能探查到关于哈包幺幺的蛛丝马迹。后来慢慢不再有人来了,我们失去了哈包幺幺的一切消息,爷爷愁容满面,终日郁郁。就连奶奶,也变得越发焦躁起来。不知道奶奶的坏情绪是哈包幺幺引起的,还是她的顽疾造成的。那个浪荡子还没回来吗?连亲爹亲娘都不管了?偶尔有人不怀好意道。奶奶听后就满脸愠怒,不发一言。可哈包幺幺有什么错?他只想治好他母亲的病。
我们深知奶奶好胜倔强,便不去谈论哈包幺幺,也没打算把哈包幺幺找回来。可那个用治疗术的人到底是不是哈包幺幺,我们半是忐忑半是疑虑,终究顾忌着奶奶,没有去求证。
大风吹刮,草木摇落。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她不断地忘掉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又不断记起一些陈年往事,她甚至主动提起了她年轻时的情形。
那时候古道溪匪患丛生,奶奶被土匪追赶,为了逃命,她跳进后山几人深的苕洞,跌断了一条腿,从此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路。还有一个几岁的孩子,被土匪倒提着晃荡,那孩子后来再没有长高过。有老人说,他在长身体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倒过来了,所以无法再长了。土匪频繁下山,到老百姓家中烧杀掠夺。人们东躲西藏,颠沛流离。后来,土匪没了,可奶奶嫁到古道溪,又遇上恶婆婆。哪怕怀着身孕,婆婆也不曾厚待她半分。爷爷懦弱,不敢对抗母亲,就让奶奶到娘家避一避。娘家住得远,世事太平一些。那时候,娘家哥哥生了重病,奶奶也想趁此机会帮着嫂子照顾一下哥哥。
奶奶到了娘家才发现,兄长患病多日,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嫂嫂起先还端水喂药地伺候,后来眼见丈夫没有好转的迹象,耐心用尽,跟一个外乡人有了私情。奶奶的亲娘已是高龄,体弱多病,神智糊涂,每日里也仅靠着米汤续命。奶奶在娘家住了两年,生下儿子,再给相继离世的母兄二人送终后才回到古道溪。奶奶回来时,哈包幺幺都会走路说话了。奶奶在娘家生哈包幺幺的这段经历,我们是知道的。这牵扯到娘家嫂嫂的丑事,再加上奶奶素来不喜哈包幺幺。我们知道,但在奶奶面前从不说起。
“你学了治疗术,就要来给我治病啊。”这话,奶奶只在糊涂的时候说,“你再不来看我,就永远别想看到我了。”她似乎在跟谁赌气,说着狠话。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哈包幺幺到底在哪里,这真是一件锥心刺骨的事情。奶奶受了那么多苦,把哈包幺幺养大,不能连死都见不上一面啊。我们没能等来哈包幺幺,最后不得不离开古道溪,搬到明溪镇上。一年年过去,每到岁末年初,我们便怀着期待:哈包幺幺说不定在回来的路上,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出现在家里。
都说奶奶恶疾复发,其实,奶奶只是不小心吞下一根鱼刺,就再也吃不下别的东西了。去过好几家小诊所,可是人家办法用尽,也用仪器照过奶奶的喉咙,那里未见异物。但奶奶总说喉咙里有东西,嘴巴里有恶臭,还有沉甸甸的石头压得她出不来气。她吃不下任何东西,吃什么就呕吐什么,连水也喝不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奶奶日渐干瘪下去,几乎要被活生生饿死了。我们一筹莫展,心急如焚,不知道奶奶的恶疾竟会将她害到如此地步。
哈包幺幺是自己出现的。就在我们千方百计到处找他的时候,他突然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自己出现了,像一只老鼠,黄须黑面,一脸寡瘦,衣服也似几年都没换过。哈包幺幺说,他听到奶奶说的话了,奶奶说他要是再不回来,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其实,哈包幺幺早就做好了被奶奶大骂羞辱的准备,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那么凶狠强悍的妇人,居然变成了眼前这个苍老得毫无生气的垂死之人。哈包幺幺愣住了,他嘴巴里几百句服软求饶的话都哽住了,再也无法说出口来。奶奶听到动静,竟然有了力气,突然从沉睡多日的床上翻身坐了起来。奶奶用力抱住哈包幺幺的头,诉说久别重逢的欣喜。哈包幺幺温顺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人之间好像从没有过隔阂和怨恨,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接着,奶奶放开了哈包幺幺,满眼热烈地看着他,说她要喝“鸬鹚水”。我们面面相觑,随即明白奶奶的意思,她想要哈包幺幺用治疗术化一碗鸬鹚水来救她。哈包幺幺蜷缩在那里,好长时间不敢相信奶奶说的话。在我们的催促下,他才迟疑地爬起来,去厨房的筷笼里取出一双筷子,往白瓷碗里倒半碗水,插香烧纸后,双手拿筷子在碗里点了点。哈包幺幺抖了抖筷子上的水,接着转身朝外,在空气中画起符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哈包幺幺用治疗术。明明是平平常常的日子,他的身上却有一层光芒笼罩,衬托得他气质凛然。我突然发觉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我认识的哈包幺幺,而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治疗师。哈包幺幺神色庄重、肃穆,仪态威严,不由让人收起以往的轻视之心。也让人猜测,他这几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一边画符,一边念念有词。我看不懂他画的是什么,也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几分钟之后,哈包幺幺画完符,用刀裁下一截拇指长的筷子,丢进碗里的符水中,让奶奶喝下。可这时候,奶奶早已虚弱不堪,哪里还能吞得下那截筷子呢?求生的意志支撑着她,她拼尽全身力气咽下那半碗水,尽管大部分没有流进她那满是伤痕的喉咙,而是顺着干瘪瘪的下巴淌进枯瘦的脖颈里。奶奶还是用力砸吧了两下嘴,意犹未尽的样子。
“我害死了自己的女儿,我对不起香儿啊。”奶奶吞下鸬鹚水后,嚎啕大哭道。干涸的眼睛里突如泉涌,她刚喝下的符水变成眼泪又流了出来。哈包幺幺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哈包,你不是我亲儿啊。这么多年,我养你也养苦了。”哈包幺幺的鸬鹚水似乎化掉了奶奶喉间的鱼刺,她长吁一口气,终于吐出了她心中的石头,吐出这个压了她一辈子的秘密。她口舌得救,灵魂也得救了。我们闻之愕然,哈包幺幺更是震惊地抬起头来。接着他颓然坐倒,满面怆色。
哈包幺幺不是奶奶的亲生儿子,而是娘家嫂嫂的私生子。奶奶去娘家时,嫂子还在家。有一日奶奶不慎撞见嫂子偷情,她气愤难耐,不顾身孕,想要看清楚对方的面目。那个男人顺着小路逃得飞快,奶奶急怒攻心,便在后头拼命追赶。一个不慎,奶奶一脚踏空,从高高的土坎上摔了下去。她最终也没认出那个男人是谁,等她醒来后,才发现孩子没了。是嫂子救了她,将她从土坎下背回了家。嫂子在娘家待不下去,不辞而别。哪知道过了一年,嫂子抱着个婴儿又回来了。奶奶当然不肯再接纳她,那女人无处可去,又无娘家后亲可以投靠。她以死相挟,逼着奶奶赌咒发誓,认养这个孩子,而后自己十分爽快地跳崖绝命。奶奶流产后,深知在婆婆那里难以交代。就把那个野孩子带回了古道溪,当作自己生下的儿子。
这才是哈包幺幺的身世。几十年来,奶奶既觉得愧对嫂子,为自己当年逼迫她自尽而内疚,又觉得对不起哥哥,她毕竟在为那个背叛哥哥的女人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更何况为了哈包幺幺,奶奶甚至舍弃了亲生女儿。奶奶对哈包幺幺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情,她不知道究竟是爱哈包幺幺还是应该恨他。
多年来,奶奶守着这个秘密,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她宁可忍受痛苦,甚至为此死去,也不肯说出口来。但只要没人在旁边,她就会一直喃喃自语。她洗衣服时说,种苞谷时说,割牛草时也说。她对着青牛说过,对着黄狗说过,对着芭蕉树说过,对着石头说过,对着星星月亮也说过。她干了多少活,受了多少苦,就说出过多少委屈。这件事爷爷早就知道,只是奶奶忘了。那年冬天奶奶把哈包幺幺抱回家,亲口向爷爷承认哈包不是他们亲生的。可不是亲生也胜似亲生,那是他们舍弃女儿也要养大的孩子。
“吃鱼记着鸬鹚。”奶奶没理爷爷,从喉腔里喊出这句话后,眼睛从我们身上一一掠过,最后停留在哈包幺幺身上不动了。“吃鱼记着鸬鹚”是一句老话,在有鱼的餐桌旁,长辈们通常这样嘱咐小孩。鸬鹚捕鱼,是鱼的天敌。吃鱼时记着鸬鹚,便不会被鱼刺卡住喉咙。
“你梦中的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在奶奶的葬礼上,我终于找到机会问哈包幺幺。可他看着我惨淡一笑:“世上没有菩萨也没有治疗术,有的不过是抚慰人心的手段罢了。”说完,不告而别,最后消匿在古道溪的十万群山中。
自那以后,再无人找到哈巴幺幺。传说他已成为一名治疗师,终日与一头无名小兽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