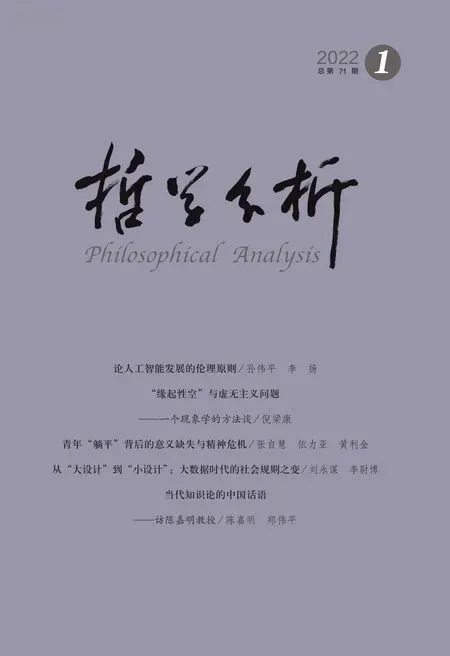西谷启治的虚无主义论及海德格尔批判
廖钦彬
一、前言
京都学派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接受海德格尔哲学并对其进行批判。例如,三木清立足于“根本经验”(Grunderfahrung)、田边元由人学发展出时空的辩证法对海德格尔的“此在”进行批判,以及九鬼周造以偶然、惊讶为基础的情绪论对“此在”及“畏”的情绪论进行批判。在这些批判之后,出席过海德格尔“尼采讲座”的西谷启治,根据自身独特的虚无主义观,描述与海德格尔相异的尼采图像,并通过对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考察,批判其存在论观点下的虚无主 义。
本文首先先介绍虚无主义在日本的历史语境,接着检讨田边元以忏悔道哲学立场如何批判尼采及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以此为基础,本文一方面检视西谷在《虚无主义》 (1949)中的尼采论以及他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与虚无之间关系的考察,另一方面探讨西谷在《宗教是什么》 (1961)中如何以空的立场克服尼采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虚无主义立场,借以分析在大乘佛教空或无的思想与现象学解释学之下,人之存在的不同含义。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思考近代欧洲与日本在哲学探究方式上的差异性所 在。
二、虚无主义在日本的历史语境
尼采思想在1890年传入日本,正好与欧洲对尼采的关注同步。其思想从一开始被介绍,接着在高山樗牛的文章中被提及,继而促成了日本研究尼采的风气。此外,又因生田长江的翻译以及和辻哲郎《尼采研究》 (1913)与三木清《尼采与现代思想》 (1935)的出现,尼采思想得以在日本发挥影响力。西谷自述虚无主义正是其本人哲学的开端。这一开端,并非来自欧洲虚无主义思潮,更多是来自他自身经历及其所处时代中的不安氛围。西谷与虚无主义的渊源,并非只是单纯的他与西方知识之间关 系。
此一态度可谓贯穿于其哲学的整体。西谷在《虚无主义》最后一章“对我们而言的虚无主义之意义”中,特别提及洛维特(Karl Löwith, 1897—1973)批评日本学生吸收西方文化的态度。洛维特指出,日本学生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不带有批判式思维及同时代的危机意识。从其批判可推测出,日本人学习西方文化,不仅会丧失自我,甚至有不明他者的危险性。当然,西谷借这一段话,是想说明自己会谈论虚无主义,并非只是单纯介绍西方哲学知识。虚无主义和他自身的生命无法分割开 来。
西谷这一自觉性的自我分析,却遭到日本当代学者的批评。佐伯启思在其新著《近代的虚妄:现代文明论序说》指出新冠肺炎标示出的当代文明危机。他在考察欧美近代文明发展到当代的人类思想进程后,试图从西田几多郎“无的思想”中找出一条能解决当代文明危机的道路。佐伯认为西谷在《虚无主义》中虽标榜虚无主义的世界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的问题,但在日本的历史现实当中,西谷本人并没有真正针对日本的传统及其价值观或绝对者作过彻底清算与颠覆。因此,其虚无主义只能算是一种氛围产物或流行现象。佐伯把西谷的思想标注为“近代日本的悲哀”。
可以推测佐伯的批判,来自他对西谷于“二战”前的右倾主义思想以及其“二战”后未对自身进行清算的保守主义态度的不满。显然作为虚无主义完成者的尼采,必不会对西谷的态度有所同情,甚至会和佐伯站在同一阵线严厉批判西谷的哲学倾向。佐伯的批判虽不无道理,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西谷在“二战”后被剥夺教职、面对日本百废待举的低迷氛围之内心呐喊稍加倾 听。
西谷认为,欧洲的虚无主义对日本人来说有两个意义。一是促发处在危机中的日本人自觉其危机,并使之在同时代的思想序列当中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让日本人能自觉自身的虚无——一种已成为其历史现实的虚无。一是促使日本人能克服、超越自身内部的空虚,为处于战败境地的日本人提供一个根源性的转换契机,以及一个能克服其精神空洞的方向。当然这种“以虚无主义克服虚无主义”的标语,到了其讲座论文《虚无与空》 《空的立场》中,有了极大变化,那便是以空的立场来超克虚无主义(将于后面讨 论)。
西谷的哲学敏锐度和同时代历史氛围、哲思动态紧密相连。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这一实存哲学发展脉络会成为流行思潮,不只因其源自近代欧洲这一特殊区域的思想,更多的是如西谷所言,已成为一种清算西欧、日本近代的旧价值观及人对存在的传统理解之思想渠 道。
另一方面,继西田几多郎之后的田边元,在“二战”后高举忏悔,借由净土真宗的绝对他力来批判其本人在“二战”前的理性主义立场,以及日本人存在的根本恶。此举带有双刃剑的性质:一是指向理性主义哲学所带来的哲学发展之停滞,认为理性唯有在四分五裂的矛盾深渊中,才有重新出发的可能;二是指向日本人的实存状况,认为日本人的实存必须通过彻底的忏悔,才能在死里求生。而包含尼采及海德格尔在内的实存哲学与虚无主义,自然也被田边置入在其忏悔道哲学语境中重新被加以讨论。西谷的虚无主义论虽是其后继之论,但和田边不同,他不从净土真宗的绝对他力出发,而是选择了龙树《中论》的“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以及《临济录》的“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此人处处不滞,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这条从空性到自在的解脱之道。(N8·185)
正如佐伯启思在《近代的虚妄:现代文明论序说》中主张现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不可分割性及差异性(如全球化、全球资本经济、民主主义、IT革命等)一样,若将西谷的欧洲近代性完全清除,并要求他遵循尼采与海德格尔的路径(回归希腊哲学传统)回归日本传统来进行传统价值批判,并从中找到重塑日本人的实存及其精神,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求。佐伯的现代文明超克论,仍旧延续西谷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试图超越近现代危机及困境的思想路 线。
三、田边元的绝对无与尼采论
如上所述,在西谷检讨尼采的虚无主义之前,田边元早已透过忏悔道哲学提出他自己的尼采论。为了回应倪梁康教授的文章《“缘起性空”与虚无主义——一个现象学的方法谈》所提出的问题,在此先作一个海德格尔存在哲学是否影响了京都学派哲学发展的俯瞰式检讨。具体先从检讨田边在《作为忏悔道的哲学》 (1946)一书中的绝对无概念之开展开始。因为这是继田边从2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的海德格尔批判之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针对绝对或无,田边如此说 道:
我一直强调,绝对便是无。能真正说是绝对,除了绝对无没有别的……然而,无无法直接存立。直接的存在都只是有。无只有在否定转换的媒介中,才会现成。当然,只要无是否定的原理,从其自体来说,必先于否定。然而,无法在否定、媒介之中被实现的无,若能事先存立的话,那么它就是有,不能是无。无并无法从存在论观点来处理。它只能够以行动的方式被信证。唯有进行否定转换的信证,才能让无的自觉成立。
“绝对”“无”“绝对无”这三个概念被田边等同视之,并被设定为必须和相对有(存在)之间形成否定转换的媒介关系。没有相对有作为绝对无的媒介,绝对无便会堕入相对有。反过来说,绝对无作为绝对无,不能缺乏相对有作为其否定媒介。因此,也不会是一种绝对无包摄相对有的情况出现。使绝对无与相对有形成这种特殊关系的,便是他力召唤下的忏悔行,亦即一种他力造就的自我否定之行动。可以说存在(空有或绝对无即有)是以实践被显露出来,不是从海德格尔那种解释学式的存在论来揭示 的。
海德格尔的早期哲学,以“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为出发点,对存在进行追问。在《存在与时间》 (1927)中,海德格尔便是从存在者(此在)来追问存在的意义,并以此为其存在哲学的基础。从对存在者、此在的在世存在、此在的情态性、时间性、脱自性、被抛的筹划等分析(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出发,重新探讨存在的意义,到中期哲学探求存在的真理、根据等转变的过程中,无(Nichts)成为海德格尔探讨存在时不得不去面对的课题。他开始集中论及“无”,可从《形而上学是什么》 (1929)中得到掌 握。
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虽处理的是“存在”问题,但绝不是要在“存在者”之外寻求某种东西或者局限于存在者、只与其打交涉,而是要通过对“超出存在者的追问”(即对“无的追问”)后,返回来对存在者进行理解。这里出现了一个分析视域的翻转。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指出“畏启示无”,认为“无”在畏的情绪中才能得以敞开其自身。无的敞开状态,便是“存在者之为这样一个存在者的源始的敞开状态(Offenheit)”。“无”显然是让存在者存在的场域。无与此在之间的交涉关系,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被凸显出来。然而,针对海德格尔对“无与此在”(田边所谓相对存在或实存)的解释,田边提出如下批 判:
海德格尔在其主著所说的虚无(Nichtigkeit)是非不(Nicht)的原理。其证明只停留在自我良心的责任自觉里,因此只是内在的应当之要求。这和绝对无的无(Nichts)在其转换中作为无化吾人自身的超越原理得以被信证的想法有不同旨趣。特别是他在其主著之后的就职演讲(1929)中,讲述了作为非不原理的无(Nichts),强调无先于否定,是其原理。然而,也因此无作为一种为了解释存在的情况,变得更加寂静。海德格尔用“畏之无的明亮黑暗”等来形容它,并主张存在被嵌入在无之中,畏的现象成为其此在的存在方式。存在因和这个无相对峙,而得以自觉,自由实存也因此得以可能。若从此点来看,这虽和绝对无有相通之处,但并非他自己在其中进行绝对转换以及死而复活的原理,反而是作为解释自己的自觉范畴,属于存在。如此,这和将自己作为自觉主体来加以维持,理性自我在理性批判中作为批判主体得以维持是一样的。实存哲学可以说始终无法脱离理性批判的立场。(T9·87—88)
据此可清楚看到,田边批判海德格尔的“无”(Nichts)的最核心主张是:作为理性主体的海德格尔本人,并没有在“绝对无即有”“空有”的绝对媒介关系中,通过他力忏悔行来信证自身的实存转换之真实。能让“绝对无与相对有”这两个在概念上的相互对立面形成辩证或交涉关系的,并非海德格尔将“无”作为分析对象的解释学存在论,而是在绝对他力的召唤下,真正对自身进行否定即肯定的转换运动理论。此便是主张“忏悔即救济”来阐释存在概念的忏悔道哲 学。
田边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论根据的本质》 (1929)中,注意到“其所谓虚无不是单纯的空虚,而是意味着绝对转换的无”(T9·90),“此在的无底、空虚,让自觉从过去的有解放出来,成为转向自由筹划的媒介”(T9·90)。但海德格尔这些无的主张,在田边看来,只是此在内部发出的“应当”“必须”之呼吁,因此仅仅是一种课题,而无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有直接关 联。
顺着这一海德格尔批判,田边将自身论述转向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共谋性关系上。田边将否定神的尼采与海德格尔视为自力圣道门的智者(超人),将自己和克尔凯郭尔放在他力净土门这一阵线上,自视为愚者。这一划分可说影响了西谷对两者的看法。针对尼采与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论,西谷主要以实存与哲学的立场来进行判释。这点和田边的做法一致。但西谷和田边的不同则在于不倚靠他力门,而是倚靠龙树的空及临济宗的“见佛杀佛、见祖杀祖”的绝对空及“见佛说佛、见祖说祖”的自在 观。
那么,让我们来检视一下田边的尼采观以及他对虚无主义的观察。总的来说,田边对尼采及其思想充满了同情与赞赏。然而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狄奥尼索斯”思想所代表的生命、自然、反道德主义,并没有走向田边忏悔道哲学所标榜的自我否定(他力忏悔行),始终保持了生命(意志)的肯定性、直接性与连续性,没将他力忏悔行中的否定性、媒介性与断裂性放入其视域中。权力意志标榜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肯定,尼采虽标榜反道德、反理性(反形而上学),却和康德一样,针对自身的理性主体没有再进行更深一层的批判(倪梁康教授所说的没有将空再进行空化,田边所说的绝对批判)。
尼采的转化生成(Werden)或变化(Veränderung)是一种生命的直接转化、生成,而不是忏悔的否定与转换。从这里可理解到尼采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将实存作为分析、解释的对象,或将“存在与存在者”“存在者与无”之间关系客体化。尼采的思想工作虽是其生命的绽放,但田边仍嫌不足,试图以忏悔道哲学立场来解读尼采的“爱命运”思想中的谛观及被动的能动性,使尼采思想靠近自己的哲学。他认为:“如尼采的爱命运概念明确所示,其思想核心可说是绝对否定的精神。不回避所有必然事物,特别是没落毁灭的死之命运,而欢喜迎接它,进而选择、接受它的绝对肯定,事实上必是以让自己在必然事物中死去的绝对否定为媒介。”(T9·103)
针对尼采的虚无论,田边亦站在同情的立场上,认为其虚无主义并非只是单纯的价值颠覆,在更深层意义上,属于尼采自身甚至是人类自身实存的生存境遇之显露,亦即“此在的破灭性、不安定性之显露”(T9·104)。当然,田边的这一善意解释,和尼采主张新价值是面对虚无、生成的结果有些不同调,但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的批判中看到类似的思考方向。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虚无主义标志的是对欧洲旧传统价值观的颠覆,而不是对存在的反思与建构。从上述内容我们一样能得知,西谷在《虚无主义》一书中何以承继田边立场,以实存与哲学来划分尼采与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的理 由。
四、西谷的尼采论
如前所述,西谷不以价值与哲学,而是以实存与哲学来区分尼采与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除了来自田边元与海德格尔的影响外,最重要的是其自身实存的问题。西谷在《我的哲学出发点》中自省是先从自在的(an sich)虚无,即先从自己的生死问题、人生苦恼开始其哲学道路的。他如此说明自己的哲学进路:“至少我自己是从那种前哲学的虚无主义开始做哲学的。因此说明在那之后的基本方向,首先是追寻虚无主义立场本身的哲学发展方向。其次是以哲学、批判的方式,来究明伦理和宗教的种种问题。最后是通过虚无主义,来寻求超克的道路。当然,这三条线是纠结在一起的。通过前哲学和哲学,对我而言最根本的课题,简单来说,即是通过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之超克。”(N20·191—192)这一态度在西谷的《虚无主义》第一章“作为实存的虚无主义”开头处中如实显露出来。他认为虚无主义首先是自己的问题。当自己变成疑问,自己这一存在根据对自己而言成为疑问时,虚无主义才会成为问题。虚无主义是切身性的实存问题,而非旁观或客观的知识与对象。(N8·4)
显然《虚无主义》最终没有呈现出西谷哲学的辩证轨迹,亦即:从自身存在成为问题所产生的虚无[自在(an sich)],到开始思考虚无主义产生的思想史脉络与自身的关联[自为(für sich)],再到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克服虚无主义[自在且自为(an und für sich)],而是在宣告第三个阶段时,西谷便结束了自己的虚无主义研究。他在此书最终章提到,尼采将大乘佛教的空或无思想理解为欧洲“极端的虚无主义”恰恰是对大乘佛教的误解,反倒是其爱命运及狄奥尼索斯思想才更接近大乘佛教的。(N8·184—185)
这里若对应到叶少勇教授的文章《对中观古学的认识论虚无主义阐释:以〈中论佛护释〉为中心》主张龙树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来看,可知西谷的空,并非真正龙树“中观古学”的绝对空,而是清辨之后“中观今学”的“空即有、有即空”之立场。西谷会采取后者立场的原因,可能是未能见到梵文《中论颂》的真正内容,亦可能是他认为绝对空尚不足以回应现实世界以及他所处情境的现实需求。笔者认为,西谷的“中观今学”立场,恰好可以符合他对欧洲虚无主义的回应。上述的讨论亦可对应到何欢欢教授的文章《缘起性空:一个流动的假名或真实》援用印顺“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之立场的主张。“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的阐释对应的正是“中观今学”立场。关于近代中国与日本对空的理解与掌握,需另辟机会重新讨论,在此先搁 笔。
西谷在《虚无主义》第一章阐明自己的哲学出发点后,开始说明近代日本人和近代欧洲文明的不可分割性,并归结出虚无主义蕴含了超时空与时空、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性),据此展开他对欧洲虚无主义发展史的掌握。西谷在《虚无主义》第二章“从实在论到虚无主义”中,企图为完成于尼采的虚无主义打造一个系谱,亦即尝试勾勒一条欧洲虚无主义的发展脉络。西谷认为虚无主义是继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实在论而产生,实在论又因这些哲学家对德国观念论代表者黑格尔的反扑而诞生。在西谷的梳理下,一条“观念论→实在论→虚无主义”的思想脉络被呈现出来。尼采则是出现在此脉络中的终极虚无主义者(N8·18—43)。
西谷指出尼采晚年思想的代表著作《权力意志》 (1901)标榜“对一切价值转换的尝试”,说明世间所有价值皆会为人带来虚无感,唯有彻底揭露潜藏在一切价值根本处中的虚无,亦即对价值本身进行价值评估与批判,才能奠定新的价值与意义(N8·45, 50)。人唯有彻底活在虚无深渊当中,才能促使自己走向彻底肯定生命的立场。西谷认为尼采所谓的欧洲虚无主义,须分成两个层次来理解。一种是基督教及其道德出现以前的虚无主义(自在的虚无主义,西谷称为自然的、无自觉的虚无主义),另一种是其出现以后的虚无主义(自为的虚无主义,西谷称为极端的、自觉的虚无主义)。关于此,西谷如下解释道:“那个被称为欧洲虚无主义的东西,和其他各种虚无主义,亦即和所谓直接的、从人类的生存直接产生的虚无主义是不同的。应该说,欧洲虚无主义是通过克服那种虚无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基督教道德)之破绽后所产生的高层次虚无主义。尼采特别将欧洲的虚无主义称为激进的虚无主义或‘极端的(extrem)虚无主义’之意义,也在于此。”(N8·54)
西谷以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尼采的虚无主义,亦可在《虚无主义》附录其一“尼采的虚无主义=实存”的结论处看到。他指出,在尼采的虚无主义论述里,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出现便是要克服上述自在的虚无主义。然而,与此同时,宗教与形而上学亦为自身带来人“对无的意志”(“和生命敌对的生命”),亦即一种意志的虚无主义。当人开始不相信这两者时,真正的虚无主义才显露出来。此为上述自为的虚无主义。西谷又将此种虚无主义称为“强大的虚无主义”,它是一种坐落在人自身的虚无主义者的虚无主义。实存在此和虚无主义被画上等号。新价值的诞生正来自这一作为实存的虚无主义。(N8·230—231)
从这点来看,西谷对尼采虚无主义的解读,可说与田边元、海德格尔是同一个视域的。直言之,虚无主义是和存在者(此在、实存)有直接关联的哲学问题。这也是为何西谷在第六章“作为哲学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从早期哲学的立场来探讨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论的原因。只是海德格尔的无和田边的绝对无、西谷的空有极大差异。这差异正来自三者各自独特的哲学 观。
秋富克哉在《海德格尔与西谷启治:关于尼采解释》中,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他指出西谷在1937—1939年恰好出席了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却不从海德格尔中期思想出发或直接讲述其尼采论,而是从其早期哲学来讨论虚无主义,并将其虚无主义思想列入在尼采之后的欧洲虚无主义发展脉络。由于秋富没有考察田边元对尼采及海德格尔虚无主义的讨论,因此忽略了田边对西谷影响的历史片段,而称此做法是西谷的特色,其实不然。在西谷之前,田边早已从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审视其虚无主义思想及其与尼采的关 联。
至于为何要从前期谈论,已如上所述,那是因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从此在(存在者)来考察存在,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 (1929)从此在的有限性来考察形而上学,这两本书皆是从此在(实存)出发来探讨存在,而不是从存在的根据(无)、真理来探讨此在。前者的立场恰好和西谷想建构的欧洲虚无主义发展脉络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想超越这些欧洲“实存=虚无”主义者的主体主义立场。详细将于下一节讨 论。
值得注意的是,西谷在《虚无主义》附录其一“尼采的虚无主义=实存”中,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作了一个区分,认为两者虽都针对形而上学有所讨论,但尼采的虚无主义更具有道德(moral)意义。换个角度说,西谷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虚无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方向。相对于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理解尼采的道德,西谷则将道德与形而上学分开来讨论与诠释。
具体来看,比如西谷分别从《论道德的系谱》 (1887)、《瞧这个人》 (1908)举出尼采针对基督教的共苦(Mitleiden)道德提出的严厉批判,目的在于阻止基督教在慰藉人各种苦痛、烦恼(即救赎人)时,让人产生了无的意识(即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这将会阻碍人们的生命意志力,而走向对宗教的依赖。尼采认为这样既不能拔人的苦、治人的病,也无助于创造人类的未来。尼采这一批判的根本就在于虚无主义的实践化。西谷的这一见解恰好是想凸显出,尼采的虚无主义虽持有基督教残余的道德,却形成了和基督教道德完全不同的道德。尼采又称这是一种“正直的道德”“连道德本身都粉碎的道德”“生成的道德”。(N8·192—195, 208)我们可以说这正是西谷有别于田边的独特尼采论或虚无主义论。只可惜这个道德的问题,并没有随着西谷的空思想而被展开在《宗教是什么》当 中。
关于海德格尔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理解尼采的道德,也让我们具体从《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1943)来进行理解。秋富依据海德格尔“尼采讲座”第三、四讲的内容,指出海德格尔从价值重估来理解尼采的道德。事实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便是将焦点放在“价值”概念上。海德格尔认为价值的本质就是成为观点或视点,它必须起作用。而生命饱满的强力意志,便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一切价值要被重估时的价值设定来源。因此当强力意志成为真实,便是新价值诞生之时,此即尼采自己宣称的“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但海德格尔并不这样认为)。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道德显然没有被视为问题来加以讨论。这也是西谷读了此篇文章后,开始强调尼采的道德论之缘由。这正好显示出西谷与海德格尔对尼采虚无主义的掌握有不同的侧 面。
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集中篇幅讨论的是强力意志(意志强烈意愿它自身、显露它自身)。强力意志即是存在者整体的本质。尼采在《快乐的科学》 (1882)中标榜“上帝死了”,透露出虚无主义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的显题化。包含基督教所有一切价值在内,其最高的存在者——上帝、彼岸世界(非感觉世界)的崩坏,正意味着柏拉图以来欧洲形而上学世界的崩坏。“上帝死了”这个标语带出的是“一切价值的重估”。可以说“虚无主义就根植于价值的统治与价值的崩坏之中,从而也就植根于一般价值设立的可能性之中,价值设定本身是以强力意志为根据的”。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通过“上帝死了”带出虚无主义、价值重估、强力意志,似乎想给予世人“终结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形象。然而,事实不然。因为这一虚无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只是用强力意志或超人来取代上帝这一超越者的地位、填补这一超越者的空位而已。价值的形而上学家、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家,便是海德格尔给尼采贴上的标签。他利用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这一组存在哲学的概念,通过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对基体(Hypokeimenon)及不可怀疑、确定可知的东西之追问,试图将尼采的强力意志视为一种根据、基 体。
关于此,海德格尔如此直言道:“在尼采关于作为一切现实的‘本质’(Essenz)的强力意志的学说那里,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到了完成”,“尽管尼采对形而上学做了彻底的颠倒和重估的工作,但当他把在强力意志中为意志的保存而固定下来的东西径直叫做存在或存在者或真理时,他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传统百折不挠的道路中”。在此,尼采被塑造成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完成者。这和西谷在《虚无主义》将尼采塑造成虚无主义的道德实践者有很大的差异。然而,情况到了西谷提出以空的立场来克服虚无主义时,却有很大的转变。西谷显然采用海德格尔批判尼采的方法,将尼采与海德格尔划分在虚无主义者的主体主义立场之中,并援引艾克哈特“作为绝对无的神”的想法,对两者进行批 判。
五、西谷的尼采与海德格尔批判
如前述,西谷在《虚无主义》第六章“作为哲学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从海德格尔早期哲学来讨论他的虚无主义思想,并将该思想列到尼采之后,是为了要在欧洲虚无主义的发展脉络中为海德格尔找一个位置,以便将这些实存主义者们的虚无主义立场进行清除与扫荡。正如《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中所言,探讨虚无不一定得是虚无主义者(当然探讨实存不一定就得是实存者),对西谷而言,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最后都成了具有主体主义色彩的虚无主义者以及实存主义者。以下将重点检视西谷所理解的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如何被联结到他所勾勒的欧洲虚无主义脉络 上。
西谷一开始就先说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特性。他认为,海德格尔承继了从实存出发而排除学问、绽放热情的克尔凯郭尔、尼采,以及在自然、历史世界中,为捍卫人类而要求学问严格化的康德、胡塞尔、狄尔泰等哲学家思想,打造出一个和传统形而上学全然不同的、实存主义下的存在哲学。(N8·144—146)在海德格尔早期哲学诸多概念中,西谷最重视的是“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西谷解释存在者与存在者的差异是“存在的(ontisch)差异”,存在者(包含实存、此在)与存在的差异是存在论的(ontologisch)差异,对海德格尔来说更重要的是后者,因为探讨存在根据才能算是哲学。前者的讨论只停留在存在者间的问题,后者的讨论才是真正面对无与存在的问题。这在田边的语境中就是相对有(有与有、有与无)之间以及绝对无与相对有(绝对无与有)之间的问题,在西谷的语境中就是有与有之间以及有与空之间的问题。《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工作集中在从此在来理解存在。这相当于田边与西谷所说的,从有来理解空或无之义。《形而上学是什么》则试图从无来解释存在与存在者,从田边与西谷的语境来看,则是从空或无来说明 有。
为了说明海德格尔的工作,西谷依序谈论了世界内存在、此在的情态性、时间性、脱自性、超越、被抛的筹划、向死的存在等概念,并指出作为此在根底的虚无必然显露出来,虚无主义被包含在实存哲学的基础当中。(N8·152—153)西谷具体以“被抛的筹划”“超越”,来说明此在是“命定的自由”之存在,以及此在与无或虚无之间的关联。西谷引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的“如若没有无之源始的可敞开状态,就没有自身存在,就没有自由”(N8·159)来说明这种超越、脱自的此在之成立可能性,和其根底的无或虚无有着紧密的关系。笔者认为,西谷应该将海德格尔紧接下来对无的看法揭示出来。海德格尔 说:
无既不是一个对象,也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无既不自为地出现,也不出现在它彷佛与之亦步亦趋的那个存在者之旁。无乃是一种可能性,它使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得以为人的此在敞开出来。无并不首先提供出与存在者相对的概念,而是源始地属于本质本身。在存在者之存在中,发生着无之不化(das Nichten des Nichts)。
据此我们不得不说,海德格尔的无已相当接近京都学派存在论的话语范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虽非对象,但它作为有的根据或本质,却是京都学派极为戒备的说法,因为空(无)并非有的根据,而如何谈论空(无)与有的交互媒介关系,才是京都学派哲学的关心所在。用田边的话来说,无是实践出来的,不是解释出来的。海德格尔的无只要是此在的根据、推动者,事实上仍属于相对有的层面。这个无,还得不断地与有的无化一起对自身进行无化,方能是绝对无(西谷的空即有、有即空的论述将于下面讨论)。若能为海德格尔辩护,那便是他说的“畏开启无”,因为无的显现始终和此在(实存者)的最根本情绪——畏,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无的显现不能切割有。无的开显也使得此在超越自己而得以是自己。除“被抛的筹划”“超越”外,西谷特别提到《存在与时间》中的“向死的存在”与无或虚无之间的关联。西谷说 道:
刚已说过,无开显在人的根底,人才能得以成为他自己,应该说才能得以回到他自身。通过无的开显,人才能作为他自己而存在,才能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是向死的存在,亦是同样意思。人是理解存在的存在,因而是自觉自身存在的存在,这意味着人从其根底的无、作为向死的存在来掌握其自身存在。(N8·161)
这里的理解和上述关于此在与无的理解,事实上是一致的。即使在他阐释《康德与形而上学的问题》中的此在有限性以及它与无、超越之间的关联时,亦是站在相同立场。西谷经常将无和虚无混用在他解释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脉络里,其最大的目的是想要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置入在他自己以辩证法方式梳理出来的欧洲虚无主义的发展史之中。西谷在《虚无主义》中并没有针对海德格尔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将其存在哲学中的哲学性格(作为一种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淡化,并突出海德格尔早期哲学与虚无主义之间的关联。那么,西谷如何以自身空的立场,来克服尼采及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立 场?
在此若回顾《虚无主义》的尼采论,可知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从一种自在(自然)型态到自为(自觉)型态的一种转变。在尼采激进虚无主义的立场下,一切价值才能得以通过强力意志被加以重估。然而,西谷在几年后写下的《虚无与空》中,对这种自为型态的虚无主义立场提出了质疑。他说:“现在有很多实存主义者,借由对自身存在的诚实,果断、自觉地立足在虚无,亦是这个缘故。这种实存主义下的积极虚无主义标榜的是,脱离人的机械化、避免沦为无自觉虚无主义下的欲望人类。……然而,同时这个虚无因为该倒逆而被开显出来,在这个倒逆根底中开显出来的陷阱,不外乎是虚无本身。只要立足在虚无,该倒逆根本无法被逃脱,因为虚无无法脱离虚无本身。”(N10·99—100)西谷在这里已经很明确地说明,用虚无来克服虚无,只能是批判虚无的无限循环,根本无法彻底脱离虚无所带来的束缚与执着。这里暗示着思想必须要有彻底的翻转。空的思想在这里被提了出 来。
事实上,同样的批判亦落到海德格尔身上。西谷认为:“虚无对人的自我存在而言成为脱自的场所,虚无主义成为一种实存的立场。虽说如此,但在虚无主义里,无仍带有无这个存在的表象痕迹。”(N10·108)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无虽说不是对象、客体存在,是一种主体自觉的存在,但它仍脱不了“对此在自身而言的虚无”,仍旧是“站在此在这一方来揭示的虚无”。无始终还是作为此在的否定概念、和其相对立的无。(N10·109)这里说的只是相对有(即相对立场的有与无)之间的关系。西谷认为要脱离西方相对有的想法,唯有将这种思维转换为空的思维。“空就是要空化将空表现为空的存在这种立场,这样方能是空。”(N10·109)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范式的大转换,而不是思想的批判循环。当然,西谷在阅读完《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后,必然会认为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判恰好是对他自己的批判。在京都学派的空(无)思想笼罩下,海德格尔恐怕很难挣脱“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之荣 冠。
西谷将东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以“意识之场→虚无之场→空之场”的序列来表示。他认为意识与虚无之场,无法离开空之场而成立。所有事物唯有在空当中,才能是它本来的、根源的面貌。在空当中,所有事物既非实体,亦非主体,而是超越主客关系的自体。针对这个自体的存在方式,西谷举出“火不自烧”(火不烧火)的例子。他说:“火不烧火这句话,就是火这个存在是无法烧火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下,这是针对火的本质存在来说的。然而,这句话也意味着现在火正在燃烧,那里现在有火。……火的本质存在和现实存在变成一个。”(N10·131)火既非实体(是、本质存在)亦非主体(有、现实存在),它是它自体(空)。“用佛教语言来说,若火有‘自性’的话,火自体就在所谓‘无自性’之中。”(N10·132)自体的存在方式完全否定自我同一性,是一种“有即空、空即有”或“色即空、空即色”的“二而一、一而二”之存在方式。这是火的如实或真实存在方式 。
根据以上西谷对空的说明,可了解到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与无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不会出现“此在即无、无即此在”这种违反逻辑的说法。海德格尔的无,可以说还是在自我同一性立场下的否定概念,并非铃木大拙和西田几多郎所说的“即非逻辑”下的绝对否定概 念。
六、结论
欧洲虚无主义与实存主义的流行,产生在某些特定的时空,却又超越时空,影响了欧洲以外的地区,大放其彩。京都学派哲学家除西田几多郎外,大多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特别是他早期的实存哲学。也因其影响,他们各自发展出自身独特的哲学。不可讳言,无论是田边的“种的逻辑”、忏悔道哲学、死的哲学,还是西谷的禅哲学(空的思想),皆是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而产生。但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在上面的探讨中,已经可以找到明确答案。事实上,作为有的西方哲学和作为无的日本哲学,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后者批判前者的批判循环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可以间接呼应倪梁康教授主张唯识宗(自性)与中观宗(空性)“二而一、一而二”的一体两面关 系。
在近现代欧洲哲学的发展脉络中,海德格尔会展露头角,绝非偶然。他借由回归希腊哲学传统对其时代哲学思潮进行批判,并从中找到一条自己的解释学式的存在哲学道路。京都学派同样受到欧洲哲学洗礼,自然也不会错失这个世纪性的哲学思潮大转换。当然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式的存在论,始终脱离不了主客二元的观点,从而不会是人自体式的自我开展之哲学。之所以会有这种景象出现,是因为京都学派背后的东方哲学(儒释道)传统,提供了日本哲学与欧洲哲学对话的思想资源。如倪梁康教授在其文章结论中所言,龙树的空性与笛卡尔的怀疑(甚至胡塞尔的悬搁),是有别于西方知识论、本体论的方法论。这种作为方法论的空,在京都学派的哲学开展脉络下,变成了一种作为“实存论=实践论”的空。西田与西谷的是宗教实存式的艺术创造论,田边的是宗教实存式的救济实践论。空不仅在看待世界的方法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还开辟了创造世界、活出世界的另一种当代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京都学派的独创,而是在中日的传统禅思想当中早已能窥见,只不过语境有所不同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