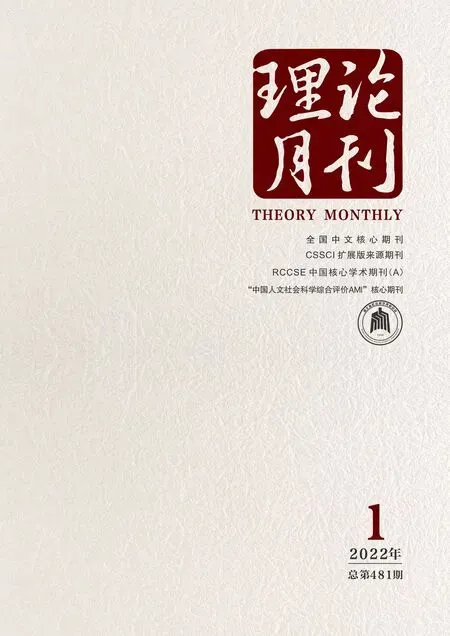《路得记》女主人公“他者”性别形象超越的层次性
□李 瑛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相对其他文学形式,女性在宗教文学中被重点记载的例子并不多见,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圣经文学中亦然。具体看《旧约》,就整体以女性为核心进行专章记载的文本数量而言,全书一共39 书,其中大多书以男性人物命名,以女性名字命名的仅有两书,《路得记》即为其中之一,可见路得形象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历史传承的重要意义。《路得记》描述的是,丧夫后追随婆婆拿俄米到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得,在异国他乡努力融入当地的父权文化,成功地与当地德高望重的富户男士波阿斯联姻。而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不仅与无夫无子的前婆婆拿俄米分享“母亲”名分,使其有了伦理意义的依靠,而且因对丈夫波阿斯家族的人脉传承贡献,后来以犹太民族伟人大卫母亲的身份被记入犹太史册。女主人公路得勤劳忠诚又勇于突破。一个女人从无依寡妇、可怜儿媳、寄居的陌生女子到富户妻子、生子让名的儿媳、未来民族领袖母亲等一系列身份纠结和伦理矛盾的调和历程,呈现出一位追求卓越的平民女子的性别形象特征,是学术界公认值得研究的经典人物。
《路得记》人物研究具体如何切入?从分析方法来看,在文学艺术领域,性别研究独树一帜,可以极大地拓展对人性深度的理解。作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女性学领域具有开创性影响力的学者,李小江强调“具体到历史文化集中浓缩的文学艺术形式,性别研究一直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从性别角度对‘文本’进行解构,挖掘出我们潜意识中的疏漏和压抑,极大地丰富了人性的内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扩展精神空间”。在《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一书中,李小江谈到,性别分析方法“在哲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同阶级分析、精神心理分析方法一样,深入切进人类社会个体生命,成为我们认识自己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性别分析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从自在的同一(远古时代)到人为的对立(文明时代)到自觉的认同(当代),是历史在高层次上的会返。正是在这个最终的‘认同’中,人的行为终于有可能挣脱纯粹自然的羁绊,在顺应自然的约束力中获得现实的自由”。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文学经典之一,《路得记》文本中记载的女性性别人物形象可能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代表性,性别视角的切入方法,应该可以挖掘到更丰富的价值。
查阅目前直接或间接涉及《路得记》人物研究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以家庭伦理类或信仰分析为主,有的强调《路得记》中人物关系中的信仰之爱,如《一首爱的赞歌——〈路得记〉的解读》(何宏伟,2009),《从〈路得记:信仰之旅〉看世间爱为何物》(张景成,2013);有的解析《路得记》中紧密联系的家庭关系或社会伦理,如《古犹太民族的和谐社会理想——以〈路得记〉为例》(梁工,2008)、《〈路德记〉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李顺华,2006)。另一类与西方女性主义哲学或与女性社会独立分析有关,这些文献或宏观或微观,有单纯从女性性别的视角分析《路得记》中人物言行,如《狭隘女性主义〈圣经〉观的弊端》(何花、胡宗峰,2012),《〈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李滟波,2004);有的从综合的社会学角度诠释《路得记》,如《〈圣经·旧约〉的女性形象再解读》(黄玮,2017)。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前一类研究偏向于粗泛神学的视角,难以对人物的复杂特质展开细腻分析;后一类研究容易陷于女性主义派别对立的政治视角,观点分歧、难以整合。同时,二者都对文本在宗教哲学里的父权文化背景关注有限,对女性性别超越方式的多样整体性考虑不足。因而本研究在宗教哲学父权文化视域下,以性别研究为主线,综合女性主义的多元视角,从女性性别“他者”超越性具体层次出发,尝试对《路得记》女主人公复杂的性别形象进行整合分析。
一、父权社会的性别关系框架
“父系社会是人类自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真正起点”,但是父权背景下的女性观却并不一致。从性别哲学的思维模式上看,“性别差异可以一直追溯到精神本身最深的根上去”,映射了人类精神的基础之源。女性主义性别分析立足于父权(Patriarchy)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制度大背景,聚焦于主体人性别区分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人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形态,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从社会历史宏观视角出发的交往进化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从多元主体关系中个体存在等价性出发的他者观等,但真正实现了人属性的二元差异对立关系“向类的回归”的是宗教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的关系本体论(the Relational Ontology)。从宗教哲学史地位看,马丁·布伯的关系本体论是将对立统一的二元关系进行美学论述的最高典范。
(一)“太初即有关系”:“我—你”,而非“我—它”。总体来看,马丁·布伯将人类二元关系分为两大类,即“我—你“(I and Thou/You)和”我—它“(IIt)。前者是立足个体的一种带有高度人格乃至生命审美的人际关系,后者是隔绝世界的孤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他人的一种工具性人际关系。
关系本体论强调,人类社会“太初即有关系”,这个关系是“我—你”而非“我—它”。具体而言,先天之“你”实现于与相遇者之亲身体验的关系中。人可在相遇者身上发现“你”,可在唯一性中把握“你”,最后可用原初词陈述“你”。这一切均筑基在关系先验之根上。但是,随着历史制度的累积和人性复杂性的发展,世俗社会却脱离本源而陷入以“我—它”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对于“我—它”,即一种人把世界以及世界上包括他人在内的所有在者都当成与我相分离、相对立的对象或客体,是为我所经验、所利用的东西。对于这种人来说,所有这些在者,即所有“他者”(the Other),便都是“它”,整个世界因此也就成了一个“它”之世界,人与对象因此便是一种“我—它”关系。马丁·布伯虽然承认人同世界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必要的,因为人离开了同世界的这样一种关系,且不要说人类进步将会因此变得不可思议,而且人的自身也会因此而变得难以维系,然而在布伯看来,“我—它”关系毕竟不是基本的人类关系。因为当我们站在一个人的面前,用主客二分的眼光把他作为一个认识对象和利用对象来审视他,那他也就因此而不再是一个主体,而是成了与物品一样的东西了,这是相互主体性价值所不容的。所以在关系本体论结构里,如果说“你”的主体性存在是被高度肯定的,那么“它”的主体性状态则是被绝对否定的。
(二)“关系的动态化”。同时,马丁·布伯指出“我—你”和“我—它”之间存在“关系的动态化”。他认为,虽然由于他人的唯一性,自我对他人产生了责任而以“我—你”方式相待,但“当关系事件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同时,“由于他人的超越性,个别之‘它’因为步入关系事件而能够成为‘你’”。也就是说,在具体的二元关系互动过程中,与“我”对应的“他者”可以从绝对工具性的“它”转换成具有高度主体性特征的“你”,或者与“我”对应的“他者”可以从具有高度主体性特征的“你”转换成绝对工具性的“它”。
马丁·布伯关系本体论是整合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观而衍生提炼的,他将此论述运用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中,强调“人类的双重性决定了世界的双重性”,即“我—你”和“我—它”两种关系虽然性质迥异,但在具体个人社会生活中同时并存、界限模糊,如果将具体的关系属性单一化成“你”或“它”将导致人无法生存。人类即需要将外界人或事物看成“你”,也需要将其看成“它”。
(三)性别关系与关系本体论。就性别关系而言,在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明确定位上,马克思进一步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也就是说,男女性别关系品质其实浓缩了具体人性价值观整体的方方面面,是个体社会价值观的集中表现。因此,马丁·布伯关系本体论虽然并不是直接针对性别区分提出的,但由于其描述二元关系的经典性,完全可以用在社会关系核心的男女性别关系中序二)。
关系本体论中,本源性的“我—你”关系是一种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工具性的“我—它”关系则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我—你”关系中,双方是相对主体,来往是双向的,“我”亦取亦予;在“我—它”关系中,“我”为绝对主体,“它”是绝对客体,只有单向的由主到客,“我”只取不予。因此“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中的“我”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前者意味着互利共赢的理性价值观,后者则是剥削利用的欲望价值观。具体到从父权社会男性本位出发的性别观中,可以对应为表示男女性别平等的“我—你”性别观和反映男尊女卑地位的“我—它”性别观;前者男性尊重女性、平等待人,后者男性蔑视女性、压抑人性。
二、女性主义研究的起点
女性性别“他者”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起点。在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中,“他者”(the Other)与“自我”(the Self)是一对重要范畴。基于性别关系在漫长历史中同一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在传统父权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奠基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明确提出了“他者”概念作为女性性别研究的起点。波伏娃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和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他者”概念,融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的身体哲学,将“他者—自我”的对立引入性别关系辩证法。根据波伏娃对女性的分析,女性作为“第二性”,父权制必然以代表“人”绝对标准的男性自我主体性第一性的需求将女性视为附属的“他者”。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传统主体论为了突出“自我”而对“他者”形成的绝对否定,女性主义性别“他者”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男女同为主体的建构,其前提是对“他者”的异质现象的尊重。
根据女性在这种“他者”位置中可能实现的自由度,女性“他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绝对他者”(absolute other),即一种绝对被动的、客体性的存在,“其自身不能给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理由,需要他人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以这种状态存在的女人“实质上就相当于物的存在水平,而失去了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地位与价值”。类比父权背景的性别关系本体论,相当于典型的男性将女性当成完全的工具价值,利用性别政治压抑女性的“我—它”关系中的“它”。
另一类是“相对他者”(relative other),即带着主动的自我定义和超越性对另一方主张相应的权利,让自己的“他者”概念以其相对性失去其绝对意义,使原来以“绝对他者”形式存在的“无我”状态被放弃、并由此形成个体自我。对于平等关系而言,男女虽然有别,但彼此互为“相对他者”。类比父权背景的性别关系本体论,相当于男性带着尊重女性为人绝对价值的起点,忽视性别尊卑的“我—你”关系中的“你”。
“绝对他者”是没有摆脱客体性的人,“相对他者”是融合了他者性和主体性的人,前者完全处于性别文化的奴役之中,后者兼有主体性和客体性,同时兼具内在性和超越性。女性超越性别的目标就在于走出“绝对他者”成为“相对他者”;在男女性别类属中彼此同为“人”,二者具有共同的主体性尊严的基础上,从父权社会关系中曾经被否定的“它”转变成被充分承认的“你”。
女性主义理论庞杂多样,“他者”维度具有多样性和内部矛盾。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形态多种多样,按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罗斯玛丽·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在其《女性主义思潮导论》(Feminist Thought: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一书中的归纳,按照历史顺序,可以归为八个类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每个类别有多种分支,例如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有至少两个经典分支:以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为代表的支派强调女性作家独立于男性作家方式的“阴性书写”,突出女性可以借用男性目光通过“他者的他者”实现性别自我的内在支持;以朱莉亚·克里斯多娃(Julia krystova,1941—)为代表的支派认为女性能够融合母性的“符号期”和父性的“象征秩序”,在社会性别意义上实现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间自由行动。总体来看,当代西方大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发展有两点共同主张:其一,肯定女性的重要性和价值;其二,女性需要进行社会变革获得安全满意的生活。面对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和历史,女性主义的核心目标是“消除所有形式的支配权,包括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支配权和发生在女性之间的支配权”。
然而从内部看,女性主义理论观点由于选择了不同立场而形成巨大的“他者”差异,一些派别的观点经常互相冲突对立,调和内部矛盾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不容置疑,女性主义“每个流派都是了解女性经历的一面镜子,每个流派都有助于对某些特殊现象的理解”——可以说,女性主义观点的多样性,表明了不同的女性主义者对同样问题持有精细的多维度见解;女性主义思想架构的丰富性是女性主义健康发展和成果丰硕的表现。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内部观点分歧,女性主义可能会引起混乱。在美国,一些保守媒体利用分歧现象,通过一些负面的新闻事件对女性主义强化一种“女人反对女人”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使女性主义者和她们的想法看起来琐碎而毫无价值的方法之一,是将女性描绘成一个彼此争论不休的群体”,由此将“女性主义”学术进行标签化和丑化。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义自身需要从更基础的哲学维度上进行有效的整合,以化解其因差异而产生的一些弊端。下文以《路得记》女性为对象,试从宗教哲学的二元关系本体论角度做进一步探讨。
三、路得性别“他者”凝聚的复杂性
“性别”(Gender)观一直是父权社会秩序的底层逻辑,浓缩着国籍、种族、肤色、阶层、伦理等各种差异,经常是政治文化争论的焦点。经典的宗教文学是生存美学的底层价值,《路得记》中女性路得在具体性别关系中即呈现出这种弱势混合的复杂性。
(一)路得在伯利恒作为女性“它”的复杂社会中的处境。虽然在故事的结尾路得赢得伯利恒女性乡民的一致赞誉,不仅成为波阿斯家庭的生育功臣,而且由于后辈的伟大贡献在当地史书中成为备受国家尊敬的“相对他者”之“你”。但是分析文本,初来乍到伯利恒的路得,从性别的社会内涵而言,她不得不承载着国籍、阶层和辈分伦理等多方面的苦楚:
国籍身份。传统犹太律法非常敌视摩押。在历史上,犹太民族和摩押族势不两立,这在《旧约》中有多处且长篇的记载。例如,在《以斯拉记》第九章和第十章专章记载了犹太族权威谴责与异族的通婚、并立法严格终止包括与摩押族在内的已有事实婚姻,立法者把以色列男性与摩押族女子通婚视为最大的“叛国罪”之一。路得第一次在波阿斯田地拾取麦穗时,波阿斯家丁描述她的一句话中就两次强调了她的国籍:“她是魔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路2:6);波阿斯在商议赎地和路得婚姻归属时为了尽力排除另一位亲属的可能性,也三次强调了路得的国籍:“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路4:5),“你从拿俄米和摩押女子路得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买死人的妻子”(路4:6)和“我也娶冯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得”(路4:10)。由此可见,来到伯利恒的异族女人路得,社会关系最大的困境可能是被完全否定乃至敌视的异国女性“它”之处境,面对当地社会民众带着强大宗主国身份的绝对自我感。
社会阶层。波阿斯在伯利恒,出身于父母在约书亚时代有建国英雄贡献的名门望族,而且他的父母是在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证婚下结合的。对于有显赫出身背景的波阿斯,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伯利恒集名利于一身。正如《路得记》第二章提到波阿斯时,特别强调“是个大财主”;同时,波阿斯以仁义公正的形象建立了非常好的公众信誉,从第二章与收割乡民的招呼互动和第四章他在城门召集商议赎地和路得婚姻归属的过程看,他可能是全城最有号召力的公众领袖,其父权男性“我”的社会影响力在伯利恒是屈指可数的。以此为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路得第一次见到波阿斯时形象是“脸伏地叩拜”,她身为一个孤寡贫困不如波阿斯田间女仆地位的底层乡民之“它”,更衬托出波阿斯拥有权贵威望的绝对优势。
辈分伦理。路得的公公以利米勒家和波阿斯家族有亲属关系,从家族辈分看,波阿斯和路得跟随的拿俄米是同一代人,因此,路得作为拿俄米的儿媳,对波阿斯来说属于晚辈。从代际伦理看,波阿斯作为父权长辈对路得是有权威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见到路得时,波阿斯和拿俄米一样,对路得以“女儿”方式称呼。从文本明显可见,在家族伦理上,波阿斯的形象更有力量,路得相当于处于代际权力之“它”的家族位置。
从路得和波阿斯性别关系地位的整体对照来看,按照经文路4:12“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她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显示,最终实现的波阿斯和路得的联姻继承的是先辈犹大和她玛的先例。比较路得和当年她玛性别“它”之处境,她玛不存在国籍和阶层的劣势,她主要是因为女性生育伦理之“它”受到许多委屈,然而路得不仅有生育伦理的约束,而且带着国籍、社会阶层和辈分伦理等多重劣势。这也意味着相对于她玛,路得“你”地位的实现需要处理来自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等多方面的困境,她在伯利恒的成功立足说明她具有比她玛更有影响力的“他者”能力优势。
(二)路得作为女性“他者”对波阿斯的多重意义。路得相对于她玛的优势,集中表现在她对于波阿斯的多重性别意义。路4:11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作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也就是说,按照性别历史传统,对于波阿斯(比当年的雅各年长)的婚姻,路得不仅有类似于梦中女神拉结的形象,有类似于利亚的生育形象;另外,波阿斯作为一个年长的男人,路得也类似于她玛,带着年轻女性充满活力的性别形象。
显然,路得作为女性“他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对于波阿斯,路得有类似于拉结的甘心付出精神,她有父权男性渴求的灵魂伴侣人格自由独立的美学意义;路得类似于利亚,她在伦理上有父权家庭期待的为妻的忠诚和为母的慈爱;路得类似于她玛,她有拿俄米所不具备的开启老年男性再次青春的生命魅力。联系到女性主义“他者”观的系统论述,路得这些能力可以有哪些理论依据,下文将作出分析。
四、路得女性“他者”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从人际影响的角度分析《路得记》,路得作为摩押女子融入伯利恒犹太文化可以从她成为冯伦的妻子开始。综合文本中路得言行和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她有许多优秀品质,从人基本的物质生存到社会文化交融,依次表现为她的勤劳和自立、她的忠诚和孝顺、她的贞洁自律和性魅力以及她的勇敢担当和谦卑柔顺四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些品质对应于女性的意义,可以发现它们分别以某种“他者”形式对应于某种女性主义派别,下面依次说明。
勤劳和自立对应“存在的他者”。这表现的是路得物质生存能力的一面,意味着实现经济独立的能力,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女性存在主义进行解释。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借助近现代经典的主体性哲学关于如何成为真正的“人”的思路,提出了同时享受自由和担负责任的女性主体性理想,集中体现在她提出的超越第二性客体位置、无限靠近绝对第一性主体的“女性他者”概念。关于女性独立目标的实现,波伏娃认为女性与男性有同等的选择自由,因此女性为了维护自我的绝对肯定性存在,在作为第二性“他者”时需要像男性一样利用自己身体力量参与社会劳动分工。波伏娃深刻认识到,由于肉身存在与物质需求息息相关,在传统性别文化社会里女性的弱势在于对男性物质资源的过度依赖,因此她特别注重女性主动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因此,波伏娃强调女性通过发展职业实现经济独立的主张,提出女性主义“存在的他者”观。
陪伴拿俄米到犹太地的路得,一穷二白且一无所知,拿俄米的生存绝望处境就是她现实的起点。显然,按照波伏娃女性“存在的他者”观,路得摒弃了女性物质依赖的“绝对他者”之“它”的卑微处境,以吃苦耐劳的主体精神成为自食其力的“相对他者”。她亲身投入社会工作——到田间拾取麦穗,保障了自己生活的需要。这显然实现了波伏娃意义上的个人“经济独立”。从文本进一步看,路得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并将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一伊法大麦。她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她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路2:17—18)。也就是说,路得不仅很好地养活了自己,而且成功抚养了她曾经的婆婆。她很好地承担着类似传统男性家长的劳作养家责任。路得在伯利恒拾取麦穗虽然身份卑微,但她独立的社会化生存却是美好的开始。正是因为如此,在物质生存上她作为性别的“相对他者”之“你”可以和独立自主的男性齐眉并肩。
忠诚和孝顺对应“伦理的他者”。这显示的是路得作为女性基本人际关系生存的能力,意味着她很好地践行了婚姻家庭的人伦关系,可用强调性别角色伦理超越的自我“窥镜”说明,这契合的是法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背景里,法露西·伊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中回溯柏拉图性别二元的传统,批判地继承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女性角色对于男性建立自身绝对主体不可或缺,即“父权制依靠男性内化的男性形象确立社会关系,根据男性的自我定义去反观女人,把女人构建成男人的他者和对立面”。因此,“由于依照男人的标准而存在,女人只能映照男人,从而丧失主体性,沦为父权制的镜像”,即一般意义上的他者。然而,伊利格瑞强调,依据这种逻辑,女人可用反窥镜的形式进行自我关照而成为自我的“他者”,由此在父权他者中以“伦理的他者”方式建立自己女性对应于男性的主体性。
路得在犹太文化中的社会关系,源于她的忠诚和孝顺。但在伯利恒,由于丈夫已死、婆婆年纪老迈,基本上是从无依无靠的外乡人开始的。她作为传统伯利恒社会歧视的敌国人,虽然有婆婆拿俄米引导,但没有父亲、丈夫或兄长之类的男性家人支持,相当于在父权制度里没有正常父权人际关系的支持。她面对人生地不熟的伯利恒世俗社会,伦理上基本上是“绝对他者(它)”。如果她不恪守伯利恒的家庭性别伦理原则,完全可能陷入被社会任意践踏或羞辱的悲惨处境。但事实上,路得成为伦理性“相对他者”,无论作为拿俄米的儿媳/女儿,还是后来作为波阿斯的梦中情人乃至妻子、俄备得的亲生母亲,她的女性性别角色都非常成功,而且给伯利恒乡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贞洁自律和性魅力对应“政治的他者”。政治的女性主义涵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几种理论形态,其中以美国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2017)“性政治”观最有影响力。在马克思主义和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阶级、经济和教育状况、神话和宗教、心理学等方面论证了男权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隐蔽性,造成女性社会地位被固化的处境。凯特·米利特主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为,女性是父权统治的对象,家庭是父权国家政治的原型,人类包括女性的“性”行为根植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传统女性的“性”意义完全由男权意识形态操纵,是父权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总体上说,凯特·米利特认为,女性他者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女性”的“性”是父权统治的中介、工具和资源,女性自我更新自立必须反对阶级父权制并重新定义和守护自己的性与性别身份。个体女人解放的获得,只有脱离男权性意识形态的统治,拥有自己独立的性意识,才能真正建立作为人的主体性。由于对男女“性”行为中所蕴含的不同主从权力地位的重视,凯特·米利特的女性他者观可以称为“政治的他者”。
《路得记》中典型表现“政治的他者”的细节集中在第三章“路得与波阿斯在簸麦场上”。整个过程可分为四段,从路得与波阿斯在田间相遇开始,以拿俄米为路得谋划婚姻为转折点,以路得冒险委身并求助为高潮,到路得带着礼物回到拿俄米身边、等待波阿斯赎地联姻和拿俄米对冒险执行者路得的安慰结束。大体上看,委身计划的策划者是拿俄米,路得努力执行,二人共同参与并成功,但整个过程关键部分由路得完成,所以路得是主角。能够实施性政治,路得年轻而且很可能深具性魅力,虽然文本没有直接描绘,但是按照精神分析观点,由于波阿斯母亲投奔犹太国的异域文化背景,路得的外籍文化身份很可能勾起了波阿斯的恋母情结,这从波阿斯第一次见到路得就对她进行称赞可以推测;同时,相对于犹太族偏重女性性别的生育伦理,路得出身的摩押文化更强调女性的性愉悦魅力,据此可以推测路得相对于当地一般犹太女子是神秘美丽的,从伯利恒田间男性和波阿斯对她的接纳可以证明。总而言之,在伯利恒乡间严厉的女性贞操观背景下,路得冒着人言可畏、身败名裂的巨大风险,主动越雷池以委身性行为征服波阿斯的心,以性政治他者方式推动波阿斯执行婚姻联盟的合法化行动。
勇敢担当和谦卑柔顺对应“审美的他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继承波伏娃和伊利格瑞等几代女性主义哲学观,在其代表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和《消解性别》中引入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理论,发展出女性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巴特勒认为,传统性别观是表达性的,而性别文化的本质是强调操演性的。所谓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都是在一个二元建构里,通过类似于仪式化的社会戏剧,通过个人的身体经由相应的性别风格或程式化的过程形成。在这样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巴特勒延续黑格尔主体构建中的“欲望和承认”共存的逻辑起点,将女性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欲、身体等范畴去自然化,认为女性的性别完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现代女性主义发展的集大成者,其“他者”行为观从性别角色的“戏仿”到“政治”,带有文化艺术表现的感染力,因而可以实现人际美学情感的唤醒,可以概括为“审美的他者”。
从文本看,路得的女性言行是带着美学特征的。初到伯利恒的路得基本上是被无视的,作为人她没有被认可的社会位置。但在这种处境里,面对老迈无力的女性拿俄米,她模仿“男性”勇敢担当,主动承担了物质供养责任(路2:2)。在路得与拿俄米到达伯利恒时,路得像伯利恒民间家庭里的夫妻性别分工一样,主动承担了男性“养家”的责任。路得作为纯粹“女性”面对波阿斯,在田间相遇时谦卑有礼,引起波阿斯的爱怜和帮助;秘密委身后主动求助、柔顺依从,赢得波阿斯全力以赴迎娶成婚的决心。总体而言,性别审美的他者方式,路得通过超越性别的责任感和美好言行在异国他乡伯利恒成功塑造出一个犹太父权贵族需要的女性形象,她作为女人性别主体的确立隐含在其操演性别的审美性言行中。
从存在、伦理、政治、审美依次递进的程度看,路得整合了四种力量,具有“他者”多种方式综合性的能力。路得能够在伯利恒获得成功的立足,她为人的卓越即在于此,她不仅勤劳谦卑,而且有胆有识,在风险中张弛有度地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逆转。总而言之,路得性别“他者”形象表现的四种能力具有整体性,从存在到审美,不仅实现一种女性性别超越性整合的闭环,而且分别在强调物质生存的存在与突出意识形态生存的政治,在强调女性对应多种性别关系(父女、夫妻、母子)的伦理和强调对应单一的性别关系(男—女)的审美方式上表现出对立统一,呈现出一个女人在性别他者形象上不容易达到的完美高度。
五、结语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分析《路得记》文学性别而言,综合从“存在的他者”表现的经济独立能力,“伦理的他者”实现的伦理关系自知,“政治的他者”显示的性意识独立,“审美的他者”呈现的规范自立四个维度看,路得作为主人公的女性形象立体丰富,在父权文化里充满美、爱和独立自由的精神韵味。大致而言,路得的“他者”能力表现在:她超越国籍、阶层、家族伦理、具体人际等多重集中于她女性性别的劣势处境,以综合性的“相对他者”方式,赢得拿俄米和波阿斯一致认同,以一个孤寡贫困的外来女人的婚姻方式加盟当地领袖家庭,不仅赢得了伯利恒民间社会的美誉,而且赢得了具有排斥异族传统的犹太族特别的历史认同。
总体上看,分析路得的四种女性主义理论侧重女性他者表现能力的不同方面,从性别“相对他者”主体建构的逻辑顺序角度,从存在、伦理、政治到审美,分别强调女性与男性性别共生共存的社会意义。于此,这一系列不同女性他者的表现,从存在到政治,从伦理到审美,以女性特有的方式从广义的公共社会领域到具体的私人生活领域;从存在到伦理,从政治到审美,将女性独特的影响从一般的社会分工参与推展到深具规范力度的社会人际层面。从关系本体论角度看,“存在的他者”“伦理的他者”“政治的他者”和“审美的他者”作为女性从“它”到“你”的四种递进的主体性建立方式,并行不悖体现在了路得的个体案例中。在父权男性本位的社会文化中,女性主义理论多样性整合的机遇似乎就在于此,即从不同维度的“绝对他者”之“它”,到多样性的“相对他者”之“你”,由此成为一个具有性别意义完全整合的、具有女性性别精神“自我”主体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