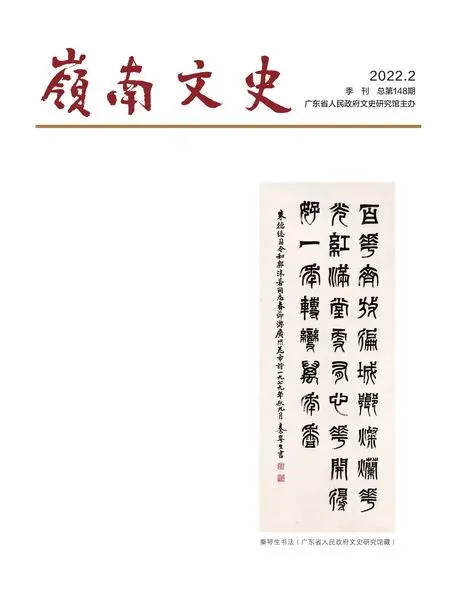南越国“四宫”考析
袁春霞
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赵佗(河北真定人)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以故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为都城,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汉朝的册封,后因吕后专权,对南越国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赵佗切断与汉联系,自称“南越武帝”。汉文帝继位后,汉越和解。至公元前111年,西汉大军“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南越国亡,共传五主九十三年。赵佗主政岭南期间,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秦征服岭南至南越国被灭前后约一百年的历史,《史记》和《汉书》的《南越(粤)列传》略有记载,但对于南越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都城情况,少有记载。
1953年以后,广州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中,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大量南越国时期的建筑遗迹和数百座墓葬,为研究南越国提供了大量科学数据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广州中山四路到中山五路一带陆续发现的南越国建筑遗迹,结合史料记载的内容,找到了南越国都城的确凿位置。迄今为止,已经确定为南越国都城重要的遗址有宫殿、御苑及围绕宫殿不远处有与城垣相关的水关遗址。尤其是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墓,墓中的随葬器物,如同一座地下宝库,为研究南越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一:广州城区南越国重要遗迹分布图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淘金坑发掘的16号南越国官吏墓中,清理出一件陶瓮,器肩上有“长秋居室”戳印文字。1983年发掘的南越王墓,墓中出土的3件陶瓮和1件陶鼎上均有“长乐宫器”戳印。特别是2003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一块有“未央”二字的陶器残片和两块有“华音宫”三字戳印的陶器残片。这四个与王宫有直接关系的戳印文字的发现,为人们了解南越国王宫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此推断,“长秋”“长乐”“未央”“华音”应是南越国四个宫的名称。对南越国“四宫”有关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深化对南越国的研究。
一、南越国考古的重要发现
(一)南越国宫署遗址
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原广州市儿童公园进行了300多平方米试掘,揭出了南越国一号宫殿的铺地砖与散水,南越国都城的核心所在地由此揭幕。2004年,对宫署遗址一号宫殿全面发掘,还发现二号宫殿和连接宫殿的廊道、砖石走道及排水设施。同年,在宫苑西北边发现一口南越国的渗水井,清理出一百多枚南越国木简,简文“番禺”“陛下”“公主”“苑”“宫门”及“廿六年”等文字,记载了当时南越国的一些相关信息。2005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北面,揭晓了一段呈东西走向的夯土城墙,确定为南越宫城北墙。分析以上发掘的材料,可以认为,南越国仿效汉长安城,在都城内还有皇城,以护卫王宫的安全。
(二)南越墓葬
围绕宫署不远处的象岗山,1983年发掘的南越国第二代王墓;老城区东部一带数组贵族墓葬区及少量生活遗址等发现,能基本确定南越国都城主体位置轮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广州市发现了182座南越国墓葬,70年代在广州淘金坑发现22座墓,80年代在广州柳园岗发现了43座墓,另广州东山等地也发现了一批南越国墓葬。
与秦汉时期的都城一样,墓葬一般分布于城外郊区。南越国番禺城的墓葬围绕王城中心,成群分布在城外东郊和北郊高低起伏的山冈上。至西汉中期以后,墓葬的分布范围愈见偏远,这与番禺城人口增加、城区日渐扩展有密切关系。
二、南越国都城、宫城的特点
从宫署遗址的发现、南越墓葬的分布、宫城北墙以及都城南城墙发掘情况看,人们对番禺城的历史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自1953年以后广州考古发掘的几百座汉墓及南越国遗迹,认识到番禺城的大概位置。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发掘明确今市区中心的城隍庙以西至吉祥路以东为番禺城中心所在。其都城内的重要主体宫城建筑遗址及大型宫殿建筑群和附属园林位于现广州中山四路一带。南越国都城的范围大概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800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
南越国宫城位于番禺都城中北部,目前已发掘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以及连接宫殿之间的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以及北宫墙等重要遗迹。宫城东部为宫苑区,主要由一座大型石构水池和一条长约180米的曲流石渠组成。
南越国都城从地理区域大势上运用了“天下之中”原则,具体到都城选址上也仿效秦汉都城。其选择在越秀山麓的南面,背靠越秀山,以山为险设屏障,西、南二面以珠江水为环壕作为防御,形成水陆综合防御体系,充分利用山环水抱、负阴抱阳地理形势发挥地貌特征的险要作用。

图二:南越国宫署遗址重要遗迹分布示意图

图三:南越国都番禺城历史地理环境示意图
宫城选址在地势较高且平坦的山冈上,起到防御侵袭及免遭水患功能,白云山的甘溪穿城而过,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可见番禺城因地制宜进行规划布局。从考古发掘的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看,南越国宫殿坐北朝南,略偏向东南,北面大体对着越秀山主峰,以越秀山为靠山,形成宫殿的轴线,符合中国传统的堪舆思想,体现了秦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念,与汉长安城有异曲同工之处。
目前已发掘的南越国宫殿建筑位于宫城的中部,揭开了一号和二号宫殿、一号廊道和砖石走道等建筑遗迹。以南北走向的一号廊道为轴线,东侧中部为一号宫殿,其北部和南部均残存有建筑散水遗迹,可以推测一号廊道的东侧自南向北至少分布3座宫殿建筑。
南越国创立者赵佗本是秦将,秦军南下岭南时又以中原人为主,赵佗称帝后,很多方面也“多与中国(汉朝)牟”。在构建都城时承秦制又仿汉朝,宫城有强烈的政治中心色彩,突出了城内的管理功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对外具有号召力,对内具有凝聚力,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皇权的统治权力。
三、南越国有“四宫”
(一)长秋宫
197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人员在淘金坑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的16号墓是一座南越国时期的竖穴木椁墓,墓中出土一件陶瓮,器形较大,直口外侈,平沿短颈,腹最大径靠上,平底较大,整体稳重,高34.4厘米、腹径34.8厘米。泥质灰白陶,火候高,质地硬,可知属典型的南方印纹硬陶系列,器身用泥条盘筑,表里可看出一道道泥条和拍打印痕。瓮肩部有“长秋居室”印文,戳印方形,长宽各5.5厘米,中间有十字格。由于印是平面的,而瓮壁是圆的,所以印的4个角和印的下边线与器壁接触不紧密,“秋”字的火字末笔和“室”字下横画未能印出。“长”字的缺损是由于清理时不小心弄破的,但“长秋居室”四字仍然可辨。

图四:淘金坑西汉墓出土瓮

图五:长秋居室戳印陶瓮及印文
长秋有两个含义:一是宫官名,二是宫名。宫官名见《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七》颜师古注:“秋者收成之时,长者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居室为少府所属,有“居室”“甘泉居室”。又见西汉齐国遗址出土的封泥“齐居室丞”,西汉封泥“齐居室印”。据《秦汉官制史稿》一书认为,居室的职责是管理宫内房屋的,可见汉初诸王国内有设长秋与居室官职。从古文献可以推测“长秋居室”应是长秋宫的居室令,它与甘泉居室令为甘泉宫内的宫署正相符合;后宫名,指长秋宫,见《三辅黄图·汉宫》:“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后亦用为皇后的代称。又《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永平三年(60)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可见,古文献记载长秋宫为汉宫殿名,为帝王、后妃的居所。南越国的政治体系、都城的布局、结构和宫苑建造无不透露出仿效秦汉中原的做法。而墓葬中出土的“长秋居室”印文无论是指官名还是宫名,都是仿效汉城建造长秋宫最好的印证。
(二)长乐宫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南越国第二代文帝的陵墓。据史载,南越王二世称赵胡,于公元前137—前122年(汉武帝建元四年至元狩元年)在位,约16年。墓中出土文物尤以铜器和陶器最具南越文化的特色,其中有十几件于外藏椁中发现的陶瓮,个体大,敛口,卷唇,束颈,最大颈靠上,肩腹部鼓突,腹下部斜直内收成小平底。器体口径25—28厘米、腹径40—49厘米、底径24—28厘米、高47—60厘米。器表拍压方格纹与几何形戳印,其中有三件肩部戳印“长乐宫器”四个阳文篆字,戳印无边框,无界格,由右竖读,笔画纤细,字体公正,字迹清晰,印框呈竖长方形,高约2.3厘米、宽约2厘米。另一件陶鼎出土于西耳室,敛口,釜腹,与盖相合处有3周突棱,三扁足较高。肩部饰对称的环形小耳2个,一耳已残。通体拍印方格地纹加菱形格的戳印纹,肩部打有“长乐宫器”印文。估计是“长乐宫器”用器的标志。经广东省地质中心实验测试结果显示,部分瓮的部位为摩氏(Fried Mobs)硬度6.5度,属典型的南方印纹硬陶系列,是当地烧造的器物,排除了这些陶瓮由汉宫“长乐宫”监制,然后由朝廷赏赐于南越国的可能。

图六:南越王墓出土瓮 图七:长乐宫器戳印陶瓮及印文
长乐宫是汉高祖刘邦立国后在咸阳城郊幸存的秦宫——兴乐宫基础上兴建的第一座宫殿。南越王墓中印有“长乐宫器”的陶器,是南越国赵佗称帝在宫廷建制方面仿照汉朝的具体表现,也标志着早在两千年前大一统的汉文化已经在南中国形成。
(三)华音宫、未央宫
2000年初,在广州市原儿童公园内发现了南越国一号宫殿遗址,2003年开始对其进行大面积发掘,揭露了多处南越王宫建筑遗迹,有宫殿、廊道、御苑、宫墙及水井等。其中南越国一号宫殿坐北朝南,面积近600平方米,东西两侧各有一条连接宫殿的通道。宫殿原是大型高台建筑,台基四周用砖包砌,台基外面的散水用精美的印花大方砖和小卵石铺砌而成,最外边再用侧砖包边,整体制作十分考究。散水主要承接屋顶檐上落下的雨水,且向外流淌,远离台基基础,避免雨水就近渗入地下,保护地基。在汉代建筑结构中以鹅卵石作“散水”是有级别限制的,如果在宫殿屋檐四周地面全都铺上“散水”,是皇宫的标准,只铺两边是王的标准。一号宫殿“散水”在宫殿北面和东面都铺了鹅卵石“散水”,目前发掘出的只是宫殿的一小角,中国建筑讲究对称原则,推测西面、南面也应铺有鹅卵石“散水”,证明这座宫殿是南越国仿照汉皇宫建造的。2004年考古人员在一号宫殿的西南面清理出南越国二号宫殿的东南角部分,宫殿结构与地砖的铺砌形式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但尤为珍贵的是在二号宫殿的散水中出土了一块戳印有“华音宫”三字的陶器盖残片,戳印于陶器盖近纽座处,长方形边框长3.8厘米、宽3.6厘米。该残片约为器盖的十分之一,盖体制作规整,火候较高,属南方硬陶系列,泥质浅灰陶,陶质致密,薄厚适中,器表盖顶部,贴有浮雕状兽形,上部残,仅存两侧内卷的角状饰,其下沿中间有一“华音宫”阳文,戳印“华”与“音”的上部字文较浅,稍微模糊,余皆清晰可辨,篆书,由右向左竖读,“华”字窄长,将右边占满,左侧“音宫”两字扁方,相间紧密,字画纤细,无边框,无界格。
此外,在砖石走道北,一号廊道南端东侧还出土了一件陶罐,口沿处戳印有“未央”印文,右半部残缺,方形边框长2.2厘米、残宽2厘米。陶片为灰色泥质陶,外饰网状细方格纹。

图八: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印

图九:华音宫戳印器盖残片及拓片印文之一

图十: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印

图十一:未央戳印残片及拓片印文
“华音宫”“未央”印文陶器、南越木简及食水井的出现表明该区域是南越国宫城核心区。在秦和汉的宫殿中,无论是史料还是考古实物材料都未见有“华音”的宫殿。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认为,“华音宫”的由来可能是因陆贾的来访使赵佗听到了许久“闻所不闻”的华夏之音感到愉悦而建造的宫殿名称。再从“华音宫”三字的字义发展来说,“华音宫”当指寓意华夏之音的宫殿,或许有南越国主赵佗思念故土的寄寓之情。推断在南越国都城里可能有一座华音宫,该印文指的是宫室,为当年南越国朝臣议事之所。
四、“四宫”所在地推测
据《汉书·诸侯王表》记载:“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知汉初诸侯国的宫室和百官建制与京师是相同的。从多处遗址发掘出土的戳印“长秋居室”“长乐宫器”“华音宫”和“未央”等有关南越国宫殿名字的陶器,以及南越国宫殿建筑形制等分析,南越国宫室的名称效仿汉廷,其建筑形制与汉廷中央的宫殿建筑形制大体相同。因此,推断在南越国的宫城里有长秋宫、长乐宫、华音宫、未央宫等四座宫殿。
南越国都城中心由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御苑构成,已发掘的南越国御苑遗迹在宫署范围之内,属大内御苑,是皇宫的组成部分。宫和苑在宫墙之内,苑位于宫的东部(即西宫东苑),与西汉未央宫(东宫西苑)、建章宫(前宫后苑),有着相似的布局。未央宫、建章宫等宫苑主要由大型水池和引水石渠组成,南越国御苑遗址也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目前发现的蕃池与曲流石渠,就地形特点充分利用自然水源,融人工水系景观于自然之中,其具有的自然式布局、曲水流觞式的理水和追求神仙境界造园理念,描绘出一幅汉代帝王园林的典型景象。
南越国是在秦南海郡治番禺城上建都城,以秦汉都城的理念,在秦南海郡治番禺城增建扩建而成,充分利用地势,发挥险要地形的优势。都城平面近方形,“周回十里”,南城墙与珠江北岸走向相同,城墙用纯土夯筑。城内东、西、南三面留进出的城门或码头闸口,呈“T”字形格局,为后世所延用。宫城区位于都城北部,亦是城内地势最高的地方,在位于今广州大厦南边发现的宫墙遗址确定是宫城北界,稍往南以一条南北走向存长逾50米的建造精致、功能完备的廊道为轴线。东边有三座宫殿遗迹:其中最南边有座秦代遗迹上清理的宫殿,在其西端出土一块戳印“未央”的陶罐残片,中间为一号宫殿,最北边仅发现部分零星的散水遗迹,但仍可看出是宫殿的散水。西边揭露了二号宫殿的局部,并在其上发现戳印“华音宫”陶器盖残片。宫殿区东南为宫苑园林水景,目前考古发掘有蕃池及曲流石渠遗迹。在新大新商业楼的地基下,发现了用砖铺砌地板的南越国大型建筑遗址,砖的大小尺寸与宫殿附属建筑的铺砖相当,但从形制和材料观察,是一处不同等级的建筑。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及出土的资料,对南越国的“四宫”位置做出如下推测:

图十二:华音宫戳印器盖残片出土位置 未央戳印残片出土位置
目前发掘的南越国宫城遗迹,东以广州都城隍庙,西以北京路东侧为界,北以宫墙遗址,南以中山四路为界,东西长约200米,南北长约28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范围,长方形的平面形制布局与汉长安城未央宫相似。目前在一号廊道以东发现的三座宫殿,合称三殿,是宫殿区的一部分。虽已破坏殆尽,却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发现的食水砖井及排水暗渠相互辉映,显示出南越国沿袭了中原王朝宫城“前朝后寝”的传统布局形制。在一号廊道最南边的宫殿,其西端出土一块戳印“未央”的陶罐残片,据此推断一号廊道以东目前发现的三座宫殿可能是南越国的“未央宫”建筑群,对应汉长安未央宫中的建筑群。
廊道以西二号宫殿为宫署建筑群,蕃池与曲流石渠水景园林区与沧池相类似。在该宫殿的散水堆积内出土一件戳印“华音宫”文字的陶器盖,为该宫殿名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二号宫殿可能就是“华音宫”宫殿。
由于缺乏证据,目前不可推测南越国长秋宫、长乐宫等宫殿的所在位置。更重要的是目前南越宫城范围内大部分未进行发掘清理,对于四座宫殿的具体位置仍无法准确判定,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材料加以验证。
[1] 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第410页,1995。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52-153页。
[3][20][21][2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11、22-23、112-113、22页,1991。
[4][6][16][23][24][25]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3期,第15-31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235-260页。
[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第3-13页。
[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基址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第31-52页。
[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页,1981。
[10][19] 麦英豪:《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145-173页。
[11] 黄淼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纪要》。《穗港汉墓出土文物》,广州市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出版,第248-256页,1983。
[12]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麦英豪文集(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16-128页,2018。
[13][15][28]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08、70、307-310页,2008。
[1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9期,第4-24页。
[17]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陇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第4-15页。
[18][30] 李灶新:《西汉南越国都城与宫城及相关问题》。《中国古都研究(第三十八辑)》,第121-131页,2019。
[26] 王鑫:《“华音宫”陶文考释》。《文博学刊》,2008年第1期,第94-101页。
[27] 吴凌云:《南越玺印与陶文》。《考古发现的南越玺印与陶文》,第196页,2005。
[29] 司徒尚纪、许桂灵:《古都的历史地理研究争议——以广州古都为例》。《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辑)——中国古都学会2003年年会暨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29-338页,2003。
[31] 黄淼章、全洪:《广州市清理出大型汉代建筑遗址》。《中国文物报》,第49期第二版,1988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