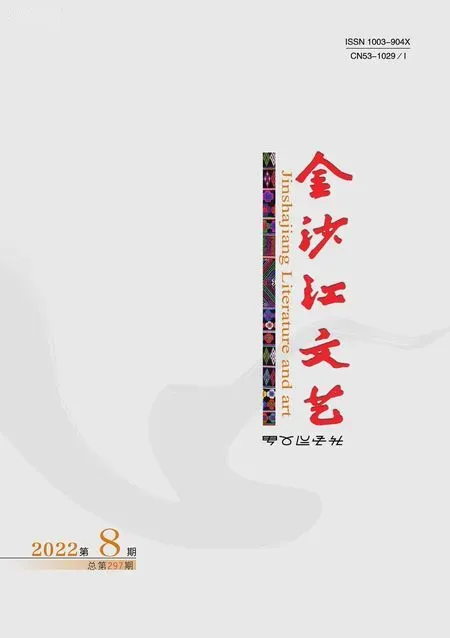城市浪人
◎刘奔海(新疆)
认识老邱已有十多年了,当时我还是小刘。转眼我都成老刘了,老邱却依然是老邱。
第一次见到老邱是在一个初秋时节,那时我刚调到一家杂志社工作,一天早上,大家正在编辑部办公,静悄悄的,突然门外传来高声地吟唱声,就像《水浒传》里水泊梁山上那些好汉们无拘无束快活的吟唱。
来编辑部的,一般都是投稿的作者,毕恭毕敬的,生怕给编辑留下不好的印象。这是谁呀,像回他家一样!正想着,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瘦削老头晃了进来,我一看,以为来了个“叫花子”,只见他的穿着单薄而寒酸,又脏又破烂。外面已寒气逼人,他还穿着短袖,特别是那裤子短得已提到了脚踝,鼻子冻得红肿,一进门就不停地咳嗽。“叫花子”咋跑到这儿来了?却看大家都没反应,继续低头办公,似乎都司空见惯了。他紧步走到每一个办公桌前和每一个人握手,可以看出,大家都认识他,却又都显得很冷漠,没有一个人站起身,握手似乎也是他硬拉着每个人的手来握。当他走到我的桌前,伸出那双黑黢黢的大手时,我站了起来,被动地和他握手。他的眼里闪出亮光,惊喜地问我:“你是新来的吧?”我笑着说:“我刚分来几天。”寒暄过后,他便从他的破包里掏出一沓稿纸来,说这上面是他写的几首诗歌,让我看看能不能在杂志上发表。原来就是来投稿的,并且也一定来过多次了。
我大概翻了一下诗稿,字写得很工整很硬朗,显然还是下了些功夫。再看内容,也完全不同于那些“老干体”,这也不难理解,老邱一天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哪能写出“老干部”那样悠闲自在的诗篇,仔细读来,个别诗句还闪耀着一点思想的火花。可从每首诗的结构来看,却东一句西一句,比较散乱。我便推脱道:这些诗作你先放在这儿吧,能用的话我再告知你。我本想把他打发走,谁知他却一下子来了兴趣,大谈起诗歌来,我听得不耐烦了,坐下干我的事,时而抬头搭理他一下。他站着说了一会儿又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继续说,自顾自地东拉西扯,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他终于也感到无趣,便说,那你们忙,我走了,我还要去找一下宣传部的张部长。
老头落寞地走了,没有一个人相送。他走后,我便小声问旁边的同事,这个老头是干啥的?同事便带着嘲讽的口气对我说,那是“老邱”,是个农民诗人,都快70岁了,二十一世纪的“孔乙己”!同事这样一说,我的心里对老邱倒有了一丝同情和怜悯。
老邱是一个居住在偏远农村的老农,可他却从年轻时就不务“农”事,不安于现状,偏偏喜欢舞文弄墨,喜欢过城里人的生活。可一个农民,首先要懂得下苦,把地种好,像他那样整天东游西逛的,让一家人跟着喝西北风,谁愿意跟他过?结婚没几年,老婆就跑了,给他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老邱带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勉强把孩子拉扯大,也给他找了个媳妇,成了家。从此,老邱也没什么牵挂了,彻底成了城里的游荡者。
老邱总是手提一个破皮包,包里装一支破笔、一个破本子,再加一个破手机,这便是他的全部行头。老邱虽然不是单位里的人,但他比单位里的那些干部职工上班还积极。其实,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似乎到哪个单位找谁都可以。他既不是来告状申冤的,也不是来找领导签字的,他就是想向领导谈一下他对当前国内外大事的看法,汇报一下他当前的“工作”和以后的“计划”。你别看他只是个老农民,却除了不关心自己的小家之事,国事天下事他都事事关心。当然,老邱最关心的是文化,怎样繁荣当地的文化事业,怎样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他都能说上个一二。可领导们一天多忙啊,哪有那个闲工夫听他瞎扯。其实,仔细听听,他有时说的话还真是针砭时弊,能说到点子上。
刚开始,他还可以随便进出各单位,后来,管理日渐严格了,那些门卫都知道老邱这个人了,或者是经过了领导授意,就不随便放他进去了。每当这个时候,老邱便愤愤地争辩:“党政机关不是老百姓进的吗?”“老百姓有事当然可以进!”“我也有事啊!”“你有什么事给我说。”“给你说管用吗?”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要么最后老邱硬闯进去,要么软硬兼施也进不去,老邱就只能在大门口“守株待兔”了。很多次,我上班路过市委大门口时,看到老邱胳膊下夹着他那个破包就站在大门外面,烈日下,寒风中,他总是伸长脖子企盼着他要找的领导出现。老邱每天除了到各机关事业单位乱窜,就是打电话。他破包里的破本子上除了记着一些他随时想到的诗句,除此而外,便是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几乎全市各单位、各阶层人士的电话都有,甚至也有市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当然,老邱最常来的是我们编辑部,有时一天几次地来。他把我们这儿当成了他在城里的“根据地”,可以随便地来,随便地走,也许他觉得我们文化人不像那些政府机关的官员,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在我们这儿可以不拘小节、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次一进门,便往办公室中间的沙发上一坐,开始自顾自地诉说他最近遇到的一些困惑和烦恼以及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全然不在乎别人在不在意他的存在。老邱有时说得情绪激昂,唾沫星子乱溅;有时又情绪低落,垂头丧气的样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老邱坐着或者站着絮絮叨叨地说上一会,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他便落寞地离开,临走时又讨好似的向我们要个信封、要张报纸。看着老邱离去的背影,我不知道下一个他又要去哪里,去找何人。老邱常会说,谁谁谁让我到他那儿去,哪位领导又让我去谈工作,好像他一天比谁都忙。可他每次拿起他的破手机拨通号码后,大着嗓门喊:“喂,是xxx吗,”那边问:“你是谁呀?”老邱赶忙满怀热望地报上姓名,“我是老邱啊—”一听就知道他们是老朋友了。可那边语气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你有啥事?”或者一句话不说就挂了电话。而老邱并不生气,只是说,这电话怎么又断了……而更多的时候,都是人家早就标识了老邱的号码,一看又是他的电话,直接就挂断了,或者直接设了黑名单,你永远打不进去。
老邱是这么的招人烦,可他也有鄙视的人,老王是我们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出了好几本史料类图书,可老邱一说到他,就带着一脸不屑的神情说:“他写的那些书算什么书?都是东抄西抄的,哪有他自己的东西,有谁看?擦屁股我都不要!”别看老邱没写出什么作品,可他对文学的认识还是有水平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老邱一再询问我他的那几首诗歌能否发表,而我总是以“稿件要经过三审才能发表,你再等等”敷衍一番。现在电子邮箱里的稿件浩如烟海,打印得工工整整的邮寄稿件也厚厚一摞堆在那里。其实,我一直就没打算选用那些诗,也根本就没再翻看它,我只是不想一口回绝他,让他太失望。终于在一个月后的一天,老邱又来询问,我便直截了当地说:“你那些诗歌不适合在杂志发表。”老邱显得有些激动,他大声说:“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标准,发不发是你们的事,但写不写、投不投却是我的事……”他说得很坚定,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真是不打不相交,从此老邱还把我当成了他的“忘年交”,有事没事总爱给我打电话。一天中午,老邱的电话又来了,他显得很兴奋,说他在我们本市的晚报上看到我发表的一篇散文,感到写得很好,我忙客气地说“谢谢”。但他接着却说文章中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商榷,说他想和我交个诗友,并让我周末和他去大街上捡矿泉水瓶,卖了钱,晚上一块去夜市吃喝,说那才叫“浪漫”!我差点笑出声来,你还要和我“商榷”?我一个堂堂的杂志编辑,去和你捡破烂,以后还怎么抬头做人!
最可笑的是,一天,市里文艺界的一位老领导给儿子在酒店办结婚喜宴,亲朋好友纷纷去酒店贺喜。可老邱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他也许觉得那位老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不请他也应该去的。可别人都是穿戴一新带着礼金去的,老邱有钱送礼吗?新郎和新娘在酒店门口迎宾,场面真是喜庆而热烈。到了酒店门口,老邱和众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要不是大家都认识,他准会被赶走,一个“叫花子”还想喝喜酒。站在门口迎宾的新郎新娘看到老邱来了,两人的表情显出了不悦,但大喜的日子又不能生气。只见老邱大大方方地走到一对新人跟前,说了一番贺喜的话,新郎新娘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没想到老邱又像变戏法似的从衣袖里抽出一枝鲜花来,双手捧到新娘子面前,说:“今天你们结婚大喜,我也没什么带的,就给你送支鲜花吧。”那朵小花大概还是老邱在来时的路边采的。
老邱身上只要有点钱,就会打电话请这个吃饭请那个吃饭,可谁会去呢,和老邱在一起吃饭不丢人吗?你好意思让他掏钱吗?最让人烦的是老邱常在深更半夜给你打来电话,一接,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今夜的月亮真圆啊!夜色真美啊!夏天晚上,老邱就睡在城市公园的长椅上。一到冬天,他就蜷缩在街边的自动取款机的小房间里。
老邱整天游走在城市里,没钱吃饭了,就到市郊的农家给人干点农活,混口饭吃,挣点零花钱,要么就是捡垃圾卖点钱糊口,老邱只有在城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才会回到他那偏远的小村里。可老邱不这样说,他说,过些天我要回到农村深入生活,积累一些写作素材。我暗笑道,你就在社会的最底层了,还需要到基层深入生活?老邱回去干几天农活,再从家里偷拿点地里收获的农产品出来,你可以想象,老邱在地里干活的情景和乡邻们嘲讽他的话语。老邱很少提及他的儿子,只有一次,他情绪很低落地对我说,他和儿子吵架了,接着又叹口气说,我们干的事他们那些人都不懂,神情里流露出一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无奈和悲哀。
老邱不愿意待在农村,宁可在城里流浪也不回去,可在城里,除了碰壁,就是吃闭门羹,又有谁会在乎他的存在呢!老邱真正令我们厌恶是在去年夏天的一天。那天中午,天气很是炎热,我们几个编辑正在认真地看稿件,突然,老邱粗鲁地推门进入编辑部,只见他满脸通红,衣服敞开着,一身的酒气。老邱喜欢喝酒,他的身上常装着小瓶的劣质白酒。这老邱要是在编辑部耍酒疯可成何体统!还没等他说话,我赶忙把他往外拉。他一下子显得激动万分,把脚上的一双烂鞋踢出去几米远,光着一双黑乎乎的脚板站在地板上,顿时编辑部里臭气熏天,我慌忙小声指责他:“老邱,你这是干什么?你冷静点!你看把人都熏成啥了……”我向两个刚分来的女大学生望去,只见她们掩住口鼻,面露不悦。谁知,老邱更加激动,他几乎要跳起来,大声喊:“我就是不冷静,我就是不冷静……”,喊着喊着竟哭出声来。老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雅和失态,慌忙找来鞋子穿好,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低着头退了出去……我觉得,老邱肯定不好意思再来了。
可没过几天,老邱又来了,这次,显得有些难为情,他走到我的办公桌旁,低声问我:“你能借我3块钱吗?我想回家,身上没钱了。”我当时衣袋里只装着一张50元钱,我手伸进了口袋,却又有点舍不得,这钱借出去就等于白给,他会还我吗?说不定以后会一次又一次地“借”,可不借,他是要回家呀—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旁边一位同事听到了,便对老邱说,来来来,我这儿有5块钱,拿去吧。老邱千恩万谢地走了。
过了好久,老邱终于又出现了,又是高声吟唱着进来,只见他抱着一个纸箱子,一进编辑部,便走到上次借给他钱的那位同事身旁,大声说,这是从他们家地里刚摘的葡萄,专门带给这位同事的,并说上次借他的5块钱过几天再还他。我们都吃了一惊,那一箱子葡萄足有5、6公斤,市场上1公斤葡萄都卖8元钱了!那位同事忙惊喜地说“谢谢,谢谢”,并说给我一箱子葡萄了,那5块钱还还什么!然而老邱却说,这是感谢你的,借的钱是一定要还的,我这几天干点活,挣了钱一定还你。
我脸上火辣辣的,我并不是羡慕那箱葡萄,我是对我的冷漠和自私感到惭愧,我忽然想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老话,然而我又从老邱的感恩里感到了一丝悲凉……
我一直想,老邱也许就这样在流浪中终了,都70多岁的人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艰难。有时也想劝劝他,让他安心待在家里颐养天年,可他能待得住吗?跑了大半辈子,也许他觉得城里再苦,再看人脸色,也比待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好些。
老邱越来越像一个乞丐,在大街上睡,捡垃圾吃。一次,我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老邱正在一个垃圾箱里翻找东西,当我走近的时候,老邱翻找到了一袋不知是馒头还是包子,老邱也看到了我,但他并没有觉得难为情,对我说:“你看,吃的东西,就这么扔了,真是可惜。”我知道老邱一定是饿了,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我对老邱说:“走,我请你吃饭。”老邱也没推辞,跟着我走进了一家饭馆,我想与老邱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老邱却对我有说有笑,真像老朋友一般,当进门的那一刻,饭馆里的服务员和食客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我们,老邱泰然自若依然大声地说笑,可我感到很难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给老邱要了两个肉夹馍,递给他,准备赶快离开,可老邱的眼睛却向每个桌上瞅去,当看到有一个桌子上食客都离席了,桌上还剩了很多饭菜,他走过去对服务员说:“这些饭菜倒了也可惜,要不你给我打包让我带走吧。”
老邱每次进城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编辑部偶尔会有人提起他,“老邱好长时间没来了,也不知道他最近过得怎样?”“大概都死了吧。”有人笑道,语气里听不出一丝的同情和怜悯。
快一年没见到老邱了,我们都以为他真的已经死去了,他的存在与否又有谁会去关心呢。忽然一个初秋的早上,老邱又来了,又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像有什么喜事一般“喜形于声”。一进门,我们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他,“老邱,这么长时间你不来,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一位同事笑着说。老邱也不生气,高声回道:“咋会死呢,你们看我还比过去活得更好了!”老邱依旧热情地伸出手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握完手,便从他新换的包里掏出一沓名片来,很郑重地一一发给我们,只见上面赫然印着“‘沙枣花’诗社社长”。我们看着名片,正在疑惑不解,老邱又从他的包里掏出一本打印的名叫《沙枣花》的诗刊让我们看,说这里面都是他们村的农民诗人写的诗。一边给我们翻看一边大声朗读,读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我翻看着那一首首整天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兄弟写的诗歌,虽然还读不出多少诗歌的韵味,有点像大白话、顺口溜,但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对老邱说,这些诗作我选上几首,修改后发在我们的杂志上。老邱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连声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