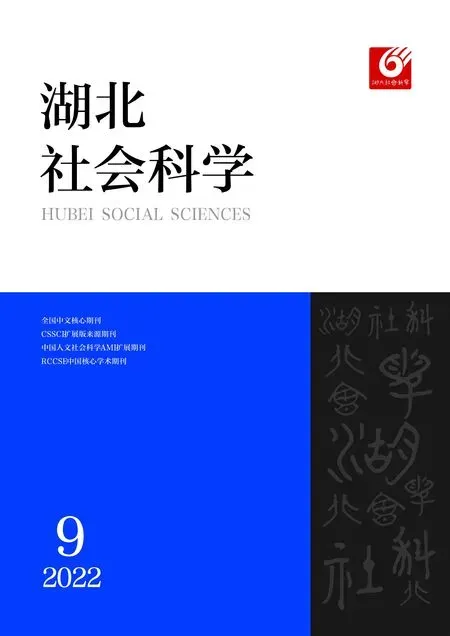元代县级司法运作:时间、空间与参与者
郑 鹏
中国古代司法体系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相对于中央官制体系很早就发展出廷尉(大理寺)、刑部等专门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一直没有从行政体系中分化出来。元代虽然在户计制度下形成司法的多元管辖局面,但路、府、州、县等管民官府无疑依然是最重要的地方司法机关。其中,“县极下,去民为最近”,录事司“列曹庶务一与县等”,元人常以“司县”并称。元代还有一些没有属县的州“得亲治民”,司法地位实际与司、县类似。在元代多级复合地方行政体系中,处于末端的县级政府不像路总管府需要负责重刑案件的审判,相比唐宋杖罪以下“县决之”,其权责亦大大限缩。但县级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体系中与民众交集最多的“亲民官府”,负责受理词讼、追证检验,并作为第一审级进行审判,在地方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在以往有关元代地方司法机关以及元代县官的研究中,学者们已对元代县级司法职责、司法程序以及县官的司法实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拟以县级政府中最普遍的“县”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节奏、空间结构以及官吏角色等不同角度,呈现其司法运作的深层秩序,进而在长时段视角下考察元代县级司法的运作模式及特点,以就正于方家。
一、滞讼背后的制度之困
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无论就个体司法救济的有效性,还是就维系社会秩序而言,司法的及时性无疑都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元代县级司法中,狱讼稽迟却是普遍现象,考察其背后的制度因素对于理解元代县级司法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司法运行中的滞讼
在元代法律文化中,审判效率与审判结果同样受到重视,“有司廉明,随事裁决而狱空”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图景。元人胡祗遹甚至认为“稽迟害民甚于违错”,概因“违错之奸易见,稽违之奸难明”。元初针对地方守令定“五事考核”之法,其中“词讼简”一项的要求之一即是“讼无停留”,这与唐代“四善二十七最”中的“决断不滞”是一脉相承的。元政府于至元八年(1271年)规定的公务程限为“小事限七日,中事十五日,大事三十日”;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又改为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相应地,元代司法监察亦将应审不审、应释不释、应结不结等淹禁稽迟现象作为纠治重点。
从诉讼档案来看,元代地方司法运作中确实有比较明确的时间规范,对勾追、检验等流程皆有具体时限要求。如黑水城遗址出土的M1·0616(Y1:W64)号文书即是一件土地案件的勾追文书,其中明确规定被告人应在文书下发后的两日内赴官。但分析众多案例可以发现,不同案件的审理周期相差极大,时效性其实很难保证。在案情不复杂的情况下,县级政府审理一个案件并不需要太多时日。如大德五年(1301 年)廉酉保被平山站刘提领打死一案,案发于八月十七日,廉酉保母廉阿罗次日向归善县衙报案,八月十九日案件已由归善县申报至惠州路,八月二十日归善县进行检尸,八月二十六日检尸文书申报到路总管府,前后不过十日而已。然而至大三年(1310年)庐陵县周左藏坟墓被盗一案,从七月二十九日案发,到十月二十六日申至吉州路,前后则有三月之久。
由于不同案件本身差异极大,其审理周期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很多案件稽迟淹禁显然并非源自案情本身。郑介夫曰:
《至元新格》该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发遣。违者量事大小,计日远近,随时决罚。今小事动是半年,大事动是数岁。婚田钱债,有十年十五年不决之事。讼婚则先娶者且为夫妇,至儿女满前而终无结绝;讼田宅则先成交者且主业,至财力俱弊,而两词自息;讼钱债则负钱者求而迁延,而索欠者困于听候。况刑名之事,疑狱固难立决,其对词明白者,可折以片言也。有司徒以人命为重,牵连岁月,干犯人等,大半禁死。但知一已死者当重,不知囚禁以至死者十倍其数,尤为不轻也。更无一事依程发遣,而违者亦无一人依格决罚,岂非虚文议狱乎?
郑介夫这段话很好地描述了元代的滞讼现象。正如其所言,当时不仅刑名案件时常出现“稽迟”“淹禁”,就连应当在司、县即应予以断决的婚田钱债等“小事”亦“动经一年、二年不决”。延祐二年(1315年)和和奉使宣抚河东陕西,决滞讼达一千二百余起。至正八年(1348年)十二月,江浙行省“共计见禁轻重罪囚一千三百一十五起,三千九百三十六名”,而罪囚之被禁月日竟有达十五年乃至二十年者。元政府虽立小事、中事、大事之限,现实情况却是“府州司县上至按察司皆不举行”,几成虚文。
(二)滞讼产生的制度因素
滞讼现象之所以普遍出现,其原因当然非止一端,或告诉者反复“缠讼”,或官员故意“掯勒延迟”,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元代县的司法权限虽然不高,但在地方司法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元制,“诉讼人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陈告”,“百姓不得越诉,诸衙门各有分限,不得受越诉”,因而,亲民的县级政府受理了绝大部分诉讼。由于判决权限的限制,县只需判决笞刑五十七以下的案件,属于这一范围的大多是民事纠纷或者轻微刑名案件。然而“民讼之繁,婚田为甚”,地方社会绝大部分诉讼案件其实正在县的判决权限内。胡祗遹就指出:“小民所争讼,不过婚姻、债负、良贱、土田、房舍、牛畜、斗殴而已,所犯若无重罪,司县皆当取决。”对于超出权限的案件,县虽无权判决,但也要进行初步的审问即“略问”,然后“解赴各路州府推问追勘结案”。从元贞三年(1297 年)《儒吏考试程式》中所载重刑案件县的呈文来看,县对于重刑案件虽无判决之权,但从立案、检验、缉捕到案情的讯问皆是其必须履行的职责,案件的最终判决正是建立在这些工作之上的。
正是由于县在地方司法体系中的制度角色,使其面临着巨大的狱讼压力,在一些人口繁夥的地区尤其突出。如龙兴路南昌县“日数十牒”;平江路长洲县“地广人稠,牒诉轇轕”;吉安路庐陵县“西江最北县,亦最剧处,讼牒文牍山积”。与此同时,县级政府本身却无暇应对。胡祗遹在《折狱杂条》中曰:
十月一日务开,三月一日务停,首尾一百五十日。每月先除讫刑禁假日四日,计二十日;又除讫冬节、年节前后各一日,计六日;两月一小尽,除讫三日;立春节,除讫一日;进年节表一日;乙亥日三日;若遇二月清明节,又除讫三日,计二十七日。中间或遇同仕上官下任,吉凶庆吊,迎送上司使客,大约又除讫十余日,总计五十日。余外断决词讼者,止有一百日。或遇两衙门约会相关,或干证不圆,或勘会不至,或吏人事故(转按、疾病、上司勾追刷案之类)。经两吏人手,又虚讫十余日,中间止有八九十日理问辞讼。又以监视造作、劝农、防送递运、府州勾追、按察司差委,得问民讼多不过五六十日。
此处胡祗遹的着眼点在于批评停务制度的弊端,但他对狱讼时间紧缺的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的。而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元代日常政务运作中有诸多“停审日”,大大削减了处理狱讼的时间。其中对于县级司法最常见的婚田词讼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停务制度。自唐代起,为防止民众由于争讼而延误农时,政府开始实行“务限法”,婚姻、田产、钱粮、债负等案件的诉讼和审理被限定在十月至次年三月的半年内。到宋代,《宋刑统》在继承《唐令》六个月务限期的基础上,又补充规定“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民众的告诉时间进一步缩减。至南宋,由于江南气候远比黄河流域湿热,为不妨碍农时,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 年)颁布的《绍兴令》又规定二月一日入务、十月一日开务,停务长达八个月。元初延续金《泰和律》的做法,规定“自十月一日官司受理,至二月三十日断毕,三月住接词状”,停务期比南宋稍有缩短,但仍长达七个月。
停务制度的初衷是避免“妨农”,但无疑极大影响了司法的正常运作,案件常常无法及时处理。许多案件在停务前无法结案,经过多次务开、务停,乃至“有经十余年未得结绝者”。鉴于此,元政府先后对停务制度进行了数次修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户部所引圣旨节文中曰:“年例,除公私债负外,婚姻、良贱、家财、田宅,三月初一日住接词状,十月初一日举行。”似乎“公私债负”案件不再适用于停务制度。大德三年(1299年),根据山东肃政廉访司经历张璘的建议,中书省对案件停务的次数进行限制,若经两次停务不能结绝则不再停务,防止复杂案件不经断决即因务限而停摆,循环往复。大德六年(1302 年)再次强调,“二次农隙之间而不结绝,所属官司拟合治罪,必要本年杜绝”。延祐四年(1317 年),规定“告争婚姻事理,如不妨农,随时归结”,婚姻类案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停务制度的限制。
除务限法导致的停审外,元代还存在许多假日和禁刑日。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便形成“五日一朝”的休沐之制,至唐宋更是发展出了主要由旬假、节假构成的假宁制度。其中,唐代除每月初十、二十、三十共3日旬假外有节假53日。宋代节假更多,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曰:“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代早期继承了唐宋旬假之制,但在节假方面无论种类还是休假日数,相较唐宋皆大为减少。据中统五年(1264 年)条令:“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旬假外共计十节十六日,其中天寿节为皇帝诞辰,其余基本为民俗节日。
至元十四年(1277 年),中书省奏请用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和元命日代替旬假。这其中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又称“禁刑日”,亦即胡祗遹所说的“刑禁假日”,源自南北朝以降佛教的“断屠月日”。不过与前代相比,元代的禁刑日不仅在时间上由“十斋日”变为了“四斋日”,更重要的是唐宋时期断屠月日只是禁止执行死刑,而元代禁刑日则禁止一切审囚断罪,“职官于禁刑之日决断公事者,罚俸一月,吏笞二十七,记过”。大德元年(1297年),建昌路南城县蓝田巡检夹谷德祯就因禁刑日将弓手殷祥、周顺“各决一十七下”,被断二十七下。所谓“元命日”,根据张帆先生研究,即“本命日”,指皇帝生年干支所对应之干支日,一年共有六日。如忽必烈生于“乙亥岁八月乙卯”,其元命日即乙亥日,前文胡祗遹所提及之“乙亥日三日”即为此。不同皇帝在位,元命日根据其生辰各不相同,但根据元代相关规定,凡元命日官员皆要“率领僧道纲首人等,就寺观行香祝延圣寿”,同时与禁刑日一样,“有性命的也不交宰杀有,人根底也不打断有”。无论是禁刑日还是元命日,司法运作很大程度上处于停顿状态。
其二,在停审日以外的正常时段,司法运作又受到其他各种繁杂公务的影响。首先,元代的地方官员作为肩负“征收赋税、调节纠纷和维持公共秩序”等广泛职责的地方治理者,其日常公务当然不限于狱讼,而是需要同时应对赋役、差发、救灾等繁杂事务。尤其亲临治民的县,其任务更加琐碎而繁重。元代县所辖人口虽多寡不一,但户至数万、口至十数万者不在少数。其甚者如温州路永嘉县有65077 户,嘉兴路嘉兴县更高达120742户。而其所设正官,不过数员而已。元代以户口多寡为标准将县分为三等,其中上县设达鲁花赤、县尹、县丞、主簿、县尉五员正官,中、下县又不置县丞,仅四员而已。按惯例,元代各项政务皆差一名正官提调,“虽舆台皂隶所当为之事,部符下州郡,州郡下司县,必曰委正官一员亲身监视”。所谓“正官有限,公务无穷”,“不三四事则无人可委”,衙署为之一空,甚至“胥吏抱案无人判署”。元人李谦论“为县难”曰:“县极下,去民为最近,凡省部符檄一出,诸道趣属郡,郡趣县,至县则布之于民,事事必躬莅之。若茧丝之赋,粒米之征,调度力役,牒诉狱讼,连证会逮,案牍填委,吏雁鹜行以进,戢戢取判其前。率则平旦视事,至日旰乃得尝食。”面对应接不暇的繁杂公务,当然难以从容处理狱讼。
除治下分内之事外,元代州县官员还经常被上级官府差委,负责工程监造、押运钱粮、起解军役以及审理他处词讼等事务。官员一经差委,常常半年甚至一年无法还职,有些官员甚至多数时间差调在外,终其一任无几日在衙署事。如江阴州同知纳琳哈喇,自任职后先后监造海塘、参与军机、管理市舶、监造佛经,“三考之中,在州仅数月”。无论州、司、县,正官不过数员,应对治下公务本已捉襟见肘,还要被长期差占,必然影响正常政务运作。世祖至元中后期,征伐事繁,大量州县正官被差委山场伐木、监造船只、收买物料、监造军器,乃至长途押军、跨海运粮,以至“州县正官为之一空,动是经年不得还职。署事之日常少,出外之日常多,是以民间无所愬苦,而府县日以不治”。鉴于此,元政府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规定不得差委长官,“止许次官从公轮番差遣”。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再次强调,路府州县长官、首领官除行省实名差遣或遇紧急军情外,“其余一切公事并不得差占”。但从相关材料来看,此后滥差正官乃至长官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元代,县级政府本质上是肩负全面地方治理职责的“亲民官府”,而非单纯的司法机关;狱讼亦只是政务的一部分,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司法运行要服从于整体治理需求,因而出现了诸如“务限法”等不符合法律逻辑的时间制度。同时面对繁杂政务,官员自然难以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诉讼。其中就前者来说,元政府已经意识到停务制度的弊端并进行了一系列修订,元代节假日相比前代亦大大减少,又以禁刑日、元命日代替旬假,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对正常司法运作的影响。但后者本质上是简约治理模式下官府治理能力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体现,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很难有根本改善。元政府虽多次强调民间词讼须“依理处决,毋得淹延岁月”,但收效甚微,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元代县级司法运作无法回避的困境。
二、县衙空间与司法流程
如前文所述,元代县级政府在简约治理模式下结构十分简单,没有设置专门的司法官员,司法运作亦混同于日常政务之中。那么元代县级司法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前人讨论元代县级司法往往关注其流程,其实只有将司法流程置于其所运行的空间,才能呈现出直观、动态的运作图景。
(一)元代县衙的基本结构
元代规定地方衙署“已有廨宇,不须起盖”,县衙原则上沿用前代旧廨,如上元县与句容县皆“因宋旧治”。不过由于元代前期连年兵燹,地方衙署颇多废坏。尤其对县来说,由于财力所限,衙署毁弃后长年无力修缮,以致“今日僧寮之借榻,明日道宫之假楹,习以成风,因仍苟且,日复一日”。如临汾县治在金末即被豪民所据,官吏长期寄居“老屋隙舍”,一直到至元十三年(1276 年)才以民居作为衙署。中阳县衙在蒙金战争中被毁,数十年未能修缮,官吏只得“侨居民舍,或听政于驿馆,或决狱于神祠”。其中有一些在国家承平以后得以重建,但一直因陋就简者也不在少数。此外,有时因行政区划变动,衙署亦会择地另建。如江宁县,其衙署本在集庆路治北门寿宁寺北,为唐代所建,宋仍其旧。至元十四年(1277年),城中建录事司,江宁县衙乃于故尉司重建。
在现存的元代建筑中,我们已无法找到完整的县衙遗存,不过通过地方志及相关文献,尚能窥其大概。按规制,元代州衙有正厅一座,附两耳房,五檩四椽;司房东西各三间,三檩两椽。县衙除无耳房外,其规制与州相同。这一规定显然仅涵盖了衙署的核心建筑,并没有完整反映出其具体结构。姚燧称元代路、府衙署之格局大致“谯楼、仪门,厅以听政,堂以燕处;厅翼两室,右居府推,左居幕府,吏列两庑;架阁、交钞、军资诸库,与夫庖厩,各自为所”,县衙虽然规模更小,但基本格局大致相同。以建德路寿昌县为例,其旧治于蒙古平宋战争中损毁,王瑀尹寿昌时重新修葺,时人叶天麟所作《重建县治记》中对修葺后县衙的格局描述颇为详细,现抄录如下,并据此绘制示意图如图1。
厅东西翼室各二:东为典史分司,又东其属居焉;西以馆台居府之委差,又西为掌故府。东廊:北六间,列吏户礼三房,南二,为农田房。兵刑工列于西廊,如东制。外:一为投牒所,一为土地祠。门台各翼一室:东作承发,其西陪台,宿直焉。屏基塞门,檐盈环护,以栅葺楼,置更鼓其上。徙旧狱于西偏之阳,为监房,前严门闑,后创堂以便听谳。右圄仿圜土制,使可辟寒暑燥湿。囿之后山原有小祠,则扩之,通民相近。又即尉之故址创营屋三区,俾戍人无淆民居。在十有二月,建台门于颁春宣诏之南。
如图1所示,重建后的寿昌县衙以仪门为界,大致可分为两大区域:

图1 元代寿昌县衙示意图
其一,仪门之内,由南向的厅事、东西两列吏舍与仪门合围所成的院落,构成县衙的核心区,为主要政务处理空间。相对于宋代,元代县衙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除了负责捕盗的县尉外,县丞、主簿皆不再有单独的厅事,这明显是元代群官圆坐署事制度的结果。有些县衙中虽保留了宋代所建官厅,如前述上元、句容两县都有县丞厅、主簿厅、县尉司,但其功能亦不同于往日。吏舍仿中书省六部之制,根据政务类别分设诸房,中以吏员掌案牍。不过,各官府诸房设立的种类不尽相同,常见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厅事东侧耳房,一般是典史幕所在,其位置临近厅事和吏舍,便于政务运作。此外,仪门内的院落中央通常还会有戒石亭,有时架阁库亦在院落中。如镇江路丹阳县衙,东西吏舍之间即有楼“以架阁文字”,厅前又有戒石亭。
其二,仪门之外,县大门、颁春亭、宣诏亭等建筑构成公共或半公共空间。通常来说,元代县衙有大门、仪门两道门,但也有县衙只有一道门。其中大门常建有谯楼,设有更鼓,又称谯门,亦有如寿昌县将谯楼建于仪门者。分别用以颁春典礼、宣读诏书的颁春亭、宣诏亭是重要的仪式空间,其位置或在大门与仪门之间,或在大门之外。如丹阳县颁春亭、宣诏亭在谯楼之外,金坛县则在谯楼之北。县狱一般临近县衙西南,即《周易》中之坤地。
此外,记文中未提及寿昌县衙是否有供官员休息的后堂,但一般来说厅事后面还多建有为数不一的堂、轩等建筑,作为官员“燕处”之地。如丹阳县衙“厅事后有堂二,前曰德政,后曰琴清;轩一,曰近民”,金坛县衙“厅事后有堂曰修己”。不过,由于政务运行由“专官署事”变为“群坐圆署”,元代县衙不仅不再像唐宋时期每名正官“各有厅事”,官员自身亦不再居于官廨,“廨宇止为听断之所,而各官私居,类皆僦赁”。
(二)衙署空间中的司法运作
在元代县级司法中,完整的诉讼审判程序可大致划分为受词、追证、鞫问、判决四个阶段,下面结合县衙空间,分别考察每一阶段的具体运作过程。
元制,民众须赴衙署陈告,严禁“于应管公事官员私第谒讬”。通常来说,告诉者须在陈告之前准备好诉状,于允许告诉之日持诉状赴衙,由衙署谯门或仪门前的当值祗候接收诉状。有些县衙还设有专门接收讼牒的场所,如上文寿昌县之投牒所应该就是这样的场所。诉状递入县衙后会由当值司吏“当厅附籍”,然后由承发房根据案件内容“布散合该人吏”。其中户婚钱债案件一般归属户房,刑名案件则归属刑房。在这一阶段,诉状主要由吏人负责,诉讼人亦不一定要进入衙门内部。不过有时官员为了防止吏人专擅和民众妄告,会在诉状递入后将原告人引入县衙厅事,“当厅口说所告事理,一一与状文相对”,甚至命告诉者直接入衙呈告,由书状人在厅下当场书状。
诉状受理后,官府须进行勾追和检验等工作,为正式审问做准备。勾追的对象包括案件当事人、证人等所谓“干连人”,由祗候、曳剌等胥役下乡勾摄,或发给信牌,由“执里役者呼之”。对于刑名案件中的案犯,通常要由县尉及手下弓手负责缉捕。元代前期,涉案的两造以及干连人等一概要羁押于狱,监狱往往人满为患。大德九年(1305年)以后仅监守奸、盗、诈伪杖罪以上案犯,田土、婚姻、家产、债负、殴詈等笞罪以下案件当事人以及干证人,等候衙门随时传唤即可。在勾追的同时,官府还要进行必要的勘核检验。如命案要检验“致命根因”,杀伤要检验“被伤去处”,贼盗案则要检验“本家失盗踪迹”。
鞫问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厘清案情,进而取得当事人的供词,为最后案件审判提供依据。元制,“鞫勘罪囚,仰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同磨问”,具体到县,则为“县令以次,公厅群问”,即长贰正官与首领官等在厅事共同审问。尤其当审问过程中需要施行刑讯时,需征得全部参与官员的一致同意,“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栲问”。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经常由一名官员专门负责,甚至不少官员“纵令吏贴私下取问”。厅事亦不是案件审理的唯一场所,于狱中就近审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如上文提及寿昌县狱就有专门供听谳的大堂。
一些比较简单的案件在审问后即可当场判决,如张辑任柏乡县尹时遇有民众争讼,即“为开譬诘辩,立与决遣”。绝大部分案件则还需经过复杂的圆议程序。首先,刑房或者户房的承行吏员会拟定判决草案——议札,并由典史签署,即所谓“事无巨细,承吏率先抱案以白首领官,详阅议可,然后书拟”。议札拟好后,所有官员要在厅事圆坐议事,“公议完署而后决遣之”。圆议中先由典史陈述议札内容,即“对读”。然后由长贰等正官讨论,进行裁决。讨论完毕后,由典史根据讨论意见,拟定最终判决书,然后与议正官书押。署名的次序,根据正官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书押,“狱讼期会署文书,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于丞若令”。典史通常不参与圆署,但若到会官员因不习文字或其他原因不能署名,则由其代书,并“具述其故于名下”。圆署完成后,文书上加盖官印即可颁行。
概括来说,简约治理模式下的元代县衙本身比较简单,狱讼事务与其他政务共享同一空间,除监狱外并没有专门的司法空间。在县衙内部,司法运作主要集中于三个场所:一为厅事,主要进行案件的审问以及判决结果的圆议;二为县狱,不仅用于临时羁押,亦是鞫问罪囚的重要场所;三为吏舍,文书攒造与案件拟判皆在此处。这种空间结构反映了元代县级司法的基本运作模式:群官集体决策,首领官总领案牍,吏员具体执行。虽然对民众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咚咚衙鼓响,公吏两边排”的厅事,但其实司法运作很大程度上完成于吏舍之中。
三、官吏角色与权力秩序
相比宋、金,元代县级政府的职官设置发生了两个主要变化:一是在县尹之上另设达鲁花赤,形成双长官制;二是改变宋、金分别以吏员中的押录、上名司吏为首领吏员的做法,单独设典史为首领官,统领吏员。如此一来,元代县级政府就形成了正官—首领官—吏员三级结构,县衙中厅事—典史幕—吏舍所构成的政务空间就是其体现。相比路、府有推官“独专刑名”,县不设专门司法官员,司法运作采取典型的圆议联署制。那么,不同官吏究竟在司法运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其中又呈现出怎样的权力秩序呢?
(一)司法中的长、贰与首领官
在县级官员群体中,达鲁花赤“于官属为最长”。达鲁花赤本为蒙古语daruqaci之汉译,意为“镇压者”。根据札奇斯钦先生研究,达鲁花赤起初是蒙古人在被征服城市所设立的监临长官。入元后,“路府州县皆置达鲁花赤一人,位长吏上,监其治也”,达鲁花赤成为各级地方官府的最高长官,而传统的县尹等官员成为其次官。达鲁花赤的最高决定权集中体现在其掌印权,按元制,官府印信“达鲁花赤封记”。不过达鲁花赤多是蒙古、色目人,他们中很多与汉人官吏言语不通,不谙律法,关于其是否参与具体司法运作,胡祗遹言县级政府审案为“县令以次,公厅群问”,似乎不包括达鲁花赤,叶子奇在《草木子》中亦言,达鲁花赤虽位居最尊,但并不参与日常政务圆署,“判署则用正官,在府则总管,在县则县尹”。不过正如李治安先生所指出的,这一情况只存在于元代早期。自中统五年(1264 年)起,元政府就规定“京、府、州、县官员,凡行文字,与本处达鲁花赤一同署押”。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又规定:“随处达鲁花赤,凡行文字及差发、民讼一切大小公事,与管民官一同署押管领。”在黑水城文书中我们能找到十分确切的证据:
宣光元年闰三月二十一曰申司吏崔文玉等
坐□□□□强夺口等事
亦集乃路总管府推官闫
亦集乃路总管府判官
亦集乃路总管府治中
同知亦集乃路总管府事[八思巴文名字]
亦集乃路总管府总管
亦集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八思巴文名字]
亦集乃路总管府达□□赤
奏议大夫亦集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脱欢
很显然,这件文书是一件案件判决文书的一部分,刚好保留了官员圆署内容,达鲁花赤是在列的。质言之,达鲁花赤在元代前后期出现了角色的变化,即由单纯的监临官员逐渐成为日常政务官员的一分子。杨维桢言,元代早期达鲁花赤并不参与圆议,政务议定后“白之达鲁赤”即可,后来“达鲁赤任与令等,昔之尊而优者,今转烦剧矣”。实际上,元代中后期达鲁花赤不仅要参与圆议,检尸、听讼等事务皆在其职责范围内。如廉酉保被平山站刘提领打死一案,负责检尸的初、复检官员,分别是归善县达鲁花赤阿都赤和博罗县达鲁花赤忙哥察儿。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任职达鲁花赤后,积极参与狱讼。如也先脱因在后至元年间任休宁县达鲁花赤,颇善听讼,“遇有骨肉之讼,语以人心天理,无不感悟悦服”。赫斯至正中监县旌德,“凡讼于庭者,辨其曲直,审其是非”。新乐县达鲁花赤马合末,出身进士,“听讼辨民曲直,必以理胜”。
县尹,“专判署,临决可否,于一邑事,无不当问”,与达鲁花赤并为长官。按元制,“诸公事应议者,皆由下而上,长官择其所长,从正与决”,县尹在司法中有很大的决断权,同时其承担的责任亦尤重。胡祗遹言:“细民之所争,若无异事,不过婚姻、良贱、钱债、土田、户口、斗殴、奸盗而已,此皆县令之职。”元代对地方司法进行全面监察,若有一切违错过犯,负责审问的正官皆要面临处罚,而县尹即首当其冲。因此,许多县尹积极理冤平反,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永嘉县尹王安桢就曾说:“理冤,令职也。”不过相比前代,元代县尹地位又有些尴尬。危素言:“上官制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强者得以把握之。”邵亨贞言:“今乃共坐一署,上又设长以兼领其事,丞、簿、尉无分职,复得以参裁可否,专制之令益不行矣。”质言之,元代县尹上有达鲁花赤,下有诸员正官,在圆署制下,其决断权受到冲击。如太湖县尹李圭卿,因同僚与其有隙,“所决狱,同官辄异议”,李镇安因虑“囚有久系者”,“独自署决遣”,被同僚告发至宪司。尤其面对多由蒙古人出任的达鲁花赤,县尹在权力、地位上都有所不如,“才者弛于承宣,庸者甘为所压”。如王构所言,县尹从容理政的前提,“必其监县之贤,必其佐贰之贤”。
元代之丞、簿、尉为一县佐贰,在元代圆署制下获得了比前代更大的施政空间,“内外百司之官有长有贰,长曰可,贰曰否,事不得行”。其中,县丞只设置于上县,有“贰令”之称。然其上有达鲁花赤、县尹,下有簿、尉,虽作为正官参与圆坐审判,但相对来说权、责都不重。故朱晞颜曰:“夫以一邑之政,居其位而任其责者,或四人焉、五人焉。簿、尉位卑,且有分职,凡狱讼、赋役、簿书期会,文牒所移,必先由是而达乎上,因得市权钓吏,以规一己之私。令长秩尊,专判署,临决可否,于一邑无不当问。丞居其间,似不相渉者,士大夫处此,率压于上逼于下,淟涊怯恧,益相訾謷而数怠其事。”概言之,县丞处中层,事务颇为清闲,任职者大多亦往往不积极参与决策。从现有材料看,县丞分管事务多为赋税,很少负责狱讼。如徐士良任嘉兴县丞,时习之任歙县县丞,皆是主要负责征税。虽然也有县丞主动参与司法,如建昌路南城县丞许晋孙曾平反天灯寺僧人凶杀案,但并不多见。
对于主簿的角色,元人评价并不一致。一方面,如郑玉所言,相比前代“分掌簿书”,元代主簿获得了与长官共同议事的权力,“今之制,长令与簿共坐一堂之上,遇有狱讼,公议完署,而后决遣之。矧一县之事,自下而上,必始于簿,簿苟可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之职,视古为尤难,而责为尤重也”。揭傒斯曰:“得与令丞列坐联署,相可否,关决事,其职乃与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行也。凡狱讼期会,署文书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于丞若令。主簿不可,即尼不行,令虽尊,亦有不得专者。”相比县丞,主簿在司法运作中往往更加活跃,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马贵为分宁县主簿,“有讼久不决,一讯立辨”。吕栗任饶阳县主簿,“凡民有讼曲直,君濯手擿爪径决于前”。另一方面,主簿职位较低,“压于为监为令与丞”。在中下县不设县丞,县尉又专司捕盗的情况下,主簿要承担繁重公务,有些下县以簿兼尉,更是如此。闽县主簿曹仲坚不无忧虑地感叹道:“吾之身一而已,职又最下且繁,彼居吾上者,若是众也,又若是尊也,吾惧吾志之不得遂也。”主簿在司法审理中固然对上司官员有一定制衡,但作为下属,实际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又是值得怀疑的。元人程渊言:“簿佐令者也,簿所欲为,令或不从,非积诚以动之,则不可以有为。”因此,主簿在参与狱讼圆议时须十分注意方式与分寸,如禹城县主簿滕安上与县尹等讨论刑狱“必揆以义,驯驯上说”。
县尉在县司法运作中角色比较特殊。县尉虽为一县正官之末位,但又是唯一有独立衙署的官员,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后还为其专设一名请俸司吏。至元八年(1271 年)规定,县尉“专一巡捕”,“不须署押县事”,“尉于县僚,以察奸捕盗为责任”。但在案件审理中,县尉其实多有参与,“作奸犯科之民,尉职捕而听其初辞,初辞而情,则其刑也不冤”。在抓获罪犯后,县尉首先要对案情进行预审,“听其初辞”,“依理亲问得实”,这对其后的案件审判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不过,县尉虽负责核实案情,但无权单独审理,预审完毕后须“牒发本县一同审问”。由于县尉在正官中地位最低,时常“曲意附县官吏”。但由于县尉负责捕盗,若主动参与,在司法中往往起到很大作用。如苏泽任新昌县尉,“县有舛令谬事,或民有冤坐,召吏切责,皆顿首服实,即理改。县有狱弗理,即委尉平决”。
元代首领官品秩虽低,但其统领群吏,负责簿书案牍,又有参与群议,乃至与长官争衡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为长官之外的又一权力中枢,作用不言而喻。在司法运作中,首领官虽然无权审断词讼,但圆议前之议札、最终判决之文书,皆由其审定。首领官虽不参与最终的签署,但按照元制,首领官有权对长官的裁决提出异议,“长官处决不公,首领官执覆不从,许直申上司”。正因如此,元代州县首领官对司法运作实有很大影响力。如宋春卿任职暨阳州吏目,精于狱讼,“两造在前,君一览辄曰:甲某直,乙某当罪”。甚至当长官持异议时,亦敢于与长官相争曰“事如是如是,不如是不得行”,以至于同僚有“州事一由幕府”之叹。典史作为县中唯一首领官,仅从九品,但职责十分关键,“持案牍之权,与官吏相可否”。元人郑玉评价说:“典史,县幕官也,其受省檄,秩从九品下,其事则检举勾销、书拟断决,禄薄位卑,务繁任重,一县之得失,百里之利害,常必由之。官所以治其民,民所以治于官,而位乎官民之间者,典史也。”由此可见典史角色之重。典史往往能够在案件判决中起到关键作用,如徐泰亨在任职归安县典史时,就平反诸多疑狱冤案。
总的来说,在元代县级司法运作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尤其县尹,在双长官制以及圆署制下,不再有专决之权。理论上说,这种权力制衡对防止专断所造成的司法违错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又对司法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在圆署制下,案件的判决必须得到群官一致同意,很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危素就曾指出:“无问事大小,必同堂论之,故人自为说,而政多旷废。”同时,当官员之间观点不一,也很容易出现“吏缘为奸,上下其中”的现象。实际上,在元代县级司法运作中,官员之间形成权力制衡的同时吏权却大大上升,甚至出现“判笔一从乎胥吏”的现象。
(二)吏的角色:从“职簿书”到“舞文法”
“今夫一县之务,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元代县级政府中,吏员是远比官员更为庞大的群体。元代县衙中吏员主要有司吏、书状、典吏、贴书等。其中司吏分管各房案牍,地位最高,为有俸吏员。按照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定额,上、中、下县分别设司吏六名、五名和四名,后县尉司又专设司吏一名。不过据《至顺镇江志》,镇江路所属丹徒、丹阳、金坛为中县,却各设司吏七名、尉吏一名,可能后来各县司吏员额有所增加。书状吏设于大德五年(1301 年),每县一名,从待缺吏员中选充,专管书写诉状。典吏负责文书收发、保管等工作,在丹徒、丹阳、金坛三县,皆设有典吏两名,分管承发、架阁。贴书是尚未取得正式吏员资格的见习吏员,大德六年(1302年)规定每名额设吏员可以保选贴书两名,后至元二年(1336 年)又规定任务繁重的司房可以选充四名。大致来说,一县约有额设吏员二三十名,但许多地方额外滥设之贴书、主案、写发等往往远超于此,如永丰县贴书曾达百余人之多。
“吏人之职,专主簿书案牍之首尾”,吏员在司法运作中主要“职簿书”,负责各种司法文书的攒造、管理、收发等。据前文,诉状进入县衙伊始,即由吏员负责登记、递送。特别在大德五年(1301年)以待缺吏充书铺后,书状亦由吏员负责。诉讼被受理以后,视其性质分配给刑房或户房,由司吏“承行”,负责该案一应案牍。承行司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主要负责记录供词,案件审理完成后,还要拟定判决草案,经首领官签署后即成为供官员圆议的议札。下面黑城文书中的M.0671(F116·W78)号文书即亦集乃路刑房草拟的议札:
(一)
(前缺)
1.刑房
2.呈:承奉
3.判在前,今蒙

5.一对款开坐,合行具呈者:
6.犯人二名
(后缺)
(二)
(前缺)
1.呈
2. 至正廿二年十二月吏贾
侯
3.阿兀告妾妻失林



7. 初□日
总的来说,在元代司法运作体制中,吏员虽不可或缺,但并没有决策权。案件的判决方案虽由承行司吏草拟,但从上引议札文书可见,其本身也是在群官“议得”的基础上拟就的,且最终还要经群官圆议商定。就制度角色而言,吏员只是“官之臂指”而已。
但是,“身躭受公私利害,笔尖注生死存亡”,现实司法运作中,吏员的角色绝非仅仅“职簿书”。一些吏员在查明案情、平反冤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天台人朱敏任吏于仙居、瑞安等地时,“前后所全活四十余人”。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吏员在司法运作中“扭曲作直,舞文弄法”。一些吏员常常趁他人纠纷而教唆词讼,甚至教人诬告,借以从中渔利。如在宁都,有吏员一日之间接受词讼十余起,“皆架虚诋讦渔猎,餍所欲则火其牍”。在湘乡,胥吏往往“嗾无赖之徒诬人以非罪”。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有的吏员因收受贿赂,设法颠倒曲直、出入人罪。如在婺州路金华县一例案件中,吏员在受贿后,将被害人死因由殴打致死改为病死。兴国县茶商吴宁七杀人,受害人之子诉官,吏员故意拖延,以致尸体腐坏无法检验。胡祗遹批评“奸吏之不奉法,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助强挫弱,见贿屈理,巧讣佞辞,把持官府,虚文诡案,愚弄判笔”,“吏弊”成为元代司法运作中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
元人认为胥吏之所以舞文弄法,源自其出身、素养和待遇,乃“势使然尔”,但“吏弊”本身又反映出司法运作中的“吏权”。元人李存言:“州县之胥,谙练乎民俗之情伪,惯尝乎官长之巧拙,……其所掌者分,而官长之务总;彼其所资谋者众,而官长之党寡。至又有同僚之暗谬者,则讬之以为腹心;编民之豪黠者,则援之以为党与。”吏员之所以能操纵司法,大致可从以下三点加以分析:
其一,吏员对文书运作的操控。张养浩言:“天下之事无有巨细,皆资案牍以行焉,少不经心,则奸伪随出。”在元代诉讼审判中,每一个环节都与案牍文书密不可分,从诉状、拦状,到尸、伤检验文状,到识认状、取状、准付文状、服辩文状,它们构成复杂的司法文书体系。这些文书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司法运作的结果,决定着案件的最终走向。吏员操纵司法,一个重要途径即是伪造、替换、篡改司法文书。如前述刘提领打死廉酉保一案,归善县司吏徐礼和博罗县吏人萧仲壬,分别替换初、复尸检文解,掩盖了廉酉保的真正死因。许有壬认为,吏人之所以能够“高下其手,舞智作奸”,源于为官者无法做到“熟于案牍,精于事情”,他批评道:“其有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事权之重,欲不归之于吏,不可得也,为吏者虽欲避之,亦不可得也。”从元代县级司法体制来看,长贰正官本身并不参与具体的文书运作。且如元人所言,即使正官与首领官“尽通案牍”,由于案牍繁冗,根本不可能“一一亲行检视”,而只能“处事皆凭口覆”。在这种情况下,吏员很容易在司法文书中高下其手,“笔尖上斟量一个轻重,案款内除减了增加”。
其二,官、吏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诉讼审判中,司法者不仅要详察案情,还要通晓律例,甚至周知民俗,但在这几方面吏员相较判署官员皆有着巨大优势。首先,所谓“吏所掌者分,而官长之务总”,相对于总揽庶务的官员,具体承行某一案件的司吏无疑更熟悉案情。而司吏相对于贴书亦如此,“问东而不知西,问首而不知尾,一听于主案贴书之所可否”。其次就社情民俗来说,官员踵足瓜代,“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而吏员久在衙署,则“谙练乎民俗之情伪”。如赵偕对慈溪县尹陈文昭所言:“苟不别求耳目以广视听,则无所见闻,何以行事?”大德七年(1303 年)起,元政府对司吏进行定期迁调,但贴书仍盘踞衙门,“他处迁来吏员不知本土事情,凡有施为,多系听从旧存贴书。贴书之久占衙门者,愈得以肆其调弄之奸,蠹官害民,莫此为甚”。最后,元代州县官员的选任机制中没有对法律知识的相应要求,官员本身亦多未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元杂剧中州县官员的形象多是“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这种艺术化的描写是有现实依据的。尤其在元代“断狱用例不用律”的大背景下,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都要依判例审断。即使官员熟稔刑名,也很难通晓层出不穷的判例,只能依靠职掌案牍的吏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员很容易“为吏所蔽”,对吏员所书写的议札亦很难有所更改,只是判署而已。
其三,吏员在案件审理中的不当介入。元政府至元五年(1268 年)设立御史台以及至元十四年(1277 年)设立江南行台时皆规定,不得委派司吏、典吏、弓手人等负责审讯,然而现实中吏员鞫狱却比比皆是。如至元二年(1265 年)成武县一例案件,祗候人李松见张宝童强奸其妻子,愤而将张宝童打死,司吏在鞫问中教令李松在供词中掩盖强奸这一关键案情,致使李松被判处死刑,后断事官重审才得以改判。又如至大四年(1311年)番禺县一例案件,因田土相争,梁伶奴用木棍打死蔡敬祖,番禺县尹马廷杰在检尸后却不亲自审问,转令司吏、贴书私下推问,并在推问过程中教唆梁伶奴虚捏案情、掩盖事实。张养浩建议“在狱之囚,吏案虽成,犹当详谳”,也侧面反映当时吏员鞫狱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委派吏员负责审讯,无疑给予其趁机渔利的机会,即使后面还有形式上的群官圆审,恐怕亦只是过场而已。而吏员既负责审讯,又草拟判决,集鞫、谳之权于一身,左右司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吏员由于长年居于官府,往往结成党羽,进而交接权豪、把持官府,“上下交通,表里为奸”,官员贪鄙者很容易与其同流合污,进而为其所挟持。由于此种种因素,吏员得以由“职簿书”而“舞文法”。在官员之间形成权力制衡的同时,吏权却难以约束,司吏架空官长,进而贴书架空司吏,成为元代县级司法中的普遍现象。许多官员尝试通过检查案牍、躬亲理讼、广开言路以及禁止吏员结交豪民等方式抑制吏权。如江宁县主簿陈遘,时常“检饬吏牍”,使吏员“无间隙可入”;慈溪县尹陈文昭,通过询问耆老以及民众封书言事,“县大小事无不周知”,吏“噤不敢出一语,惟抱文书呈署而已”;胡祗遹建议“钤束吏人”,令其“非事故,白昼不得出离各房”,同时对诉状及时登记、处理,使其“毋落吏手”;张养浩建议“诸吏曹勿使纵游民间,纳交富室,以泄官事,以来讼端,以启幸门”。然而吏权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与元代县级司法体制息息相关,吏弊也就很难从根本上予以杜绝。
四、结论
自秦以降,县作为最为稳定的基层政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尤其中唐以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支配由设置乡官直接掌控转为间接支配,“拉开了‘县令之职,犹不下侵’的序幕”,县成为国家正式行政权力的末端,亦是国家和民众接触最为集中的地方。而对于县级政府来说,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之间的矛盾则愈演愈烈:作为亲民之官府,县级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治理压力,然而受财政和技术限制,又只能维持简约的建制体系。具体到司法来说,由于混同于日常政务之中,县级司法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司法运行要服从于地方治理的整体需求,因而经常表现出非法律的逻辑;另一方面,受其他繁杂政务影响,官员面对层出不穷的狱讼往往难以招架。在民风“好讼”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司法效率很难予以保证。元代县级司法中的滞讼现象,很大程度正是这一制度困境的反映。
在延续“简约治理”的同时,元代县级司法运作又有一些新变化。在元代县衙中,厅事—典史幕—吏舍构成了核心政务空间,这正是元代县级政府正官—首领官—吏员三级结构的体现。相比路级政府专设推官掌刑,元代县级政府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在圆署制下,其基本运作模式为群官集体决策、首领官总领案牍、吏员具体执行。元代圆署制度虽很大程度上源自草原集体议事习俗,但在中原王朝亦早有渊源。如唐代就有“四等官”审判制度,司法官员按权限和职掌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四等,各司其职、联署文案。宋代在州、县日常政务运作中建立集议制,“诸州通判、幕职官,县吏丞、簿、尉,并日赴长官厅议事”,州之通判、幕职官还要于长官厅或都厅“签书当日文书”。宋代还特别规定重刑案件必须经过“聚录引问”,其中就县级政府而言,“其徒罪以上,令、佐聚问,无异,方得结解赴州”。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元代圆署制至少在宋代已经开始萌芽。不过相比元代,唐、宋时期的集议联署制度尚有许多局限性。唐、宋时期聚问基本局限于徒以上重刑案件,而元代则推广至一切大小公事。宋代虽规定州、县皆须实行集议制,但其中县一级不仅相关制度建立晚于州,其实施状况亦不理想,尤其对县一级是否实行“通签连书”亦没有明确规定。概言之,元代圆署制相比前代,适用范围大大扩展、执行力度大大加强。
在圆署制下,元代县级司法中形成了官员之间的权力制衡,特别是由于双长官制度和首领官制度,县尹的专决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机制有利于防止专断造成的司法失误,但互相掣肘造成的效率低下也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吏员却由“职簿书”得以“舞文法”。在元代县级司法运作体制中,虽由群官圆议做最后决策,但拟决之权却在吏员。借助于对文书运作的操控、官吏之间的信息失衡、在案件审理中的不当介入以及与地方社会的特殊关系,吏员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司法运作,官员被架空,圆议联署也形同虚设。从宋代起,吏权便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而元代圆署制下吏员的制度角色为其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至明初,朱元璋将“谋由吏出”视为“胡元之弊”,要求官员“所任之事,各必躬亲理之”。而随着双长官制的取消和首领官第二中枢地位的丧失,主官负责制再次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