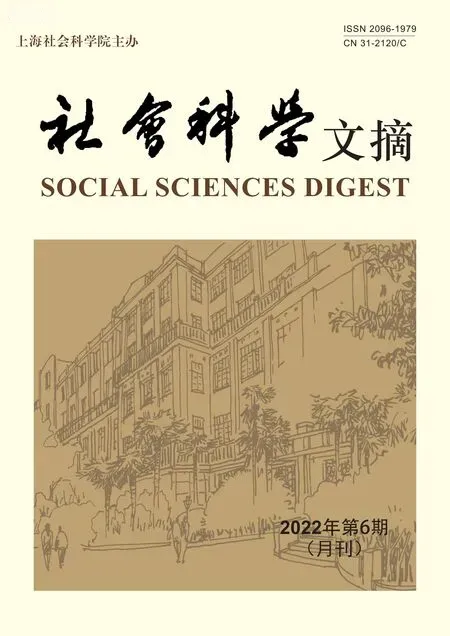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文/瞿林东
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助于厚植中华民族之民族自觉性的知识基础和历史情怀,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根基和历史自信。本文的旨趣在于,一则是概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的历史条件及其阶段性特点,二则是论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
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从中国历史进程来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皇朝的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形成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华夏族出现;同时,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汉人和胡人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形势。
这种民族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是由以下原因促成的:第一,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约500年,历史久远的夏族、夷族、蛮族、戎族、狄族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周王室各封国为代表的“诸夏”得到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夏文化的覆盖面;而夷、蛮、戎、狄等“诸夷”和“诸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分别形成了以东方齐国、南方楚国、西方秦国、北方晋国为中心的民族融合体,成为秦汉统一皇朝的民族构成的基础。第二,秦皇朝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字”等诸多统一措施,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而当“汉承秦制”继续推行这些措施时,它们的作用就更加充分显现出来。第三,儒家文化官方地位的确立为民族间文化认同提供了标准。第四,司马迁《史记》撰写出了当时中华民族史的全貌和中华民族初祖及其以下的历史,班固《汉书·地理志》则写出了中华民族当时的生存空间。第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之最重要的物质条件。
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蛮、戎、狄等族深入融合的华夏族为核心,包括中原及周边的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秦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阶段。从《史记·匈奴列传》可以看到汉、匈双方互通信函以及“和亲”之“约”、“关市不绝”的情况;从《史记·东越列传》,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东越的赞叹之情;从《史记·大宛列传》可以看到张骞出使西域,亲身经历或了解匈奴、月氏、胡、越的复杂关系,并得知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以及西南夷等域内外情况。班固在《汉书》中用“诸夏”和“八方”来概括当时全国的范围。东汉时期,称“华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而且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诸夏”与“四夷”的不同是文化上的差异。思想家王充深刻地指出:诸夏之人所以贵于夷狄者,以其通仁义之文,知古今之学也。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中华民族,不论在密切的程度上还是在活动的地域上都比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新的提升和扩大,尤其是对民族包容的认可和民族间文化差异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华民族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东汉灭亡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和西晋的短期统一,继而是南方东晋和北方十六国的南北分割以及南北朝的对立,直至隋朝的统一,中国历史经历了370年的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这期间,从东晋、十六国开始的约270年间,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来看,发生了值得关注的几件大事:一是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纷纷南下,在广大的中原和北方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在相互矛盾、冲突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二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魏政权(史称后魏或北魏),在实行一系列有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统一北方,与南方宋、齐、梁、陈等朝形成对峙的政治局面,凸显出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三是“华夏”作为族称或地域的代称的观念有更加准确的涵义和广泛的使用。四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这四个方面大事,为隋唐新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的和民族的基础,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隋唐时期走向发展阶段的政治前提和民族根基。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志:
第一,在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华、夷狄作同等看待。唐太宗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五条政治经验时,他郑重地说过这样的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唐太宗在朝廷上对群臣总结经验时讲的这番话,可作为当时的国家政策看待。同时表明,“中华”“夷狄”是作为族称来表述的,自亦包含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第二,“族类”意识的提出。唐玄宗在《赐突厥玺书》一文中认为:“汉日有呼韩邪,是卿族类,既率部落,来慕中华,终保宠荣,足为前鉴。”这里说的“族类”,当含有“民族”的成分,说明突厥与中华的密切联系。
第三,理性的民族观的发展。中唐史学家杜佑在其巨著《通典》中指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这段论述表明,“中华”与“夷狄”在古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处在同一文明进程上的民族共同体,都具有“朴质”的特点,只是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历史进程的差别。杜佑这样看待中华与夷狄在风俗上的差别,与前引王充所论,都着眼于文化,是当时最进步的民族观念。
第四,民族交融的标志性著作的出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在这一广泛的民族交融的新阶段,在当时的历史地理的撰述中也有标志性著作的出现。唐代的历史地理学家贾耽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从《海内华夷图》可以得到三点认识:一是自秦汉以下,“海内”乃是当时政治统一体的代称,是“全国”之意;二是“华夷”从对称演变为合称,表明民族交融的密切关系;三是这种民族交融状况需要而且可能用地图表现出来,正是历史进程本身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是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又一部反映中华民族面貌的重要著作。
第五,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完备的修史制度及其重要意义。唐代先后修成“五代史”及《晋书》,使《史记》《汉书》以下,历朝皆有史。这一做法,反映了历史自信的精神,后代因之不绝,成为传统,使中华民族拥有一部不曾间断的历史。
综上,隋唐时期人们民族观念的发展、提升,在政治、文化、历史撰述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表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发展阶段的突出标志和特征。
中华民族的壮大和巩固(从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及相关特点来看,辽宋夏金几个皇朝并立及相互冲突的政治局面,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以党项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西夏、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金,都是一度强势的皇朝。它们同两宋皇朝形成复杂的关系,时战时和,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持续了300多年,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辽、夏、金三朝的政治、社会、文化进程表明,契丹、党项、女真等族,都已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阶段,而两宋皇朝在隋唐皇朝的基础上,在经济、文化方面继续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政治上的格局,同样会影响到当时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但比之魏晋南北朝的形势来说,这是一个文明水平更高的历史平台,必将给历史带来更大的进步。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争战、和议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时代。
从辽宋夏金时期到元明清时期,各族在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过程中,其积极成果,是把中华民族从发展阶段推进到壮大、巩固阶段。这个壮大、巩固阶段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中华民族生存空间的扩大。继辽夏金时期,元皇朝的建立,既是这种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的结果,又为这个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壮大和巩固——提供了政治条件。在这个政治条件下,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的联系都得以实现,从而壮大了自身。
第二,民族交融的加深与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在《辽史》《金史》和《宋史》等史书的记载中,这种深度的民族交融和民族观念的变化、发展都有突出的反映。从过去一些对立的理念和称谓到出现和谐的理念和称谓,再到“华夷同风”“混一中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这种民族交融和观念的变化,不论在朝廷,在军营,还是在民间,都已经十分深入了。
第三,重视修撰正史,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恢宏的包容性。元朝建立之初,便有修撰辽、金二史之议,继而更有修撰辽、金、宋三史之议,但因“正统”问题多有歧义,故迟迟未能修撰。元朝是一个盛大的朝代,但它脱胎于辽宋夏金这个复杂的政治局面,如何把“正统”问题理顺,一时成了难以抉择的困局。当元顺帝君臣决然承认辽、金、宋三朝都是“正统”时,表明蒙古族贵族集团在民族问题上更看重“混一中华”而不再强调民族界限。说到正史修撰,明修《元史》和清修《明史》,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明太祖朱元璋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是推翻元朝统治的胜利者。朱元璋在元亡之后十分关注修撰《元史》,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胸怀。清修《明史》则新设“土司传”,反映了中央和地方之关系的新形式,也反映了民族交融的新进展。《明史》修撰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古代史上修撰前朝正史的收官之作。中国古代每一皇朝都有翔实的历史记载,构成了中华史学连续不断的历史典籍,它们以前后接续的事实记录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历史。
第四,续修典章制度史,贯穿中华制度文明进程。元修的《经世大典》一方面保存了“本朝典故”,具有民族特色;一方面又按照唐、宋《会要》的体例进行编纂,这是在继承中有所丰富,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各民族的创造而越发丰富多彩。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史同样十分重视。从对“三通”的重视到撰《续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从撰《续通典》《续通志》到撰《皇朝通典》《皇朝通志》,反映了清朝对典章制度史的认同和继承、发展。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地续修中国古代制度史,是从历史撰述上贯穿了中华制度文明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领域的创造和实践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简短的结论
当我们简要地回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壮大与巩固之自发阶段的历史后,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理论上的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武王伐纣时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夷、蛮、戎、狄,从西汉时期的匈奴到西域各族,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到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以及经济重心南移与南方各族,从辽宋夏金时期的契丹、党项、女真各族到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满洲、回、藏等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间,汉族的发展也是因有其他民族参与、融入而不断进步。汉族人口众多,但同时也是由许多少数民族混血形成的,故汉族的贡献也包含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一言以蔽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第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有必要认清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在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有和好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什么是主流,我们要有明确认识。如著名学者白寿彝所言,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来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需要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同考察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形势联系起来分析,揭示其中存在的规律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因对权力和利益的贪婪而引发战争,并且往往把一些民族卷入其中,造成大规模的民族迁移苦难。但同时,民族迁移促成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当全国出现统一的政治局面时,这种交往交流交融所获得的成果则可得到巩固和进一步提升。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辽宋夏金至元明清时期,看得十分清楚,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现象。这样看待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第四,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史,要认识到中华文化是滋养中华民族生长、壮大的养料。在中国历史上,先秦诸子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汉唐文化、修史传统等思想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十六国时期各国办学校、兴教育、学习儒家经典以及北魏孝文帝采取的诸多改革措施,到辽夏金元清等皇朝时期,统治者都重视对中原历史文化典籍的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华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中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