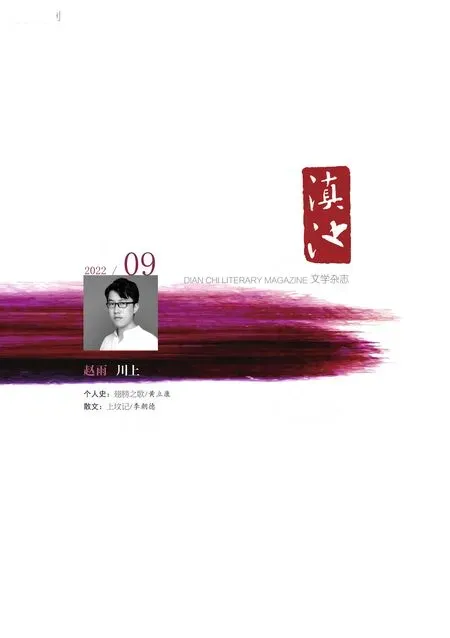垂杨柳
短篇小说 杨永磊
当年12月
下午睡起来后,我到街口的地摊上买了一大堆食材,有菠菜、白菜、芫荽、豆腐皮、土豆片等等,又去对面的羊肉铺买了一斤羊肉卷,准备晚上吃火锅。洋洋下午四点半休班,晚上七点半又要上夜班,如果她回来,就跟她一起吃,如果不回来,我就一个人吃。
这一带的房子被刷成了赭红色,外观看上去崭新,实际上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老楼。街道两旁柳树成荫,但很拥挤,小车随便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骑车从路这头到那头,要好几分钟。早上有早市,花鸟鱼虫,古玩字画,针头线脑,熙熙攘攘的,图个热闹。上午九点一过,早市就像露水见到朝阳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经常上夜班,按说看不到早市,可是失眠症时常发作,凌晨三四点躺床上,头脑清醒得像明镜,翻来覆去一会儿,外面就蒙蒙亮了。天一亮更睡不着,索性不睡,坐在床上抽烟,看烟头一明一灭。几根过后,清醒了一些,穿衣出门,到早市上逛一圈,听一帮老北京讨价还价,买几个荠菜包子,站着吃完,回来再睡。
我给洋洋发了微信,问她晚上回不回来吃饭,她没回。约莫五点钟的时候,我听到门响,寻思是她回来了,开门一看,她正在换鞋。我说,洗手吧,咱们吃火锅。她没说啥,跟我进了屋,瘫在床上。我想在她身边躺下,她推了我一把,说,起开,添锅去。菜择了没?我说,都择好洗净等着你呢。她来了精神,从床上起来,坐在餐桌旁。这个餐桌是我去年刚搬进来时在早市上淘到的。那天早上我照例睡不着,逛早市,看到了炸鸡店外面那张桌子。桌子上没放什么东西,落满灰尘,油腻不堪,桌腿上满是泥点。我问老板这张桌子卖不,老板说两百块钱搬走。我说,顶多八十。老板没理我,我转身要走,老板叫住我说,一百五。我没答话,老板说,一百二,不能再低了。我说,一百块钱,现在搬走。老板说,不卖。我又要走,老板说,搬走吧搬走吧。我说,我一个人可搬不动这大家伙。老板招呼一个伙计帮我把桌子抬回家,我用洗洁精和铁刷子把桌子上上下下清洗一遍,铝合金的质地露了出来,搬进屋里,闪闪发亮,有蓬荜生辉的感觉。
吃着火锅,我刚想引出话题,洋洋停下筷子,说,咱俩现在算什么关系?我愣了一下,没料到她会问这个,说,不知道。搭伙过日子吧。她说,谁要跟你过日子。我说,咱俩是什么关系重要吗?重要的是咱俩现在是这样的关系。这就够了。她不再说话,低头吃菜,我往她碗里夹了一筷子羊肉,她夹回我碗里,说,晚上节食,只吃菜。我说,你经常值大夜,天亮下班,有时候下午也得上班,吃不饱能顶得住?她说,我想换个工作。我说,能不能跟你们领导商量一下,别总值大夜,把身子都熬坏了。我上夜班,凌晨两三点也下班了,你是女孩,一值还值一宿。她说,整个医院好几十个护工,给你排什么班你就上什么班,你想不值大夜就不值?我说,换了工作你想做啥。她说,啥都行,只要别天天让我上夜班就行。我说,前几天我去十里河喝胡辣汤,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她说,招什么。我说,收银员、服务员、面点师、炸锅师、洗碗工,月薪三千到五千。她说,你喝个胡辣汤跑那么远。我说,没办法,一周总得去喝一次,骑车也就二十分钟。主要是那味道。她说,不是很辛辣吗?我说,要的就是这种刺激,一周一回。她没说话,我说,你要是怕烟熏火燎,可以去当个收银员,轻轻松松一个月三四千。她刚要说什么,手机响了,她掏出来,皱眉接了,是一个男人的腔:在哪儿呢?还回不回来了?她说,你让不让人把饭吃完!挂了电话。我说,他还在联系你呢。她放下筷子说,不吃了,我回去睡一会儿。我说,你该吃吃,别因为一个电话影响心情。她说,真不吃了。我说,你就在这儿睡吧,我出去一趟。她说,不了。出门进她的隔断,拉上了玻璃门。
6月
月初,我搬了过来。当时我刚被上一家房屋中介赶出来。那时候我打算租住在天坛周边,一来离我上班的印刷厂近,二来天坛附近有很多等待拆迁的老房子,虽然破旧,但价钱便宜。我相中一家,打电话过去,中介带我看房。那一带的房子是半个世纪前盖的老房子,外面都被刷成了鹅黄嫩绿色,清新怡人,一年四季都是春之将至的样子。我看完房,中介说,一个月两千一。我心中窃喜,心想这样的大主卧怎么的也得两千五六吧。最后我俩以一个月一千九成交,我欢天喜地搬了进去。二十多天后,我接到了那家中介公司的电话,说这家的房子月底到期,房主不再跟中介续签合同,我们中介也没办法,只能要求租户搬走。我听完后脑袋发懵,心想,刚搬进来二十多天,这是要搞什么,莫不是嫌当时租金太低想涨价吧。不搬,坚决不搬。中介说,你赶紧找地方吧,只收你一个月租金,其他的租金退给你。我说,中介费退不?中介说,想啥呢,收了中介费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再退了。我说,那我不搬。中介说,随便,到时候不搬押金也不退。我挂断电话,心想,你就是把天掀下来,老子也不搬。正想着呢,电话又打过来了,中介枪林弹雨般的脏话骂了过来。我将中介的手机号拉黑,很快另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又是一顿骂。我将这个手机号也拉黑,十几分钟后,外面响起了震耳欲聋般的擂门声。我从床下抽出臂力器放在一边,假装自己不在家,屏气凝神,门外响起了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我还没反应过来,中介窜进我的卧室,揪住了我的衣领。推搡一会儿,中介整理好衣服,扬长而去,我瘫倒在床上。三天后,我就搬到了这里。
这个地方叫垂杨柳。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天推搡过后,我联系了另一家中介,我对中介讲,房间一定要大,房子再老都无所谓,交通再不便都无所谓。中介说,到垂杨柳西街北口等我。我用导航找到了垂杨柳,中介把我领到现在的房子里,好说歹说,价钱定在了一千九百五一个月。交割完,我躺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想一块石头落了地,突然看到天花板上一根拇指粗的钢丝绳贯穿房间南北。我赶紧起来,头伸出窗外看,看到房间外面一侧一块巨大的钢板,深扎在地下,紧紧地固定着墙体。我给中介打电话,说这是危房,中介说,有牵引绳固定着呢,放心住吧,多少年了也没出过事。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中介说,你要这么说就别住了。我说,你把钱退了我就搬出去。中介说,交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这个道理你不懂?说着挂了电话。
对门是小次卧,住着一对情侣,男孩送外卖,每天骑着电动车在街上风驰电掣,左冲右突,女孩是商场导购,每天到了上班时段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往外走。我搬进来后,他们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关紧房门,仿佛怕我把女孩抢走似的,偶尔在客厅遇见,也只是点头致意。没过几天,隔断就搬过来一对母女,女孩约莫二十四五岁,脸蛋精致,穿着红T恤、蓝色牛仔短裤和白球鞋,母亲约莫五十出头,皱纹很深。随同母女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应该是女孩的男朋友或者丈夫,看上去比女孩大十几岁,像个老北京,挺着啤酒肚,满口京片子。我帮他们把东西搬进来,收拾好,女孩跟我打了个招呼,说,我妈以后就住这儿了,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还请你多担待。我说,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阿姨。男人在旁边显得有些不耐烦,说,收拾好了咱们回去吧。女孩说,我还要陪我妈买生活用品,忙完我自己回去。我看到男人的样子,回屋关上了房门。关上房门我就开始为女孩叫屈,心想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找了这样一个男人。我听到他们在客厅说话,男人好像在交待什么,交待完,男人拿着车钥匙下楼了。男人刚下楼,我就听到了敲门声。我说,请进,女孩进来了,说,我叫洋洋,以后多有打扰。我说,哪里哪里,互相担待。我俩加了微信。
12月
洋洋的母亲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我正要去上夜班。听到客厅里有叹气的声音,我知道是她,开门说,阿姨回来了。洋洋母亲说,你没去上班?我说,马上去。洋洋母亲说,天冷,穿厚点。这几天降温厉害。我说,好。阿姨吃饭没?冰箱里菜、肉都有。洋洋母亲说,吃不下,我先躺会儿。你忙你的吧。我回屋拿了一箱坚果给她,说这个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您尝尝。洋洋母亲说,一袋就行。谢谢你的好意,改天我给你带别的东西。我说,坚果是单位节假日发的,您随便吃。洋洋母亲还是只拿了一袋,关上了玻璃门。我回到房间,收拾东西,又听到了洋洋母亲轻轻的叹气声,叹气中夹杂着呻吟,唉呀——唉呀——唉呀,仿佛一个人被拆散了骨头,气若游丝。有一次我跟洋洋在一起的时候,洋洋说,她母亲这几年心脑血管一直不好,血脂黏稠,干一点活就头晕,得不停地坐下来休息,缓一会儿,才能起来再干。她其实不想给母亲找这份工作的,她非要来,说再干几年,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去。那时候医院恰好缺清洁工,她就来了。我说,出来看看也好,老在家闷着,闹心。她说,好什么呀,刚来北京没多长时间,就得了糖尿病,不轻不重,啥甜的不能吃,买来西瓜,馋得不行,只能吃一口,橘子,只能吃一瓣。有一次忘了,吃了一整只橘子,吃完病就加重了,遭罪。我给她买了每日坚果,里面有葡萄干、蓝莓干,她吃不了,又不舍得扔,每次都用卫生纸包好,等我回来的时候吃。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问,你爸呢。洋洋没说话,我看她眼角有点红,说,过去的事,不提也罢。洋洋说,过去很多年了,说出来也没什么。我爸原来一直在北京给人安装空调,跟我妈是搭档,两人配合很默契。有一天我爸妈从早上六七点安装到晚上七八点,累得不行,晚饭没吃,灰头土脸,想赶紧回去吃饭休息,一个女孩的电话打过来了,说都约四五回了怎么回事,到底来不来安装,再不来我就向厂家投诉了。我爸妈没办法,开着货车过去,到她家,三下五除二挂好风机,我爸跳到外面的铁壳子里安主机,腰里系着安全绳,安全绳的另一端要挂住一个地方,在她家房间里找了半天,找不到,我爸说,算了,三两下就安装完了。她家在十一楼,安装的时候又是晚上,她买的空调排水管太短,连不到主机上,我爸踮脚去够排水管,重心不稳,从十一楼跌了下去。
我工作的地方在印刷厂,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百来号人,老北京居多,外地人也不少,除我是河南人外,还有东北人、上海人、安徽人、河北人。印刷厂主要印报纸,也印些教辅图书、养生书籍什么的。什么报纸都印,《邮政报》《食品报》《证券报》《科技报》哪样报纸先完事就先印哪个。完事早晚,全看那些夜班编辑们什么时候把稿件编辑完,排版、校对、定版、传版,版样传过来,我们就开始了。机器轰鸣,说话根本听不清,只能打手势。时间一长,大家都养成了习惯,手语打得很好。遇到国际国内发生大事,就会很晚,往往凌晨三四点版样还传不过来。厂子里到处摆着行军床,等活的时候,大家睡成一片。睡不着的打扑克,侃大山,聊喜欢的妞和喝过的酒。我比较喜欢东北话,因为我在东北待过几年,东北话听起来比较亲切。上海话也喜欢,当然是上海版普通话,上海人说话总是喜欢说“我讲”“我讲”,不紧不慢,像邻居间聊家长里短。大家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荷尔蒙旺盛,又几乎全是单身汉,话题自然离不开女人。进厂三年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个刚进厂的女工,叫薇薇,眉清目秀,平时不咋爱说话,经常盘着大辫子,有时候来上班的时候穿旗袍,披肩发,到厂里再换成工装,把头发挽起来。没活的时候很少睡觉,喜欢读《红楼梦》,做女红,听工友说,她把《红楼梦》完完整整读了五遍。我对这样的女孩很感兴趣,有一次走到她身边,问她在看什么,她说,《红楼梦》。我说我也喜欢《红楼梦》,跟她聊起来,留了联系方式。回去之后我开始憧憬着跟她交往的种种细节,连以后结婚生孩子都想好了。我试着跟她联系,她表现得并不主动,我想这事只能顺水推舟,急不得。有一次侃大山的时候,我把我的心思对工友说了,让工友们帮我出出主意,没想到有好事的人第二天就告诉了她。她觉得自己的秘密被泄露,非常生气,立即断了跟我的联系。工友们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见面互相开玩笑的,现在都变成了调侃、嘲笑,有时候下班撸串也不带我。我感觉别人都在针对我,下班回到垂杨柳,心里面就堵得慌。躺在床上,横竖睡不着,就开始想洋洋。
那时候我刚搬到垂杨柳不久,不能确定洋洋有没有结婚,心想如果结婚了,一切到此为止,如果没结婚,我真心实意盼望她是单身,希望那天来的男人是她的亲戚,或者她的朋友。即使她不是单身,我也愿意做她的备胎,万一哪天分了,我可以随时补上,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一瞬间,我甚至盼望着她能分手。我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可耻,狠狠掐了掐自己。
8月
听到钥匙扔进碗里的声音,我知道是洋洋回来了,到客厅跟她打招呼,她提着香蕉说,这是给你的。我说,你吃吧,我那儿有。她说,快拿上,专门给你买的。我心跳得有点厉害,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她说,同一个屋檐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说,我打算今晚包饺子,如果你不嫌累,就跟我一起包吧。她说,你还会包饺子?我说,当然比不上你们女孩子。我让她在家等着,我出去麻溜买了肉馅儿、芹菜和饺子皮,回家来把芹菜洗净剁碎,拌好饺子馅儿,跟她包了起来。女孩子毕竟心灵手巧,我包一个的功夫,她能包仨。她说,你别求快,捏严实了。我说,一看就知道你在家没少包。她说,天天上班累死了,谁有功夫包这个。我说,你家那位想吃怎么办?她说,谁家那位?我说,就是那天搬进来的时候送你们的那位呀。她说,他呀,我早跟他分了。我说,什么时候分的。她说,我妈刚搬进来没多久就分了。我说,还以为你们是夫妻。她说,怎么可能。我说,那你平时下了夜班住哪里。她说,我在垂杨柳东南边租了一个小次卧,离劲松很近。我说,那一带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有空一起看电影,安慰一下你失恋的心。她说,好呀,最近有什么好电影,记得推荐。
饺子煮好,我给她盛了一碗,自己也盛一碗,我俩吃着饺子,她说,有没有人说你长了一张娃娃脸。我说,有呀,我妈是娃娃脸,我也是娃娃脸。她端详了一会儿我的脸,眼神迷离起来,我心里感应到了什么,她放下筷子说,吃饱了,我回去睡一会儿。我说,你就在这儿睡吧,我待会就去上夜班。她说,不,我得回去。我说,你就在这儿睡。你那隔断小成那样,多憋屈,以后我给你把钥匙,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在我这儿休息。她不依,要回去,我拦住不让她回。她没办法,只得在床上躺下。过了一会儿,她说,你不去上班吗?我说,刚吃完饭,待会再去,说着在她旁边躺了下来。她没起身,我顺势握住了她的手,握了一会儿,说,做我女朋友吧。她望着天花板,没说话,我翻个身,搂住她,我俩吻了起来。她的唇很糯,很滑,我被撩拨得性起,一只手不自觉地扒她的衣服。她清醒过来,按住我的手说,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我喘着气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整理好衣服,给她一把房间的钥匙,俯身在她脸蛋上轻轻吻了一下,出门上班去了。
10月
跟薇薇一起工作时间长了,我发现薇薇对我没那么讨厌。她只是不习惯自己的秘密被别人发现,因此对我那番想追她的言论感到愤怒。其实我那天只是想让大家为我出谋划策,完全没料到会有人在背后插我一刀。事情慢慢过去了,虽然工友们对我的态度依然冷淡,但薇薇见我不再躲着我了,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平静自然起来。我试着联系了一下她,她没回复,我想,修复关系需要时间,再等等吧。
“双节”期间葡萄降价,我到街上买了几串,回来的路上,想起了什么,又折回去买了炸鸡和啤酒。到家后,我把葡萄洗净,放在桌上,等洋洋回家。洋洋到家,我说,快来吃葡萄,你的最爱。洋洋一听,进了隔断,换上一身漂亮的裙子,踩着高跟鞋走进来。我拿起一颗葡萄喂给她,说,今晚咱们吃炸鸡和啤酒吧,这是特意为失恋的你准备的。洋洋说,你不用特意安慰我。我说,你俩到底因为啥分的手。洋洋说,一言难尽。我说,愿闻其详。洋洋说,我俩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时候我刚来北京没多长时间,在一家台球厅给人家摆球。来打球的大部分是有钱人,一小时一百多,酒水另算。有一天我刚摆完一桌球,退到一边,有个人操着满口京话跟我搭讪。我当时才二十出头,那人说,小姑娘,家哪儿的?来北京多长时间了?我说,河北的,不到一年。那人说,有对象没?我说,没有。那人扭头对另一个人说,真是个美人胚子。两人抽着烟端详着我,说,改天给你介绍一个老北京。我说,不敢不敢,往一边躲,两人哈哈大笑。没想到那俩人是当真的,转天就把人领来了,就是我妈搬进来那天你见到的。我当时一看,心凉半截,心想这人都能当我爸了,想拒绝,旁边那人说,这可是纯正的老北京,祖祖辈辈生活在皇城根下,家里面好几套豪宅。我没说啥,回去后心里面很矛盾,没想到这人对我动了感情,疯狂追我,我就同意跟他交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说,先让我怀孕,怀孕半年后再结婚。我当然不同意,到时候顶着大肚子,怎么穿婚纱?结婚可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我打断洋洋,说,在北京都是这样的规矩吧,外地女孩嫁给一个老北京,一般都是怀孕五个月再结婚。老北京一套房子上千万,一套四合院上亿,万一女孩结了婚后反悔,闹着要分房子怎么办?洋洋说,孩子能拴住两个人的婚姻吗?我说,没办法,除非你也是千万上亿的主儿。洋洋说,这就是我俩矛盾的地方。我说我年龄还小,先结完婚再说。他说他已经很大了,想先生个孩子慢慢养着。我俩交往了两三年,谁也不让步,我就把他踹了。我听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说,你醉了,不能再喝了。她说,我没醉。我扶住她,她软软地倒在我的怀里。我说,醉成这样,待会儿还怎么上夜班。她说,睡一觉就好,扶我回去。我说,你就在这儿睡吧,说着把她抱了起来。她惊叫一声,勾住我的脖子。我把她放床上,躺在她身边。她翻了个身,搂住我,我顺水推舟,做成了好事。晚上七点钟,她醒了,我赶紧闭上眼睛,假装在睡觉,她从床上慢慢起来,穿好衣服,吃了几颗葡萄,蹑手蹑脚走出房间,带上了门。几分钟后,我听到她从隔断里面出来,拿走碗里的钥匙,出门上班去了。我伸了个懒腰,洗把脸,下楼骑上自行车,也上班去了。
洋洋的母亲回老家了。那天我上完夜班,回到家,轻声经过客厅,没有听见隔断传来的呼噜声。第二天洋洋休班,我问她,她说,我妈糖尿病加重了,向医院请了一个月的假,回老家调养去了。我说,早该这样了,遭那罪干啥。洋洋说,我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家没几天就闷得慌,你信不信她过段时间就会回来。我说,你劝劝她呀,她干清洁工能挣多少钱,不够仨核桃俩枣的。洋洋说,我劝不住,下次来你劝劝她。我说,我还想着在阿姨面前好好表现呢,我未来的丈母娘呢。洋洋说,你想啥呢,谁同意跟你交往了。我说,那天之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洋洋说,笑话,我跟我前男友那么多次,我也不是他的人。我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人的人。我说你这话很有点女权主义的味道。洋洋说,女权不女权有啥用,穷死了才是真的。我说,那天我给你说的收银员,你想不想干?洋洋说,比我值大夜挣得少多了。我说,你可以试着做微商,现在有挺多女孩子做微商的。洋洋说,就那些衣服、鞋子,谁会去买。我说,你要是当个网红,再开网店,以后来钱哗哗的。洋洋说,开网店的那么多,成网红的有几个?我说,那你就去当演员吧,先从群众演员做起,慢慢就会有导演相中你。百子湾知道吧?出了咱们垂杨柳,往东走是双井,双井坐上地铁,过几站就是百子湾。百子湾租金便宜,离双井也不远,双井北边就是国贸,北京的经济、文化和娱乐中心,大部分的北京网红、模特和十八线艺人都在百子湾那儿住着。听说很多导演和星探天天在百子湾的高档公寓附近溜达,很多女孩也天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百子湾的路上走来走去,哪个瞬间两人看对眼了,女孩的明星梦就起航了。洋洋笑了一下,说,哪有这等美事,听说百子湾的很多星探都是红娘,是专门给那些富人服务的。我说,你比我懂得多。洋洋说,我认识一姐妹,以前就是做这个的,在百子湾的豪华公寓里住着,名牌包包、各种衣服买到手软,男人每周来住一晚,剩下的时间,那个姐妹就坐着飞机满世界乱飞。我说,咱正经人不做那个,以你的相貌,当个演员绰绰有余,你有空可以去电影制片厂门口守着。洋洋说,不去,受那苦干啥。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大明星都是蹲那儿被导演相中成名的。洋洋说,要去你去。我说,我又没想过一夜成名,再说,我对当演员也没兴趣。
洋洋做起了微商,卖衣服。她推掉了一些班次,空闲的时间除了在家补觉,就是在朋友圈发各种照片。我说,你们不是不让随便请假吗?洋洋说,我跟领导讲,我长期大夜班,内分泌失调,神经功能紊乱,领导还能不让我休息?我说,好吧。洋洋说,你帮我转发一下啊,转到你的朋友圈和群里。我转了几次,结果被几个群移出群聊,截屏给她看,她才作罢。衣服卖不出去,洋洋消沉了一段时间,又通过一个姐妹认识了一个做美容护肤品直销的区域经理,跟着区域经理听了几次课,又拉着我听了两次课,正式决定加入直销行列,准备大干一场。他们的直销产品叫“碧缇福”,英文谐音Beautiful,寓意用了他们的产品会变得更漂亮。加入碧缇福团队后,洋洋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比宗教徒还要狂热和虔诚,说不上三句话一定要提到碧缇福,朋友圈每天铺天盖地般狂轰滥炸。我不知道她的业绩怎么样,反正她在家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不上班的时候上午一般十点多起床,洗漱后,就开始坐在镜子前精心化妆,衣服也是精挑细选,反复比较。有时候我在她化妆的时候从后面抱住她,她用胳膊肘把我推开,说,别闹,化不好重化,耽误时间,那边要着急的。我松开她,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就感觉很幸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独坐,心里也没那么空,变得安定一些了。
次年6月
房子到期了,中介说,想住可以,一个月租金涨五百,一年涨六千。我巴不得早点告别危房,决意要搬。问洋洋,她说,那个隔断她也不住了。洋洋的母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中介说,你到别的地方也是这个价。我说,那也比住危房强。转念一想,自己竟然在这危房里面住了整整一年。不想便罢,想想着实让人害怕。有时候我跟洋洋缠绵完,我俩并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根牵引绳,我说,这房子要是这样下去,不拆,总有一天会倒的,你怕不怕?洋洋钻进我怀里,说,有你在,不怕。我说,我原来也害怕,有时候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认识你之后,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了,也就没那么害怕了。趁房子倒塌之前,咱们多疯狂几次。翻身又把她压在身下。
新居还在垂杨柳,不过这次从垂杨柳的西北搬到了西南。住的这家虽然不是危房,但离工地更近,每天机器轰鸣,很多住户受不了,纷纷搬离,因此租金也压得很低。洋洋偶尔会过来住,说跟她合租的那姐妹比较闹腾,经常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了还嘻嘻哈哈到卫生间冲澡。我很乐意她来,因为我一个人在长夜里,辗转反侧,实在难捱。有时候睡不着就坐床上抽烟,但越抽烟越精神,越精神越睡不着,第二天就会越困。我问洋洋,阿姨还来不来北京,来北京了住哪儿。洋洋说,她前几天还来了一趟北京,到北京的医院做检查,我陪她去的。那几天我在你这儿住。我没说话。
次年12月
洋洋给我打电话,说她这一周都不用上班。我说你来吧,咱们一起包饺子。她就来了。吃完饺子,我俩躺床上休息,洋洋说,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能接受一个男人出轨吗?我没料到她会问这个,说,不能吧。洋洋说,如果夫妻一方出轨了,又不想离婚,另一方会怎么办?我说,没经历过,不知道。另一方也会出轨吧。这样心理上有了补偿和安慰,日子才能过下去。但应该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了。洋洋没说话,眼睛盯着天花板,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洋洋说,没什么,就是好奇。说着翻了个身,把脊背留给我,我抚摸着她的背,不知不觉睡着了。
劲松电影院一到晚上就霓虹闪烁,流光溢彩,很有旧上海的味道。进了电影院,地上一色暗红的水磨石,又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段时间电影院在上映《南方车站的聚会》,我对洋洋说,你不是喜欢胡歌吗?你偶像主演的电影,还有桂纶镁和廖凡。洋洋说,讲什么的。我说,算是残酷叙事吧,关于自我救赎的,最后的结局让人唏嘘感叹。洋洋说,听不懂,你就说好看不好看吧。我说,工友们都说好看,我还没看。明天咱们都休班,过去看看吧。洋洋说,行,中午十一点半见面吧。垂杨柳去劲松那条道上,有一家手擀面,咱们在那儿见吧。手擀面店的后面是公交场站,你知道那地方吧?我说,知道,去那儿吃过几次。我干脆去你楼下等你吧,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连你在垂杨柳哪个小区哪栋楼住都不知道。洋洋说,不行,今天我姐妹在家,看到了不好。我说,她能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去,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去一趟?洋洋说,她是她,我是我,听话,就在手擀面店碰头,这几天我想念那里的味道了。
这家店的手擀面确实正宗,量大,管饱,还香,最重要的是面条筋道。来吃的大部分是农民工,工地上干活,到饭点,工装也不脱,点一大碗手擀面,就一瓶啤酒,吃得满头大汗。我跟洋洋各点了一碗扁豆肉丝面,吃完,去看电影。电影开场,灯光暗下来,洋洋依偎在我身上,我轻轻搂着她,跟她十指相扣。看到枪战的场面,尤其是“血伞”的情节,洋洋吓得不敢看,往我怀里钻。电影结束,我俩往外走,我说,感觉怎么样。洋洋说,场面太血腥,不过胡歌确实挺帅的。我说,那是,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洋洋没说话,我说,你那碧缇福最近怎么样了,怎么那么长时间不见你更新。洋洋说,好几个月没去提货了,挣的没有投的多。几个姐妹也都赔得血本无归。我说,无所谓,现在就算是试水,积累经验,以后肯定能东山再起。任何经历都是最宝贵的财富。洋洋笑了。
我领着洋洋到了我那儿。缠绵过后,我说,天无绝人之路,你真的可以去试试当个演员。洋洋没说话,搂着我,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我也开始抚摸她的身体,手指滑过她的肚子时,突然摸到了她的妊娠纹。之前我从来没摸过她的肚子,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手指从她的肚子上滑过。我赶紧将手移开,抚摸她的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洋洋身子轻轻抖了一下,头勾在我怀里。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洋洋的秘密,但我一直没说出来。刚认识洋洋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洋洋和她母亲躺在隔断里,关着门,我去洗手间,经过客厅的时候,听见洋洋的母亲说,他还是死抓着房子不放?洋洋说,是。律师前两天说,我要是现在闹离婚,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洋洋母亲说,那就再等等吧。找到啥证据没有?洋洋说,没有,他挺老实,晚上基本不出门。本来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开门声音极轻,因为怕打扰母女俩休息,但我听到她们的对话后,不小心在洗手间弄出了声响。我听到洋洋的母亲马上呻吟起来,唉呀——唉呀——唉呀——,听着让人揪心。我用完洗手间,蹑手蹑脚出来,轻轻关上了门,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此刻也是,我看了眼怀里的洋洋,继续若无其事地爱抚着她。洋洋说,晚上我想去吃那家鱼厂的铁锅炖大鱼。在垂杨柳住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不舍得吃。我说,好呀,正好我也想去尝尝。洋洋说,我把你的餐桌和锅碗瓢盆收拾一下吧。我说,不用收拾,天天都用,脏不到哪里去。洋洋说,正因为天天都用,才得好好收拾一下。她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把锅里的剩饭倒掉,用洗洁精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餐桌上的油污也用铁刷子蹭掉,用清水冲洗了好几遍。餐桌又变得熠熠生辉,像新买的一样。
这家鱼厂算是整个垂杨柳最高档的餐厅了,环境整洁、优雅,私密性很好。特色菜是铁锅炖大鱼,东北风味,大活鱼当着顾客的面捞出来,称重,宰杀,放入客人面前的铁锅中,咕嘟嘟地炖。洋洋选中了一条四斤多重的大青鱼,我一看价格,暗暗肝儿疼,心想洋洋今天是怎么了,我俩在一起吃饭,从来都是手擀面、香河肉饼这样的,火锅也是在家吃,一顿只花几十块钱。服务员说,先生,一共消费三百九十八。洋洋只顾看手机,我乖乖去前台付了账。鱼炖好了,我夹起一块鲜美的鱼肉放进洋洋的餐盘里,自己也夹了一块,一入口,才感觉这钱花得真值,实在太美味了。但转念一想,一顿饭就花了四百,心里面又难受起来。洋洋的手机响了,是微信语音电话,洋洋接了,那边是男人的声音:你终于回我微信了。你现在在哪儿?在不在垂杨柳你住的地方?有几次我去找你,你姐妹都说你不在。洋洋挂了电话,继续吃鱼,我说,他又联系你了?洋洋说,不用理他。我不再说什么,埋头吃鱼。吃完,洋洋已经收拾好了手提包,我起身,挽着她的手往外走。走到没有路灯的地方,洋洋突然挣开我的手,说,今晚不去你那儿了。我抓住她的手说,怎么了,是心情不好吗?洋洋说,松手。我说,你一个人回去生闷气,心里更难受。拉着她要走。洋洋说,松手,我数一二三,再不松手我就报警了。猛然挣脱一下,挣开了。我看她挎着包,向路灯下面走去,一点点消失在夜色里。我愣了一会儿,拐到路边的摊上,买了一些香蕉和橘子,提着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