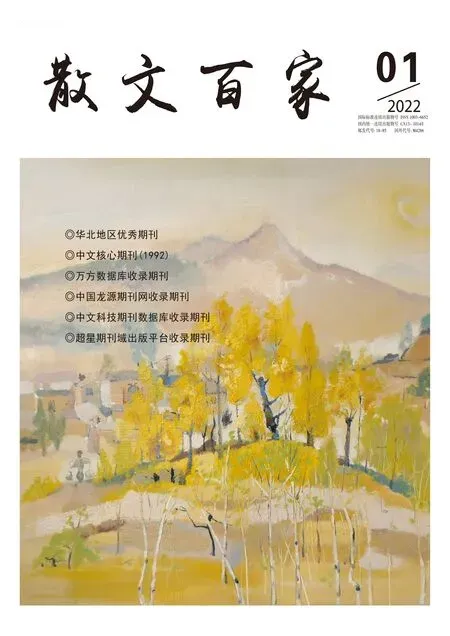当代“娜拉”的生存之困
——付秀莹《他乡》翟小梨形象探析
符文静
江西师范大学
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在戏剧《玩偶之家》中塑造了走出家庭的叛逆者“娜拉”,提出了女性独立解放的问题。易卜生之后,鲁迅《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发出“我是我自己”的呐喊,此后有关“娜拉出走”困境的思考就从未停止。张爱玲、铁凝、张洁等作家都用自己的文字思考这一问题,并着力探究娜拉走后究竟如何,“娜拉”形象也因此贯穿了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付秀莹的长篇小说《他乡》讲述了农村女孩翟小梨的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双重成长历程,聚焦城乡变迁中女性生存问题。小说的主人公翟小梨,从农村考到当地一所不错的学校,走出芳村成为了大学生,后来又在结婚生子的重压下毅然坚持考研,走向城市,她凭借着自己的天资和勤奋,不断成长前行,遭际种种心灵悸动、情绪动荡、感情迁移,被蔑视和被压抑的心生长出强大的自救力量,实现了故乡和家庭两个层面的出走与归来,是娜拉形象在当代的重构。综合来说,娜拉出走主题经历了“恋爱至上主义”、“革命至上主义”和“生存至上主义”三个阶段,翟小梨的形象承继了“生存至上”的主题,并在新时代变迁中从职场、家庭、感情三个维度展现出当代娜拉的生存之困。
一、经济独立的艰难之路——女性职场困境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指出娜拉出走后的两条道路,即“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避免成为傀儡的第一要务便是获得经济权力。《他乡》根据翟小梨去北京前后的不同阶段分成上下两篇,涉及两个出走文本。相比于早期娜拉,当代娜拉显然已经通过教育和自身努力获得了基本的经济独立,避免了娜拉出走后饿死的命运,但是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当代女性职场困境问题依然是严峻的,在《他乡》中主要表现为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和男性权力体制的影响两大困境。
1.事业与家庭的永恒矛盾。
《他乡》的上篇写主人公翟小梨离开贫穷的故乡——芳村,与初恋男友结婚,拿到了S市的户口,进入婚姻的围城,构成了当代娜拉的第一次出走。在这个阶段,翟小梨从一个大专毕业的普通农村女孩成长为S市一所重点中学的编外老师,一头撞进了梦想中的城里人生活,生活也有了基本的经济保障。当代职场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是学历较高、年轻单身、长相平凡的女强人,翟小梨显然不在此之列。尽管翟小梨在校十分优秀,但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得益于与初恋章幼通的这段婚姻。大专毕业的她依靠章幼通父亲的关系,才能够在S市一所不错的中学教书,也正是因为和幼通的婚姻,她能够在省会城市落户,实现人生的第一次飞跃。这时的翟小梨是欣喜的,家庭和事业都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婚姻组成了家庭,家庭铺垫了她的事业,却也限制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婚后生活中,翟小梨逐渐经历了公公家的凉薄冷漠,丈夫的事业不振,她被迫与丈夫贷款买房、养育幼子,不仅是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支柱,还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一边是需要照顾的幼子和失业后自尊心亟须安慰的丈夫,一边是需要投入十分热情的教育工作和整个家庭柴米油盐,这写琐碎而又繁杂的小事使她深陷婚姻的围城,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如何更好地立足于这个城市。为了脱离生活的囹圄,翟小梨决定准备研究生考试。
2.男性权力体制的影响。
翟小梨的第二次出走是发生在成功考取研究生之后,从S市出走到北京。为了追求现实与精神上的自由,翟小梨摆脱妻母身份的围困,勇敢去追求自己更高的人生价值,一步步实现了当作家的梦想。这一次出走,翟小梨看似是学业事业双丰收,但是在她独自一人在职场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依然时刻受到来自职场男性权力体制的影响,无法回避男性眼光,这是娜拉在职场生存中无可避免的抗争与妥协。研究生毕业后,翟小梨这一次通过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获得了心仪已久的工作——在北京的一家知名报社的副刊担任编辑。诚然翟小梨天资聪颖、专业扎实、工作努力,却依然遇到了当代女性职场中的一大难题——来自上司的骚扰。拒绝分管领导万副总的过分要求后,万副总便以个性太强为由阻止翟小梨进副刊,获得从实习生转为正式员工的资格。来自男权的压制静静地潜伏在职场的方格间里,翟小梨为代表的娜拉们拒绝成为男权的牺牲品,被迫为女性权力抗争,形成自己的生存策略。然而,比被动遭受男性权力体制迫害更让人担忧的是,女性主动寻求上位者男性庇护的潜在意识,男性权力于无形中侵染了女性思想观念,形成依附男性的惯性思维。翟小梨无力独自解决性骚扰事件,于是,只能把事情托付给自己在北京的情人老管,又在老管的指点下主动联系报刊的社长,完成以权力制压权力的循环,解决自己在职场上遇到的性骚扰。这种借助男性力量爬出男权泥沼的方法充满危险,稍有差错就会再次落入深渊,然而付秀莹还是以这样的情节给予给翟小梨,使作者笔下的这位独立勇敢的女性成为颇具争议的“娜拉”。也许作者也想强调,在强烈的男性文化优越感之下,娜拉们的职场突围依旧困难重重。
二、封建伦理下的沉默之语——家庭失语困境
翟小梨是“芳村的女儿”,性格中拥有农民的美好品质,却也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沾染了民间的世俗性。传统伦理道德于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难以消弭,潜在影响着翟小梨的日常行为。当代娜拉在步入新生活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消除旧思想,需要在出走中克服自身的局限性,逐步实现精神解放。
1.父权至上的压迫。
莫言说:“作家写乡土,是一种命定的东西。”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付秀莹在其多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芳村”文学世界,这一部《他乡》通过翟小梨的故事于“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的路径上做了一次切身的实验。但是任何的转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翟小梨带着传统观念进入城市,必定与现代社会产生激烈的碰撞与冲突。作者很巧妙地设计了两个出走文本,保留了翟小梨原生家庭的温情幸福,选择用她嫁入章家之后的经历将其隐藏在心的父权问题逼出水面。翟小梨的芳村生活单纯朴素,她知道伦理秩序中每一个微妙的转折和敏感的拐点,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血缘、家庭的复杂关系。章家虽然是城市家庭,但是掌权者章大谋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权主义者,生活在此压迫之下章幼宜和其姐姐章佩竹各自麻木,虚度毫无意义的人生。正如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造成的”,佩竹、幼宜之所以会成为依附男性的弱势群体,父权社会的压力难逃其咎。翟小梨也一样,她闯进冷漠无情的城市生活,始终压在心底的等级伦常应时抬头,在公公章大谋身上感受到实在的父权压力。面对公公婆婆的虚荣浅薄、拿腔作势,要强敏感的翟小梨只是沉默。翟小梨对公公一味逢迎讨好,是娜拉家庭生活失语的表现。翟小梨用这段婚姻换得了阶级跃升,从乡村出走到了城市,在婆家人面前是心虚的;她身体里流淌着农民的血,在省城人面前是自卑的。这些不对等在当前的父权代表人章大谋和章家面前无处遁形,翟小梨缺少反抗父权的经验和勇气。
2.夫贵妻荣的约束。
在和幼通的感情上,翟小梨坦言骨子里有一种“夫贵妻荣”的观念,所以翟小梨坚定追随幼通生活,幼通的城市人身份是翟小梨的荣耀所在。婚后的幼通满腹牢骚、不求上进,失业之后也眼高手低,不肯另找工作,作为翟小梨的依靠,她依旧全心期盼幼通能够有所作为。“家族制度与礼教是女性的天敌”,其实权力压制伤害的不仅是女人,作为章家唯一男丁的章幼通也是畸形家庭的受害者。章幼通的无为态度打破了翟小梨夫贵妻荣的幻觉,在家庭隐形的压力面前,翟小梨没有战友和同盟,渴望丈夫成为救世主的希望破碎。苦口婆心的劝说无果,反唇相讥的激怒无效,走投无路的翟小梨最后竟然选择在丈夫面前下跪。受过高等教育的温婉雅致的翟小梨,为了让一事无成丈夫参加人才招聘,毫无颜面地一次次下跪恳求。家庭生活艰难,翟小梨终是失败了,她以蚍蜉撼树的力量表达抗议,被生活封住所有嘶吼,无声地流泪下跪,接受无法改变现实。翟小梨在家庭生活中承受父权和夫权的双重压力,昭示着新世纪城乡关系的复杂,也体现出新女性在出走之路上思想过渡的的重要性。正如处于失语状态的翟小梨认识到对外抗争无用,最后只能将沉默化为内在动力,开始第二次出走。
三、顺从与叛逃的矛盾之心——婚姻情感困境
1.伦理道德的苛求。
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娜拉面对的境遇也发生巨大的改变。相比物质满足的需要,当代娜拉更重要的是精神成长。翟小梨在娜拉出走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她的出走并不彻底,仍然摆脱不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苛求,困于男性世界的限制中。
小说中多次强调翟小梨丰盈健康的体态,这一方面吸引着男性欲望的眼光,一方面又被严苛的审美标准大加评判。翟小梨也服从于这样的眼光,懊恼自己过于红润健康的脸庞和过于饱满的胸脯,完全没有小女人的娇态,于是老管把翟小梨打造成一个男权社会中的出色女性,翟小梨由此获得更多的自信和从容。学业与事业之外,与男人的感情纠葛贯穿了翟小梨的一生。她与章幼通的婚姻实现了基础的爱恋,和老管相识后成了敏感多情的女人,和郑大官人短暂相处体验到了精神恋爱的幻灭。翟小梨通过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抓住不同的男性解放者实现精神满足感和人生的完整意义,类似于几十年前的《青春之歌》。林道静根据时代的既定路线投入革命领袖江华的怀抱,翟小梨历经风波,最终选择回到幼通身边,重新拉开了娜拉出走时的那扇门。
《他乡》后半部分,翟小梨成为著名的作家,不过她成为作家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讨好情人老管,认清现实后的翟小梨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再一次爱上无能的丈夫。从道德层面上来说,翟小梨与其他男人的感情纠葛显然存在污点,但是她的回归让这部小说在传统道德意义上又趋于圆满,这一走向无疑是现实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规范性定位。付秀莹以个人的女性经验讲述了城乡中的女性成长困境,通过当代娜拉的命运开辟出一个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审美世界。
2.本我的反叛欲望。
荣格原型心理学理论提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双性同体”原型,认为男性性格中存在女性气质,而女性性格中潜藏着男性意识,即“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对立。作为家中最小的姊妹,要强上进的翟小梨自小勇敢坚强,这是她性格中的阿尼姆斯特质,而她爱上的章幼通和老管却又是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这不仅仅是巧合,更是翟小梨潜意识中本我作祟的表现。谦和顺从的外表背后,隐藏的是连她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反叛之心。事业、情感和家庭生活的不顺利逼迫翟小梨走出家门,像男人一样站在社会中央,为自己争取一片天地。北京的繁华和上层社会的吸引力促使翟小梨沉睡的本我意识觉醒,和老管的疯狂爱恋是翟小梨年轻时代冒险精神的集中迸发。小说中多次暗示她的这一精神特质,大学时大胆坐上混子的自行车,工作被骚扰时企冀获得对方承诺的好处,一直到异乡睡在了另一个男人的怀里。弗洛伊德的理论里,意识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崇尚快乐至上的本我被自我和超我调整和约束。翟小梨的前半生被巨大的道德压力制约着本我,而在沉沦的那个晚上,翟小梨质问自己为家庭牺牲的意义,然后抛弃了自我和超我的压制,成就了她自己。这时候她发现,这世上有两个翟小梨,“一个含辛茹苦温良贤惠。一个妩媚妖娆内心艳丽。”分裂的二者体现着翟小梨作为现代知识女性觉醒后的挣扎和痛苦,激发了内心的反叛欲望,任由身体中蛰伏的另一个放荡的翟小梨向整个男权文明社会发起攻击。
四、结语
翟小梨的身上映射着五四时期勇敢走出家门的“娜拉”们的影子,同时“娜拉走后怎样”又呼应着新时代中女性成长的困境与抉择。但是正如梁晓声提出的,如果付秀莹故事中的女性褪去美貌依然可以完成人生考验,那么娜拉出走的意义必将扩大化。相信随着时代进步与人的努力,“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的难题终将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