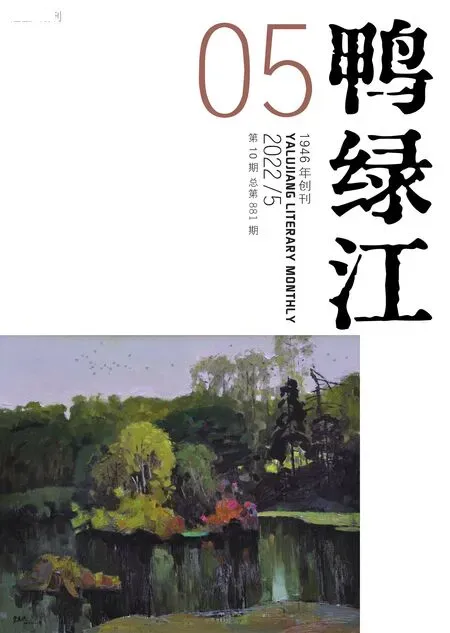恋恋乡土
黄福生
家对我的意义,不只是家人,更是土地,所以我才会在我的迁徙中感受到痛苦的流浪感。也许这是一种和谐化辩证。我的暂时忘记和搁置,曾经对我有帮助,但我却不能只有忘记和暂时的搁置。
无论生活,还是书写,浩浩荡荡的历史,都是我无法逃避的故乡。我终究要回到那黄河沿岸,回到鲁西南小村庄,回到父辈的历史,回到土地。这所有的历史,就是我要回去的“土地”,我终究要入“土”为安。这是我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我长大的地方是山东菏泽,这里是黄河屡次决口冲积形成的扇形平原的中心地带。每当黄河决堤,滚滚黄河水漫延开来,农田被淹没,房屋被摧毁,当地人们受灾严重。黄河屡次决堤改道,这里便一遍遍被淹。发黄水后,人们举家外逃的景象,是先祖们留给我们的集体记忆。虽然饱受其害,但黄河始终是母亲河。
人们常说“闯关东”,意思是成年人为了生计,需要离开家乡,到东北去挣钱。在战乱和贫穷的年代,对村里人来说,东北是一个富饶之地,一个充满着馒头的地方,一个寄托着让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的地方。有些人举家迁往东北,也有人年轻时去东北,然后在东北安家。更多的人像候鸟一样,去东北讨生计,然后寄钱回家,过年时回来过年。
到城市里去讨生活,成为成年男女的主要选择。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像候鸟一样,春节后离家,春节前回家。有些人家是爸爸和妈妈双双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也有些人家是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们家是爸爸一个人外出打工,妈妈留在家里照顾我们三个小孩。爸爸像候鸟一样,从城市向家乡搬运着财富,也从家乡向城市搬运着我们的命运。
“如果不好好学习,你们以后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村里所有的家长都会对孩子讲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似乎,离开土地是最好的命运。土地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只能给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离开土地,是村里年轻人注定的命运。
父亲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搬运着我的生命。终于轮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城市,先是去读书,然后争取在城市里留下来。但填写大学报考志愿时,我感觉到的是家乡对我的召唤,我决心读一个对家乡有用的专业。我一心要读农业大学,专业选的是机械自动化一类的。但老天爷没有遂我的愿,我被录取到一所师范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专业。
1999年9月,我离开家乡,来到烟台,直到2000年1月才回来,那是我远离家乡后第一次回家。我卷了全部的行囊回来,坐20个小时的火车,再坐4个小时的汽车。回到村口时,雪还在下,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甚是好看。我终于回来了,熟悉又陌生。想象即将看到的家人,我已开始泪崩。还要再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家,我努力让自己注意周围的东西,调整情绪,让这十几分钟的步行不要显得太漫长。很快,我家的房子已在眼前,似乎很平静,远没有刚进村口时的激动,我心想,也许激动一下就过了。到大门口,我就开始叫妈妈,这是我以往每次回家时必做的仪式。叫声妈妈,我的声音是颤抖的,我整个人也开始颤抖,不知怎的竟伴随着哭声。我连哭带喊,妈妈在屋里回应我,爸爸和弟弟从堂屋里出来迎接我。三叔和三婶也在,他们知道我今天回来,所以特意过来玩。“哭什么呢,回来就好。”大家都这么劝着,妈妈也这么劝着。我把行李放好后,跟妈妈简单对话了几句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这里是我永远的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和思想拉锯之后,我决定回去继续未竟的学业。家乡虽好,但时过境迁,我已不适合久留在家乡,留在妈妈身边。就像一只小狼长大了,必须离开妈妈,不然它将来无法生存。我也必须离开家乡,成为一个游子,到遥远而冰冷的城市里继续打拼。
大年三十下午,村里的男人都会到自己家的祖坟扫墓。扫墓的程序很简单,就是去烧纸、添土、磕头和放鞭炮。扫墓的活动只有男人参加,我是从高一那年开始参加扫墓活动的,那相当于我的成人礼,之后便年年都去。
扫墓是家族的集体活动,所以男人们会约齐之后集体前往。爷爷辈不需前往,家族中的晚辈有我爸、二叔、三叔、启柱叔、波叔、良叔、我、我弟、堂弟。我家在最南边,一般是下午3点多,我们家的三个男人准备好之后便出发,从南往北,一路叫上良叔、二叔、三叔、堂弟和良叔,最后在启柱叔家门口等候大家。集结完毕,我们便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向田野走去。在村子里大概走500米,出村口后走100米,便到了我们家族的墓地。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小麦还趴在地面上,完全不成气候。墓地就在麦田中,没有墓碑,只有弧形排开的几个坟头,像扣在地上的馒头。哪个坟头是哪个祖先的,没有任何标记,但叔叔们记得,应该也是爷爷们告诉他们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些烧纸,我们会把烧纸汇合在一起,然后再分到各个祖先的坟前。在点燃烧纸前,我们会先把那些烧纸折叠一下,弄出一些棱角,可以帮助烧纸燃烧。我们通常是从最长辈的祖先开始点燃烧纸,然后用一小捋烧纸做火种,依次点燃其他坟前的烧纸。为了帮助燃烧,需要用一根小木棍时不时挑一下那烧纸。大家会各自散开,自觉负责各自的事情。有几个人用小木棍挑烧纸,让火更旺,以让烧纸燃烧完全;有人拿铁锹给各个坟头添些新土;也有人开始在旁边放鞭炮。鞭炮有冲到天上才响的闪光雷,也有很大颗的“地雷”,也有编成串的小鞭炮。在烧纸和添土时,叔叔们常念念有词,叫祖先们收钱,祝他们在那边过得高兴,提醒他们过年了,人们放鞭炮,他们不要乱跑,就乖乖地待在那边,也请求他们保佑后辈们有好的人生。最后是磕头环节,我们会排成两排,爸爸和叔叔们在第一排,我、弟弟和堂弟在第二排。通常是年龄最大的在最中间,其他人依次向两边排开。磕头一般磕三次,双手抱拳举过头顶,然后放下,左膝盖着地,再右膝盖着地,弯腰,低头,双手着地,匍匐在地面上大概三秒钟,然后直起身来,右膝离地,左膝离地,再把双手抱拳举过头顶,放下,算是完成了一个磕头。重复两次,就完成扫墓仪式。
我一直都觉得扫墓仪式是重要的,觉得那是对我身份的认同和强化,也是和祖先们的近距离接触,觉得庄严,也有美感。好像觉得,每年做一次这种仪式,以后即使出门在外,也会受到祖先们的保护。
去年夏天,四爷爷去世,我回家乡奔丧,这才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家乡。因为女儿出生需要照顾,家乡在我心中的位置继续下降。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有义务降低家乡在我心中的权重,好好地活在当下,以下一代为重。
出殡那天中午我才赶到家,一样是弟弟开车接我,我们直接奔赴葬礼。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葬礼。中午时分,天气炎热,气氛也热烈。我和弟弟先到四爷爷的棺材前跪拜,亲人们都在,巨大的温热感袭来,不需要调动情绪,我已哭得不能自已。嘴上念叨的是四爷爷,心里头激动的是家族带给我的归属感和感动。亲戚们都在,他们似乎永远在,何时见到他们,我都还是那个生妮,都是那个小孩。之后,我便领了白衣服和贴有烧纸的小木棍,到棺材旁守着。家族里的男人都在,我一一跟他们打招呼,复归平静。当有人进来祭拜时,我们附和着发出哭声;当祭拜结束,我们便招呼他们到树荫下找地方坐下休息。
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有大雨。大家都惴惴不安。午饭后便马上举行送葬仪式。主持人一声“发丧啦”,大家便开始大声哭喊,念叨“我的四爷爷”或“我的四叔”,同时哀乐奏起,大家有序地往外走。男人走在队伍的前面,和四爷爷关系最远的晚辈走在最前面,之后是他的侄子,最后是他的儿子,然后是棺材。棺材由八个壮实的村民负责抬着。后面跟着是女宾,女宾们坐车子,三个人一辆,她们负责很大声地哭。四爷爷家在村子的正中间,从他家往东到村口大约有500米,从村口到他的墓地还有500米。走在村子里时,队伍井井有条,看起来是很严肃的送葬队伍。等出了村子,便有人提议,村外没人了,大家不用那么辛苦,天气热,又怕下雨,干脆走快点。
夏天的午后异常炎热,可能有暴雨,因为当时是闷热。墓地在一片玉米地里,那时的玉米已经快要成熟,植株都比人高,从地头到墓地之间的玉米已经全部被清掉。队伍很顺利地到达墓地,一切准备妥当后,便下葬,然后盖土,培出个馒头样的小山包。主持人感谢大家的利索,并说:“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没什么比入土为安更好的了。现在入土为安,大家辛苦啦!”
是的,入土为安,我们都希望看到去世的人能入土为安,老人们也希望自己能入土为安。以前是土葬,人死后直接放在棺材里,然后葬在田地中。现在是火葬,人死后要去火葬场烧掉,然后把骨灰放在棺材里,仍然葬在田地中。村庄与村庄之间是大片的农田,农田里零星分布着各个家族的墓地。土地是公有制,大家都是承包,墓地选在哪里,通常由风水先生决定,并不一定是自己的田地。以前,我看着田地,只觉得那是生产粮食的地方,是供养人们生活的宝地。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这田地也是村里人所有人的墓地,是死去以后的归宿。我们靠着土地的供养生活,也要在死后复归土地。所以,土地是活着的人的故乡,是死后要回归的地方。
老丁问我:“你之前的自我叙说多写和家人的关系,从关系存有的角度来切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努力向内去寻找答案以回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土地。我的生命在不断挪移,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大学教师。这种挪移像极了先祖们的迁徙,也像极了老一辈不断外出讨生活的命运。但我身上有浓厚的土地文化,那是由林林总总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家对我的意义,不只是家人,更是土地。所以我才会在我的迁徙中感受到痛苦的流浪感。土地是固定的,是带不走的,所以我注定了要享受分离与乡愁。
我本来也可能像家乡的其他青年一样留在土地上,或者像候鸟一样往返城市与农村。但因缘际会,我成为比较特别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发展,也吹来了农村青年的上升通道。高考恢复正常,就业实行双向自由选择,我被改革开放的洪流夹裹着离开土地,走向城市。但我身上的土地文化并未消失,我承受着不同文化和价值的冲击。我努力让自己不跌倒、不发疯,让自己在现实的环境里活下来。暂时地忘记和搁置,是适应环境中的权宜之计。也许这是一种和谐化辩证。我的暂时忘记和搁置,曾经对我有帮助,但我却不能只有忘记和暂时的搁置。在逐渐适应和慢慢站稳脚跟之后,我需要开始做些相反的工作,那是认回和连接。我要认回我身上的土地文化,连接我的家乡人情,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真实活泼的人,成为一个上衔历史、下接现实的羽翼丰满的人。
土地对我如此重要,黄河冲积的平原是我脚下的土地,我的先祖从山西老鸹窝迁到这片土地,在这土地上繁衍生息。快乐、悲伤,都在这土地上。我记忆中和所有家人的故事,也都伴随着土地。我们在田里劳作,在田间奔跑,在路上拉车,在葡萄园里种植花草。等人到老了,就埋到土里,土地里埋了多少先祖。我始终眷恋着那一方黄土,始终眷恋着形塑我的鲁西南风土人情。对我来说,土地是浓浓的情怀,是我的先祖,是我的历史。
我要入土为安,那是我的历史。
无论生活,还是书写,抑或浩浩荡荡的历史,都是我无法逃避的故乡。我终究要回到那黄河沿岸,回到鲁西南小村庄,回到父辈的历史,回到土地。这所有的历史,就是我要回去的土地,我终究要入土为安。这是我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