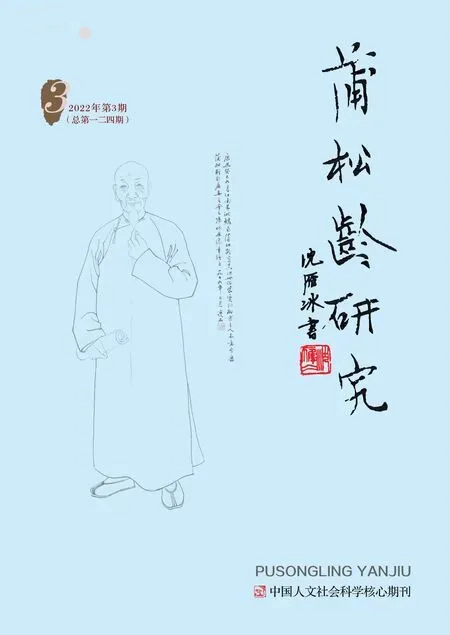马来文中的第一篇《聊斋志异》
——峇峇马来文《莲香》的翻译策略
[马来西亚]赖静婷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吉隆坡 50603)
前言
关于《聊斋志异》被翻译成峇峇马来文的相关课题,新加坡学者辜美高的三篇论文里提供了线索,也是目前对马来文和印尼文(两者同源)《聊斋志异》最详细的研究结果。
二、《印度尼西亚〈聊斋志异〉的译介》(1987)。本文提到印尼华侨梁友兰(1904-1973)对《聊斋志异》的关注,他在其著作《中国文学一瞥》里,用了一章来介绍《聊斋志异》,译了《凤仙》《黄英》和《促织》,译文前略加评论。另外,他还有一篇文章《短篇小说集——〈聊斋〉》,发表于《印度尼西亚》1954年11月号。
辜美高这三篇论文除了在第一篇中对内容有较详细的对比和论述外,第二篇和第三篇对于《聊斋志异》译文最多只停留在介绍程度,并没有对内容进行深入地探讨。但欣慰的是,从这三篇文章,我们知道了在新马和印尼,共有33篇《聊斋志异》马来文译文(包括3篇《莲香》)。
目前针对峇峇马来文翻译文学的学术研究里,以资料的搜集与统计分析为主,针对语言内容的,除了以上第一篇,还有Teo Lay Teen的“A Study of The Mala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y the 6.Baba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hian Leong Koon Yew Kang Lam”(1981),以译本《乾隆君游江南》和原文的比较,分析马来译本用词、语法等的特色。
一、峇峇马来语《莲香》的故事简介
有一个乡下的教师洪伯瑞(音译),被朋友戏弄,以为遇到女鬼,吓得想要搬走。知道真相后,他决心下次再遇到有女人半夜敲他的门,他一定会捉住她,让她后悔。一天晚上,一个美丽女子来敲门,自称莲姐(音译),因受不了后母而想逃到表兄家去,经过这里,请求留宿,当晚两人就发生了关系,如此天天往来四个月。一天,莲姐不住哭泣,说必须离开去见她父母,不能再来。她留下一只自己的鞋,说如果洪生把鞋放在桌上喊三次她的名字,她才会出现。从此他们大约三四天见一次。一晚,洪生见有一女子从窗下走过,以为是莲香自己来了,就跑出去开门,才发现是一个年纪更轻一点的美丽女子。女生带着装满花的篮子,说要送花给“大哥”。她自称彩云(音译),原本一家人要随父亲到苏州府上任,却被山贼杀死,她逃过一劫,被老妪收养。洪生邀她入房,当晚两人也发生了关系,从此天天往来两个多月。洪生得到美貌相当而更年轻的彩云,这时已经把莲姐忘记了。而莲姐因是修行多年的狐狸,知道这一切,她打算等洪生得病才过去相见。彩云是鬼,当看见洪生生病,就渐渐疏远。洪生病得无法自理的时候,莲姐带着两颗仙丹去找他。而当天刚好遇见愧疚的彩云去熬粥给洪生吃,莲姐大骂她是不仁不义的鬼,她则骂莲姐是狐狸妖精,洪生这才知道真相。最后彩云向莲姐下跪,说自愿当妾,莲姐这才答应医治洪生。她拿出两颗仙丹,一颗让他吃下,一颗弄碎了往他身上擦,第二天洪生就痊愈了,于是三人要好地过了三年。一晚,彩云哭着说她必须去转世,三人抱着大哭。彩云告知二人她会出生在农人叶家,十六岁时就会被卖,嘱咐二人记得买下她,还有要拿扇子敲她的头三下,同时喊三遍“彩云醒来”,她就会记起往事。十六年后,果然一切如彩云所说,买下她后,三人像从前一样过着快乐的生活。
从故事大纲看来,无疑是由《聊斋志异》的《莲香》篇改编而来,不过在译文里这个故事并没有篇名,而是以“这个故事是从以前的一本名为《聊斋志异》的书传下来的”代替。强调作品的来源是中国的“古书”,是峇峇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特色,甚至会特意澄清并非从印尼马来文翻译文学继承、复制而来。这似乎说明了读者群对于书籍的来源是有要求的,因为显然“来自中国”或“古书”的说法会让这个翻译作品更受到喜爱。中国学者莫嘉丽分析峇峇群体接受中国通俗文学时认为:“土生华人群落在具有特殊地位的社会环境下,既有优越感——由于得到殖民者的另眼相看而优于其他中国移民,而在文化归属感上,又未能西化而依然趋向于认同中国。这种心理使他们在尚未建立自身的文化体系时,对本源民族文化抱完全认同的态度。然而,他们生活的环境很难直接给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精神需求……中国古典小说,对土生华人而言,恰恰是他们了解遥远而亲切的祖宗之国,一解乡愁的媒介。”“他们当时面临这样一个矛盾:既想亲近中华文化又只有阅读马来文的能力……其主要手段,就是以马来文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以满足精神需求。”可见,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他们接近祖国文化的途径,如果原书不是来自中国,那这个翻译就没有阅读的意义,因为它承载了当时峇峇群体渴望的“中国性”,用以填补他们已经遗失了的“中国认识”和好奇心。
二、原文与译文的比较
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原文与译文在各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与其说陈明德的译文是《莲香》篇的翻译,倒不如说是改编。改编后的峇峇马来文《莲香》,在形式、结构、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都跟原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以下会一一论述。
(一)形式不同
文言文的书写已有几千年历史,进化出一套系统和规范,长久以来都是正统的书面语言。蒲松龄在白话章回小说兴盛的时代,选择以文言文创作《聊斋志异》,有凸显其才学和文章之法的用意。但明伦序言说:“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可见,《聊斋志异》处处有经典的“文章之法”。但明伦点评《莲香》篇,“文势已不鹘突,已不疏散……此钩连法也。通篇鬼狐并写,俱用此法,即所谓紧字诀”“处处俱用穿插之笔,双管齐下……此作两扇题之妙诀也”“笔笔跌宕、字字婉折”等,极度赞赏蒲松龄在创作此篇时运用的技巧。《莲香》为《聊斋志异》名篇之一,不惟因其故事曲折、引人入胜,其通篇快节奏的叙事和生动的语言紧紧吸引着读者的眼球,是一种文字经过提炼、设计,“有意为文”才能呈现出来的效果。
而陈明德改编后的译文,则更接近“话本”的形式,例如翻译版本总共出现了四次的“这里暂且打住,我们来说说(某人)”,以“话就说到这里”作为整个故事的结束语等等。还有,译者会在正文中自行加入解释性文字,其中一句写道:“这个彩云是谁?她不是人,是鬼……”足见其口语性,这与峇峇语的特征有关。根据推断,峇峇马来语大致形成于18世纪:在15到17世纪马六甲王朝国际贸易兴盛时期,马来语混杂各国语言形成“低级(通俗)马来语”,以达到协商和交易,变成了马来半岛上通用的语言。而当身为劳工的华裔男子娶了当地女子后,因沟通的需要,再混入华人方言(以闽南话为主),混血族群的扩张以及形式的大致定型,形成“峇峇马来语”文化与族群。顺带一提,这个族群的“族群认同意识”直到19世纪初期才形成,以区分“自我”与“他者”(19世纪才到当地的新客华人)。由此可知,峇峇马来语的形成,由贸易和沟通需要催生,因此是一种注重口头运用的语言,既没有所谓规范的峇峇语教程,也没有书面运用(直到1838年罗马拼音产生以前),在使用过程中,以大家“心知肚明”为主,有浅显易懂的特征。陈明德翻译《莲香》时是1889年,距离首次出现罗马拼音把语言书写下来的方式才50年,期间还包括传播和学习等阶段。可以推断,对陈明德来说,把自己的语言书面化,这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因此,峇峇语的“口头语言”特征也在翻译过程中显现出来,变成一种有某人在“说故事”的模式,这样才符合这个语言(文字)的运用模式。
(二)译本插入“解释性文字”的策略解读
上文提到,译者在故事叙述的正文中间,插入了自己的语言,主要是用来解释、补充故事里他认为读者会不理解之处。第一次用来解释莲姐:“这个莲姐是山里的狐狸,已经修行多年,因此可以变化成女人,与洪先生成为夫妻。在中州(negri China,指中国),如果娶了狐狸,这个人肯定赚到了,前世他一定有做善事,他才能得到狐狸当妻子。”
第二次用来解释彩云的身世:“这个彩云是谁,她不是人,是鬼,好多年前,她的父母带着她,还有四个随从,要去上任新职(赴任,Hoch Jim),那时彩云才十六岁,未嫁。刚好到了此地,彩云患上重病,死在这里。她的父亲买下棺木葬她于此,当时这里还没有房屋,刚巧先生在这里建学校,彩云的墓面对着学校,还有,彩云与先生也有缘分,所以这时才能成为夫妻。”
第三次用来解释洪生生病的原因:“虽然彩云已经‘接近’成为人了,但是,鬼,始终是鬼,她的血是冷的,我们人的血是热的,所以,被称为‘阴间鬼’‘阳间人’。如果‘阴’跟‘阳’一起,成为夫妻,慢慢地他一定会得病,不能避免。”
这里不难看见,解释一和解释三里,都和带有“中国色彩”的民俗观念有关。译者在加入这些文字时,已经预设读者不熟悉或是不了解这些“基本概念”。当然这些解释并不是准确的,如关于“娶到狐狸就是赚到”的说法,但确实是《聊斋志异》里一个很普遍的基本概念。虽然狐狸精也有“采阳补阴”的坏处,但面对李氏“狐能死人,何术独否”的质疑,莲香澄清自己非此类精怪。因此,译者这样的解释,用在这个故事里,已经足以涵盖莲香(莲姐)主要的角色设定。关于人鬼不能在一起的原因,《聊斋志异》的《小谢》篇里,男主角拒绝与女鬼有亲密关系时,说道:“阴冥之气,中人必死。”用的是阴阳之气的概念。而解释中,因中国文化里“气”的概念太博大精深,不容易说清楚,遂用了更具体的“冷血”和“热血”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称赞译者在“文化讯息”处理上的细心和巧妙。虽然译者在做出解释时有点避重就轻,但面对读者群文化概念上的缺失,这样做显然是最简单有效的。
至于第二个解释里,说的是彩云的身世。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本身的置入作用。对照原文,李女自道身世:“妾,李通判女,早夭,瘗于墙外。已死春蚕,遗丝未尽。与郎偕好,妾之愿也;致郎于死,良非素心。”可见译者改变了叙事方式,又自行将其身世添加得更丰满。但这个添加没有精彩巧妙之处,纯粹是使这段插入的文字显得信息完整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连同第一个莲姐是狐狸的解释,译者都是提前为读者“揭露真相”,造成了与读者阅读原文时感受的差异。原文中,读者是与男主角一起获得“两女为一狐一鬼”的真相的。译文中虽没有改变男主角是在狐鬼对骂时知道真相的情节,但是,“解释性文字”的插入,使“真相大白”时读者的惊讶感被消除,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文学性张力”的消解,大大减低了艺术效果。但,这是从作为中文原文读者的角度来做的批评,并没有考虑到译者的苦心。
译文这种“提早剧透”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关照读者,不让他们带着疑惑进入高潮情节,也不想在一个两女对峙的高潮情节里,有更多的细节来搅乱叙事。而如果根据原文的叙事,峇峇群体在知道她们为狐鬼的真相后,必然也会产生疑惑,而到时再来解释狐和鬼的作用、危害,只会让峇峇群体读者觉得索然无味,毕竟狐狸的好处和鬼的危害都已经在故事情节里看出来了。因此,虽然解释性文字的插入把蒲松龄的伏笔消解成平铺直叙,但考虑到读者群的接受过程,这不失为一个折衷的聪明做法,显示出解释性文字的插入是译者针对读者的认知而做出的翻译策略。
(三)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的生硬转换。翻译版本总共出现了四次“这里暂且打住,我们来说说(某人)”,这句话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明显是要将刚叙述的故事和接下来的故事分开,当作是开始新的一节的小标题。因此,每一小节的开始,都同时是叙事视角的转换。
但是这个却牵涉到叙述方式的问题。译者只使用顺叙方式,当一个场景中的情节发展至结束时,时间点已经超过了接下来要描述的另一个人的故事,所以便只好运用这个方式来弥补情节。举两个例子:译文里,莲姐知道洪生病重,带着药到他的住处,情节发展到这里打住。视角转换到彩云处,描述彩云独自害怕和伤心,内心挣扎后决定去照顾洪生,煮粥给洪生吃时,莲姐走了进来,然后情节就继续往下发展。直到彩云去投胎,莲姐和洪生生活了十六年等她回来团聚,叙述至此打住。视角转换到彩云投生的家里,叙述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如何被卖的情形,直到三人重逢。
冯镇峦在评点《莲香》篇时,针对“一日,婢忽白:‘门外一妪,携女求售。’”这一情节,说道:“如此陡入,扫却多少语言,文字断不茸沓,若顺叙莲娘如何投生,一一写来,便是呆笔。”恰恰说的就是译者陈明德改写后的写法,无奈译者显然没有蒲松龄删繁就简的功力,只好落入“呆笔”之窠臼。不妨看做是译者顺叙法中的“补笔”策略或技巧,这也造成了叙述方式的不同。原文中蒲松龄以书生为主角,故事情节围绕他展开,大部分使用的是桑生限知视角。而译文却不停转换叙述的主角,通篇使用全知视角,有个无处不在的叙事者。以莲香等待桑生病重才来探望的情节为例,《聊斋志异》是以莲香之口对桑生说出:“请从此辞。百日后当视君于卧榻中。”而改编后则是从叙事者的视角说出:“另一边的莲姐知道一切,对于洪生与彩云的勾当,她不予理会,她知道,再过一些时日,先生肯定会得病,那时才是她过去见面的时候。”此类情形很多,不缀述。
(四)内容
在内容方面,译文有很大程度的删减和改动,以下分几方面说明。
1.细节增加。上文提到,译文喜欢“一一写来”,自然比原文多了许多细节。除此之外,也有译者为了增添趣味性而加入的,如洪生被妓女作弄的情景:“他一开门,看见一个披散头发的鬼,心里大惧,径直跑回房间,急忙用被子把自己从头至脚盖起来,大门都来不及锁上。椅子、凳子被撞得东倒西歪,他的头也因碰到门肿了起来。那个女人看见他害怕地跑走,追到房门前,看见房门已经锁了,假装推门想要进去。洪生听到鬼想推门而进,害怕得快要在床上尿出来了。女人感觉恶作剧得差不多了,就离开了。先生听见鬼已经离开,才掀开被子,汗湿一身,他想:‘幸好门没被打开,不然我就死定了。这个地方有很多鬼,我还是搬离这里比较好。’他就这样任由大门开着,不敢去关门……”还有就是洪生知道被捉弄后生气的反应,并天天期待艳遇的心理,写得非常朴素生动。
2.情节删减。译文对原文的情节删减颇多,一开始如狐鬼互窥、皆告诉桑生对方是疾病的根源,桑生却不以为意,以两人嫉妒对方视之,为桑生治病、养病时二女的互动,李氏附体张燕儿尸重生,莲香生子后去世等情节皆被删去。从情节上看来,译文有意弱化二女之间斗争的张力和互动,只留下两人初见面时争论的一段。显然,译者对于二女之间情感的细腻变化不感兴趣,只注重于基本情节的推动。
3.角色转换。译者对于原文的后半部分,进行了角色转换和改动,如把留下绣鞋的女鬼李氏变成狐女莲姐、把投胎的狐女莲香变成女鬼彩云。当时的峇峇群体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小说,并不晓得中国小说里的“套路”情节,狐狸精的神异性不需要经过解构(死亡)来达到阅读新意,而女鬼附尸后脱皮换形的情节自然也可以删去,取代狐女嵌进投胎转世的情节。这个改动,从情节上完全符合了狐女的神异性和女鬼投胎的逻辑性,把原著中转折重重的情节巧妙地裁剪缝合,毫不显得突兀,甚至可以说更贴合当时读者群的阅读期待。
另外,有个不大不小的改动,即原文中本来是狐鬼同时期来往,改编成莲姐离开了,彩云才出现。这里涉及一个“精气复原”的概念:因莲香本着桑生这个年纪“房后三日,精气可复”的想法,三四天才与他相会一次,这才造成了李女在这几天里乘虚来相会,“彼来我往”的做法。译本写洪生与莲姐是天天相见,因此彩云没有“乘隙而入”的机会。而后洪生喜新忘旧,天天与彩云一起,便不再召唤莲姐,巧妙地避开了“精气”的问题,也省略了两女你来我往的指责、互窥的情节。
但是,译文在改编中也产生了故事情节前后不合逻辑的漏洞。莲姐初见洪生时,说父母已死,而后母太坏,想到表哥家去投靠才经过此处,过后却说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去见父母,所以和洪生离别。或许可以说一开始莲姐的说法只是留宿的借口,但聪明如她,当时既没有打算透露自己狐精的身份,怎会无法找一个更可以自圆其说的离别理由。总之,这两处原因都是译者的创作,反而如采取原著中狐精自言是“西家妓女”便不会产生这个矛盾。译者在改编过程中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是在自行的创作中产生这样的破绽,确实让人遗憾。
(五)人物形象
从人物的形象塑造方面来看,女鬼依旧是比较单纯无辜的形象:她直到男主角病了,才知道是因自己而引起,并且一直都处于较弱势的状态。反观男主角和狐狸精的形象与原著有较大不同,对比桑生和洪生,桑生对二女都是同样的态度,并试图从中调解两者的妒意;而洪生则明显地被塑造成“获得了更年轻而美貌相当的彩云,已经忘记了莲姐”的薄情人。同时,洪生也更加好色,故事里他是天天期待艳遇,并且有主动勾引二女的举动,达到目的后甚至心生窃喜。这样一个毫无美德的登徒子,可以享受齐人之福,只能依靠译文中提到的“前世修福”和“有缘分”来勉强解释了。另外,比较莲香和莲姐,可以发现莲姐的形象更刻薄、城府更深。原著里莲香尝试规劝桑生,警告他接触女鬼会丢命。而译文中莲姐“遥知情况”,却冷眼旁观,盘算自己要等洪生病重时才出现。而两女见面时,莲姐的语言行为更是厉害和势利,不但描写她“盛怒”“生气”和“咒骂”,还一直逼彩云医治洪生,彩云无奈下跪求她:“我多次地求求大姐怜爱地帮忙,把先生治好,如果先生痊愈了,大姐当正妻,我当妾。刚才我违反礼节出言不逊,我多多请求大姐的宽恕。”莲姐听了彩云的请求,她开心地大笑,带着笑容故意说道:“我也一点能力也没有。”直到彩云再次求她,她才答应。反观原著莲香一见李氏,几处对她“笑曰……”,只问了一次“何以处郎君者?”在争取自身权益时,只说道:“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杨梅也。”处处展现了她说话的智慧和情商。
但有趣的是,莲香吓唬桑生“病入膏肓,实无救法,故来永诀”的情节,被译者移植并放大到莲姐对待彩云上,俨然一副“女人为难女人”的画面。从逻辑上说,桑生虽然被莲香屡劝不听,但至少在莲香无奈告别时是“留之不可”,对她是有情的。而较刻薄的莲姐一早就等待喜新厌旧的洪生病重,更应对他带着怨气,但居然没有为难他的情节。从整体看来,温柔大度如莲香者,都会想要薄惩有情的桑生,而性格厉害的莲姐则只为难彩云,对薄情的洪生却理所当然地救治。译者把三人相遇的张力全部投注在二女尖锐的对话和冲突的行为上,原本丰满的人物形象被扁平化和丑化,甚至还隐约透露着男性本位视角描写“女性他者”为了争夺男性而上演闹剧的味道。
另外,在对男主人公的介绍上,可看出着重点的不同。桑生“为人静穆自喜,日再出,就食东邻,余时坚坐而已”,初见李氏时在“独坐凝思”,是个内向而勤勉好学的书生。而译文中对洪生的介绍则是“在一个村里开学校,有17个学生,独居,早午饮食都靠学生带给他”,初见彩云时则是在读信。明显前者注重人物的性格,后者关注人物的营生。当然,桑生好学精思,也是为了考取功名使前途光明,对于这个“中国式步骤”,峇峇族群显然是有隔阂的。19世纪末的新马一带,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直接面对生存的压力,科举是遥不可及的事,更不十分了解中国围绕科举制度而衍生出的那套品格审美观。译者陈明德所在的新加坡,1829年已有私塾学堂,而著名的崇文阁,则于1849年由峇峇陈金声创办。但在当地,读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参加科举,比起中国,他们大多数人更想为英国服务,就算有能力上学,峇峇族群多数接受的是英国式教育。对当时以经商为主的峇峇族群来说,上学的内容、目的和心态等都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的追求有极大不同。有了这层认识,我们可以想见,译者对读书备考的桑生的形象进行修改是必然的。而洪生的角色设定,既保留了原文中的书生形象,又拥有了读者群注重的谋生能力,还是读者群体更为熟悉的私塾老师,可说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完美改编。
三、译文的“中国性”和“南洋性”
译文的书写语言是刚从口语发展成书面语不久的峇峇马来文,其特色上文已有提及,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译文许多名词使用了闽南语的音译,只有两个名词特别有中国色彩,既彩云自称为“苏州府”(Soh Chew Hooh)人;和彩云在随父亲“赴任”(Hoch Jim)途中去世。这两处都是译者加入的内容,以符合读者认识中国的期待。另外,有南洋色彩的词语相对较多,名词有南洋一带常见的楝树(Pokok Kaya,Khaya Tree),还有马来谚语,如比喻单相思的“像猫头鹰想念月亮”,比喻干柴烈火的“将火绒和火绑在一起”。熟语方面,有“不见了石头,钻石代替;糟糕的沉没了,美好浮现了”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译者将男主人公居住的地方,由“红花埠”改成了靠山、树木茂盛和人迹稀少的乡间。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英国先后殖民了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开发了国际港口。而红花埠虽在清初时已是个贯通南北的重要码头,但其规模与百年后的新马港口却是不可同日而语。译者考量到读者群认知里的“埠”,是个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并不适合上演天天夜里有鬼魂、精怪敲门的故事,只好把场景改为适合鬼和精怪出现的乡间。经过了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虽然“埠”(码头)是中国、南洋皆有,但由于实体的差异过大,译者只好选择放弃文字的精确翻译。
整体上来看,译者一直在避免中国文化上难以解释、读者不熟悉的内容和概念,不断消除“中国意象”。如蒲松龄精心安排的“共结连理(莲李)”,莲李白骨同穴背后的文化意涵。另外,李氏还阳后的名字“张燕儿”,让人联想赵飞燕的轻盈,继承了当女鬼时的“身轻若刍灵”“踡其体不盈二尺”的特征。而莲香投胎后的姓氏“韦”,即“去毛熟治后的柔软兽皮”,暗示了莲香由狐成人的过程。叒,古代神话中日初升时所登神木,因此桑生名晓,字子明。而且,桑字也暗示了男女幽会的“桑中之约”,暗示了桑、莲、李的结合。这些丰富的文化意涵,因语言和文化隔阂,解释起来太费力,所以在译文里都被消除。中国地名的置入,算是为故事里弥补中国色彩而做的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说,译者努力地洗刷“中国色彩”,让《莲香》篇译文变成一则不必拥有中国文学常识的峇峇也能理解的作品。同时,为了吸引想亲近中华文化的读者,又不能显得太“本土化”,不能加入大量的南洋特色丰富叙事。因此,译文最终让人惊讶地呈现出中性(相对地)色彩。
结语
《莲香》篇作为《聊斋志异》里第一篇、也是被翻译成峇峇马来文次数最多的篇目,在峇峇马来文翻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本文着重讨论了由陈明德翻译和改写的译文与原文的异同,分析译者如何通过翻译策略,以达到读者的阅读意趣和期待。从艺术手法上来看,译文的叙事策略倾向简化,还没到自觉表现“艺术性”或“文学性”的阶段,单一的结构削弱了原文中的转折、冲突、情绪渲染等艺术效果,人物形象也被平面化。整体看来,译者去除了牵涉中国文化意涵的意象或情节,以符合读者的理解能力。
翻译文学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差异,译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作品的品质。不过,译本最重要的就是必须符合读者的阅读、语言习惯。陈明德可说是尽力在读者期待、接受度和原文之间达到平衡,才能运用极具独特性的峇峇马来文,向独特的峇峇族群呈现出《莲香》。当时读者具体的接受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此篇被重译两次,可以推测反响并不小,可看作是对陈明德翻译策略的肯定。在陈明德的峇峇马来文《莲香》译文之后,往后两篇译文有越来越忠于原著的趋势,这是译者在前人的基础上,配合读者拥有更多的阅读经验和体会后,才能做出的进化。总而言之,20世纪前中国小说的峇峇马来文翻译策略,从此文中可见一斑。陈明德的努力和尝试,在《聊斋志异》的翻译史及海外传播史上,皆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应该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