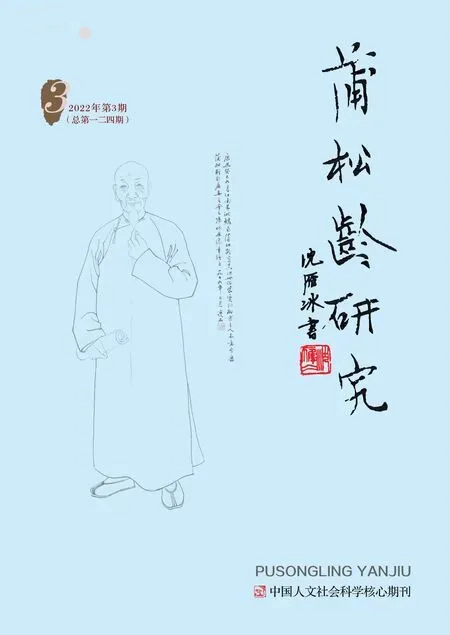《人妖》《丐仙》在《聊斋志异》中之位次
郑子运
(贵州社会科学院 文化所,贵州 贵阳 550002)
任笃行辑校的八卷本《聊斋志异》(下称“八卷本”)可以说是目前原著全本中最好的版本,它的一大优点是基本上恢复了原稿定稿的编次,之所以说“基本上”,而不是“完全”,主要是因为《人妖》《丐仙》这两篇的位次都缺乏足够的依据,很不可信。这两篇不见于现存的半部手稿(定稿)、残缺的康熙抄本、铸雪斋抄本以及黄炎熙抄本,也不见于基本上保留了原稿编次的铸雪斋抄本总目,只见于青柯亭本和二十四卷本。在青柯亭本中,《人妖》位于卷十三的《骂鸭》与《韦公子》之间,《丐仙》位于卷十五的《张贡士》与《耳中人》之间。在二十四卷本中,《丐仙》位于卷一的《种梨》与《僧孽》之间,《人妖》位于卷二十四的《梦狼》与《五羖大夫》之间。这种差异导致它们在原稿中的位次成为谜团。朱其铠等人校注《聊斋志异》,出于无奈,只得将这两篇置于全书末卷之末。
杨仁恺早已指出现存半部手稿是清稿、定稿,任笃行证明了定稿是八卷,并且基本上恢复了定稿的编次。如此一来,问题是《人妖》《丐仙》在八卷本或者说在定稿中属于第几卷呢?揆之以情理,应当属于第六卷。蒲松龄的好友张笃庆为该书的题词在全书之末,纪年是戊子(1708),这表明蒲松龄在该年已经终止创作《聊斋志异》,即初稿全部完成,随后才开始全书的定稿工作。在定稿过程中,尽管也有晚辈代蒲松龄誊录少数篇章,主要的誊录人还是他自己,全书四十多万字,蒲松龄年近七旬,杂事纷扰,而且有一边誊录一边修改的习惯,既然是定稿,也须谨慎对待,所以必然耗时甚久。在定稿过程中,一旦灵感闪现,创作冲动不可遏制,蒲松龄也会打破全书已成、不再撰写新作的决定,破戒写成《人妖》《丐仙》。八卷本卷六的《夏雪》《化男》都有丁亥(1707)纪年,这是全书记载的最晚的年岁,所以《夏雪》《化男》明显属于最后一批作品,而最后一批作品都在第六卷。蒲松龄在写定第六卷时,将《人妖》《丐仙》修改之后直接置入即可,然初稿早已装订成册,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一时没有将这两篇抄写入册。初稿供人传写,以广其传。抄于雍正末、乾隆初的《异史》收文较为完备,没有收录《人妖》《丐仙》,可见这两篇当是乾隆初年以后才由蒲家人抄写并置于初稿的;铸雪斋抄本没有这两篇,它的底本殿春亭本抄录于雍正初年,当然也不会有;康熙抄本更早,即使到现在不残缺,也不会有。
乾隆前期,福建人郑方坤到山东做官,抄录了一部《聊斋志异》,后来的青柯亭本以之为底本,则最迟在郑方坤借抄《聊斋志异》时,蒲家人将这两篇依照定稿抄入初稿最晚完成的那一卷,重新装订成册,结果青柯亭本以及抄录于乾隆中期以后的二十四卷本才都有这两篇。如此解释,虽然失于简单,但也很难有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此猜想,即使不误,也不知道这两篇是否相邻,以及不管是否相邻,它们又与何篇相邻,即位次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八卷本中,《丐仙》位于卷六的《张贡士》与《爱奴》之间,《人妖》位于卷八的《外国人》与《韦公子》之间。为何如此编排,任笃行没有给予任何说明,不过很明显,他只是采用了这两篇在青柯亭本位次的一半;在青柯亭本中,《丐仙》位于卷十五的《张贡士》与《耳中人》之间,《人妖》位于卷十三的《骂鸭》与《韦公子》之间,任笃行由此将《丐仙》置于八卷本卷六的《张贡士》之后,将《人妖》置于八卷本卷八的《韦公子》之前。任笃行为何不将《丐仙》置于八卷本卷一的《耳中人》之前,将《人妖》置于八卷本卷四的《骂鸭》之后?这是第一个疑点。青柯亭本、二十四卷本都打乱了原稿的编次,这两篇的位次采用青柯亭本的一半,对二十四卷本却视而不见,岂能是合理的?这是第二个疑点。
青柯亭本与二十四卷本虽然打乱了原稿的编次,但不可能乱到极致,因为那样会导致重新编次异常复杂,工作异常辛苦。青柯亭本十六卷与邹宗良考证出的初稿本卷数相同,若是按照初稿本的抄本即郑方坤抄本依样画葫芦,即可成事,但事实并非如此。刊刻者赵起杲在例言中说:“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卷中有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删之,计四十八条。”既然“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遂续刻之”,而成十六卷,则必不能“卷目一如其旧”。又照文义,青柯亭本最后四卷的编次不如前十二卷接近郑方坤抄本,不同的是,《人妖》在卷十三,《丐仙》在卷十五。不过,出于方便省事,每一卷初选遭遗落者,最好是数篇相邻置于后四卷的某一卷。卷十三的篇目是:《偷桃》《口技》《王兰》《海公子》《丁前溪》《义鼠》《尸变》《喷水》《山魈》《荍中怪》《王六郎》《蛇人》《雹神》《僧孽》《三生》《耿十八》《宅妖》《四十千》《九山王》《潍水狐》《陕右某公》《司札吏》《司训》《段氏》《狐女》《王大》《男妾》《汪可受》《王十》《二班》《募缘》《冯木匠》《乩仙》《泥书生》《蹇偿债》《驱怪》《秦生》《局诈》《曹操冢》《骂鸭》《人妖》《韦公子》《杜小雷》《古瓶》《秦桧》。前十八篇之中,只有《口技》在八卷本中属于卷二,其余十七篇在八卷本中都属于卷一。接下来三篇在八卷本中属于卷二。即前二十一篇之中,属于卷二的有四篇,其中一篇插入原来属于卷一的诸篇之中。后二十四篇之中,《泥书生》《蹇偿债》《驱怪》《秦生》属于卷三,《局诈》属于卷五,《募缘》《冯木匠》《曹操冢》属于卷七,《骂鸭》属于卷四,其余的十五篇属于卷八。看来赵起杲似乎是从卷一、卷二、卷三、卷七、卷八中抽取多篇,然后从卷四、卷五中各抽取一篇。而《人妖》不属于这几卷,因为只有属于卷六,才能看出抽取的规律是八卷本每一卷都被抽到,这样就与《人妖》属于卷六的推测一致了。赵起杲实际上是从郑方坤抄本中抽取,既然该抄本十六卷,换言之,不会相邻的两卷一篇都不抽取。
卷十五的篇目是:《念秧》《武孝廉》《阎王》《布客》《农人》《长治女子》《土偶》《黎氏》《柳氏子》《上仙》《侯静山》《郭生》《邵士梅》《邵临淄》《单父宰》《阎罗薨》《颠道人》《鬼令》《阎罗宴》《画马》《放蝶》《鬼妻》《医术》《蚰蜒/夏雪》《何仙》《潞令》《河间生》《杜翁》《林氏》《大鼠》《胡大姑》《狼》《药僧》《太医》《农妇》《郭安》《查牙山洞》《义犬》《杨大洪》《张贡士》《丐仙》《耳中人》《咬鬼》《捉狐》《斫蟒》《野狗》《狐入瓶》《于江》《真定女》《焦螟》《宅妖》《灵官》。在八卷本中,《念秧》属于卷三,从《武孝廉》至《郭生》十一篇属于卷四,从《邵士梅》至《单父宰》三篇属于卷六,从《阎罗薨》至《医术》八篇属于卷五,《蚰蜒》属于卷八(有的翻刻本因为有所顾忌而以《夏雪》代替),《何仙》属于卷七,从《潞令》至《林氏》四篇属于卷四,《大鼠》属于卷六,《胡大姑》《狼》属于卷四,从《药僧》至《张贡士》八篇属于卷六,之后是《丐仙》,之后从《耳中人》至《狐入瓶》六篇属于卷一,《于江》属于卷二,从《真定女》至《灵官》四篇属于卷一。抽取的规律与卷十三相同,八卷本每一卷都被抽到。既然推测《丐仙》属于卷六,而它之前的八篇正好属于卷六,很难说出于巧合;既然从《武孝廉》至《郭生》连续十一篇都属于卷四,那么从《药僧》至《丐仙》连续九篇属于卷六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
再看二十四卷本的编次情况。面对十六卷的初稿或其抄本,对二十四卷本的编订者而言,无法中分原稿的每一卷而最后形成二十四卷。任笃行最早看出二十四卷本的编次规律,“二十四卷抄本,俨然从铸雪斋抄本总目中抽取一百一十九篇,分别移入卷八、九和二十二以外各卷”。任笃行虽然一语中的,但所言太简略,没有解释清楚二十四卷的编订者究竟是如何把十六卷划分为二十四卷的,容易理解的表述是:每卷平均划分为新的1.5卷,即第一卷划分出新第一卷和新第二卷的上一半,第二卷划分出新第二卷的下一半和新第三卷,依此类推,直至第十六卷划分出第二十三卷的下一半和第二十四卷。不过,实际上又不是这么整齐划一,一些短篇遭删除不计,新卷次每卷有一到数篇被抽散到其他的卷次里面,同时又有一到数篇被抽出插进来(任笃行提到的三卷例外),这就大大打乱了编次。以卷二为例,该卷的篇目是:《劳山道士》《长清僧》《蛇人》《斫蟒》《犬奸》《雹神》《狐嫁女》《娇娜》《妖术》《野狗》《三生》《狐入瓶》《真定女》《焦螟》《叶生》《四十千》《成仙》《新郎》《灵官》《王兰》《王成》《梦别》《李公》《鄱阳神》《骂鸭》《柳氏子》。从《劳山道士》到《王成》被保留下来,但本来在其中的《僧孽》《鬼哭》都被抽出插到第一卷,《鹰虎神》被抽出插到第十六卷,本来在其他卷的《梦别》《李公》《鄱阳神》《骂鸭》《柳氏子》都被抽出插入。与八卷本对照,二十四卷本卷二不但保留下来的篇目顺序不乱,插入的篇目也顺序不乱,八卷本卷三里的《梦别》《李公》在二十四卷本卷二里仍然依次是《梦别》《李公》,八卷本卷四里的《鄱阳神》《骂鸭》《柳氏子》在二十四卷本卷二里仍然依次是《鄱阳神》《骂鸭》《柳氏子》。至于任笃行提到的卷八、九和二十二,卷八只是删除了三个短篇,卷九和卷二十二只有抽出去的,没有插进来的,比其他各卷更简单易成。如此一来,重新编次的工作就不至于太繁难。
二十四卷本卷一的篇目是:《考城隍》《耳中人》《尸变》《瞳人语》《画壁》《山魈》《咬鬼》《捉狐》《荍中怪》《宅妖》《王六郎》《偷桃》《种梨》《丐仙》《僧孽》《鬼哭》《蛇癖》《庙鬼》《义鼠》《地震》《猪婆龙》《陕右某公》《好快刀》《江中鬼》《戏术》《蛰龙》《小髻》《金永年》《夏雪》《美人首》《车夫》《杨疤眼》《鼠戏》。该卷共有三十三篇,而在八卷本之中,从《考城隍》至《猪婆龙》二十篇属于卷一,从《陕右某公》至《小髻》六篇属于卷二,《金永年》《美人首》属于卷四,《夏雪》属于卷六,《车夫》属于卷八,《杨疤眼》属于卷五,《鼠戏》属于卷三。若《丐仙》属于卷七,则与青柯亭本相同,即八卷本的每一卷都被抽到。但其实不然,二十四卷本的编次方法与青柯亭本并不完全一致,二十四卷本的编次规律是原来各卷中的部分作品汇成新的一卷,大体上是多的排在前面,少的排在后面,绝没有抽出来的单篇插在抽出最多的那组作品中间的现象。卷一的《车夫》《杨疤眼》《鼠戏》都是从其他卷次里单独抽出插入的,排在最后。卷二、卷五、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二、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二没有从他卷单独抽出插入的现象。卷三的《头滚》是从八卷本卷三单独抽出插入,《猴静山》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两篇相邻排在最多的那组作品之后;卷四的《化男》是从八卷本卷六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卷六的《泥鬼》是从八卷本卷三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卷十一的《木偶戏》是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多的那组作品之后;卷十三的《梁彦》是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卷十九的《上仙》是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卷二十的《龙》是从八卷本卷二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卷二十一《狮子》是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蛙曲》是从八卷本卷三单独抽出插入,两篇相邻排在最后;卷二十三的《酒虫》是从八卷本卷四单独抽出插入,排在最后。《丐仙》若属于卷七,就与抽出来的单篇不插在抽出最多的那组作品中间的规律冲突,所以《丐仙》不属于卷七。既然推测《丐仙》属于卷六,与《夏雪》合起来是两篇,与这条规律也不矛盾。《金永年》《美人首》都属于卷四,中间被《夏雪》分隔,《丐仙》与《夏雪》都属于卷六,也被分隔,位次恰好都在从原先三卷各抽出一篇的《车夫》《杨疤眼》《鼠戏》这三篇之前,大体上符合由多到少的排序。照不打乱顺序的规律,《丐仙》在八卷本卷六中应当位于《夏雪》之前。
卷二十四的篇目是:《周生》《褚遂良》《刘全》《姬生》《韩方》《纫针》《桓侯》《粉蝶》《锦瑟》《太原狱》《新郑讼》《房文淑》《秦桧》《浙东生》《博兴女》《一员官》《龙戏蛛》《阎罗宴》《放蝶火驴》《鬼妻》《三朝元老》《梦狼》《人妖》《五羖大夫》《夜明》。该卷共二十五篇,而在八卷本之中,从《周生》至《一员官》十六篇属于卷八,从《龙戏蛛》至《梦狼》六篇属于卷五,《五羖大夫》属于卷三,《夜明》属于卷六。编次规律与卷一相同,也是原来各卷中的部分作品汇成新的一卷,大体上多的排在前面,少的排在后面。任笃行将《人妖》置于卷八,就导致最前面的并且是最多的一组作品有一篇排在次多的一组作品之后,这未免不合常理,因为排在最前面的那一组是保留下来的,不是抽取穿插进来的,只是偶尔有一篇抽出来的作品插在其间,若将《人妖》置于卷八,反而是将第一组的最后一篇安插到第二组、第三组之间了。而且再细审卷一,来自原来同一卷最多的两组作品在新的一卷里并不混杂,而《人妖》若属于八卷本卷八,则对应八卷本卷八、卷五的两组最多的作品出现了混杂。综合这两点来看,《人妖》不属于卷八。《人妖》属于卷六的推测就不会陷入那样的困境,《人妖》《夜明》都属于卷六,排在前两组作品之后正合适。卷一第三组作品《金永年》《美人首》被分隔,卷二十四《人妖》《夜明》被《五羖大夫》分隔也就不奇怪了。
二十四卷本与八卷本之间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八卷本下一卷的首篇与上一卷的作品在二十四卷本中必相邻,中间不插入其他卷册的作品。八卷本卷二的首篇是《某公》,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一,其前一篇是《猪婆龙》,《猪婆龙》在八卷本中是卷一的末篇。八卷本卷三的首篇是《刘海石》,《刘海石》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七,其前一篇是《鸲鹆》,《鸲鹆》在八卷本中是卷二的末篇。八卷本卷四的首篇是《鸦头》,《鸦头》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九,其前一篇是《秦生》,《秦生》在八卷本中是卷三的末篇。八卷本卷五的首篇是《大人》,《大人》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十二,其前一篇是《考弊司》,《考弊司》在八卷本中是卷四的倒数第二篇,末篇是《阎罗》,而《阎罗》在二十四卷本中遭删除,实际上可以认为在二十四卷本的编订者的眼中《考弊司》是末篇。八卷本卷七的首篇是《云萝公主》,《云萝公主》在二十四卷中属于卷十八,其前一篇是《查牙山洞》,《查牙山洞》在八卷本中是卷六的倒数第三篇。八卷本卷八的首篇是《王者》,《王者》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二十一,其前一篇是《白秋练》,《白秋练》在八卷本中是卷七的末篇。最后看八卷本卷六的首篇是《夜明》,《夜明》在二十四卷本中属于卷二十四,其前一篇是《五羖大夫》,而《五羖大夫》在八卷本中是卷三的第十二篇,不在卷五,与下一卷接上一卷的规律不合,也就是说《夜明》不是卷六的首篇。卷六的首篇应该是《人妖》,而《人妖》在二十四卷本中的前一篇是《梦狼》,《梦狼》恰恰是八卷本卷五的末篇,这与下一卷接上一卷的规律正好一致。既然《人妖》本应是八卷本卷六的首篇,也应在卷六的《丐仙》只能排在其后为第二篇,《夜明》由第一篇退居为第三篇,其余各篇依次后退两个位次。
以上是从青柯亭本、二十四卷本的编次规律上判定《人妖》《丐仙》在八卷本中应当是卷六的前两篇。从内容、意蕴上看,《丐仙》应当是哀悼友人朱缃英年早逝之作。《丐仙》数次暗点朱缃之“朱”。《丐仙》的主人公是高玉成,即他出自“高门”,双关姓高的人家、门第高,文中确实又有“高门”,双关高大的门、门第高,而“高门”与“朱门”相当。丐仙自称陈九,古代朱陈村两姓联姻的典故广为人知,容易由“陈”联想到“朱”。“有大树一株,高数丈,上开赤花,大如莲,纷纭满树。下一女子,捣绛红之衣于砧上,艳丽无双”。“异红如锦”。赤、绛红、红,无非是“朱”。朱缃字子青,文中也有数处暗点“青”,如“青鸾黄鹤”;又有“苍石”,苍石即青石,犹如苍天即青天;又有“殊觉汗愧”“着汗弥盛”,容易联想到“汗青”。丐仙善手谈,而朱缃著有《耳录》,“手谈”与“耳录”字面意义有关联,而且对仗工整。高玉成急行山中,不慎坠入山谷,后来“觉云气拥之以升”,暗点朱缃的云根清壑山房。丐仙说高玉成“君寿不永”,暗点朱缃英年早逝。高玉成醒悟“己所遇者仙也”,而蒲松龄字留仙,朱缃结识蒲松龄,岂不是遇“仙”?天上女子以杵投中高玉成,后来“高每对客,衷杵衣于内,满座皆闻其香,非麝非兰,着汗弥盛”。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诗云:“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叶葱奇解释说:“从此远离后,我所得的只有柳仲郢难忘的知遇而已。”明白指出了“衣香染未销”的象征意义。杨亿《夜宴》诗云:“月落乌啼人散后,衣香数日未能销。”象征对数日前夜宴中人和事的念念不忘。蒲松龄可能受到李商隐、杨亿两人诗句的影响,也可能是文心相通,以衣服上所染香气长期不散象征着对朱缃的情谊久久不能相忘。蒲松龄特意强调“非麝非兰”,因为麝香、兰香多为女子所用,如元稹《莺莺传》描写莺莺“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强调“非麝非兰”,意在暗示读者不要理解为男女之情。
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蒲松龄曾写《挽朱子青》诗哀悼,诗云:“蕴藉佳公子,新诗喜共论。如何一炊黍,遂已变晨昏!历下风流尽,枫香墨气存。未能束刍吊,雪涕赋招魂!”该诗与《丐仙》构思相通。“新诗喜共论”,类似于后者之中高玉成与丐仙共听佳人歌唱一首七言诗;“一炊黍”用黄粱美梦的典故,卢生遇仙,犹如高玉成遇丐仙;“变晨昏”类似于丐仙在园中将严冬变为暮春;高玉成与丐仙饮酒、赏舞、听歌,又异鸟成群,月色如洗,此情此景可用诗中“蕴藉”“风流”形容;“枫香墨气存”,类似于高玉成穿的杵衣香气长存;鬼卒来勾取高玉成的魂魄,与“赋招魂”可以构成因果关系。由此也可见《丐仙》是悼念朱缃之作。高玉成的妻子告诉他“君去三年不返”,应当是暗示朱缃之卒距此文之作已经有三年,按照古人超过两周年可以算作三年的习惯计算,《丐仙》当作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以后,而《挽朱子青》在蒲松龄的手稿《聊斋草》中恰恰列于己丑(1709),所以《丐仙》应当作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之间。路大荒编订的《蒲松龄集》将《挽朱子青》改列于1707年,至此可知是错误的。《丐仙》两次点明的季节是严冬、秋杪,则《丐仙》当作于1709年末或1710年初。在追忆朱缃的时候,蒲松龄按捺不住,写诗追挽,又破戒写成《丐仙》,曲折地表示追念。至于《人妖》,有无弦外之音,尚不得而知,它和《丐仙》实为《聊斋志异》的封笔之作。此时《聊斋志异》初稿已经完成两三年了,定稿即使没有完成,也应相当可观了。
综上所述,不管在何种版本中,《人妖》《丐仙》都应该在《夜明》之前。在八卷本中,《人妖》《丐仙》应当是卷六的前两篇,其后才是《夜明》《夏雪》等篇;任笃行将《丐仙》置于卷六的《张贡士》与《爱奴》之间,将《人妖》置于卷八的《外国人》与《韦公子》之间,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