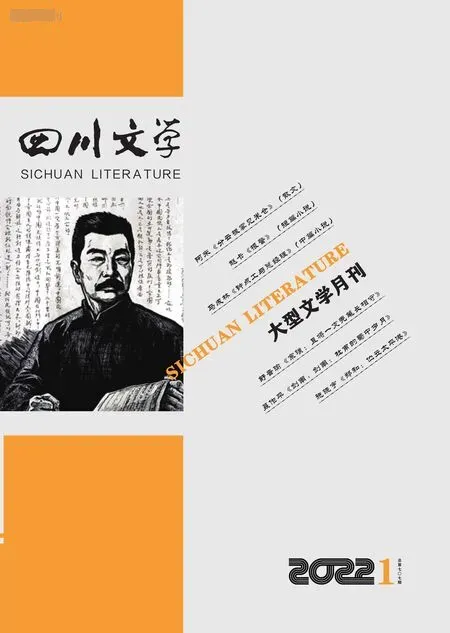乡村妇女宋正先
□文/赵以琴
当一个平凡如草芥的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都应当烟消云散,可人之生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蹊跷且充满各种意味的,也唯有他们的后人,才会在一定时间内对他们念念不忘,醒时梦里的追念。就像我的母亲宋正先,这一个乡村妇女,无论生还是死,于我们这个庞大世界,芸芸众生,都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数字或者说个体的存在,除了亲人,她构不成对外界的影响。没有人知道和探究她曾经怎样活过,更不会有人在乎她怎么死去。
九岁那年,母亲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母亲的人,一个没有母亲的人怎么能当好母亲呢?这是姐姐们对母亲的质疑,也是街坊邻居嘲笑挤兑母亲的一个理由,为此,母亲常常落泪。问及她为何落泪,母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我也没有母亲。
二十一岁那年,母亲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嫁给我的父亲。父亲那时,还是一个稚嫩的只有十七岁的未成年男人,母亲回忆说,当时见到父亲时,父亲连一件得体合身的衣服都没有,说是穿了一件爷爷的军大衣,都拖到地上。母亲每每说起此段既有哭声也有笑声,哭父亲家好穷,笑父亲好可笑,好笑到定亲都不穿体面点。
母亲往往也会补上一句,那时候,你们的父亲很帅。我们于是就哈哈大笑起来,笑母亲是贪图父亲的帅气,父亲随后也会补上一句,你们的母亲也不错,当年两条大辫子,乌溜溜的,也黑黑的,从后脑一直垂到了腰上。因此,父亲母亲的结合自然就生出了我这样的还算漂亮的女子,不过也生出如大姐那样的“胖嫂”、四姐那样的“傻姐姐”、六弟那样的“老实人”。
传宗接代,是那时婚配的第一使命。父母亲婚后的第二年,大姐呱呱出生;第三年二哥也跟着来到人间。可不幸的是,一个冬天的夜里,二哥高烧不退,烧成脑膜炎,仅在世上活了六年,就与世长辞。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位夭折的哥哥,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所以,我们后来的几个兄妹不知道是该感谢夭折的二哥,还是该感谢那个最后才拱出来的六弟,也不知道是不是更该感谢街坊邻居,说我母亲只会生丫头片子,连个接香火的男丁都生不出来。
母亲父亲不停地进行着造人计划,这期间辛酸不断,泪水不断。母亲回忆说,她生四姐的那一年最苦,冬天,下了好大的雪,没过膝盖。寒风之中,母亲突然觉得肚子疼。有过生娃经历的她知道自己要生了,赶紧滚回床上去,等待着四姐的降生。可四姐就在肚子里折磨着母亲,生了大半夜,才慢腾腾地从母亲的肚子里滑出来,此刻的母亲已经筋疲力尽,外面的大雪却更加肆意疯狂,怒吼的风呼呼地敲打着并不结实的门窗,发出啪啪的响声充斥着屋内屋外。
当时,父亲在木生台(地名)背炭,对于四姐的出生,他毫无察觉,也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幸好有祖母在,母亲在床上冻得瑟瑟发抖,祖母把矿煤放在火炉里,因为煤质比较差,冒出的烟熏得母亲睁不开眼,连咳嗽都如赌了一团棉花似的,由于煤气中毒,刚出生的四姐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傻姐姐”。
等父亲的炭来救急时,母亲的身体冰凉至极,差一点就背过气去。可女人都有一个烂脾气,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生了四姐发现是个女娃,母亲哭咽道,看来还要生。等我平安出生以后,又是一个女娃,母亲心中五味杂陈,也想偃旗息鼓,却不知如何诉说。
因为我是母亲用二百五十斤菜籽换来的,原因是,当时要缴纳二百五十元钱的罚款,家里穷,拿不出来,就只好用菜籽换,不然的话,我就会被其他人抱走。全家人看着我这个交换品,一个个都唉声叹气埋怨道,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男娃呢?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这么紧,要再生的话公社就要把房子拆了,到时候全家人住哪儿呀,难不成都想变成“山顶洞人”,看来我就是一个烫手山芋,可又不能像丢小狗小猫那样随意扔弃。
祖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说是离我家不远的另一个村,有一户人家生了三四个男娃,巴不得生个女娃,可这次又生了一个男娃,正好和老五生的时候悬殊一两天,于是,我就顺理成章被调包了。可才去一日,父亲就又将我抱了回来,理由是女娃也要亲生的好。紧接着,父母亲又开始了他们的造人计划,说是就算跑到北京去,也要再拼一把,生个带把的出来,好给赵家传宗接代,灭了村里的那些多嘴舌。
真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母亲的最后一胎,在东躲西藏的窘况里出生了,居然真的是一个帅小伙,尽管这个小伙子后来因为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身体就朝着畸形方向生长,酷似日本的相扑运动员,但家人无疑是欣喜异常的,母亲生娃的使命至此胜利完成。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养育这些张嘴吃饭的家伙。生和养,是一个古老的主题,贯穿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基本命运。
为了孩子们活命,也为了日常生计。母亲第一次学着做生意。她背着咿咿哇哇的六弟前往人山人海的电影院,手里提着自家做的歪瓜裂枣的油糍粑,还没等母亲叫卖,糍粑就被一抢而空。母亲尝到了做生意的快乐,也真的领略到了做生意实在比挖土种地强多了。改革开放初期,母亲用自己积累起来的启动资金,开起了村子里第一家水豆花饭店,又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豆腐西施”。要说起来,这个绰号还是我给她起的,那时候,我刚上中学,学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故乡》,文中就有一个叫“豆腐西施”的人物。
不过,母亲这个豆腐西施和先生文中的豆腐西施截然不同,起码,母亲没有如圆规一样的细脚,也没有擦得如白纸的一样的脸,母亲是高大的,也可以说经过生娃的地狱式历练,母亲现在是肥硕高大的,当年的长辫子挽成土包扣在了后脑勺,偶尔还会盖上一个白色的荷叶边的确良帽子,说是防灰,也为了遮掩住她的那些早生的华发。
母亲的水豆花做得细嫩白净,吃起来爽口顺滑,就算空口吃,也能在嫩豆腐里吃出淡淡的甜味来。我们几姊妹是母亲水豆花饭的粉丝,几乎每一天都会吃上两大花碗,才有满足的感觉。来赶场吃饭的人,也是母亲水豆花饭的粉丝,加之母亲的豆花饭便宜,还送酸菜,告水管饱,油辣椒更是一绝。到县城里读高中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名叫《母亲的油辣椒》的作文,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边写,涎水一边浸满了口腔,馋得我都连续吃了半个月的豆花饭,可却怎么也吃不到母亲的味道。
油辣椒随便加,鱼香菜随便吃,更是让赶场的人喜欢母亲的水豆花得不得了,就算有人挖墙脚,吃过一次照样回到母亲的摊子前来索要,美美地吃起来,擦擦嘴角留下的豆腐渣渣伴油辣椒,才心满意足地离开。其中,有一个蒜头红鼻子的老人,每场都会挎着一个胀鼓鼓人造革皮包来到我家,进到店里先是笑眯眯地看着母亲,随后喊一句,宋先。我母亲其实叫宋正先,可这位老人喊的时候总把中间正字给囫囵吞了,听起来母亲的名字就叫宋先了。
母亲迎过去,慢条斯理地接过老人从肩膀滑落的人造革皮包,随即进到自己的房间里,腾空人造革皮包,也不问价格,就把钱数给了老人,老人总是会非常细声客气地说句谢谢咯!随即母亲说,我舀碗豆花给你吃。有时候,老人会拒绝;有时候,老人又欣然接受。母亲也是有时候收钱,有时候不收分文。一切都是很随意,不随意的就是老人每一次必定拿东西给母亲。后我问母亲,那个人是谁?母亲说是赵家坡的一个伯公,拿些米、鸡蛋、豆子等等来卖给她,还让母亲保密,因为那些东西是伯公平日里悄悄攒起来的,攒够了一定的分量,就拿来卖给母亲。在那以后的每一个赶场天里,我都能看到他,他都会进到母亲的店里,哪怕是那天没有攒够买东西的钱,后来,直到母亲生病,饭馆停止营业,伯公才没有挎着人造革皮包来到母亲的店里。
母亲生意越做越大,也越做越齐全,也可以说母亲的生意囊括了乡场所有吃的全部。后来,母亲卖起了饺子、粉条、米皮,还学会做凉粉、包子、发糕、麻花。大姐夫常常说母亲的饺子是空心饺,他吃着不过瘾,每次到母亲的店里,他就自己动手包饺子,本来可以包五十张饺皮的馅儿,却让大姐夫三十张饺皮就包完了,一旁劳作的三姐总会瞪上两眼,母亲却啥也不说,默默地干着其他活。
不幸的是,三姐在十八岁那年突发心脏病去世,母亲哭晕在医院的长椅上,瞬间苍老了许多。我无法体会母亲连失二哥三姐的痛楚,可如今,我却能深深体会,因为我也是连失父爱母爱,还失去了祖母祖父。
失去亲人,悲伤无济于事,生者还要继续生活,这看起来残忍,又有些理所当然。尽管我们姐妹几个很馋母亲做的凉粉,可母亲给我们定了一个规矩,说必须要饭店开张以后才能吃,可开张时,往往就到了人群拥挤的大中午,来来往往的人根本停不下来。我们几姊妹眼鼓鼓地看着凉粉一点点变少,心里着急得犹如猫抓,生怕凉粉被人群一扫而空,都悄悄地企盼着母亲的凉粉不要卖完,能够给我们几姊妹剩一点。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我们的愿望都会落空,只有雨天或农忙时节我们的愿望能实现,甚至赶场过后五天都有剩凉粉吃,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母亲看到我们如此喜欢吃凉粉,就让我们几姊妹和她一起干活,一人搅凉粉,一人递柴烧火,一人打杂。洗盆盆、捶辣椒、搞盐酱、剥蒜瓣、摘葱葱,一家人都有活可做。其中一次,四姐搅凉粉的时候,由于锅下火力过猛,凉粉跳了起来,一颗滚烫的凉粉巴在了四姐的脖子上,甩都甩不下来,四姐跳起脚妈呀妈呀地喊,最后,脸上起了一个如小指头粗的果子泡。可这并不能阻碍她吃凉粉的激情,等凉粉彻底熟了以后,母亲就特意给我们几姊妹装上一小钵,放在冷水里冷却,说当天的下午饭就是吃凉粉,我们几个非常高兴。吃完凉粉,就去河边踩水、玩石头、追鸭子,玩得不亦乐乎。而母亲则没有这份闲情,她依然在灶前灶后忙来忙去,一会儿洗锅、一会儿腌酸菜、一会儿又喊,老五,赶紧去把鸡窝给关了,把苞谷碎给鸭子放好……母亲好像一直都在忙。
20世纪80年代,能有包子吃已经是小康生活了,况且我家还有包子卖。可想而知,我家那个时候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问母亲,是谁教会你做包子、炸麻花的,母亲却说,这个要谁教嘛,自学的。二十年后,我以为自己堪称包子世家的后代,肯定也能自学成才,在闲日里买上几斤面粉,叫上女儿说一起做包子吃,还夸口说我家是包子世家,做的包子好吃得很,今天妈妈就给你做外婆的包子。但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发面、揉面,捏好了包子,可蒸出来以后却个个如屎疙瘩一般,一咬牙齿就黏上了。我不服气,我不可能做不出母亲那样的包子,我一定行。我再反复试验,最后还是宣告失败,那一刻,我才从心底里真心地佩服母亲,为什么母亲那么能干,可当时的我们却没有感受到,只觉得揉面好玩,母亲的白色荷叶边的确良帽子也好玩。
母亲把包子摊子支在了马路边上,四姐非常愿意去卖包子,母亲顺势把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四姐。四姐因此攒够了买旅游鞋的钱和给我买皮鞋的钱,母亲只是笑。有一年,四姐居然在坎下的田埂上捡到了一百多块钱,据四姐后来回忆说,当时,那钱如做梦一般躺在地上,她那个心啊,都要快跳出了胸腔。四姐屏住呼吸,四处扫射了一遍,发现空无一人,加紧脚步上前弯腰佯装扯裤腿捡起钱,快速离开,到其他更加僻静的田埂上溜达了几圈才回到家中,疙疙瘩瘩地把钱给了母亲,母亲却又转交给了父亲。
还有一次,四姐被食品站的刷锅水烫伤了脖子,又被大铁门压断了腿,还偷了拖拉机上的一把李子苗,还骂她的老师是四脚朝天,老师气得让她滚,她却说,我不是圆的。母亲对我们这个淘气的四姐也只能哈哈大笑,笑四姐的“傻气”,笑自己所生的女儿们居然如此多彩,这个家居然如此丰富生动。母亲和父亲把四姐偷的李子苗种在后院的自留地里,不过几年的工夫,漫山遍野都是李子树,特别是花开时节,那个美呀,没法说。如果那个时候知道有桃园三结义,那我们几姊妹估计就要在李园里来个山盟海誓。李子还未成熟时,弟弟偷摘李子放在书包里,给了他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涩得嘴巴都张不开,说道,某某,你这个李子也太酸了吧。母亲知道后,戳了弟弟一下,笑说道,小屁孩都晓得哄人了。
母亲会做的吃食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什么酸豇豆、大头萝卜丝、臭酱豆、臭豆腐、甜米酒等,好像就没有母亲不会做的,我记得母亲连泡粑、苞谷粑好像都会做。有这么一位能办吃的母亲,我们几姊妹自然就茁壮生长起来,个个站出来都是“重量级”的人物,特别是大姐,现在全村人喊大姐“胖嫂”或者“胖姐”,而她自己却说:“我胖得均匀。”眉宇间露出的自信与坚定是不可亵渎的。可有时候别人说多了,她还会补上一句:“我又没有吃你家的饭,关你卵事。”不过,后面这个“卵事”只有她自己能听见。也有人说,大姐越来越像母亲了,身材、长相、脾气都是母亲的翻版,只是稍稍比母亲胖了那么一点,大姐说,我是我妈生的,我不像她,难道像你吗?
可惜的是,当大姐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两年。我们把母亲满含笑意、满头白发的笑脸挂在了墙上,和父亲一起,一个笑,一个愁。大姐拿着木棍如授课老师一般站在遗像前,自言自语道,妈,你笑得开心吔,去见到爸了?爸,你愁个啥吗,妈现在来陪你撒,说完转身背着手一摇一晃地离开,却看到肩膀耸动得厉害。我也跟着抽泣起来,却听到母亲好像在喊我,说,老五,快点,快点把这背花生背回家,我们煮盐花生吃。蚂蟥哪里听得了水响,就算力气用尽也狠命背起花生朝家的方向跑去。母亲为我们几姊妹煮了好大一锅盐花生,还悄悄对我说,老五,你把盐花生藏点在海椒洞里,等她们把那些吃完,你还有。老五,快点来喝甜酒酿子咯,估计现在能喝酒就是因为母亲的甜酒酿子惹下的祸,要不然怎么能喝不醉呢?母亲的甜酒曾把只有几岁的侄儿给醉倒了,侄儿斜靠在祖父的柜台前,高声大气地说,我谁也不怕,外公也不怕,外祖也不怕,说着说着,整个身体就拉抻了。等侄儿成年以后,问及此事,侄儿说,他记得非常清楚,喝外婆的甜酒都喝醉了,可如今没得喝了,一句话呛得大家都阴下了脸,说侄儿好端端的过年,补这一句真是扎心。
没有母亲的年,还叫什么年啊?没有母亲的家,还叫什么家啊?没有母亲的日子,还叫什么日子?我们几姊妹成了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孤儿,无父无母,连祖父祖母也舍不得我们的母亲父亲,也跟着他们一起凑热闹去了。大姐说,他们刚好凑一桌,四姐说,可母亲不会打呀。大姐又说,她早就会了,只是没闲,现在闲了。
我们愁眉苦脸地坐在母亲的遗体前。四姐擦拭着母亲的脸庞,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捏着母亲的手指,抠了一次又一次。弟弟则埋头哭泣着,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最爱的人远走了,弟弟是最伤心最难过的。我们大家都无话可说,一直就这样默默地待了半夜,却见风吹翻了母亲脸上的纸钱。四姐赶紧站了起来,喊我们说,不要打瞌睡了,母亲好像有话要说。我们都伸长了脖子,朝母亲的脸看去,看到母亲居然是笑眯眯的,这个笑就像母亲看到自留地里的海椒、茄子、豇豆、黄瓜、苦瓜一样,母亲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下饭的好家伙,我家那群娃儿肯定不会挨饿了。
可不就是这样吗?母亲除了会做生意、办吃的,还会种地。母亲的自留地是精彩的,什么色都有,春天一到,母亲就带着我们几姊妹去到自留地捣鼓起来,一会儿种上葱、蒜、姜,一会儿又种上西红柿、海椒、茄子、豇豆、黄瓜、苦瓜、捧瓜,一会儿又种上芹菜、牛皮菜、青菜、白菜、萝卜,反正母亲的自留地一年四季没有空过。三姐是自留地里的重要人物,我们其他几姊妹是带着好玩的心态去种地,三姐却是一五一十认真种地的态度。母亲很喜欢三姐的能干,我们也佩服三姐如母亲一样的能干。
大姐和四姐在自留地里偷奸耍滑,被三姐提起粪罐,或者拿起泥团砸在了身上,却不敢言语,反而还会加快劳作,免得一会儿又被三姐砸。母亲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浅浅说一句,你们活该,谁叫你们偷懒。大姐不服气,总是寻着机会和三姐打架,可她不是三姐的对手,经常被打得哭哭啼啼。她索性就开骂,骂三姐是半条命。三姐一听这句话,就气得直打哆嗦。我们不知道三姐对半条命这句话为什么如此敏感,后来三姐因心脏病过世,我们才知道原来那句话的意思是这样,都有些埋怨大姐,说她说话狠毒。母亲也会说上几句,让大姐收敛一点,不要别人那儿疼,你就直打那儿,这样伤元气。
记忆里,母亲好像就没有大发过脾气,也没有打过人,反正我没有被母亲打过,也没有被骂过,母亲就算生气,也只是咕噜几句,你听不清楚的话。可到母亲过了五十岁以后,姐姐们开始埋怨起母亲,说母亲不会整理家务,不会做吃的,家里的灶头冷冰冰的,床上的衣服、床底的鞋子扔得到处都是,还说父亲遇到我的母亲简直就是受罪,一碗热饭都讨不到吃的。我无从插嘴她们说的这些话,但我可以选择不听,我选择帮助身体已经每况愈下的母亲的忙,我把衣服叠起来、鞋子收起来、灶台热起来,就像母亲当年的样子。一日,我问大姐道,你学会母亲的煮甜酒了吗?大姐面带难色地说,哎,我不会,也不晓得母亲当年是怎么煮的,煮出来就那么好吃。我只是笑嘻嘻地说,我也不会煮,但我会包粽子,是看着母亲包粽子自学的。那你会做水豆腐吗?会包包子、会做凉粉吗?好像都不会。我也把同样的话问了四姐,四姐的回答也是不会。那既然不会,怎么母亲就成了不会整理家务的人呢?
姐姐们也总是埋怨母亲老了喜欢走西家串东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摆起龙门阵就停不下来,还说因为母亲不会说话,经常引起邻里矛盾,合不来人,让母亲哪里也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可大姐打电话说,她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和隔壁的那个女的合不来,话里带着气愤,说,那个女的太讨嫌了,居然悄悄在后檐沟打大姐的红公鸡,大姐看到,气得瞪眼吹胡子,和对方大吵一架,发誓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我听后,心里非常释然,说,现在懂母亲了哈。是啊,懂了懂了,怪不得母亲养的鸡、养的鸭老是不见,也怪不得了母亲老是吃哑巴亏,那个女的太坏了,欺负母亲这个老实人。我记得当年母亲和那个女的还是好友,那个女的来我家借一升豆子,可在还豆子的时候,她却短斤缺两,母亲提了出来,她就说母亲这个婆娘强势得很。和母亲吵。母亲吵不过,就发誓从此不再和她往来,直到母亲过世,那个女的在家关门抵户好几天,不曾露面。
母亲的遗体在家停放了几天,我们准备让母亲和父亲安葬在一处,可却因地选不上,母亲只得和三姐、祖父、祖母一起守着我家退耕还林的那片林地。在起坛准备抬棺离开时,却听六弟扑通一声跪在湿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大姐也跪在地上起不来了,旁人一直在劝说让大姐起来,但她因太胖腿又有疾病,在大家七手八脚的拉扯下才站了起来,却又抱着母亲的棺木不松手,开始哭诉起来,哭母亲拉扯我们六姊妹实在不易,哭母亲年轻时丧子、中年时丧女丧父、刚进入老年丧夫,如今把自己也丧了。
越是说,越是哭得伤心,惹得送丧的人都掉下泪来。我们几姊妹更不用说了,都哭喊起来,如浪声一浪高过一浪。送丧队伍如一条蠕动的爬行动物,母亲装在棺木里的骨灰轻得风都可以抬起来,可我们的脚步却如灌了铅一般,怎么都挪不动。母亲死得太突然,突然到我们连棺木都没有给她准备。她还那么年轻,在我们心里,坚强的母亲至少再活个十年没问题,可父亲才走一个多月,母亲就忍不住追随而去,她说她想念我们帅气高大的父亲了,生怕哪个小妖女在阴间给抢了去。
安顿好母亲的后事,中午已过,大家都甚感饥肠辘辘,好多天没有正常进食,只顾伤心与哭泣。就在我们几姊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时,却听掌勺大娘脆生生地喊道,宋大妈豆花饭出锅了,饿了的幺儿些,快来吃哟。在听到的刹那,我又忍不住悲伤,放声大哭起来。果真是物比人长久,母亲宋正先不在了,可她生前做的豆花还在,还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大概是最好的事情了,也是对母亲这样一介乡村妇女最好的惦念与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