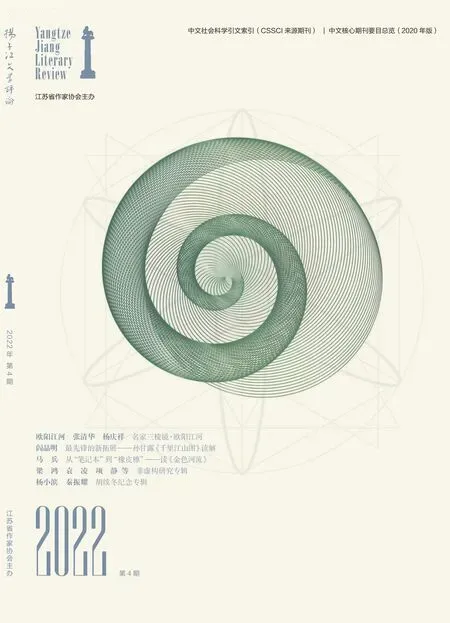生态文学:特征与概念
刘晓飞
如果从1980年代开始算起,中国生态文学迄今为止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当下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创作都处于瓶颈期;生态批评翻译和运用国外理论较多,中国原创性的生态理论建构较少,像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理论和曾繁仁的“生态美学”这样突出的成果近几年更是付之阙如;生态文学创作方面,主题单调且创新寥寥,审美空间狭窄,缺乏动态多维的艺术空间。造成如此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态文学最本源的两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生态文学的内涵及特征到底是什么?这关乎生态文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生态文学存在的根基。
迄今为止,国内对于生态文学的界定,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的说法获得较多认同和使用,“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一定义提出近20年了,回头审视这一说法,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尽管王诺在下这个定义之前区分了生态文学、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并认为生态文学与其他两类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此书在随后章节梳理欧美生态文学的发展进程时,又提出“生态文学自古有之”,“人类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很明显,他把蒙昧状态的生态意识也当做生态文学了。这一定义的表述与其具体的运用之间存在着范围上的不吻合。
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近二十年来,中国生态文学界基本没有脱离开王诺的概念,同时也继承了这一定义的特点。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对于生态文学的内涵还是含混模糊的,其外延范围也不甚明确,这导致对于生态文学的认知和表述出现了要么狭窄化,要么泛滥化的问题:或者认为只有描写环境污染的才算生态文学,或者认为出现动植物就是生态文学,甚至把诸如古人的山水田园诗、一些宣扬生理欲望自然需求的文本也囊括入生态文学之内。这些不良倾向对于生态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害的,会导致生态文学走向狭路或者虚无。
一、两个相似的概念辨析
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中,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生态文学这三个概念常常被混淆使用,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继承了这一“乱象”,而这背后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应该对其加以清晰地辨别。三个概念中,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从这一角度入手进行辨析是比较正确的途径。这三种文学有相似之处,这也是导致它们之间相互混淆的重要原因: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友好的,最起码不是征服和统治。日本学者结城正美总结了自然写作的三种类型:“在自然写作中存在着以‘自然共感、自然礼赞’和‘耶利米式的悲叹’为两个极端的修辞可变动区域。越接近前者则间接的(认识论性的),越接近后者则直接的(政治性的),参与到环境行为主义中来”,还有“一种把依据于‘故事’的语言表达作为环境行为主义的参照基准的可能性……故事特有的位相转换成行为主义的基础……这种新的趋势……更加具有综合性”。笔者赞同并借用了这个说法,并做出以下区别:自然文学属于前者,即间接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共感和礼赞式的,环境文学则是直接的、政治性的“耶利米式的悲叹”式的,生态文学则以故事性和综合性为主要特点。
自然文学,主要来源于中国台湾、美国等地区或国家的“自然写作”“自然书写”的说法,只要自然出现且在作品中占有不小比重,且写作者亲近自然,这样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称为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基本是景色描写,或者景物描写。在笔者看来,自然文学有三个特征:第一,自然文学中的“自然”,指自然界的现象、生命、物质等,被强调更多的是“物”的属性或者工具特性。自然文学里的“自然”更多是作为审美客体被人对待的,它们大多是作家抒情叙事的工具和背景,人利用了自然,而自然的生态意义和自身价值是被忽略和遮蔽的。李泽厚在分析《庄子·秋水》时说:“这并非‘鱼之乐’,而是‘人之乐’;‘人之乐’通过‘鱼之乐’而呈现,‘人之乐’即存在于‘鱼之乐’之中。……是人的情感对象化和对象的情感化、泛心理化的问题 。”这里的鱼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然文学中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文学带有很多非理性的前现代的痕迹,这也造成了倘若用科学的生态眼光来看,有些自然文学作家是带有人俯瞰物的人类中心主义痕迹的,所以,宣称“自然是精神之象征”的19世纪美国作家爱默生的散文和中国现当代的一些“卒章显其志”的写景抒情散文都属于自然文学,不能算是生态文学。第二,自然文学的审美风格具有明显的抒情性。在自然文学中,个人感情自发地融入自然,自然反馈和折射了人的情感和思想,自然美和情感美融为一体,情与境交融,“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而且在自然文学中,情感许多时候带有私人性质,展示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和私密的个人情感。相比之下,生态文学中的情感则是涉及社会和共同体,显示了集体性的面相,更多从全人类、生态、地球甚至宇宙角度着眼的。第三,自然文学最终的指向是写作者投射到自然上的人格精神,追求的是人之精神与自然的契合,也就是人的“物”化,所谓“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菜根谭·闲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和山被写作者捕捉并加以描写,但此时的自然只是人的一个影子或者镜子,菊和山是虚写,人才是创作最终的表达和展示对象。也就是在自然文学中,自然成为折射人的精神的镜子,即使作品中没有出现人,但其实人已经隐身于作品中,他的态度通过文字折射出来了。综上,在自然文学中,自然是人的审美客体,更多地承载着个人情感,最终指向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自然文学的历史悠久,很多所谓的生态文学中皆包含自然文学的因子,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式的审美特点和思维模式,其中,自然文学的典型体裁是散文和诗歌。
1984年,中国作家高桦在《中国环境报》 首次提出“环境文学”这一概念,以徐刚的《伐木者,醒来》 《长江传》等作品为代表。环境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问题文学”,是描述环境被破坏状况、肯定环保成就的文学,相对来说揭露问题更多。“环”的意思是环绕围绕,意味着以某物为中心,“境”的意思是某一场所或者空间,所以“环境”就是“指与某一中心事物相关的周围事物”。通常,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等类型,但无论哪种环境都是以人类为中心进而给周围世界的命名,所以环境文学天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基因。环境文学有以下特征:第一,环境文学描述的对象和出发点是自然,但自然是现象和结果,人类的破坏行为是本质和根源。人的负面作用被显著强调,人如同盘踞在蛛网当中捕食的蜘蛛一样,为了其自身的生存攫取资源构筑关系,人类处于环境文学的主导地位。第二,环境文学的风格一般是批判揭露,强调现实性和真实性,“对于时代的那种强烈的愤怒支撑着……作品的强度”。环境文学作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作家多是运用报告、纪实文学形式,大信息量地报道了令人震惊的环境危机问题……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作为社会问题之一,尖锐地提到公众面前,可以说它是文学对环境危机最初的呐喊,是对抢救环境的呼号”。第三,在一定意义上,环境文学属于生态文学的早期状态,因为它已经开始较为理性地反思人对自然的影响,这也是《寂静的春天》 《伐木者,醒来!》等揭露人类破坏行为的文本被视为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的原因。但环境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烙印的,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目的地还是为了人的发展和生存,而且自然仍旧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只不过因为破坏环境的后果影响到了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总之,环境文学致力于批评谴责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征服,尤其以真实性和问题性取胜,环境文学的典型体裁是散文和报告文学。
二、生态文学的特征及界定
在辨析了两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后,可以对生态文学进行较为准确的辨认和界定了。生态文学突破了环境文学关注的“问题”核心,从具体的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上升到关注生态整体的生存,它是视野恢弘的大文学,是环境文学的升级版。生态文学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生态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交互主体性。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人类与自然界的“他者”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互为对方的客体,同时也都是作为自然界一分子的主体,两者同样重要且产生交互和融合,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主体间性”。“生态”这个词汇本身来源于古希腊,是住所或者栖息地的意思,更强调在地性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着力于维护整体生存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生态文学的关注点并不是单独一方,而是探索两者和谐共生的可能与路径。而且,生态文学既追求人类与自然界他者的完整,这是广度;也强调人类心灵内在的自我完整以及灵魂与肉体的统一,这种双重圆满是深度,两者的圆融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学的大境界。比如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中,花仙在山野中的激情裸奔就是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景象。
第二,生态文学呈现出现代的理性色彩,它是出于生态整体利益与生态整体共存的理性考量。生态文学是在生态危机出现后的亡羊补牢,它不是自发的纯粹喜欢,也不仅是愤怒的控诉和批判揭露,它具有自觉的清醒的意识,“将已经穷途末路的现代社会这个怪物改编为温暖的故事世界,并为它重新注入灵魂”。生态文学不放弃人的生存权利,但同时由于人有理性且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生态文学的使命在于反映人、影响人,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仍旧是“人的文学”,尤其重视人在自然中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自然文学中,你可以摘下一朵花表达沉醉,在环境文学中,你可以谴责摘花行为,但在生态文学中,摘花可能就有了多重意蕴,《森林沉默》中美到醉人的醉醒花更是被人摘下来酿酒杀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学的“主题先行”不仅不应该被诟病,而且是一种必要的存在。
第三,生态文学具有超越性和整合性。生态文学是被现实生态问题催生激发出来的文学,承载了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但它不局限于生态问题和具体生活,而是反思社会、历史、文化与文明等,注重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开掘,其最终指向和目的,是塑造人的生态观和价值观,所以生态文学是从自然到人类的由外而内,它的路径走向是“生态-生存-精神”,具有强大的超越性。同时,生态文学的整合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审美意义上、抒情意义上,一定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运作出来的结果”,生态文学涵盖了生态、历史、文化、社会、伦理、心理学、文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具有跨学科多层面的艺术和阐释空间以及延展生长能力。在文体上,除了散文、报告文学,生态文学还可以采用小说、诗歌、非虚构等各类体裁,尤其以小说最为典型。
第四,生态作家的专业性、科学性。这个特征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值得拿出来加以强调。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不会闭门造车或者满足于感性慨叹,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生态知识或专业能力,所以他们才能窥见问题甚至提前预警问题,才能用宏观视野维护生态的整体存在,中外皆如此。这种科学性和专业能力的获得又分为两种情况:或者作家本身同时也是生化医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卡逊是海洋生物学家,所以能够发现杀虫剂等化工产品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写出了《寂静的春天》,科学家利奥波德能够分辨动植物和自然环境告诉人们的“语言”,所以写出了《沙乡年鉴》;或者作家深入自然环境,有长时段的田野生活经验,比如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生活了两年多,对瓦尔登湖及周边环境有了深入了解,才写就了《瓦尔登湖》。中国生态文学作家大多是后一种类型。苇岸在北京郊区长时间观测动植物和自然节气,所以才写出了《大地上的事情》,陈应松曾经到神农架挂职,后来每年都要去住上一段时间,所以才写出了《森林沉默》,胡冬林长年驻扎在长白山,所以写出了《山林笔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对自然界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具有科学的知识储备,更具有长远的目光。
综上,在对比和总结了生态文学的几个特征之后,笔者试着给其下一个定义:所谓的生态文学,是在现代性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背景下,作家具备了一定的生态知识,以现代的生态理性意识为基础,并秉持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坚持人与自然生存权利平等,其最终指向为人的精神生态的文学。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学的表现中心,其生态审美品格是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然文学、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这三者在实际运用中经常被混用,甚至已成常态,这也说明了三者具有一些共性或有一些重叠和交叉,特别是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但甄别三者的不同之处,会使生态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更清晰明确。
三、生态文学的科学性
与其他文学相比,生态文学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具有科学性,笔者想就这个特征展开进一步阐释。除了科普作品,生态文学应该是极少数具有鲜明科学性的文学类型了,但科普作品的创作主旨是为了形象地传达科学知识,而生态文学的核心还在于艺术审美。学界在讨论生态文学的不足时,一个被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过分强调生态性而审美性不足,或者说科学性冲淡了审美性,似乎科学性与审美性不可两全。但这样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怀疑的,“科学分析真该被斥为破坏了构成文学作品和阅读独特性的东西,而且首先破坏了美学乐趣?”“环境文学在拓展和发展过程中亟须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在艺术殿堂中徜徉,环境文学还要与自然科学(大气、地貌、水质、林业、噪声学等)、与社会科学(经济、文化、法律等)建立多边的、广泛的联盟。一个环境文学家比别人需要更为丰富渊博的现代科学意识与多种学科知识。”其实,科学性应该是生态文学的必备特质,科学性是生态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知识基础,同时,如果没有科学性,生态文学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靠理由。
何谓科学性?科学性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表现和形态。自然科学建立在理性逻辑的基础上,它关注的主要是物质领域,其中的科学性,应该是用严谨的数据和理论,解释、推演或者创造某种事物或者现象,它重视过程的逻辑严密、结论或结果的准确,它的科学性是环环相扣的。相比之下,文学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人类道德情感、理想信仰、审美风格等精神领域。好的文学作品是情理交融的,它动用直觉情感,但也不应该缺乏理性,其中的科学性,并不过分在意过程的严密和结果的准确,而是强调对事物、现象和人性的观察力、洞察力的敏锐度,它可以超越当下提前做出警示,也可能需要深入精神层面的挖掘。也就是说,文学中的科学性重视过程的呈现和细节的刻画,这种科学性致力于事物和问题深度与广度的开掘,它的形态是立体多元的。具体到生态文学中的科学性,有学者认为,“自然科学话语进入生态写作叙事的符号层面,从符号代码角度看,主要表现为三种维度:其一是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的直接镶嵌对文本形态的影响;其二是自然科学的思维特征、研究方法对文体特征的影响;其三是自然科学认知推动生态写作中叙事模式、伦理立场的现代化”。可以简单概括为,生态文学中的科学性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叙事和科学思维。也就是,生态文学的科学性以自然学科知识为基础,同时也在文体格式和叙事表达中表现出来,最终抵达的是宽广深邃的生态价值观和科学思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与技术不能划等号,科学更多的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它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目标,而技术是科学有缺陷的果实,它是不完美的实体。人们盲目迷恋的是技术立竿见影的效果,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妄佞之心,而技术本身的不完美以及其强大效用带来了严重的“现代性的后果”。
生态文学产生的知识背景是建立在现代化工业以及海洋环境科学的自然学科基础上的。一方面,之前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杀虫剂给环境以及人类自身带来的严重危害,所以造成了“寂静的春天”,也就是化学工业产生的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另一方面,如果卡逊不是海洋生物学家,她便不会将环境污染后出现的反常现象与化工产品的滥用联系起来,也就不会有《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可以说,没有科学就没有生态文学的诞生,虽然早期生态文学的科学性显然偏向于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也有了人文学科的对生态问题的警觉,它是采用近似寓言或者童话的诗意方式来表达作家的忧虑的。
众所周知,生态文学中的核心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如何将双方关系调试到合理的程度?这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最终恐怕也需要依靠科学来实现。人是地球上唯一有思想有理性的生物,不能指望非人类来约束行为和遵守协议,“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做出审慎的选择”。掌握并按天地运行规律加以调整,以促进万物的正常生长,不逾越也不遗漏,也只有人类能做到。所以说到底,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需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理性智慧来调节维护生态平衡,特别是为人类划出行为红线,制定行为与思想的规则。其实这种观念古已有之,比如老子所说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淮南子·原道训》中所说的“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其实就是在合理有效地控制人类的行为与思想,特别是合理遏制人类的欲望,从而给非人类留下生存空间。而两者关系的进与退,以及什么是合理有效的空间与界限,需要根据科学角度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进行界定,“如果科学界人士不与生态主义者合作,从自然的角度分析科学存在的危机,他们不可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应当)和他们一起设想科学的发展是否可以采用另一种模式”,这可能是一种人类对自身有所约束和超越的有效方式。
随着生态现实及文学本身的发展,生态文学中的科学性的表现也是处于演进中的,从而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在生态文学的早期阶段,科学性压倒了文学性。《寂静的春天》中,作家开篇就讲述了一个生态灾难故事,该书的英文题目为“Silent Spring”,中文世界中的“寂静”一词带有一丝静穆的意味,而翻译者很巧妙地运用了这个词,很明显带有哀悼的意味。但作家显然志不在于文学表达,或者说,这个故事只是一个引子,在全文最短的一章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接下来的十六章,卡逊都是用专业详细的数据描述了杀虫剂等化工产品的滥用对人类自身以及地球生态造成的可怕后果和严重危害,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在作品中占有压倒性的篇幅,老实说,如果读者不具备化工知识,后面的大量内容其实是无法阅读的。这是一种由“虚”到“实”的写作路径,是一个文学加科普的嫁接文本,所以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其实扮演了双重角色:作为生物学家,她冷静地用准确真实的科学数据告诉科学家同行,我们研究的这些化学品的毒性剧烈,对环境造成了可怕后果;作为文学家,她用故事的方式提醒不知情的普通民众:再不提高警觉,春天将永远是一片死寂。而且根据篇幅所占多少,很显然她的预设读者是前者,当然,也可能加上政府有关部门。所以,早期生态文学的风格是用科学数据来批判现实以引起生态警觉,在一定意义上属于“问题”文学或者说是环境文学。
二十多年后,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第一声,《伐木者,醒来》有了新的表达方式。第一章开篇用优美的文学语言描绘了一幅春天欣欣向荣的景象,中间罗列的大量的数据揭露了世界范围内,人类对自然界特别是植被的破坏。在之后的章节中,作家用焦灼的目光扫描过中国的大好河山并一再聚焦,南到海南岛、北到科尔沁,从山林到城市、从大漠到草原,用详实的数据和事例来展示中国环境遭到的严重破坏,最后回归世界和历史,用空间和时间的双重坐标来警示国人。该作品的体裁是报告文学,虚构的成分几乎没有,也符合报告文学准确真实的文体特征;同时,作者直接运用了大量准确翔实的数据和历史案例,这都体现了生态文学的科学性。《伐木者,醒来!》的潜在受众是广大公民,相比卡逊的专业冷静,徐刚在作品中直接跳出来大声疾呼,他慷慨焦灼的呼喊大大张扬了文学激情,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历史事实,成为他唤起大众生态意识的有力武器,“从新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涌现的世界图景启发一种深刻的责任感”,很显然,徐刚的写作策略是情理结合,以事实说话,最终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文学的科学性表达进入了一种新的阶段,可以用陈应松于2020年出版的生态小说《森林沉默》作为例证。相比卡逊的生物学家背景,陈应松明显具有广博的博物学和地方志相关知识的储备,森林里那些数不清的动物、植物和一些尚未被命名和认知的神秘物,它们多姿多彩又群声喧哗,被作家写成了一部相对于人类来说的他者之书,生物学科知识被巧妙自然地镶嵌进文学作品中,这说明作家生态意识的表达更加自在从容。而且,《伐木者,醒来!》和《森林沉默》虽然都是森林题材,但后者不仅仅局限于滥砍滥伐等环保主题。由于小说本身的虚构性,作者超越时空纵横捭阖地关涉了历史、社会、现实、人性、精神等诸多层面,这显示了生态文学的观照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但虚构不代表不科学,而是作家对观照对象和生态意识合理有效的艺术整合。所以,晚近的生态文学丰富了表达手法,拓展了涉及领域,构建起了科学性与人文性兼备的生态文学样式,体现了宏阔的生态文学大格局。
应该注意的是,科学性虽然是生态文学的特性之一,但也不应该过分拔高,归根到底,包括生态文学在内的文学的本质还是人学。而且科学技术本身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所追求的理性、规则和井井有条很大程度上是跟自然原本的感性、个性、鲜活相对立的,它越强势和膨胀,就越会对后者形成挤压损伤。还有应该加以注意的是,科学的产物技术本身具有时效性:“现代科学赋予我们思想的自然观念是如何地令人惶惑而迷惘。…… 科学的标准概念会不会只在一定的限度内才具有真实性,而这限度对于科学本身来讲也都嫌太狭窄了呢?”科学知识和科学话语会过时,科学观念也会持续更新,但生态科学性的最终指向不变——人类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使生态文学闪耀着恒久的科学之光,而这种“变”与“不变”也恰恰是生态文学本身科学性的体现之一。
【注释】
①②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80-81页。
③⑦⑨[日]野田研一、结城正美编:《越境之地:环境文学论序说》,于海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27页、159页。
④⑤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9页、177页。
⑥朱贻庭主编:《应用伦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页。
⑧⑫张韧:《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文学的天空:张韧文学评论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155页、158页。
⑩李敬泽:《人与自然、人民与生态——在〈十月〉生态文学论坛和〈诗刊〉自然诗歌论坛的发言》,《十月》2022年第1期。
⑪[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⑬李玫:《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⑭[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⑮[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1页。
⑯[美]欧文·拉兹洛:《布达佩斯俱乐部全球问题最新报告》,王宏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197页。
⑰[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