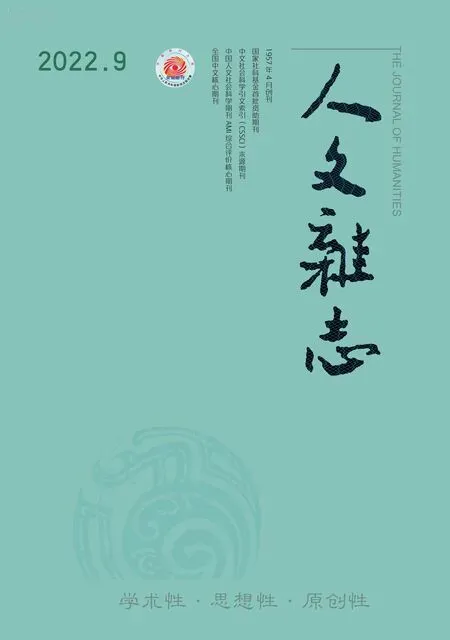论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桐城派书写及学术反思*
一百年前,桐城派遭受风雨激变。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学术争鸣浪潮的到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严词抨击桐城派,斥它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百年来,桐城派从被否定、斥责、打倒一直到新时期重新“站立”起来、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再次成为学术经典,经历了多个阶段,与多种复杂因素有关。其中,既有新文化运动对承载旧有道统的古文流派之打击,也有新时期地域文化资源开掘与复兴的追求。我们认为,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其早期研究,初步奠定了其经典化的格局。在它被激烈批判后的数十年间,以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各自的文论著作中是怎样书写桐城派的?他们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如何看待、评价桐城派的?又以怎样的角度和方法书写桐城派?其批评观点和治学方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风貌?这对当下学人之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从现有文献看,少有涉及,值得深入探究。
一、桐城派书写的整体概观及其经典化
五四至今,桐城派日益成为学界的研究载体和文化界的重要资源,依然在焕发着它顽强的、长盛不衰的生命力,虽桐城派在创作上辉煌不再,但在批评界和文化界却历久弥新。1949年之前,这一流派在被新文化运动彻底打倒后长期背上了斥责和骂名,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政治运动的卷入和主流话语的支配下,依然被否定。直到80年代后期在逐渐远离“文革”的阴影后,学界逐渐走向了风清气正的新阶段,一批桐城派研究新著相继问世,这一流派才以“正能量”资源被人关注,并逐渐得到高度肯定和广泛认同。
1908年,李详率先在《论桐城派》中分析了“桐城派”名称的来由和确立,肯定了姚鼐及其弟子在流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开启了此后数十年文论界对桐城派持续研究的先河。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勾勒桐城派的演进脉络、作家构成与派别谱系,文献翔实,但整体属于文献和考订方面的研究。而在1908—1949年四十余年间,涌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有十余部,主要的有:(1)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5)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6)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7)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8)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此外,民国阶段涌现出的中国文论选本大约有五种:许文雨《文论讲疏》、程千帆《文论要诠》、叶楚伦《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李华卿《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另外还有李长之、宗白华对桐城派的介绍、评析文章。学界已有研究,因较少论及桐城派作家,故大体可略去。从选本的体例和构成来看,许文雨选姚鼐《古文辞类纂序》为其一种,叶楚伦则探讨了“义法”观的桐城派古文理论。总之,在当时的古代文论批评史著作中,真正范围有别、程度不同、角度各异地研究桐城派,主要有陈著、罗著、朱著、方著四部。日本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也极具代表性,为海外学者书写桐城派之典范。本文所论大体以这五部民国时期的文论批评著作为基础展开。
最具影响力的几部文论批评著作均产生在20世纪20—40年代,它们在编写体例、结构和篇幅方面各有优长,均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就桐城派研究而言,它们彼此互补,共同体现了民国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桐城派研究的认识水平。由于受时代因素和著述条件的制约,如上四部本土文论著作在论析桐城派时角度、方法和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清代批评史”设诗评、词曲评、曲评、骈散文评四节,在“骈散文评”中简略论及桐城派,将其与浙东派、魏晋派、仪征派相并列,分析了此派的由来、义法之内涵,提及刘大魁的文论观点及曾国藩的中兴之功。但陈著对桐城派的发展、演进,尤其是对姚、曾及其弟子,甚至晚清桐城派等均无涉猎。
以批评家为纲建构全书的朱著,在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共76节,有5节论及桐城派主要作家如方苞、刘大魁、姚鼐、刘开、恽敬、张惠言、曾国藩等,涉及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三祖、分支阳湖派以及中兴代表曾国藩。朱东润选取“天才闳肆”“深得骈散文体之关键”的刘开论述,大约是将其作为姚门弟子之代表。虽本着“远略近详”之原则,但对曾门弟子及晚清桐城派未曾涉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民国学者书写桐城派,在视角与视野方面有可借鉴处。一方面,他们关注文学批评和学术思想、时代风气的关系。这以郭著最为突出。郭绍虞非常重视儒释道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便染上了文化的印记。郭先生在书写桐城派时,一如既往地贯彻了这一视角和理念。论桐城派之前,专设“清初之风气”,指出“我们假使不以人废言,则他的思想言论也与清代学术文艺有一些关系。清代学风重在实事求是,……”此后,他在分析桐城派成立之因素以及辨析义理考据时,皆始终紧扣清代朴学思想和传统儒家文化的渗透。而方著在研究桐城派时,首先交代清初立国崇尚和平文学的风气,选文重实用、“平正通达”,也从科举、世风方面对清初学术环境进行了揭示,从而建构了时代学术和桐城派“清真雅洁”文风之间的关联,为人们理解该核心范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民国文学理论家普遍格外重视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联。方著重视总集的时代价值和批评意义,故在论析中不能只顾“文史”(诗文评包含其中),其谓:“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他研究桐城派便常围绕方苞和姚鼐的选集(《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来展开,实现文学作品和文论思想的汇通。这种论说方式似乎有“述多论少”之嫌,但这些引文皆出自桐城派的具体作品中;有的则能侧面反映出民国文论家对作品和文论关系的深切理解。立足典籍,材料真实,民国学者的治学方式与精神值得传承。
3.3.4 田园风光规划 田园风光规划包含环境绿化、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规划要考虑地域特色、景观特色,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此外,这批学者在书写桐城派时大量运用文本细读法来评析其文论观点,提炼其批评思想,紧扣作品展开评析,使研究结论深刻、可靠。从语体建构来说,这是基于引文来谈认识进而得出结论。相比而言,当今的桐城派研究著作则以作者的阐释、分析居多,引语往往成了一种佐证,或有一定的篇幅限制。如引语过多,对作品关注过多,无疑就会冲淡书写者的分析和评论,这恰恰是不被当前学术体制认可的。但在文论草创时期,大段引文、作品展示恰恰与详尽的材料搜集以及作品的分析紧密结合。郭著成就了他在这个学科中的宗主地位。在这“阴差阳错”中我们看到他长期对文学作品的积累和对文学史的把握,为后面撰写体系庞大、材料丰赡、评析深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方著明确反对割裂二者,如“所有这些,既不是丢下文学批评史去谈文学,离了本题,也不是背弃文学而高谈文学批评史,隔靴搔痒”。批评史与文学史相结合,能使文本的细读及分析真正落到实处。
此外,汉学家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第八章设“中叶以后桐城派及其他文说”,有三大明显的特征。一是他选取包世臣和阮元作为桐城派代表,在同类型著作中不拘一格,尤其是论及阮元的骈文理论,将其视为桐城派中期文体变异(即古文和骈文实现一定程度的调和与汇通,并为刘开、曾国藩等人的文论奠基)的先声,极具眼光。二是他均衡用笔,论桐城派不求全面,而是建构章节。三是他的研究角度较独特,如论方苞反对古文使用、论刘大魁的“钝拙”论与道家关联、论曾国藩以选学调和古文等。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作家之多、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为文学史所罕见。它前后发展、延续了数百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纵观来看,桐城派经历了两次经典化,演绎了创作和批评的双重乐章。先是作为全国重要的散文流派,其经典化源于古文创作,方苞、姚鼐等大批作家创作了大量散文精品,并提出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等理论主张,奠定了它在18—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五四至今,桐城派成为学人关注和探讨的重镇,不断被阐发和研究。而这离不开民国时期文论史著作对它的多元书写,郭绍虞、朱东润等学者评析桐城派的成就与特点,功不可没,为后来学者深化、拓展研究桐城派搭建了框架、树立了范式、提供了视角,他们在共同的学术谱系中为桐城派的经典化添砖加瓦,成为学术史上桐城派经典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桐城派书写的多元探索及脉络演进
晚清民国时期,以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为代表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自幼熟读古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国学功底深厚,在文史哲等人文社科领域崭露头角,他们书写桐城派的角度、成就无疑染上了浓厚的时代印记,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治疗结束后处死小鼠,剥取肿瘤并用电子秤称取肿瘤质量,计算抑瘤率。表2示,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DDP(d4~d6)组抑瘤率最高,为53.91%,与包括单药组在内的各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31.69,P<0.001。
民国学者在书写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时,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体现的治学精神,印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学科走过百年的今天,值得学界全面总结和镜鉴。首先,他们在书写桐城派时,取材详密,并对材料充分加以挖掘、利用。学术研究是在不断发展和推进的,有着承前启后性。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在草创阶段,并没有后来繁荣阶段名目繁多的研究方法。民国时期以朱东润和郭绍虞为代表的学者,在浩如烟海的民族典籍中耙梳和提炼,从数千年文学长河中精挑细选百余位批评家作为论述对象。一方面在篇幅方面,有的材料引用占据大半,评析有时极其简约,他们以“接着说”的方式来研究,让材料来说话,显得有些“述而不作”。另一方面,在材料的广度方面,不惟取自桐城派作家本人作品,还大量取材于前后时代的各类总集,文人别集,甚至从经史子集中、从学术文化典籍中搜寻一些边角材料来论证,使其“推阐”(方孝岳语)和评析有理有据。如郭绍虞研治中国文学批评之目的在于“求真”和“实用”相结合,前者离不开对文论资料的科学整理,后者则离不开对资料的意义阐释。他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同时投入了大量精力从事《陶集考辨》《明代文人集团》《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等方面的资料整理工作,不遗余力,极其虔诚。这些辑佚、考辨工作,对其评析桐城派是大有帮助的。诚如朱自清所言:“取材范围之广,不限于诗文评,也不限于人所熟知的‘论文集要’一类书,而采用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序,笔记,论诗诗等;也不限于文学方面,郭著相信‘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联……,所以随时征引思想方面的事件。这已不止于取材而兼是方法了。”此外,搜集和整理资料,灵活运用材料,让原文说话,在朱著、方著的桐城派评析中,也格外鲜明。这也体现了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
2)给排水控制系统构建与应用过程中,若能重视PLC使用,则有利于提升该系统的智能化控制水平,还可以避免给排水管线布置出现过于复杂的现象;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相对于物证而言,人证的取得更容易而且更直接,另外受制于之前职务犯罪侦查实物性证据取证能力不足,突破人证往往是比获取物证、书证、电子证据更便捷的渠道。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几乎通用“由供到证”的取证模式,由于办案机关侦查手段的科技化水平不高以及其他因素影响,在现行保障体制下客观上难以摆脱“传讯——问供——抓人”的传统侦查模式。 [6]
在新时期国内编写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古代文论》著作、教程中,对于清代文论,多数主要提及桐城派三祖文论思想,此外一概不谈;或者将重心放在叶燮、梁启超、王国维之上,对桐城派简略带过。尽管后期桐城派在清末民初激烈的社会转型中遭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猛烈的批判,给后人的认识留下了阴影,但对于理性而客观的学者而言,还是应当公道地言说,实事求是地评析。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授课时编写讲义,率先设节来评刘开文论思想,从行文来看他将刘开与姚鼐并列还提及管同、方东树等,显然是以点带面地把刘开作为姚门弟子来重点论析的,其谓刘开“天才闳肆,光气煜爚”,“《与王子卿论骈体书》《与阮芸台论文书》两篇,深得骈体文体之关键。孟涂之文,兼通骈散,又值阮氏父子别树赤帜,欲夺古文一席之时,故力主文无所谓古今,亦无分于骈散。”朱先生一方面高度赞赏刘开的才气,另一方面将其置于中期桐城派语体发生变异(由早期的纯粹古文而排斥骈文逐渐走向通融与吸纳)的节骨眼上来论析,显示出朱先生圆融通达的学术鉴别力。刘绍谨曾称道其中不乏“一些精妙的解析、一些富有穿透力的识见”,这与郭绍虞近似。朱东润论侯方域之才与法,论袁枚、曾国藩对骈散之态度,论桐城派分支阳湖派与其文风的差异等,都显示出民国学者独到的见识。
单就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体例结构来看,他们研究桐城派也能体现出一种独到的眼光。朱著贯穿始终地以桐城派人物为纲,便于具体分析每个文论家的批评活动和文学思想,“在对具体批评家的论述中也注意到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特点和自身规律这些宏观问题的揭示,使读者并不感到这是一串串单个批评家的排列和堆积”。基于此,他在民国时期同类著作中,敢于大胆地展示桐城派批评家的整体面貌,而方著“立片言以居要”,始终兼顾方苞的经学家身份,并不忽视中国文学批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一民族特征,凝练精要地论析桐城派“义法”的内涵,以及对“雅洁”文风的孜孜以求。
在研究桐城派过程中,民国学者对有的人物或现象不过分拔高,也不含糊其词,而是直接下断语,颇为果敢。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从道家角度论析刘大魁文论思想,别开生面,具有创见。他写道:“他的思想之中,看来确实潜伏着庄子的影响。这一点与其师方苞坚持儒教思想的文说大异其趣,他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宣扬‘载道’说。”方著侧重于论析个人的心得,其曰:“通观全书,每一论断都是从自己心得中来,即使论点并非他人所无,体会和论证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民国时期批评史桐城派书写论著中,除郭著、朱著外,其余都比较简约。民国学者、文论家书写桐城派,善于抓住关键问题,突显要害。在学科拓荒阶段,为批评史的桐城派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桐城派书写而言,五部著作中均不约而同地深入剖析“义法”这一总纲。郭著以“前驱”(渊源与奠基)、“文派”(三祖及门人)、“羽翼”与“旁支”建构了其发展演进史,抓住关键人物,以主带次,点面结合展开论述。在论及“桐城派之旁支”时,更是以关键问题——而非论著名称、人物名称——作为标目,如“文统”“本末条贯”“文学大旨”“论文大旨”“用字与行气”。方著在标目上以人物、书籍、专题相结合,如“清初的清真雅洁的标准和方望溪的义法论”。相比当今同类著作多以人名、流派名或朝代名作为书写标目,民国学者抓住关键问题展开评析的意识,是相当强烈的。这既有助于在纷乱中集中精力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避免陷入作品和材料的海洋中不能自拔。
报道说,金正恩夫妇提前在机场迎候。军乐队、仪仗队和市民为文在寅举行了机场欢送仪式。7点30分左右,文在寅与金正恩一道乘车前往白头山将军峰。若天气良好,他们将在下山途中经过天池。文在寅结束登山后,将从三池渊机场乘机回国。
在台北迎接跨年,有很多民众涌上街头,看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的免费的跨年演唱会;在101大楼周围的大街小巷穿梭逛夜景,品尝夜市香飘四溢的小吃;在街头看艺人的花式表演……这一切,都是为了等待101大楼的烟火秀和新年的到来。
三、桐城派书写的学术方法及当代反思
通观民国时期数部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基本上在桐城派退出历史舞台后十多年,建构起了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框架,厘清了其渊源关系、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虽然每部著作在书写桐城派时都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明显的不足,但综合来看它们取长补短,共同奠定了桐城派研究的基本格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代学者对它展开深入研究做出了必要铺垫,尤其为当代学人不断完善桐城派的师承图谱、分支关联、发展脉络、传播路径等夯实了基础。我们认为,民国文论家奠定桐城派研究格局,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阐发桐城派命名的缘由,描绘该流派的总体特征。李详在1908年《论桐城派》中率先指出桐城派得以成为流派的原因。青木正儿认为方苞开创文法后,其门人、同乡刘大魁传承衣钵,最终形成乾嘉年间蔓延极广的流派,谓之桐城派。二是揭示了桐城派数代作家之间的师承关系。朱著、郭著、方著以详细的史料揭示了桐城派早期三祖及其后学围绕古文创作形成了代继相传的密切关系,虽对晚清桐城派关注不多,但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曾国藩及其弟子群与中期桐城派的关联。其研究共同揭示了桐城派横跨清代数百年的图谱,尽管是初步的,在详细和全面上不及民国时期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三是初步探究了桐城派作为古文流派得以成立和兴盛的各种因素。郭著从学术品格、清代的学术流变、共同文学主张的确立等多个维度,分析了桐城派立派成因。这为后来众多论著(如《桐城派学术文化》下编第一章“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派文派述论》第一、二章等)纷纷从学术传统、地理空间、社会历史、文学因素等角度全面深入剖析桐城派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打下了基础。郭著中对命名缘由亦有揭示。四是从发展和变异角度研究桐城派与阳湖派、湘乡派的关联。青木正儿用一节评析“恽敬(阳湖派)”看似和前一节论桐城派“三祖”并列,但具体论析中透露出与桐城派古文创作既有关联又另创派别的念头;郭著则辟专节深入论析阳湖派和湘乡派,并明确视其为“桐城派的旁支”。总之,民国文论著作研究桐城派在中后期的变化、扩大和蔓延方面,也为后人继续探究它们之间的关联打下了基础。五是论析中透露出桐城派有文派、经派、诗派之别,体现出该流派巨大的包容性,酝酿着巨大的研究空间。近30年来从经学、史学、诗学、教育学等多个维度研究这一流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民国文论家在采用纵横比较来定位和书写桐城派方面,亦较为鲜明。如方著中,评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时为彰显其特色,与此前经典的选本相比较:“惜抱有建立广大门庭的意思,论诗则熔铸唐宋(《惜抱尺牍》里《与鲍双五札》),论文论学也有兼人之志。”“《古文辞类纂》也是志在兼济,所以把昭明《文选》里汉魏的辞赋差不多全数收进去了。在他心中,似乎以为文章的内容,也应该参酌汉赋那种气魄和笔势,然后才能尽文家之能事。”姚鼐选本的特色一目了然,论及诗与文、骈文与古文的差异时,也是在比较中突显了两种文体各自的特征。郭著在研究桐城派时,一方面将桐城派文论置于文论发展史中与此前纵向对比,另一方面将同类型或近似时代的文论家进行横向对比。如引方东树之言:“他于《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一文称方深于学,刘优于才,而姚尤以识称;称方文静重博厚象地之德,刘文风云变态象天之德,姚文净洁精微象人之德,于是此三家遂若鼎足之不可废一。”就将三祖文风与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又如论三祖道:“他可以说是方、姚之间的联系。方重在道,刘重在文,而姚则兼擅其袭;方局于唐、宋,刘出入诸子,而姚亦兼取其长。”对于桐城派名家有怎样的特点、不同乃至推进,他大多是在横向比较中完成。再如论袁枚和桐城之别:“明白这一点,然后再知道随园为文,所以与桐城不同之故。他正因为要吃得住大题目,所以尚奇峭而不尚平钝,主宗唐而不言法宋。……这可谓与桐城派的论调一样。然而其切入点不同,桐城由时文入,而随园则最反对功令之文(见《与俌之秀才第二书》);其归宿又不同,随园兼取六朝骈俪,而桐城则只尚散行而远绝骈偶(见梅曾亮《管异之文集书后》)。”正是在鲜明对比中看出袁枚诗学的特色。又如,论及恽敬诗学的特色时说:“他要比桐城有些枪棓气,比侯、魏有些袍袖气。他要于粗豪中带些学养,学养中又足于气势。醇中见肆,肆中有醇,这才是他的理想。”再如青木正儿将曾、欧比较,道出了曾国藩之功绩和不足,他论曾国藩与包世臣对骈体的态度,也是通过比较揭示出来的。总之,比较能突显各自特色,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这需要研究者慧眼识珠、前后贯通,具有很好的识见与功力。
郭著在下册“第四编 清代(上)”中,用了约98页畅谈桐城派,篇幅之长、容量之大、论述之细密、阐发之精微,在当时的同类著作中首屈一指。这也为其后的桐城派评价和研究奠定了框架。郭绍虞在“第二章 古文家之文论”中论及桐城派的前驱——侯方域、魏禧、魏际瑞、汪琬,在第二节中紧密围绕桐城三祖及姚门弟子论析其文论观点,做了系统耙梳,紧接着设“桐城派的羽翼”论袁枚、尚镕、吴敏树等文论家,设“桐城派之旁支”论析阳湖派的恽敬和湘乡派的曾国藩,基本明确了桐城派从早期产生、中期繁荣、后期变异的几个关键阶段,勾勒出流派的发展脉络。尽管如此,郭著在该编末尾一段写道:“如张裕钊、吴汝纶诸人之论文,大率不外于姚、曾诸氏的见解,桐城文派到了清季,乃真日渐衰歇了。”郭绍虞对曾门弟子群以及清末桐城派(如严复、林纾和姚永朴等人)没有展开。显然,他将评析和研究的重心放在19世纪中叶以前。
方著在下卷第42章中重点论及方苞“义法论”及与清代“清真雅洁”的文风。他在此标目下重点论及姚鼐的选本思想、梅增亮对骈散文的看法,以较多的篇幅对方苞上承《左传》《史记》进而及于六经的古文脉络进行了仔细钩沉,对他的选本批评实践体现儒家道德精髓等多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显然属于“内行”的主观洞见。方著对于桐城派前后人物的关联做了交代,但非常简略,对于曾门及其后学亦未涉及,对于桐城派的枝叶、余晖则数语带过。因此,该流派很多重要的文论家及其文艺思想也被遗落了。
四、桐城派书写的突出特征及学术反思
一代学者研究的风格、特色和成就,与其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民国学人书写桐城派,是在该流派刚遭受新文化运动健将猛烈炮轰后不久,是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占据意识形态高地之前,是在各种政治运动尚未影响学者们的价值观念之前,也是在各种新的研究工具大量使用之前,更是在各种研究资料汇编和整理全面展开之前。在这一段历史的夹缝中,其桐城派研究和书写体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风格,他们整理桐城派资料、评析桐城派文论,引发很多话题,这些都值得后人思考和总结。
这批学者书写桐城派有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鲜明印记。民国间大批研治古代文论的学者,自幼或传承家学,或在私塾里受到较好的国学教育,都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而在成长过程中又遇上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成为社会主导的官方书面语,受其影响,所以他们的学术著作的语言游走于文言和白话之间,表达介乎古典和现代之间。用文言而不晦涩,用白话而不俗气。如朱东润论阳湖派曰:“皋文持论,如《七十家赋目录序》等,皆有条贯,然其《词选》之作,开常州一派,尤为其成功之大者。”“皋文之说,欲逆挽颓波,返诸寄托,此为《词选》成书之中心思想,故其叙云:……”“皋文论词,创为寄托之说,立论甚高,而案之事实,不能尽当,故止庵创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之说以救之。”郭著也是随处可见的半文半白式表达,如“古人自视甚高,不可谓妄;古人称许甚靳,也不可谓陋。……所以宗派之建立,原不必非难;不过宗派既立,途辙归一,末学无识,竞相附和,当然也不能无流弊”。“由这一点言,必须如古文家之体玩,才可以窥道,必须由学文的方式,才能得古人之精神。”1927年出版的陈著文言气息更浓厚,如“夫桐城派之文,虽不足邵;然其清洁雅正,足江湖叫嚣之习,其功亦何可尽没哉?”类似的语言风格在几部著作中大量涌现,体现出民国学者对古典语体风格的自觉传承。
民国文论家书写桐城派普遍基于讲义而不断修订、完善,其精益求精的精神难能可贵。民国期间出版的几部文论著作,其共同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被多次印刷,并被舒芜、章培恒、陈尚君等名家导读或评析,成为民国学术经典而广为传播。对其进行评论和反思,也成为国内多种学术史著作中“逃不过”的章节。这固然与这批著作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形成有关,也与这批著作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有关。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它们走向经典还与著者不断打磨及修订有关。除罗根泽早逝而未完成元明清文论外,其余著者都年事较高,他们在有生之年不断打磨和完善其著作,包括对桐城派部分章节的校修乃至重写,从而缔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这尤以郭著为突出代表。
此外,民国文论家书写桐城派体现出对学术个性、学术独创的极力推崇。他们在书写桐城派时表现出对文人创造力的推崇及个性的激赏。这似乎与民国文人本身的气质特性有契合之处,也与他们书写古人勤勉用力、常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有关。如朱著以引文表达了自己对桐城三祖的态度:“方东树《昭昧詹言》亦云:‘愚尝论方刘姚三家,得才学识之一,望溪之学,海峰之才,惜翁之识,使能合之,则直与韩欧并辔矣。’二人之言,于方、刘、姚间,品评略当。”朱先生的态度和看法就很鲜明。所谓“才”“学”“识”,不仅概括准确,也表达了朱先生的钦佩之情。再看其引王先谦语论曾国藩曰:“曾文正以雄直之气,宏肆之识,发文章,冠绝古今,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謦欬不亲,而涂迹并合。”称赞曾国藩有雄直之气,并对其在桐城派中兴期融通文道、强化经济的作为深表赞同。无论是从引文还是从评析来看,朱东润在选本中增加“叙记”“典志”的见识、认同骈体文、提炼“雄志怪丽、澹远茹雅”的古文风格,都体现出他对独创——善于创造并能形成独特风格——的学术喜好。
至于对停在路边未上锁的车上私锁的行为,笔者认为同样构成侵占罪。理由在于停在路边未上锁的车属于遗忘物,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别在于遗忘物是由于财物的所有人、持有人的疏忽,或者遗忘而暂时失去占有、控制的财物。其特点是遗忘的时间短,遗忘物依然处于失主可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失主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将会很快恢复对该物的控制。在共享单车停在路边未上锁的情况下,共享单车公司还能够通过电子锁对其进行定位,但是由于其未上锁,因此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下,可以认为其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但当再关上锁时,就可回复到一种完全的占有状态。
郭绍虞高度称赞曾国藩文论的创见,体现出著者对创造力的充分肯定。他批评桐城派后期过于讲求严格标准而丧失活力,他论道:“大抵立法愈严,则标准愈简化。标准一简化,则一般庸才,全可以藏在这简化的标准之下以高自位置,以深自掩护。桐城派之所由成立在是,而其末流之病也在是。”其鲜明的态度也流露出对后期桐城派缺乏创造力的无限遗憾。再看郭先生论阳湖派:“阳湖文人的作风,不惟与桐城异趋,正可以药桐城文平钝之敝;我们须知桐城派的功臣,原不必是拘守桐城义法的文人。”他肯定了遵守义法而不死板,指出至阳湖派又有新变,这是对文化创造的肯定。方著论析桐城派批评家言简意赅,似乎留有余地,他格外看重批评家的贡献和创新。因而他在评析方苞之后的姚鼐、梅曾亮、方东树等桐城派文论家时,都力求凝练地揭示其独特之处。此外,民国学者研究、书写桐城派还体现出多种学术方法和视野的融合,也注重相对纯粹地治学,如“论从史出”而不过多地受政治运动牵连;重视探索文学批评的规律,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方位挖掘,通过文学批评促使读者读史书、读典籍,这些都值得当今继续继承和弘扬。
民国时期的几部文论著作写成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创阶段,在桐城派书写方面多有创获,为后来学者沿着其道路继续深入开拓打下了基础。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年年有新变,代代有高峰。站在当今的学术发展史上重新审视民国学者的桐城派书写,我们发现其研究在资料局限和认识程度的制约下,也呈现出诸多的不足,存在诸多的缺憾。比如他们对桐城派的书写、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还不是很全面。他们建构了桐城派书写的主要框架与方法、勾勒了桐城派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发展阶段,分析了前后的师承及代表性观点,但大多论到中兴期的曾国藩即止,对曾门弟子群以及末期桐城派鲜有分析。这在学科史的建构中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像朱著本着“略古详近”的原则,“本书的叙述特别注重近代批评家”(“自序”),然对姚永朴兄弟、吴汝纶、严复等后期桐城派古文家、文论家则只字未提。以厚重和翔实著称的郭著,对曾国藩以后的桐城派文论也未展开论述。又如民国期间这批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总体上以材料的搜集和引用取胜,在具体评析中不时地体现出真知灼见,但总体上呈现出“述而不作”之特点,甚至缺少必要的理论阐发,更遑谈深入、全面和系统。如方著引用戴钧衡评方苞的话用了八行,便以“这几句话,可以说明望溪在古文家里面的立场”收束。从今天的论述条件来看,阐发显然还不够充分。如朱著曰“今不赘。曾国藩之言阴阳刚柔,本于惜抱,略录其说如次:……”,接着是两段近20行的引文,引文结束后也毫无分析,只是用数百字印证“阴阳刚柔”论与姚鼐的承续关系。类似之处比比皆是。笔者所举绝非偶然性地断章取义,在国内的四部著作中材料的密集引用中穿插著者评析的特点较为明显。这体现出学术发展早期对相关问题研究尚不够精专和深入,这是当时很多著作的普遍情况。青木正儿的桐城派研究相对论多述简一些。因此,民国学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总体而言,不同于当前学术语体和研究特征,“述”多“作”少,阐发力度还有待加强。基于这种原因,它们目前基本上作为批评史研究者的参考书,鲜有高校将其作为教材使用。尽管如此,时过境迁,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民国学者,毕竟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局限,他们在烽火岁月完成了那代人的学术使命,其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功不可磨灭。如何有效地处理“述”和“作”的平衡关系,也是需要分寸的。再如民国文论家的桐城派书写中,部分观点也有待商榷。如方著反对方苞融通时文和古文,殊不知在阐发其“义法”观时标准过严,对方苞的身份处境以及当时古文传播路径的阐释是有一些问题的。此外,把与桐城派差异极大的尚镕纳入桐城派之羽翼,也还值得商榷。
桐城派在当今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受到研究明清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艺术学、史学、经学乃至地域文学、教育学、传统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学者们高度关注,也得到安徽省和桐城市政府的积极响应。数十年来也涌现出了不少精品力作,成就斐然。自古以来,学术研究在薪火相传中不断前进并发扬光大。民国时期的著名文论家博古通今,视野开阔,他们以扎实的材料功夫从事桐城派研究,无疑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研究、书写桐城派的内容、角度、方法等值得今人重新审视,他们的研究特点、研究得失等尚可做进一步思考,这将会给当前桐城派研究提供更多的学术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