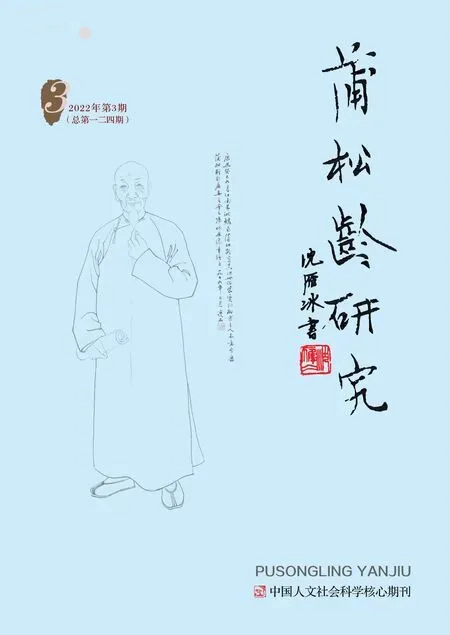结构神话学视域下的《聊斋志异》创作动因探究
——以《白于玉》的深层结构与潜在思想为例
张姣婧
(北京交通大学 文化教育中心,北京 100091)
一、结构神话学对《聊斋志异》文本研究的适用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了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为后世的神话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借鉴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参照其对语言现象所作的“言语”与“语言”的区分,将神话现象划分为“神话言语”与“神话语言”两部分。前者是历时性的、不断变化的、表象的神话叙事,后者则是共时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层的神话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探索即是通过“神话言语”所反映出的历时叙事来探究“神话语言”的结构,以此揭示神话背后人类无意识的,亦或可称其为潜意识里的思维方式。
在具体对神话结构进行分析时,列维-斯特劳斯首先将神话文本中的事件按出现的先后次序加以排列,而后观察总结出这些事件的含义,将表意相同的事件归为同一序列,每一序列由此形成一个关系束,亦称“神话素”。在同一神话中,通常会存在两两之间相互对立的神话素,而不同对立组合中的神话素在内部构成矛盾的同时,亦能够与本组合外其他组合中的神话素构成转换关系,如此既矛盾又可转换的关系,即为该神话的深层结构。结合神话的具体背景对其深层结构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出潜藏在文本表象背后的个中深意,而这番深意并非神话叙述者的有意设置,而是其自身尚未能察觉到的潜意识的表征。
由此可见,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是挖掘神话文本背后无意识因素的强有力的理论工具。那么,倘若借此工具来探究具有神话意味的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譬如清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否可行并存在其特殊的价值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就研究对象而言,《聊斋志异》为志怪之作,其所叙花妖狐鬼、佛道仙魔的故事,在描述的内容与想象性的构思方面皆与神话具有高度的共通性。而若谈及原始神话与《聊斋志异》的时间距离,诚如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告诉人们的那样:“原始人不仅具有未驯化的野性思维,还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在思维的层级与深度方面,原始人与现代人并无二致,二者的差异仅表现在思维对象的不同上而已。”故神话与《聊斋志异》的时间距离问题并不能够妨碍我们以神话结构分析的方法来阐释《聊斋志异》文本的深层结构。而最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的应用,可以将《聊斋志异》的文学意涵研究从表象的主题阐释,即探究作者有意而为之事转向至开掘作者创作时的潜意识,发现其书写文本的深层动机。由此可为更深广地理解小说作品诞生的原因,认知作家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模式,提供传统研究所未能带来的助益。
目前学界以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法研究《聊斋志异》文本的仅有陈然兴的《列维-斯特劳斯与意识形态批评——以〈聊斋志异·乐仲〉为案例的分析》与贾舒的《母职下的悲剧——〈婴宁〉的结构主义分析》两篇论文,二者揭示出了《乐仲》与《婴宁》的深层结构,在理论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然其对小说深层意涵的解读尚未能触及直接关涉蒲松龄个人情况的潜意识领域,不失为一种遗憾。依目前的研究状况可知,《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大量未被深入开掘的文本,且尚未出现以神话结构分析法来探求作家个性化思想状态的尝试,如此皆为相关研究的进行提供了充足的开拓空间。
本文将以《聊斋志异》的《白于玉》为研究对象,借助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方法,发掘出文本的深层结构,并从中揭示出蒲松龄的创作动因,为该篇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聊斋志异·白于玉》的深层结构
《白于玉》是《聊斋志异》中一篇讲述凡人在遇仙后放弃世俗生活,修道成仙的故事。小说主人公吴青庵颇具才华,葛太史对其赏识有加,想要在其高中时将女儿嫁给他。吴青庵在初次科举中未能得志,于是请求葛太史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备考期间,吴青庵与仙人白于玉偶遇,二人情谊甚笃,吴青庵向白于玉表达了他对美色的喜好。白于玉离开后,一天吴青庵在梦中与之相见,被其引入广寒宫。吴青庵在与宫中众仙女把酒言欢时看上了紫衣仙女,于是,在白于玉的撮合下与之同眠,并向其索要了金钏为赠。一觉醒来后,紫衣仙女消失不见,而金钏仍在。数日后,紫衣仙女再入吴青庵之梦,将孩儿吴梦仙送来后,彻底消失不见。吴青庵告诉葛太史自己要去学仙,难赴前约。葛太史的女儿葛琳不同意,硬是嫁给了吴青庵。吴青庵为学仙离家,葛琳抚养吴梦仙长大。长大后的吴梦仙开始寻找父亲,在途中偶遇道人,托其带信给母亲,并以金钏为报。葛琳告诉梦仙,道人就是其父。葛琳于信中得一长生药丸,与父亲分食,二人皆变年轻。后城中大火,金钏飞升于空,保得一家人平安无事。
从表面上看,小说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否定欲望、离俗求仙的思想倾向,然而吴青庵求仙的原因与对美色的极度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其成仙之后,俗世里的家人仍牵绊其心。仙与俗的此番纠葛让我们很难说绝俗弃欲即为小说的主题思想。此外,小说中的葛琳为何在吴青庵单方面背弃约定的情况下,硬要嫁给一个即将离家不归的男人,且心甘情愿地将别人的孩子视为己出,抚养成人?紫衣仙女在将孩子送给吴青庵时曾言有缘再会,然而却彻底放弃了孩子,亦不知其此后是否又与吴青庵相会。凡此种种,让我们很难断定此篇小说的核心主题。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无主题或多主题的小说,亦或蒲松龄不过是在叙述一件波澜丛生的奇闻异事。然而,蒲松龄何以书写上述的若干细节,那些令读者难解的情节设置是蒲松龄的疏漏还是故意的留白?抑或是其无意识的书写?若后一种猜想成立,那么这些看似纷杂的文本细节背后所指向的无意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若要探究这一问题,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法找到《白于玉》文本的深层结构。
依照神话结构分析法,我们将《白于玉》的全部细节加以重新整合,得出以下四组神话素,其中每组神话素内部的不同情节具有相同的意义指向:
(A)吴青庵遇仙,言己好色;吴青庵梦中与众仙女把酒言欢;吴青庵与紫衣仙女同眠,得金钏为赠;葛琳执意嫁给吴青庵。(B)吴青庵欲要学仙,背弃前约;吴青庵为学仙离家。(C)葛太史欲将女儿嫁给吴青庵;吴青庵不得志,请求葛太史再给他一次机会;紫衣仙女将孩儿梦仙送到吴青庵身边,而后失去音信;吴梦仙长大后寻找父亲;吴梦仙遇到父亲,得到长生药丸;葛琳与父亲葛太史分食药丸,二人皆变年轻。(D)葛琳抚养吴梦仙长大;紫衣仙女所赠金钏在大火中飞升,保得一家人平安无事。
在(A)组情节中,所有的事件皆指向对人的欲望的肯定,而(B)组情节则恰恰相反,学仙与离家都意味着对世俗欲望的节制与否定,与(A)组构成矛盾关系。而在(C)组中,葛太史对女儿婚姻的主宰,吴青庵对他的请求皆反映出了父亲的重要权威。紫衣仙女将孩子托付给吴青庵,孩子长大后寻父,父亲给家庭以帮助,葛琳又将珍贵的药丸第一时间献给葛太史,凡此皆表现出了对父亲权威的高度肯定。与(C)组相反,在(D)组中,吴梦仙被父亲丢下由母亲抚养,父亲的缺位使其权威被弱化。而最终保护一家人平安的是紫衣仙女的赠物,吴青庵在此最多只起到传递金钏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在此情节中,母亲的力量要远大于父亲,实为对父亲权威的否定。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小说文本结构中的两组矛盾关系,即肯定欲望———否定欲望,肯定父亲权威——否定父亲权威。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探究上述矛盾关系中更为深层的关系。由于(A)组情节与(B)组情节皆涉及人性本能的欲望,故二者在矛盾中仍存在共性。同理,(C)组情节与(D)组情节都有关父亲权威,关涉到社会伦理的规范。此外,(A)组情节对符合人本性的欲望加以肯定,而(D)组情节否定了父亲的权威,即在试图挑战与瓦解现有的社会规范,由此走向的是不被规约所束缚的自然状态。两组情节形成了同属“自然”领域的关系范畴,而因二者具有相同的归属,故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同理,在(B)组情节中,对欲望的否定意味着对自然天性的压制,对父亲权威的肯定则是对社会规约的强化,二者皆属“文化”范畴,可互相转换,且又与同属“自然”范畴的(A)组与(D)组情节构成了一组矛盾关系。
如此,《白于玉》文本的深层结构可表现为如下矛盾与转换关系的组合:
(一)矛盾关系:肯定欲望(A)——否定欲望(B)
肯定父亲权威(C)——否定父亲权威(D)
自然(A)(D)——文化(B)(C)
(二)转换关系:肯定欲望(A)——否定父亲权威(D)
否定欲望(B)——肯定父亲权威(C)
人性本能(A)(B)——伦理规范(C)(D)
不难发现,一个看似简单的弃俗求仙故事的背后实际上融合了多种潜在的矛盾与可转换因素,构成了足以反映蒲松龄潜意识的深层结构。那么,此结构向我们揭示出了蒲松龄怎样的潜在心路,具有何种深隐意涵呢?
三、潜意识里的自我疗伤——《白于玉》的创作动因
《白于玉》故事的表层叙事思想指向对俗世的背弃与对成仙的追寻,而由其深层结构可知,在表象化的否定欲望背后,强化父亲的权威,即男子在家庭生活中的绝对性地位是蒲松龄在文本书写时所流露出的潜在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具有充分的现实与情理依据。

在蒲松龄的潜意识之中,他渴望能够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家长权威,得到家人与自我的认同。然而,面对事与愿违的现状,他力不从心,只能通过文学创作来消磨心中的苦闷。《白于玉》这篇小说的书写看似只是在记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然而,透过其文本的深层结构,我们却发现这是蒲松龄在宣泄被压抑的情感,一展心头的“孤愤”,甚至是在进行自我疗伤的创作。换言之,写故事不是蒲松龄的根本动机,通过写故事来满足自我的内心诉求才是其创作的原动力。而这也恰恰反映出了蒲松龄何以始终满怀激情、笔耕不辍地撰写近五百篇聊斋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此,我们再来看文本中若干看似不合常理的细节,便会发现那些所谓的不合理的背后,皆存在着关于欲望与父亲权威的共同指向。也就是说,小说所有的细节皆为蒲松龄在其潜意识支配下的创作,那些看似错杂的文本表征下隐藏着的其实是蒲松龄深层的心理诉求,只要能够准确发掘文本的深层结构,所有字面上的疑惑就皆可因蒲松龄潜意识地浮现而不攻自破。
结语
在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时,我们往往会将小说情节中那些看似散乱、不合常理的情节置之一旁,或美其名曰这是作者的“多主题”或“无主题”设置,从而陷入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作家所思所想的尴尬境遇之中。然而,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分析法的有效借用,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窥见隐藏在小说文本背后的作家的潜意识,进而由之把握作家的创作动机与文本的思想意涵。本文对《白于玉》的分析即为借助结构神话学的理论工具来解析蒲松龄创作动因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这一理论的确可帮助我们开掘到一方表层分析所无法到达的领域。笔者认为,若能将此方法进一步运用到对《聊斋志异》里看似头绪纷杂或不易解析的篇目,乃至其他类似的古代小说的研究之中,或可对深入理解作家思想与文本意涵产生意想不到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