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路上无法倒退
文/弦月 图/松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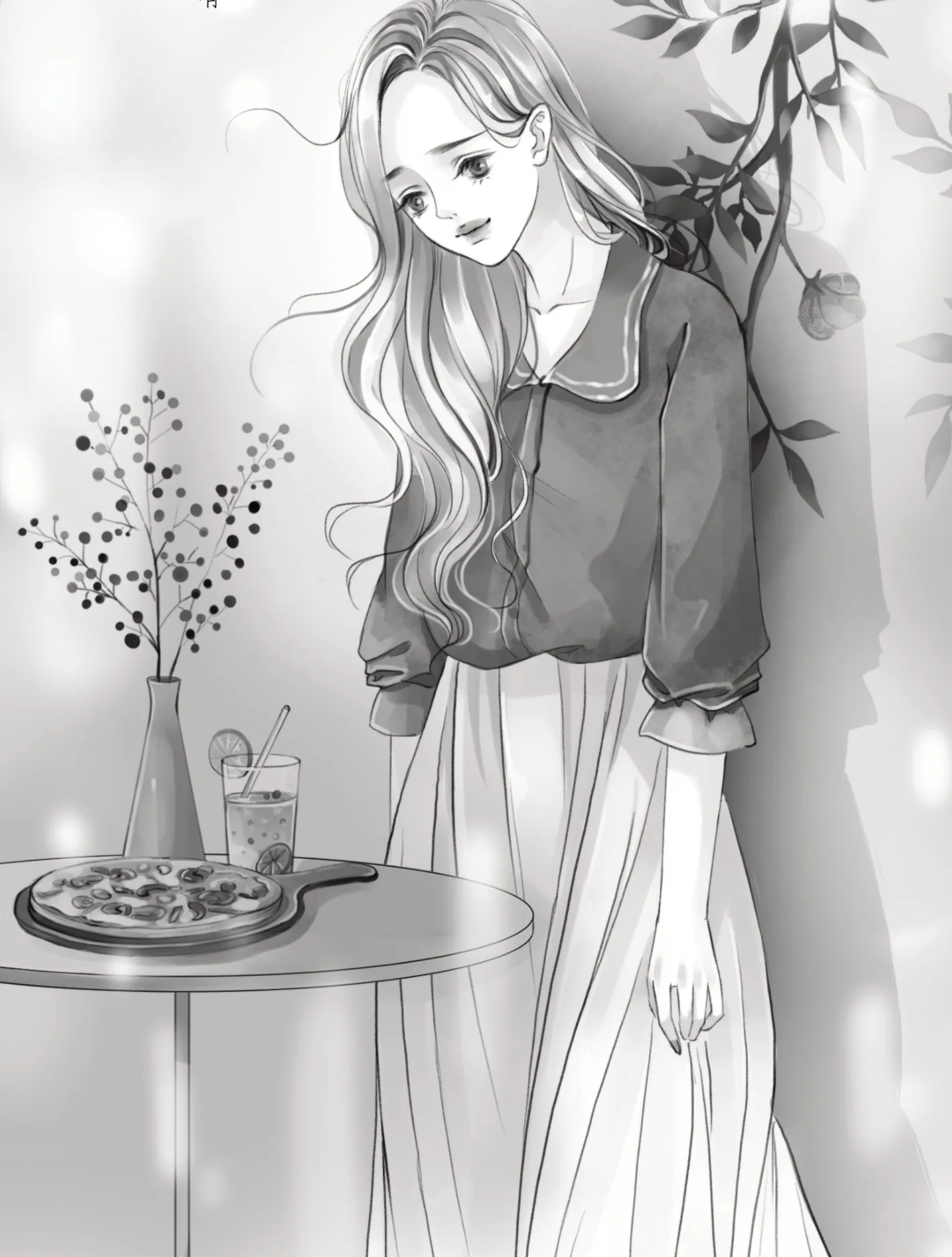
零
金色之下,他的眼中有河山,有落日,有我。我多希望如此。
当夕阳火红,斜晖朦胧。当微风送晚,莲荷微茫。我想舌蕾还余西瓜冰凉的香甜,于残温中麻木神经。看火红的车轮潜入西边云层,西南方残留绯云的天空亮起维纳斯的光辉。不知在这世间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光景。
一
他赴往日本留学那年不过十七岁,年纪轻轻的他已是名誉满身,而那时的我对荣誉一无所知,对珍惜毫无概念,以至他在我眼中那样普通,普通到不过是一个仅长我六岁、很会逗我开心的领家哥哥而已。若实在要将当年的不识泰山归罪,我会毫不犹豫、也只能让当时年少背锅。毕竟他离开那年,我不过十一岁。
年纪小是最好的托辞,也是最体面的借口。因为年幼,可以在滑雪场摔倒时,不顾旁人的眼光扑到他怀里抹泪,感受他取下手套的手轻抚我发丝,听他温柔地安慰我别哭,说等会儿一起去吃水果披萨。
最后一次与他吃水果披萨,是在他出国前一天,那日立春,元宵还未过。当我同往年一样与他说着元宵节的活动,他白皙干净的脸上笑容凝滞几秒,待我说完,他向我道歉,带笑的声音温柔依旧,更像是在说着玩笑,他说:“今年不能陪你过元宵了。”
霎时我耳边一阵嗡嗡地响,嗡嗡声渐渐盖住店内其他客人的谈笑,渐渐盖住店内播放的钢琴曲。嗡嗡声在耳畔回响,使得大脑蓦地沉重,使得一切都不真实得像是在梦里。我多希望是在梦里,多希望嗡嗡声将他的声音也盖住。我想,也许那样,他便不会说话。但他的声音那样清晰,他说他马上出国,明天早上的飞机。
不知为何,我的心脏骤然一停,仿佛与他是永别,仿佛他这一走,我们便再不会相见。我第一次那样小心翼翼问他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小心得像是我犯了错,祈求他不要生气。他看着我,眸光温柔,其中流露出的情绪却很复杂。
我想,当时我看上去一定悲伤极了,若不然他的眸中不会流露出怜惜,那双戴着一次性手套的右手也不会试图抬起。我确信,若当时我们没有在店里吃披萨,当时他的双手没有戴沾上油的手套,他没有坐我对面,他定会如以往每一次一样,抬起右手摸摸我的脑袋,笑如午阳灿灿,柔若南风熏熏。
我想,定是因当时我们在吃披萨,他戴了手套,他坐我对面,所以他在与我对视良久之后才回答,却只答说不知道。
“那我能去找你吗?”我期待着什么,但我不知自己在期待什么。
他明显一怔,而后轻松地笑笑,反问我:“找我做什么?”
“嗯……”我认真思考,答得也认真,“找你吃紫米饭团!”
他笑了。十七岁的少年,笑容那样干净,那样纯粹。
即使初春的风依旧冷冽,天空阴沉得似要飘下雪花,街头人群依旧熙攘,汽车鸣笛也偶尔聒噪,但与他漫步回家,我只觉得城市的一切都格外温柔。
次日我难得早起,只为与他去机场,共他走过我们不知何时才有的重逢之前的最后一段路。但当我出了庭院,看见邻家灯火通明,衣冠楚楚的中年男人将行李箱放进停在路边古铜双头欧式庭院灯下的黑色轿车,我前进的脚步蓦然变得沉重,最终迈不出步子向他走去,只远远看着他。
清晨的风格外凉,似刀子割得我的脸生疼。雪越下越大,我的视野越来越模糊。我多想上前几步,向他说声再见,但我第一次发现我是那样胆小,甚至不敢向他挥手。
我在怕什么?怕这一别便再也不会见面?
当视野模糊得眼前只剩白茫茫一片,两行湿润的温热顺着我的脸颊滑下,回神发现自己已然落泪时,有人替我擦去了泪水。而俯身替我擦去泪水的,正是我不敢上前去道别的他。
“哭什么?”他指腹柔软温暖,如他的微笑令人舒心,“太冷了?”
我想回答,却如鲠在喉。
他轻笑两声,以认真温柔的口吻说着明显给我台阶下的话语:“出来做什么,都冻哭了。”
我没有回答,听他说他要去机场了,鼻头又是一酸,第一次觉得眼泪是如此易落的东西。
他不厌其烦地用指腹轻轻为我擦不住下落的泪,柔声安慰我别哭,说下次见面请我吃水果披萨。不知是水果披萨安慰住了年少的我,还是下次见面,我蓦地将眼泪止在眼眶里,湿眼看他,却得寸进尺说还要紫米饭团。
他爽快答应,便要转身,我鼓起勇气伸手拉住他白色羽绒服的衣摆,对上他低下的目光,支吾地说着并不擅长的道别:“就是……你在别的国家……要照顾好自己。”
“好,我会照顾好自己。小学生也是,要好好的。” 他抬起右手,轻轻摸摸我的短发,停顿片刻,又作出恍然的模样,笑容泛着苦涩,他说,“开学就是初中生了。”
我怯怯抬手,僵硬地向他说着再见,他笑容始终温雅,带着安慰的口吻柔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再见。”
他转身往那辆黑色房车走去,高挑的身影在风雪中显得格外清瘦。
少时的离别总带着感伤,而那感伤,却最易被时光消抹。我记得我们会有下次见面,这是承诺亦是约定,但我忘了,初春的风雪易逝,也易带失那所谓承诺。
二
当六年时光转瞬即逝,我到了当初他离开时的年纪——十七岁。步入高三正临高考这样的人生大事,也是最该安分守己、做一个乖学生的时候,我心里却莫名升起了十几年都未有过的逆反。
“我不想高考,不想上大学。”又一次旷课回家,我抱着心底最后一丝愧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试图得到素来庄严却温柔的母亲的支持。那时的我,已然忘记先前六年一直支撑着我保持名列前茅的、能被称为信仰的东西——与他再见。
“理由?”母亲问。
“没意思。”我拉过身后的枕头抱在怀里,抱怨着每天累得要死要活,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累。那时的我觉得,就算没考上一所好大学,对我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母亲沉默了许久,却没有生气,只说:“如果觉得自己选的路是正确的,就走下去。”
那时我从未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即使只上了一所普通的三流院校,学业荒废了整整四年,实习时找了份连我自己都觉得烂到完全不敢与家里说的工作。那年我二十一。
实习那半年,我经历了迄今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而令我无数次独自蜷缩在出租屋的沙发上因思考人生而后悔十七岁时错误选择的是看见他二十一岁时获得国际奖项的领奖视频。我怎样都想不明白,十七岁时的我到底为什么会有那样幼稚的想法。
夜里,黯淡的橘色灯光下,水果刀泛着幽光的锋利刀刃莫名刺眼,随着火龙果被切开的声音,橘色灯光下呈现出朱红色果肉,我莫名觉得那像极了数年前夏日里夕阳下的西瓜汽水。
“请问您有想过结婚吗?”旁边手机推送到的视频,是某位大咖的专访片段,提问的年轻女士明显是专访的记者。
余光不经意扫到镜头给到的人,我觉得熟悉,细看,屏幕上那个西装革履的人确实是他。岁月仿佛将他遗忘,使得他还是十七岁的模样,仅为其眼眸中添了成熟与稳重。他的笑容也如当初十七岁,那样干净、那样纯粹,他说:“想过。”
“您已经有想结婚的对象了吗?”记者表现出惊讶。
“暂时没有。”他声音始终温柔,如夏日黄昏笼罩街道的斜晖,带着遥远朦胧的记忆踏入旧人的心窝。
“大家都很好奇,您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呢?”
他带笑的声音表露出他刻入骨子里的温柔与教养,添了玩笑意味的口吻使人觉得他本就只是在说玩笑:“要是喜欢上某个人的话,那个人就是喜欢的类型吧?”
而我知道,他的玩笑素来是为真实裹上虚假外衣以迷惑人们产生怀疑的假象。
那是他二十四岁时的专访片段。这些年,他活在世界这个大舞台的聚光灯下,明明不是爱豆,却像爱豆一样备受关注,在舞台中央闪闪发光。大多数人给他的评价,从不吝啬人间一切美好辞藻。我想,那样的他也许早已将在这昏暗灯光下的角落里自暴自弃的我遗忘。
三
终是不甘心被他彻底遗忘,不甘心与他有着云泥之别,那时想着,至少要被他看见。十二月初,我毅然辞职回到故乡。
出机场时已近傍晚,没有我想象中的夕阳,也没有所期待的阳光。笼罩着城市的天空阴沉,暮冬的风伴着细雪穿肆于城中的每一条街道。打车回家的路上,透过车窗看着灯火辉煌的都市,恍惚觉着那些繁荣不过海市蜃楼。
天空越发阴暗,夜来得突然,细雪在灯下展现自己优雅的舞蹈,旋转,旋转,旋转。倏忽雪大了起来,本优雅的舞者变得疯狂,一个劲往下奔,似重逢久别的恋人,落在车窗外向归家的人诉说着欣喜。
从机场到家的距离似乎比印象中的远了不少,其实是如肥胖的司机师傅所说,现在是高峰期,堵车得厉害。
车内空气安静几秒,我听见雪轻拍车窗的声音,似有什么话要向车内的人讲述。我想,它们一定是太寂寞,如这世间大多数人,如半年在外漂泊的我。
“姑娘,你对现在的社会有没有什么看法?”司机明显想找些话题。
“没有。”我却只觉莫名其妙,并不想与他聊天。
司机沉默几秒,又开启新的话题:“姑娘,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我想尽快结束话题。
“怎么不找个呢?”
“没遇到合适的。”
“你不要太高傲,觉得谁都配不上你。”司机突然像在自说自话,“现在这社会挺开放,但是谈恋爱女娃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现在好多未婚先孕。叔叔跟你说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你说是不?你跟你男朋友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不知道司机为什么突然扯到性,也不明白司机为什么会将分明下流的东西归于政治,我没搭理,只看着窗外。当时我想,也许我该告诉对方传播黄色淫秽是可以被判刑的,但担心明天的头条新闻会是“某妙龄女子打车与司机发生争执而被杀害”。我想,如果他在我身边,明天的报上必会出现类似“某司机因性骚扰女乘客而被拘留”的新闻标题。但他不在。
“姑娘,姑娘?姑娘!”不甘唱独角戏的司机一直试图唤起我的回应。
我忍无可忍,决定先发制人,迅速移开话题:“师傅,你是专门跑车的?”
“我不是,我们是搞建材的。”
“那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我又问。
司机犹豫片刻,刻意提高音量以表现出的自信更暴露出心虚:“我嘛,平时就看看仓库。”
我没回答,空气安静几秒,在我以为会一直这样安静下去的时候,司机又说:“现在你们九零、零零后不结婚的想法是相当非常错误的。”
我觉得好笑,懒得多说,只讲,活着又不只有结婚这件事可做。对方却反问我,不结婚还有什么事做?
在那一瞬,我深刻领悟了那句“夏虫不可语冰”,也为自己的对牛弹琴而自省,于是我选择了彻底的沉默。沉默时看着窗外的阑珊灯火,我又想到他,不知他是否遇到确立他喜欢的类型的标准的女生,而他喜欢的女生,是怎样的类型?
但司机十分厌烦我无视他的话,总问我“是不?是不?你说是不是?”且一定等到我应答才停止重复。我也从未如此讨厌堵车,本只十分钟的路程,一个半小时才到。而这一个半小时,我明白了满脑子黄色垃圾的社会蛆虫只知道释放本能欲望,所以觉得世界上只有繁衍后代这件事可做,所以能将婚内出轨说得那样冠冕堂皇:“这是开放。”
我打开车窗,看见大雪纷飞中,街灯下那熟悉的店铺,店内明亮的金色灯光照到薄雪覆盖的路面,似铺了一层温暖的地毯。我知道我不必再担心自己的安危,耐着最后的性子让司机靠边停。
司机有一瞬间的惊讶:“到啦?!就这靠边?”
“对。”我生怕车不会停下。
“你家住哪?”司机又问,慢慢将车靠边。
我没有回答,待车停好,打开车门迅速下了车。
“叔叔跟你说的这些,你要记住。你爸不会跟你说这些,你妈没文化也不会跟你说这些,是不?你说是不?”我一声不吭将行李箱往外拉,许是不甘受到冷落,司机从前座回身看我,又说,“叔叔这是教育你。”
一瞬,我脑海里闪过数百句话,骂车里那看工地仓库的社会蛆虫的话。若非九岁那年的暑假,在东南亚旅游时与十五岁的少年遇到过迷之自信且蛮不讲理的人,我不会本着不作孽的原则对司机说:“谢谢师傅,你真是个好人!”记得九岁那年我忿忿然,少年却很平静,他说:“自作孽不可活,必然会被收拾的人,我们没必要费力。再说跟那种人争吵,不就是作孽了吗?”但我到底不如他那样大度,终是没忍住朝车里的司机甩了句:“但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那不是开放,是禽兽不如!”
我希望他还在我身边,我想他会说令我宽心的话语。我又突感恐惧,所谓人以群分,上天安排我遇到这样的社会蛆虫,是否意味着我与其相似,而这样的我,哪有资格让他在我身边?
踩过柔软的雪毯推开熟悉的店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似夏日的午后在树荫下小憩,积蓄了一个半小时的恶心也渐渐被暖流融化。店内顾客依旧很多,点餐口却并没有如记忆中那样排着长长的队。我上前点了十二寸香橙披萨和一杯香草拿铁,点餐员明显一惊,问我是否独自一人,我点头。
“十二寸的有点大哦。”点餐员眸眼带着善意的笑。
我正思考着怎样回答才不显得我吃很多,旁边一个女人唤了我的名字。我疑惑地对上旁边女人的目光,思索着她是谁。“还是十二寸水果披萨和香草拿铁?”女人问,察觉到我的疑惑,她拉下口罩,露出蜡黄瘦削的脸庞,笑容在店内的暖光下格外亲切,她说,“半年没见了吧?”
“啊,秦姨!”看着那张四十四五的脸,我脱口而出。秦姨是这家店的老员工,五岁时我第一次来这吃披萨就是她接待的我——准确说,是我们,我与他。
“听说你在苏州实习?”秦姨问我,我还未回答,她又问,“怎么瘦了这么多?”
“没有,只是口罩戴着显脸小。”好在戴着口罩,我不用刻意以笑脸相迎,只保证自己的语气算得礼貌,目光算得和善。
秦姨拉上口罩,目光在我肩上的背包带上停留一秒,又问:“刚回来?”
“对。”
“今天下午我还看见杨法官了,没听她说起。”秦姨口中的杨法官,便是我母亲。
“没跟他们说。”
秦姨的目光中闪过几分情愫,让人感觉她有千言万语,她却只说:“回来就好。”然后抬手指了我右侧的方向,告诉我那边有空位,让我去坐着。我道过谢,拿了号牌拖着行李箱往秦姨所指的方向去。
空位靠窗,放下背包坐好,看着对面空空的深绿色软皮长椅,脑海里蓦地闪现一个画面——夕阳洒下,为绿椅罩上一层金纱。周边顾客的谈笑声放大了不少,店内播放的流行音乐也格外清晰。谈笑声与流行音乐逐渐混合,形成一种杂乱的、聒噪的、甚至有些刺耳的声音,很快所有声音迅速减小,化作一股电流声。最终电流声消失,世界寂静得可怕。窗外的夜空也被灯光照亮,亮如万里晴空,仿佛橘色的路灯是遥远的夕阳。
时光,在一刹回溯。
四
十岁那年的夏日,黄昏之时斜晖毫不吝啬为雪白的街道铺上金箔,那样温柔。十六岁的少年身影清瘦,绣着校徽的洁白衬衣很是合身,背后的黑色双肩包与学校统一定制的制服长裤同色。他迎着风停好单车,自马路对面信步而来,带来一片炙热,满目素金。少年于风中微微凌乱的黑发被阳光染上一层金光,呈现出与他的瞳仁相近的红褐色。当他停下脚步与我隔窗相望,我清晰地看见他眼中光景。
他的眼中,有河山,有落日,有我。河山与落日源于玻璃上的反光,而我真真实实在他眼前。
我向他招手,示意他进来,他的目光从我面前桌上的披萨和汽水上一扫而过,背光却仍不难见白皙的干净脸庞露出温雅的笑容。他左手握住背包肩带,加快了步伐从我面前走过。很快,他出现在店内,取下身后的背包往座上轻轻放好,与我打过招呼便转身去了洗手处。
数年后回想起那时他从我身旁走过,少年独有的清香似如仲夏傍晚带着栀子花香的微风轻轻拂过心房,添了对温柔与浪漫的万千遐想。
“小学生可真幸福。”他坐我对面,用纸巾擦干手上与脸上的水,如此说道。
“高中生更幸福吧。”我回答。
“高中生不如小学生幸福,小学生已经放暑假了,高中生还要回学校上晚课。”
“今天不是周五吗?”我问。
“这周不放假,只是今天下午放学比较早。”他说着,将用过的纸巾折成整齐的方块放到桌边,蓦然震惊的目光落在冒着寒气的西瓜披萨上,却端起面前的西瓜汽水,问我这是什么胃溃疡套餐。
“夏日限定!”那时我总觉得长我六岁的他并不比我懂得多,“夏天不就是吃西瓜的季节吗?”
“直接买个西瓜对半砍了用勺子挖着吃不更好?”他表现出嫌弃,却在将汽水迅速喝过一半后拿了块西瓜披萨。
“那样吃是没有灵魂的!”我反驳。
“那样吃才有灵魂好吧。”他不甘示弱。
“好吧。”我终先示了弱,“那下次我去买个大西瓜,咱俩对半分。”
他说着以后少吃冰的,对身体不好,却迅速吃着那份披萨。
“那西瓜呢?”我只顾与他说话,没注意到被他吐槽的披萨却只剩了三块。
“下次再说。”我第一次见他吃得那样狼吞虎咽,生怕我多吃似的。
我终于注意到盘中残余的三块披萨,有些不满地看他:“你不是不喜欢吃披萨?”
“这不是冰镇水果?”他喝着汽水,反问我。
我打算起身去柜台再点一份,却被他叫住。他说着他还有晚课,放下手中的汽水提过旁边的双肩包,从包里拿出一个热腾腾的紫米饭团递我面前,说我应该更喜欢这个。
我眼前一亮,立马伸手将其几乎是夺了过来。而在饭团到我手中的一瞬,他将背包放回原处,提起仅剩冰块的的汽水杯晃了晃,说:“一物换一物,我的饮料喝完了,你得去帮我买一杯,不加冰。”
“你不怕得胃溃疡吗?”口是心非这点我定是跟他学的,否则我不会一脸不情愿地去给他买饮料。
待我端着不加冰的西瓜汽水回来,他已将本属于我的那杯喝了大半,还不忘一脸嫌弃地对我说:“下次买饮料少加点冰,牙齿会被冻掉的。”我嘟囔着那本就不是他的,目光幽怨地落于他手中的西瓜汽水杯上。杯中微微晃荡的红色液体于余晖下呈出半透明状态,其中碰撞发出声响的冰块剔透得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红色宝石,耀眼夺目。拿着宝石的少年,如夏日黄昏的斜晖笼罩街道般温柔。
但现实不是夏日,没有斜晖与西瓜汽水,也没有他。只有黑夜与白雪,以及冒着热气的披萨与拿铁。
餐后离开时在门口又看见秦姨,她正擦着靠门的桌子,让我回家注意安全,我本能敷衍点头。但当我独自走在没人的街道,险些被人拽进旁边黑暗的丛林,我才意识到最不该的就是对“安全”二字敷衍。
“做什么!放手!我报警了!”一个女人气势汹汹的声音透过幽暗盖过我的呼叫,拽我的男人匆忙松手,肥胖的身躯隐匿于旁边黑色的丛林。直觉令我笃定,那个人,就是两小时前恶心了我一个半小时的司机。
有些破音的女人大步向我跑近,她拉下口罩,瘦削的脸上满是担心,大口喘气的同时还不忘关心我,问我有没有受伤。
“没有,谢谢秦姨。”不知是被吓到,还是感动于久违的别人的关心,我险些哭出来。
秦姨松一口气,重新拉上口罩,说她刚下班,正要回去,听见我的声音就过来了,还好我没出事。我忍着泪,除了谢谢,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能说什么。
秦姨说天晚,建议我打电话让我父母来接,而我的印象中,父母亲总是很忙,于是我说自己回去。秦姨却急了,担心我出事。最终秦姨放心不下,不顾我拒绝,坚持送我回家。路上,秦姨对我说,二十年前就因她的疏忽,她的女儿被拐走,至今没有找到。
回到家,我摸出钥匙开门打算进屋,心中骤一个咯噔,回头,见秦姨还站在围栏外。
飘落在她黑色羽绒服上的雪花被庭院灯的暖调光芒照得清晰,仿佛来自天国的精灵即将带领她踏上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霎时风起,夜中风雪朦胧,模糊了双眼,于模糊中,有一瞬产生一个想法——那条深入夜色的幽暗道路,也许与奈河桥并无两异,也许路的尽头,有她的女儿。
我忽然很想上前给她一个拥抱,也很想对她说声谢谢,但我只抬起手向她挥了挥以示告别,她挥手回应我,我抬手示意她回家。见她转身消失在朦胧中,我才对着那沉重的灰白夜色,轻轻说了句:“注意安全。”
不久后某天吃晚饭时,母亲将一沓看完的文件推到桌边,突然问我是否记得秦姨,我问怎么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秦姨去世了。母亲总是如此,对任何事都轻描淡写——哪怕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冷漠透过她不怒而威的平静双眸,让我感受到她在法堂之上的沉稳与震慑。
我问起死因,母亲始终淡然,连夹青菜的动作都未有半分停滞,她说:“被人奸杀。”我第一次觉得,眼前我自以为熟悉的母亲是如此陌生。也第一次好奇,她经历过多少,才会对这种事司空见惯。
我脑中浮现出那晚被人突然拽拉的画面,竭力想要记起那个人的脸,脑子却像突然失忆了般,一片漆黑。我问,更像是自问:“什么时候? 被谁杀的?”
“你回来那晚。”
“凶手抓住了吗?”那张恶心了我一个半小时的中年肥胖男人的脸清晰地蹦现于我脑中,挤得我的神经一阵胀痛,也引起我一阵反胃。
“抓住了,犯罪嫌疑人是一个跑车的。”
我急切地问有没有判刑,母亲说没这么快。我第一次如此希望一个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人不得好死,但我想,如果是他,他定会保持素有的沉稳与从容,于是我保持了冷静。
五
秦姨入殡那天清晨,昏黑的雾色中飘着鹅毛大雪,书房的窗户铺上一层厚重的冰霜。我抄了一整晚佛经,却消不掉我心中的懊悔与愧疚。悔于那晚没能给秦姨一个拥抱,没能对她说声谢谢,以及——注意安全。而如果那晚我没坐那辆车,如果那晚我没去吃披萨,如果那晚我打电话给了父亲或母亲,没让秦姨送我回家,现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时光不会回流,在时光之路上的我们也无法倒退。
抄完一整本线本的右手早已冻得通红,将毛笔搁于笔山时只觉麻木,麻木却能感觉到疼痛。我坐到椅上,将双手靠近旁边的暖炉,看见墨快干的砚台,倏忽担心,人生如此无常,生命如此脆弱,我是否真的能与他再见?
后来母亲对我说,凶手被判枪决,年后执刑。我没有说话,看着夜雪中庭院里衣着素洁的大树,又想到两个月前归家的晚上,栅栏外大雪中的黑色身影,以及在抄了一整晚佛经后产生的担忧——我怕来不及与他再见。
我看着书,故作不经意地问母亲:“以前对面那家好像有个哥哥?”
“怎么了?”
“啊,就是……”我轻轻翻着书页,心虚地不敢看母亲,生怕心思被她看透,“突然想到了。”
“你小时候天天跟人家后边儿。”母亲的声音仿佛带着笑,我脑补出她莞尔的模样。母亲说十年前他与父母出了国就再没回来过,三年前他的爷爷奶奶搬进他们的房子后,母亲时不时会听老人们提起他。我多想知道他在哪,多想知道他的近况,我想母亲应该知道,但我没敢问。
春节那天清晨,天空格外晴朗,与家人登山去庙里祈福,他的爷爷奶奶也与我们一起。路上偶尔听长辈们提起他,我知道了他前段时间在东京。老人叹息他工作繁忙,二十七八了连孙媳妇都不给他们找一个,我一路沉默,心中却窃喜。
我不记得自己在窃喜什么,只记得年年都拜神祈福,那次我头一回满心虔诚地祈祷——愿我们各自平安,愿我们能再相见。
化雪的清晨,我以商量的口吻与在客厅看报的母亲说想去日本留学,母亲那素来庄严平静的脸上起了几分波澜,看我良久,她问我怎么突然想去日本留学?
我苦思于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母亲先开了口:“想去的话就去。如果觉得自己选的路是正确的,就走下去。”我觉得这话熟悉,她又补充道,“时间到了你自知对错,发现走错了路,及时回头,任何时候都不晚。”
那时我才明白,母亲对我从不是纵容,她的不言便最具教导。也是那时我才明白,人生如棋,落子不悔。若我要与他再见,若我要有资格站他身边,便定要偿还十七岁那年因做错选择而负下的累累债果。而哪怕我一次次怀疑自我,哪怕一次次想要放弃,较之因海量陌生的知识而害怕考试不合格,我更怕来不及见到他,更怕来不及有资格站到他身边。
那时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害怕来不及,而我努力的唯一动力,只是他还活着。我庆幸还有些许概率,我会与他再见,在世界上某个我还未去过的城市。那里有河山,有落日,有被斜晖笼罩的街道,以及,如斜晖笼罩街道般温柔的故人。
尾声
我往前奔赴,向你而去,只期待有那么一个傍晚,共你漫步斜晖笼罩的出羽二见,听南风过耳,雀啾鸥鸣,看夕阳入海,月转星移。但一直与时间赛跑的我,似乎从未赢过,我也从未追上过你。
有时我想过放弃,也不解你为何不愿回头拉我一把?但当我入读你曾经的母校,知自六年前你远赴美国深造便再鲜回日本时,我想,时光之路无法倒退,所以你从未回头,也无法回头。
我度你曾度过的春夏秋冬,也爱你曾爱过的风花雪月,但被雨水点点打落揉入石板夹缝的樱花,实在像极了尸首烂进泥里的轻生少女。感受到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一瞬,我将命运交给了命运,也只能如此。
我在向你奔赴而去的路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以至即使我拼命加快步伐,也仍追不上你。如果时间来得及,抑或你愿在这条无法倒退的时光之路上停留片刻等我,我想,金色之下,你的眼中会有河山,会有落日,也会有我。
然,在这苍黄翻覆的大千世界,如沧海一粟的我们会否各自平安,会否终复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