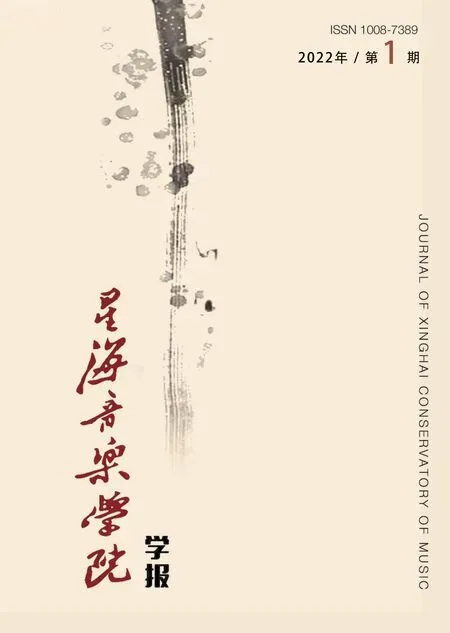中西交流中中国乐派形成的思想传统
夏滟洲
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每一种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在世界文明总体发展中,各个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差不多都经过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交汇,在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还有可能走向世界。因此,无论是具有血统、文化、制度同一性的汉民族族群文化,还是世界性文化的形成,都可以归因到一点,即“交流”。正是由于交流的存在,极大地拓宽了人类关于自身和社会发展是视野,不断丰富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进步。尽管交流的方式不一,或通过和平,或基于武力征服,甚或血腥镇压,而且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既有融合也有冲突,但总的趋势都会因交流而走向融合。以悠久的中华民族为例,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互动中,就呈现出了明显的冲突与融合的特征。
回望中国历史,自汉唐以降,中西交流之间以佛教传入所产生的冲击虽大但最终成功地为中国文化所融合,完全本土化;而沿丝绸之路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也给中西音乐文化发展造成深远影响的史籍也多可寻访,期间还有基督教抑或“西学”先后两次传入我国,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却无具体记载,以至于中国音乐文化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异。逮至明清时期,中西音乐交流顺海上丝路传入时有发生,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之时中国人开始正式接触到了“西学”。此间持续200余年西方文化传入,造成了西方音乐文化在19、20世纪之交对现代中国音乐产生强势的影响。
有学者研究认为,从时间坐标上来看,文明之间的接触导致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新陈代谢,基本发生在15、16世纪以前,主要通过野蛮的游牧民族的中介进行。从空间坐标上来看,文化的嬗变则发生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之中。(1)赵林:《协调与超越——中国思维方式探讨》,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但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中国,显然在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影响,既久远又复杂。与之相比,15世纪前的欧洲在政治组织和经济方式上都无法相比。然而由于国家的主权观念的出现,导致世界发生变化,却决定了中国与欧洲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世纪出现的民族国家都以其民主政治、官僚机构、统治者们还要承担若干义务等特征,有国际认可的疆界,有创建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在汉代就已见“国家”二字的表述(2)如:“永元五年(93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洛阳出土铜镜》彩图版四及图版说明,东汉银壳画像镜。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出土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页。,但根据欧洲角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国家”(3)[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中国迈入“民族”观念下的“国家”行列之时,正值中国进入近代之际。然而,中国进入近代的特殊方式,非为自身孕育而是深受西方的冲击而促使自身的回应的结果。在欧洲人将其国际秩序扩及中国后,随之带来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但一套出自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模式是否就适合中国?这些科学和民主精神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冲击会有多大?因此,中国民众阶层的思维方式仍旧受着儒家的伦理规范支配;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国家一直在“非官方”和“不正统”的道路上摇摆。然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西方国家,他们受启蒙思想影响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4)《礼记正义》卷12“王制第十二”,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38页。的儒家统治理念大相抵牾,无法解决近代中国对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秩序的控制诸问题。然而,西方启蒙思想尤其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是存在的,尽管那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很肤浅也很片面。
除了“国家”观念之外,近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还受制于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影响,毕竟中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尤其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近代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强行瓜分的猎物,及其他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而形成诸种思潮,都以其探索精神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出路加以考察。这些思潮主要有:或主张维护国粹以抵御外侮(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主张学习西方以求变革(所谓“文化自由主义思潮”或“激进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主张“中西结合,融会贯通”的,等等。
上述思潮或以具体的理论观念形态而存在,或以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存在,或以一种艺术表达而间接地存在于音乐作品之中,堪称对不断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多面观照:无论是“自西徂东”式的文化转移、还是从江山形胜到都市幻象式的时代风气的描绘,无一不与文化和政治的变化、近代中国“感觉世界”(structure of feeling,如自认天下,视西方为泰西)与“自我认知的框架”(frames of self-perception,有真知的存在,也有自由的想象)的变化有关。中国乐派深受西方启蒙传统的影响,以多样化的方式而存在,经历了一个两眼相看从朦胧走向清晰的过程。我们看到的西方是想象的异邦,西人看到的远东是神秘的东方。下文试采用思想史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做具体的分析。
一、觉醒在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观念作用
在现代性时间节点里,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模式,以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用以承载各种不同的社会目标如自由民主制或共产主义的理论等普泛性的意识形态(5)[德]施特劳斯著,丁耘译:《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101页。。在晚清现代性时间中,知(knowing)是一种做(making),政治社会来自人自由形成的理想。特别在“一战”后,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吸引了很多西方人来华——尽管多数为流浪者或逃难者;加上去外国的中国人——使者、留学生、商人和苦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西文化交流构筑起重要的影响力。泛泛而论,除传教士外,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启蒙和传播西方思想时,以“自西徂东”式文化转移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影响,既有外因的作用,又有音乐艺术内在演变的因素,基此形成的思潮弥漫于本土化路线中,有觉醒、有坚守、有适应、有创新。
显然,现代性是可以揭示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所有变化的基本线索,其内化形式为现代条件下人的文化心理与性格气质,外化为科学化和民主化。现代性伴随着“国家”(或“政府”)观念的出现而存在,有别于中国人意识中的“天下”观念。“天下”的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经济体,因大一统而自足,如此形成的“天下”王权观念,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心理力量,王权的政治思想顽固地主宰着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切。迥异于“天下”中国的,是欧洲“国家”的工商业文明对其物质文明的促进,加上政教分离带来文化的独立性。直到郭嵩焘出使欧洲,看到这些中西之别同时,才知道“天下”之外,还有民主制度和民权国家,时在鸦片战争爆发不久。彼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遭受全面的“现代”。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西方社会被看成更为先进的社会,因而其文化要高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流行一时,以社会进化论为代表的思潮揭开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幕。一如梁启超所看到的,世界风潮自西而东,便主张利导而不可逆拂之。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大炮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同时,也让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先进性,于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期间,西化的教育体制移植到了中国。“西乐”在中国迅猛拓展,掀起晚清中国人了解、学习西方音乐,进行乐歌教育的潮流,冲击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因素,但真正造成中国音乐文化出现中西之分、新旧之分的,则到了五四运动前后。
五四之前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诸种思潮的出现缘起于中西之争的发生。起初的中西之争,源自19世纪末期开始的学者们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到了五四前后转化成了中西文化之争。所谓中西之争,要说与传统的观点“夷夏之辨”有着某种一致性,二者虽然都是在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有着本质区别。自古以来,这个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人围绕文化方式所做的选择。只不过,古代沿丝绸之路发生的文化交流抑或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更多的反映在文化意义的追求上,古老传统形成的国家意识用乐地位之巩固,表明在任何政权分裂割据的时代、华夷之间碰撞剧烈的进程中,作为中国汉文化核心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都是把那个时代生活着的人们联系起来的重要因素。譬如唐朝,由于文明的优势与自信,以至于人们即使有“夷夏”观念存在,但自信也是溢于言表,恰如唐太宗所语,“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6)[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247页。因为“夷”之谓,兼具民族地域之分与文化高下之含义。虽然“西”“夷”界限还不清晰,但其中所包涵的精神成分已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大一统的惯性作用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以来的数次中西交流之中,即便如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走文化适应策略,在始将西琴和为琴曲配写的坎佐纳《西琴曲意》歌词传入宫廷时,留下西方音乐文化东渐中国最早的史迹。入清之后,西方音乐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犹存,但终未形成燎原之势。
鸦片战争的失败,我们看到了“天下”观念中的“夷”在“国家”观念中发展转变,和尚在古老社会的中国思维与进入现代化了的西人的激烈冲突,必然导致华夏中心主义的地位发生偏离。在“古今中外”的汇合点上,即鸦片战争后的晚清阶段,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传统经世致用观念已随之发生转变,让包括西方音乐在内的西学已不同于先秦以来的“华夷”之“夷学”(7)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了。当时间发展到曾国藩时代,他始作洋(夷)务,兴西学以发展中国的思想,走着“枪杆子里出政权”之路。同时依托江南制造局开设译馆译格致、政艺之书,想借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兴中国文化,带动中国制造。其时有魏源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选择,却让“夷夏之辨”处于尴尬地位,既然有“夷夏”的存在,可还要去“师夷”?虽然此间朝野人士亦视中西关系为“夷务”,可见“国家”观念中的“夷”,乃指“国际”。因此顺传统而来,自然要受到专制的清朝政府的抵制,也就与洋务运动的作为相抵牾了。究其原因,在于本位主义,维护王权统治而做的主动改革(也是一种改良),目的是在寻求改变日益没落腐朽的王权专制,所以《海国图志》也就将当时的世界分成了“天朝”和“海国”。于是,晚清时期,一方面,封建王朝竭力维护君主集权的社会政治秩序,心怀老大心理(所谓“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页。),欲以夷从夏,或者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同时加强文化专制,致礼乐崩坏,新乐不振,更遑论西乐之兴了;另一方面,一切不甘心国家沉沦的仁人志士在振兴中华的路上思索、奋斗,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的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要创造一种新文化。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节点上,由于政治理念与文化认知的重大变化,他们或批判反思,或变革改良。就西乐之关注,尤以一众欧游或出访日本的清使专注于音乐教育与功能考察为重(9)参阅余峰:《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9-15页;以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鲜见对音乐本体的认知,但“袭用外国音乐”(10)黄绍箕:《中国提学史东游访问纪略》,载张静蔚编选、校点:《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第92页。的思想粗备。总之,在融入“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中,他们上承传统,下启现代,随着历史的进程,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铺垫。
在历史的转折处,现代性时间中的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主张整体性地将思想文化启蒙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去改造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1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104页。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近代知识分子从思想深处,都默契地,也许是无意识地受到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影响,印证了“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2)[德]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但现实中,恰如林毓生所谓,近代前两代知识分子都看到了“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变革的基础”,“然而,在思想内容改变、价值观念改变的同时,传统的思想模式依然顽强有力”(13)[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48页。,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特有倾向影响了晚清至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都“变成了全面反传统主义者”,但这种文化倾向中的“反传统主义”并不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深受强调政治—文化是一元论和唯智论的儒家文化的影响。(14)[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页。对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主流思想界的保守与沉闷,金观涛指出西方的影响仅限于器物层面,因为晚清儒生在“尽力做到引进西方事物不破坏儒学价值和一体化结构的社会整合”(15)金观涛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44-245页。。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身也产生了分化——“只要向往自然产生的先古传统,在传统的重压下必然产生体制内知识分子。相反,将自己的思想、性格顺应外来思想并加以变革的人则能从体制内挣脱出来,成为体制外知识分子。”(16)[日]三石善吉著,余项科译:《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实际上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传统儒家品格的知识分子。这种分化囿于个人禀赋、知识结构与实处世界的差异,在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主张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等问题时引向更趋复杂化的地步;在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里,持续多元化、多频次、多问题争论。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渐深入,特别是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一战”而产生了前后不同的看法。
甲午海战的失败带来的耻辱感与危机感,使得此前中国学者了解到的西方文明的理想化与“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进步的科学理性所有的优势,加之“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故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17)本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北京:《学习时报》2000年6月19日,第1版。,落后挨打的社会现实,促使他们开始新的思考和可能有的选择,但又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心理。这种大的背景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音乐文化,其中随之出现的新旧之分,在围绕中国传统音乐的兴废与乐教等问题的争论声中,形成了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中西音乐观。作为众多观念中的一种,音乐界接受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强调以人为主体,吸收西方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以一种现代性的选择,对中国音乐或中国音乐文化做主体性(中国性/Chineseness)知识建构。这种建构以自我认知为重,不在中国传统,也不在西方现代性,而在于深入理解本民族、本地域的主导性文化模式。
然而,思想领域形成形色各异的派别,由于取向不同,他们围绕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的阐述有离合,有交织,有论战,有妥协。但就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近代中国关于自身文艺发展从对世界的感觉中,既有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也不乏国人主动的求学与纳新,又有大量来华的西方人士的主动输入。充满期待与积极实践。行动形式上,有译书办报、创设学堂、出洋求学等。结果上,文学艺术在不断充实中,形成了进步的潮流。踵晚清文学改革之后尘,传统戏曲的发展,改良与设立新舞台同步推进(18)据“丹桂后移十六铺称新舞台,为海上改建舞台之始”。1908年,上海始设“舞台”,从而带动新(舞台)剧的勃兴。胡祥翰:《上海小志》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戏曲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如王国维、吴梅等;音乐的发展,以十余支军乐队的活动和学堂乐歌的蔚然成风为载体,而国人在音乐领域所采取的现实行动,除关注演出、音乐教育必然地忠于本体形式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的有机结合外,还有理论研究和创作,则需要在本土的环境中以培养本国人符合人性的音乐社会行动;同时,也只有深度结合中国文化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符合人性的音乐社会行动的意义。历史中,从张德彝、王韬到梁启超、匪石,再从王光祈到郑觐文,又从沈心工、李叔同和曾志忞到萧友梅、赵元任和黄自等,各以其文化心态,与社会行动者的目的意义,面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及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发生,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结合国人的思想意图加以取舍改造。夹杂其间的诸多音乐理论家们,深受复杂多样与多变的时代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倾向与态度上呈现出复杂与摇摆不定的特点。
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理论家,他们对中西音乐文化碰撞交流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不仅要处理中西关系还要从古今维度上来认识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时与西方音乐所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可能会有的融会贯通,相应形成全盘西化(欧洲音乐中心论)、国粹主义(民族主义)、中西结合(国乐改进思潮)几派而波及各个阶层。其间,具有代表性的中西结合观念从一开始就以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参与社会行动,以刘天华为代表的音乐家们,“立足国乐,一方面以西方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整理、研究、改进旧有国乐,一方面从现在做起,从事新的国乐作品的创作。”(19)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 年,第248页。这种国乐改进思潮在音乐文化领域中实际行动中的影响不一而足,但总体上基于传统而与外来音乐文化发生交融,既能推动传统音乐的发展,又能促进音乐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这一思潮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家在各个时期都会采用的行动方式。
二、启蒙之中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标识探寻
有着八千年历史的中国音乐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整体(主体)。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音乐,素来以其鲜明的主体性——固有的、相对独立的特点存世。处于历史的交汇点,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直接影响,造成中国音乐文化出现主体性危机。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现代性时间中,中国音乐文化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或重建或创新,如何立足本位保持特色吸收外来而获得发展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殊为复杂,更重要的是因为主体性认同的缺乏,导致理论上着实难以归于一派。因此,造成“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问题凸显,而为此后学界持续关注,吸引诸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音乐文化本质主义的诘问与知识建构,以余峰、管建华、邢维凯、李诗原、刘桂珍等人的研究为代表(20)余峰:《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再识》,《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音乐研究》1995 年第4期;邢维凯:《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论”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学》1997年第4期;李诗原:《文化主体性·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对话——有感于当代中国音乐批评中的“主体性危机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李诗原:《反本质主义音乐现象及其理论观察——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探讨(六)》,《音乐研究》2020年第6期;刘桂珍:《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重构》,《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直至王黎光明确提出建设中国乐派的主张,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基于国家文化战略考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的现实需要、基于建设“一国之乐”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和着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来建设中国乐派,“将音乐作为国家形象和文化主体性的标识,都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和治国理政功能,都充分吸收外来音乐充实自身。这就使我们在中国乐派及其话语体系的建设中,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那些已相当成熟的音乐制度与音乐实践”(21)王黎光:《中国乐派及其话语体系建设》,《音乐艺术》2020年第4期,第12页。,既是国家文明的重要内容,又是国家文化战略中的一部分。这一目标最终要达成的,是要在世界音乐中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音乐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和人文价值取向。
对音乐的主体性的追求,其实也是现代性时间进程中一个具有推动力的更新机制。试举一例分析。众所周知,国歌,“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国歌和国旗、国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政治生活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22)钱仁康:《世界国歌博览》“前言”,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页。下引国歌诸例均据此书。。清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出使欧西,曾编写一首《普天乐》作为清廷国歌,以应付国际交往之需;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军歌,亦作国歌之用;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亦以一首古曲填词为国歌(一称《李中堂乐》),但这些皆非清政府批准和正式颁布之国歌。宣统三年(1911)典礼院请旨颁行《巩金瓯》为“国乐”。翌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命教育总长蔡元培负责征求国歌,2月,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中华民国国歌》(拟稿)问世。由于无精当之作,几经增修,最后在1919年11月,教育部设立国歌研究会,经国务会议决采用萧友梅作曲《卿云歌》为国歌,定于1921年7月1日起施行。这一系列的动作,使中国具备了一个民族国家应有的观念形态,亦与传统所遵从的“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23)《礼记正义》卷37“乐记第十九”,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30页。的思想相合,这是中国现代精神及其心性结构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一种主体性的“知”(knowing)与“做”(making)。
照李诗原的研究,“文化本身并不存在着‘自性危机’或者‘主体性危机’,而只有‘自性’或‘主体性’的蜕变。任何一种文化都曾是/正是/将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24)李诗原:《当代中国与“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由“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引发的思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年第4期,第37页。以此论断分析五四前后音乐界的行动,面对西方音乐传入带来的挑战,大家从生存状态的改善、优化入手,在音乐创作、表演、理论研究和音乐教育几方面的实践,基本遵从国家观念的体认,和民族主义观念的自觉,在其活动与表达中注重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发展和重构本土音乐文化,终至西方音乐文化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受启蒙思想影响而走文化思想的变革,中国音乐界渐渐聚焦“民族复兴”内容,并参照西方国家观念而憧憬中华民族的复兴,从梁启超的系列关涉“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概念的探讨,不仅有曾志忞之“新音乐”概念与之一脉相承,还影响了其后的王光祈,更给其后活跃的各思想流派以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在全国境内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历史话语的影响。
再看王光祈。在他26岁时即以“创造”为目标而立志改造社会。其时,在他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中,就视中国为世界的一部分,指出他所理解的“中国”二字是Place,而非Nation,他的理想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25)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一卷二期,1919年8月15日,第1页。。王光祈以改变其所生活时代的现实、希冀建立一个梦想的大同世界,实为古老“大同”思想的现代回应,是一种基于兼容世界大同的民族情感的驱动。他将“少年中国”的“大同”理想付诸音乐实践,也是潜在说明建立“少年中国”的意义。1922年,他撰文“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民族之声’。”(26)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一)著书人的最后目的”,载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次年起改学音乐,主张宣扬救国,振兴民族。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自序”中,他写道:“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27)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 “自序”,载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485页。王光祈的这种进化论观点,在中国音乐现代性选择之路上,较早地提出中西结合的主张,及调和民族与国家的愿望。因此,从民族主义角度,远在德国的他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申明,“我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最近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赞成。民族主义系以征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汉、满、蒙、回、藏统称为中华民族。)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1925年10月11日)(28)《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载张允侯、殷叙彝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14页。而“国乐”恰好就是“足以发扬该族的向上精神……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舒畅民族感情”(29)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40-41页。的音乐,并且认为“凡有了‘国乐’的民族,是永远不会亡的。因为民族衰废,我们可以凭着这个国乐使他奋兴起来;国家虽亡,我们亦可以凭着这个国乐使他复生转来”(30)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九)欧洲音乐进化概观与中国国乐创造问题”,载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41页。,王光祈的这一表述及其多元统一的思想追求,与同时代音乐家如萧友梅、赵元任和黄自等人积极地跟进与“比较”的音乐学术和文化观点相映衬,及刘天华、吴伯超等人对“国乐”乃至“国民乐派”的阐发和强化,(31)参阅拙文:《“中国乐派”的构成及其传统与方向》,《音乐研究》,2020年第3期,第18-20页。代表了五四后音乐界就中国新音乐发展中较为成熟的思考,标志着中国音乐文化的时间与历史框架自此奠定,同时让世人对新音乐追求民族性的内容与形式有了明确认识。
众所周知,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中华民族素来重视文化这种人的生存方式。五四运动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前,以王光祈为代表的音乐家个体的活动中,一种超越传统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模式的人文意识开始萌生,它主要体现在个体的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增长和推动高等音乐教育走向大众化方面。之所以称其超越传统,是因为他们首先是立足传统讨论当时的中国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社会音乐生活。然而,并没有鲜明的标识凸显其主体性,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矛盾的现实之中:虽然现代性时间已经到来,但从民众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上,现代性尚未生成;为中国人民提供安身立命的传统文化虽然产生动摇和危机,但其所具有的超稳定结构仍在以其自在自发的作用参与社会活动、规范个体行为,反倒在某些方面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阻力。这两种现象的背后,是多数抱持音乐新思潮的诸学者,虽然取向不尽相同,但都相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文化是优秀的、认同的,认为当时中国所欠缺的只是西方坚船大炮。这一观念下的主体性,可以说是文化人在主张中彰显自己身份的行为,而非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性”)。
流淌在历史长河之中的中国音乐文化其主体性标识,隐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之中,显于西学之于文化的浸染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影响。在“采西学”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已经落后于西方现代、抱持全盘西化观点的各派声浪此起彼伏之中,必然会造成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丧失。五四以来主张全盘西化的声音,在音乐界的影响自匪石以后,以青主、欧漫郎为代表,延时至20世纪30年代明确宣示出来。倾向于全盘西化观点的人把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加以比较,或高下或优劣或先进落后,试图以一个普世价值来一以贯之,或先立定西方为创作基础后再据此创新等等。客观地看,他们作为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代表,一方面在寻求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紧迫感,而致中国新音乐发展在实际需要与实践中的脱节,这是从社会改造层面而言,它实际对音乐本体影响很小;一方面,认为中国新音乐全盘西化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甚或将西方音乐理论拿来简单化地分析中国传统音乐,造成偏颇的价值取向,这是从音乐本体出发;还有一方面,全盘西化观念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因为,在不破不立的历史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情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至少在策略上,敢于正视现实人生的启蒙主义观点,反过来会触动人们去主动思考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链接。
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派中,沿袭洋务运动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被梁启超、沈心工、曾志忞等人以“保守”的立场延续了传统的民族认同感,以“改良”的立场“输入文明”后又“制造文明”,从而“为中国造一新音乐”(32)曾志忞:《乐典教科书》自序(1904),载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47页。。然而,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立场并未受到真正的触动,“中体西用”式被迫的现代化,给拒斥、批判现代主义的思潮以泛起的理由。如此一来,除了国人自我感知中的江山形胜式的传统音乐文化主体稳定存在,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感觉世界的两种方式,如自西徂东式的文化转移产物、都市幻象式的现代性想象作品,皆成为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中出现的载体。因中西交流带来的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以上述三种载体为表征,隐含于其中的思潮,一是借助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来改造中国社会,二是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意识,都带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是实用性和直观性特点。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中的好东西,即使人家不送来(不管是用大炮送来、让传教士送来,还是请音乐家送来),我们终究会去‘拿来’的,‘人类的共同财富’嘛。”(33)汪申申:《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问题的两点思考》,《人民音乐》1999年第8期,第8页。我们着实要在观念上互相摄取,互相吸收,互相转换,尤其是在世界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更要看到文明的互鉴与交流所具有双向效用。因此,反观五四时期存在的一种“以创造、宽容的魄力,主动吸取改造外来音乐文化,以完善发展自身为目的的”(34)余峰:《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再识》,《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3期,第130页。传统,才是中国音乐现代化的主流,才是构成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标识的根源所在。所以,就曾志忞提出的“新音乐”概念,音乐学家张静蔚分析其本质后指出,“应当是不同于当时的封建主义旧思想,而能够体现出可以‘改良中国社会’,‘感动’当时‘社会腐败’的新思想的音乐。自然,它不是对传统音乐的因袭。但它也不是把西洋音乐都照搬过来。”(35)张静蔚:《论学堂乐歌》,载张静蔚编《触摸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第27页。可见中西交流带来的中间之途,基于音乐文化又超越于音乐文化的人文价值取向,立足传统进行“双创”,才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生成的必由之路。所不同于五四时期对主体性的探寻,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发现这种生成既非割裂传统,也非“去现代化”或“去西方化”,而是伴随着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将“现代”“西方”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思想、思维、观念予以整合,直至形成一种能够为当下中国人服务或有利于中国的东西。毕竟,在中国乐派思想启蒙阶段,体现一个健全的文明形态的各个层面和构成要素的诸方面,未能做到协调同步运行而已。
五四前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转型过程,揭示出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特殊的稳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和平常的百姓生活中,如若不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消除一切文化中心论和相对论,打破中西关系的二元对立,是很难通过一般的启蒙来实现彻底的文化转型的,由是音乐启民思潮、激进的全盘西化、保守的保存国粹、改造中乐的定势等思潮并进流行,众声之中,人自身的现代化的实现、音乐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困境可想而知。但五四文化启蒙中确立的对人的主体性的追求,为成为此后音乐界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的目标,引导他们从自在自发的传统主体向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主体性发展,只不过音乐界认识到这种“双创”行为,其要旨在于创造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音乐文化时,已经到了21世纪的新时代。
结语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中国乐派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积淀的核心介质和精神标识。回归中国乐派的叙事起点,抑或讨论中国乐派思想最初的萌发,起始于明后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开始接触之际。其后的发展,由于中西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各有其特性或个性,因此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交流和渗透,这一背景恰逢现代性时间到来。从中西交流之间,具有当代价值的启蒙思想和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19、20世纪之交先后传入我国,造成了西方音乐文化对现代中国音乐强势的影响。正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导致音乐界多种思潮泛起。从五四运动宣传的形形色色的新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局限,也看到了发展的趋势,那就是,一方面着实要在观念上互相摄取,互相吸收,互相转换,尤其是在世界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更要看到文明的互鉴与交流所具有双向效用;另一方面,中国乐派的肇端和确立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即文化问题着实是现代化诸问题中的一个。但众所周知,文化的转变需要一大批人在充实自己后静心地做,同时抱持一种基于音乐文化又超越于音乐文化的人文价值取向,旨在使中国当代音乐文化成为一种有利于改善和优化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并使之在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统一的文化价值判断下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正是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流以来,作为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范畴、一种观念、一种理论,甚或一场实践所有的蕴涵,中国乐派辩证地坚守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生动形象地保持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自信,并使中国音乐文化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持久地对外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