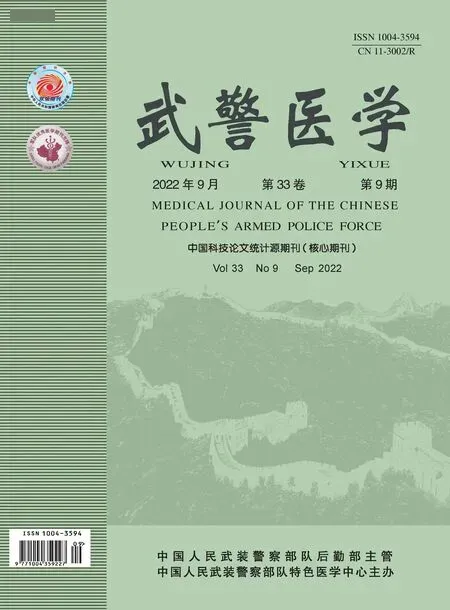高原环境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及其防治措施
张建起,石 蕊,张 芯,杨 帅,李立敏 综述 陈少伯 审校
目前,将海拔2500 m以上的地区定义为高原。我国幅员辽阔,其中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及四川的部分地区都属于高原,随着海拔高度不断增加,环境温度不断降低,会出现低气压、低氧、紫外线照射强度大及空气湿度低。这些变化会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不同于平原地区的影响,甚至诱发或加重原有的心血管疾病。近年来,高原环境对入驻高原官兵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结合国内外有关文献,对急性、亚急性暴露期高原环境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进行综述。
1 对心血管系统的主要影响
1.1 病理生理变化 长期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居民,在进入高原环境后,会产生主动适应性改变,涉及一系列生理生化的变化过程。初入高原3 d内称为急性暴露期;3~14 d后称为亚急性暴露期。心血管系统的变化是机体全身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系统改变相互影响,严重时会限制机体的运动耐力,甚至危及生命。肺通气量增加,是最早出现的变化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外周化学感受器受体密度上调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加的影响。低氧也会造成肺血管收缩,引起肺动脉压升高,但升高的程度因人种而异。肺动脉压升高后,增加了右心室后负荷,并最终导致左心室回心血量减少。体循环的最初变化包括心动过速和心输出量增加,而每搏输出量则维持不变。处在高原环境下3~5 d后,心率水平仍高于正常。由于每搏输出量下降,心输出量恢复正常。每搏输出量下降的原因可能与高原环境下,低气压、低氧导致抗利尿激素分泌减少,尿量增加从而血容量降低导致左室舒张末期容量减低有关。有研究对已经适应高原环境的对象研究发现,不论是在低海拔环境或高海拔环境,工作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心输出量维持不变,但是最大输出量会减低,说明高原环境可使心脏储备能力受损。 关于高原环境下,心室收缩功能的变化目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心室收缩功能短暂增加,而后维持正常或者轻度减低;另有研究认为,即使高原环境下心肌供氧会发生一些改变,但左心室的收缩功能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还有研究认为,高原环境下心房收缩功能也会产生变化,尤以右心房为甚,主要是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导致的结果。
1.2 急性或亚急性暴露期内心血管系统的变化 高原环境下急性或亚急性暴露期内,血压会有所增加。如果患者血压超出正常范围且回到平原地区能恢复正常,则称为高原性高血压。高原环境下血压增加会在24 h内均有所体现,但是当进入极高海拔环境下(海拔5400 m以上),血压升高主要发生在夜间,血压杓型曲线减弱甚至成为反杓型曲线。这种现象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交感神经活性增强,内皮素释放增加,大动脉僵硬度增加,血管内皮受损,血容量增加。除此以外,在高原环境停留16 h以上,体内促红细胞生成素浓度增加也是造成血压升高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的变化。这是高血压发生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的水平与海拔高度正相关。有趣的是,高原低氧环境下,运动过程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活性降低,肾素与醛固酮的紧密关系会打破。在运动初期,血浆肾素活性增加,血浆醛固酮浓度和ACE活性维持正常;随着运动带来需氧量增加,低氧相对更加明显,肾素进一步增加,但醛固酮和ACE却出现降低。这种现象可能与血管紧张素Ⅱ降解酶活性降低和(或)肾上腺皮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浓度降低有关,结局是避免了醛固酮的过分增加,却导致肾素相关的血压升高。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对于指导高原驻守官兵的体能训练具有重要意义。
1.3 急性高原病的特点 急性或亚急性暴露在高原环境下,高原病的发生屡见不鲜,是影响由平原进入高原环境新训官兵生活训练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是机体对于高原环境的适应不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急性高原病几乎可以发生在所有人群。所以,在进入高原环境前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避免紧张情绪是必要的。在海拔2500 m环境下,急性高原病的首发症状在暴露于高原环境下6~12 h出现。主要症状包括运动或者休息时呼吸困难,咳嗽,恶心,乏力,头痛,失眠,甚至精神状态异常。急性高原病包括:急性高山病(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高原脑水肿(high altitude cerebral edema, HACE)及高原肺水肿(high altitude pulmonary edema, HAPE)。造成急性高原病的首要原因是低氧。低氧可直接引起低氧血症,导致毛细血管压升高(大脑血流量增加的结果),大脑血流量增加及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由此造成脑水肿及脑脊液的缓冲作用减弱,导致AMS,甚至发展为HACE。最新研究发现,某些基因与高原病发生关联密切。单核苷酸多态性决定了是否为AMS易患体质。而且,EPAS1 和 VEGFA基因变异具有这种关联。这为将来预测高原病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肺泡低氧会对体力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内皮功能失调,严寒,体力活动均可引起毛细血管压升高而导致血管内皮紧张度增加,最终引起肺动脉高压。血管内皮紧张度增加,炎症,肺泡对钠和水的清除作用下降引起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可能是AMS,HACE及HAPE的直接原因。
处理急性高原病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快转移至低海拔地区并吸氧。预防急性高原病最简单的方法是缓慢进入高海拔地区,让机体有充裕的适应时间,有专家建议,每天前进300~500 m,隔3~4 d休息1 d。服用乙酰唑胺和地塞米松对预防AMS和HACE也有效。如果患者不耐受乙酰唑胺或地塞米松,可用布洛芬替代。理论上讲,使用布地奈德对预防轻度AMS有效,但不能用于重度AMS。有关布地奈德的使用,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硝苯地平、他达拉非、西地那非对预防HAPE可能有效。
2 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措施
2.1 高血压 我国高血压人口众多,知晓率、治疗率、达标率低仍是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的主要临床特点,近年来年轻化趋势明显。不仅是高血压患者,即使血压正常的人群,在进入高原环境数小时后,收缩压、舒张压都会有不同程度升高。Zhu等发现,对于已经确诊高血压的患者这种升高会更加明显。正因如此,这类人群进入高原环境后,出现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几率会大大增加。有意思的是,Duke 等发现,血压升高和罹患AMS之间并没有显著关联,反而有减低AMS风险的趋势。
低海拔环境下,一些治疗高血压的措施在高原环境中可能并不适用,比如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ntagonist, ARB)。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会造成血氧饱和度降低,进而影响运动耐量。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长效ARB类药物,比如替米沙坦,在海拔3400 m时仍具有降压效果,而在海拔5400 m其降压作用却消失了。ARB类药物降压作用消失的现象,与高原地区血液循环中的肾素血管紧张素活性受抑制的情况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确切机制并不清楚,可能与高海拔环境下肾动脉压力感受器受抑制和肾素释放受抑制有关。如果联合使用钙离子拮抗剂(calcium antagonist, CCB)和ARB类药物,对于高海拔环境下轻度高血压仍然有效。不仅如此,这种联合用药方式还具有增加肌肉供氧的效果。副作用包括体重下降,血容量减少及肾功能轻度下降。这种联合用药方式安全、有效。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规律监测血压,必要时对降压治疗方案进行调整。考虑到不同个体受高原环境影响的差异,应该重视使用动态血压监测及家庭自测血压。
2.2 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进入高原地区风险高于健康人。高原低气压、低氧环境会引起肺血管收缩,使肺动脉压进一步升高,加重右心负担。此类患者能否进入高原及是否可以乘坐飞行工具,取决于患者心功能。对于NYHAI-II级的患者,可以进入高原地区并不需要额外供氧;而对于NYHAIII-IV的患者,则需准备必要的供氧设备,确保患者氧分压>60 mmHg。对于肺动脉高压患者而言,其进入高原地区的风险甚至比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哮喘的患者还要高。
2.3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是所有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最终结局,人口数量庞大。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高原环境并不增加这类患者额外风险,只有少数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要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所带来的机体舒适度的下降,心力衰竭患者要甚于健康人群。海拔高度每升高1000 m,舒适度(基于活动量评估)下降最大可达10%,而健康人群在海拔700~6300 m,每升高1000 m,舒适度下降8%。另外,一个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是此类患者同时罹患的其他疾病,如肺动脉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缺血性疾病,都会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适应能力。有研究表明,在海拔2590 m时,心衰合并中至重度COPD的患者,活动量下降54%。心力衰竭患者能否乘坐飞行工具,取决于患者心功能情况。对于NYHAⅠ-Ⅱ级的患者,基本不需额外供氧;而对于NYHAⅢ-Ⅳ级的患者,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必要时进行氧疗。氧流量一般<2 ml/min。高原环境下,对于心力衰竭患者药物选择要慎重。β受体阻滞剂、ACEI、ARB类药物在平原地区对心力衰竭有效,但在高原环境下,情况则有所不同,尤其要关注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可能会影响机体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ACEI和ARB类药物减少肾脏促红素分泌,影响红细胞生成。ACEI和非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通过对肾上腺素受体(主要是β受体)作用,减低肺泡气体弥散和换气功能。因此,建议使用选择性β受体阻滞药。高原环境下,可以使用碳酸酐酶抑制药,如乙酰唑胺,但不建议和其他利尿药合用,以减低脱水和电解质失衡的风险。
2.4 冠心病 高原环境不利于冠心病患者。高原低氧环境下,心脏需要主动增加输出量来满足组织器官的正常氧需。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会限制动脉扩张,而导致心脏本身供氧不足,甚至诱发急性冠脉综合征。高原环境对于冠心病患者影响复杂,可能的机制还包括氧利用率下降引起的原有症状恶化、及日常活动量下降、脱水、精神紧张,失眠等。所以,对于冠心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要高度重视,避免由于适应不良而造成病情急性发作和加重。
但冠心病并不是进入高原环境的绝对禁忌症,个体化的病情评估和恰当的预防十分关键。在平原轻体力活动就有心绞痛发作的患者要避免进入高原,否则会加重心绞痛发作。新近发作过心脏事件的患者也不应该在高原环境下长时间停留。对于稳定性心绞痛或有无症状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暴露于高原环境似乎并不增加额外风险。Schmid 等研究表明,如果心梗发生在6个月之前,并接受了血运重建,评估为低危的患者,进入高原后,虽然需氧量明显增加,乳酸水平升高,但能够承受亚极量的体力活动 。冠心病患者进入高原后,必要时可使用乙酰唑胺,可对心肌供氧量下降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5 心律失常 高原环境可以诱发心肌缺血,并产生心律失常。其他与心律失常相关的因素包括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低氧,右心室负荷加重,碱中毒及钾离子跨膜转运异常。在进行高山运动死亡的患者中,猝死的发生率高达30%。有研究指出,在中等海拔高度(1350 m)室上性早搏和室性早搏的发生率是低海拔地区(200 m)的2倍。基于这种观点,证明已经确诊的心脏病患者,在进入高海拔地区后,各种心律失常的发生率都会增加。但也有作者持不同观点。Woods等认为,高原地区心律失常发生普遍,随着海拔高度增加,人们无论运动或者休息都会有不同程度心悸,但并不增加运动中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风险 。有关高原环境下QT间期变化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一项对于5895例65岁老年患者的24 h动态心电图的分析表明,QT间期并无变化,但室早二联律发生增加。
对于已经确诊心律失常的患者,进入高原地区,需要综合考虑患者本身与环境诸多方面的因素。阵发房颤的患者,进入高原地区是安全的;对于病情稳定的NYHAI-Ⅱ级室上性心律失常患者也没有限制。但对于治疗效果欠佳和室性心律失常分级为4b的患者禁止进入高原地区,NYHAⅢ-Ⅳ、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室性心律失常患者,也不宜乘坐飞行工具。
2.6 外周血管疾病 四肢低垂部分发生水肿是长途飞行(7 h以上)中的常见问题,发生率可高达86%。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飞行过程中毛细血管滤过率增加,机舱内低压,活动减少及体液失衡。飞行和登山是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的危险因素。高原环境、脱水、过紧的服装都可以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有症状的DVT发生率不超过0.28%;而无症状的DVT发生率可高达10.34%。长途飞行8 h以上,与下肢DVT形成或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发生风险增加有关。高原环境下DVT形成发展观点不一,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证实。口服β-羟乙基纤维素能降低毛细血管滤过压,对水肿有抑制作用,并与剂量呈相关性。另外,美国相关学会建议具有DVT高危因素患者长途(4 h以上)飞行过程中使用弹力袜、低分子肝素或者阿司匹林。
综上所述,高原地区气候、地理环境具有特殊性,人类对于高原环境的适应是长期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居民短期进入高原环境,身体功能及内环境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而发生适应性改变。一定程度上,这种改变会对机体造成损伤。所以研究高原环境下身体功能变化,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或减轻对于机体伤害,对提高高原驻守官兵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