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作家”贾平凹
王悦

陕西作家贾平凹已经70岁了,却突然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浅爹”。他女儿贾浅浅差一步就进了中国作协,这事闹得沸沸扬扬。
以“屎尿屁”题材或“回车体”文体所写的一些诗句,被当作贾浅浅的代表作流传网络。后来贾浅浅又声明,那些诗与她毫无关系。但人们依然怀疑,贾浅浅才华不够格进入作协,而她一直顺风顺水不过是因为父亲的名气与“关系”。
对于这一切,贾平凹始终沉默。
贾平凹曾经与路遥、陈忠实并称陕西文坛“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先后离世,如今“三驾马车”中只有贾平凹还在独撑,依然保持着每一两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步调。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73年,21岁的平娃将名字改为“平凹”,用“凹”表达自己正视人生道路的崎岖。
与女儿贾浅浅相比,作家的人生道路确实是崎岖的。
41岁那年,小说《废都》出版没多久就被查禁,直到16年后才获准再版,而贾平凹也被扣上“流氓作家”的帽子。后来,因为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贾平凹又背上“为拐卖妇女辩护”的骂名。
贾平凹自嘲:“声名既大,谤亦随焉,骂者越多,名更大哉。世上哪里仅是单纯的好事或坏事呢?”
但舆论却不允许贾平凹这样“通脱”,而是对作家有着更多的期待。
陕南的文学青年
在成为“流氓作家”以前,贾平凹是一个出身农民的文学青年。
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在陕西南部一座偏远的小镇—商洛市丹凤县的棣花镇—度过了童年。
贾家2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极度贫困,内部矛盾也不少。贾家四个媳妇轮流给家族做大锅饭,每家的媳妇都尽力让自家的孩子吃上稠饭,别家的孩子就只能吃稀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贾平凹的父亲原本是乡村教师,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接受劳动改造。
没有了父亲的工资,贾平凹一家的处境更加艰难。母亲没日没夜替人纺线赚钱,但日子还是一日不济一日。
多年以后,贾平凹只要听见“嗡儿、嗡儿”的声音,就会想到母亲深夜纺线的景象。他在散文《纺车声声》中写道:“一个灰发的老人在那里摇纺车,身下垫一块蒲团,一条腿屈着,一条腿压在纺车底杆上,那车轮儿转得像一片雾,又像一团梦,分明又是一盘磁带了,唱着低低的、无穷无尽的乡曲……”
1972年,贾平凹由于在苗沟水库工地帮忙写标语、播广播,办《工地战报》,受到工地赞赏,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在这一年4月底走出秦岭,去西安的西北大学读中文系。
上大学的贾平凹几乎天天写作,到处投稿,四处求教。
他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但一篇都没有发表。终于在1973年,贾平凹与同学冯有源合写的革命故事《一双袜子》在《群众艺术》发表,他也从此沿用着贾平凹的笔名。
贾平凹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文学事业百废待兴。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文学上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理论。贾平凹坐不住了,他贪婪地阅读和写作,想要在文学上闯出自己的天地。
贾平凹否定了以前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也不再为一向得意的编故事才能沾沾自喜。贾平凹决定写自己熟悉的家乡、熟悉的人和事。
他的视野也渐渐扩大,不仅看到了生活的光明面,也洞察到了生活的阴暗面。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作家的一双眼,不再是孩子般的单纯明快,而是成年人般的复杂和沉思”。
师长和朋友对贾平凹的“离经叛道”深感疑虑,批评文章也如潮水般涌来。
贾平凹的文风从《山地笔记》的光明、《满月儿》的纯净,转变为《山镇夜店》《年关夜景》对群众愚昧麻木的精神痼疾做鲜明揭露。师长和朋友对贾平凹的“离经叛道”深感疑虑,批评文章也如潮水般涌来。
29岁的年轻作家只有独自把委屈往肚里咽。他后来反思这段创作,向人们道出他心中的爱与恨:
“我太爱这个世界了,太爱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容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慌恐,迫切的嫉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老作家孙犁则给予了年轻的贾平凹精神支持。1982年,孙犁在为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所写的序文中劝慰道: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会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废都》与“流氓作家”
贾平凹定居都市西安,却从没有忘记他的故乡商洛地区的农村。
他结束了随波逐流如“流寇”般的写作,频繁地回到故乡采风,与朋友为伴,把商洛地区七个县主要村镇都走了一遍。
从1983年到1988年,贾平凹接连发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避开“商洛”而用古称“商州”是为了防止读者对号入座。“商州”固然来源于真实的商洛,但从根本上来说,那是贾平凹自己的文学世界。
《商州初录》给贾平凹带来很大的声譽,有评论家说他“几乎创造了一种文体”。
贾平凹则一步步自觉起来,长期坚守着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商州和西安分别代表了乡村和城市两种冲突的文明。贾平凹在两者间来回切换,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
一方面,贾平凹通过文学作品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反照出现存城市文化弊病对人性的扭曲。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扼杀人性的一面,因而热诚呼唤现代文明,认为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有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中,才能存续和发展。
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浮躁》也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
商州的州河“古怪得不可琢磨,清明而又性情暴戾”,是贾平凹眼中“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这条流淌在小说中的S形河流,隐喻了中国被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的时期,整个社会浮躁的精神状态。
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贾平凹的作品大获成功,可是当他开始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一顶“流氓作家”的帽子就扣了下来。
1993年7月,长篇小说《废都》发表在《十月》杂志第四期,单行本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出版。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并不容易。贾平凹在《后记》中说,他在城里住了20年,却还没写出一部关于城的小说。等到他克服了内疚,要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又遭逢了离婚、疾病、官司缠身、父亲病逝等等变故。
贾平凹在《后记》中写道:
“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了却把我烧毁。”
这部“在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作品将来的命运如何,贾平凹自叹“一切都是茫然”。
《废都》以西安为原型,虚构出了一座“西京”城。小说主人公庄之蝶,是一个迷失了自我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无疑是颓废的,但是贾平凹有意避免触碰庄之蝶的精神世界,而是模仿明清旧白话小说,不厌其烦地写着庸常琐事,这就更显得庄之蝶精神之空虚。
这本书多细节却没有连贯的情节,行文也少有戏剧性的形容词,照理说是没有人看得下去的。但《废都》还营造了传统中国男人“一男多女”的白日梦,穿插了庄之蝶和女人们的性爱描写,这就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
《废都》刚刚出版,一时长安纸贵,读者争相购买。评论界则是一片讨伐之声,庄之蝶成为批评的对象和争议的焦点。
书出版不到半年,就被北京市出版局以“格调低下,夹杂色情描写”为由查禁。
《废都》的盗版仍在地下流行,贾平凹转述内行人的评估,正版和各种盗版,加起来超过一千两百万册。
当他开始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一顶“流氓作家”的帽子就扣了下来。
在很多读者看来,《废都》是贾平凹创作的分水岭。《废都》前的贾平凹是“纯洁的”,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奋斗者形象;《废都》后的贾平凹则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流氓作家”。这顶帽子一戴就是近20年,“20年里,我像受伤的兽躲在洞里舔自己的伤口”。
城市与农村的批判
历经《废都》一劫,贾平凹继续在商州和西安两块土地上耕耘。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逐渐发现,不管在城里生活多久,他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村人。
他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的后记中写道:
“……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鸦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
贾平凹意识到,农村于他而言是宿命。
本着这样的自我认知,贾平凹把目光投向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落寞的人群。国家实行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这是伟大的功绩,但国家的注意力随后转向了城市。
贾平凹曾在散文《从棣花到西安》中写道: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
农村的社会压力累积起来,形成种种社会问题。贾平凹站在故乡街巷的石碾盘前思索:
“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贾平凹一部接一部的长篇小说,都在对农村的落后和城市的弊病作“双重的批判”。《土门(1996)》写大城市的发展吞噬了农村的故事。《高老庄(1998)》则批判传统农耕文化的种种弊害。《怀念狼(2000)》想要表明,没有了天敌的狼群,商州的人也就没有了生气。《秦腔(2005)》更是要“为故乡竖一块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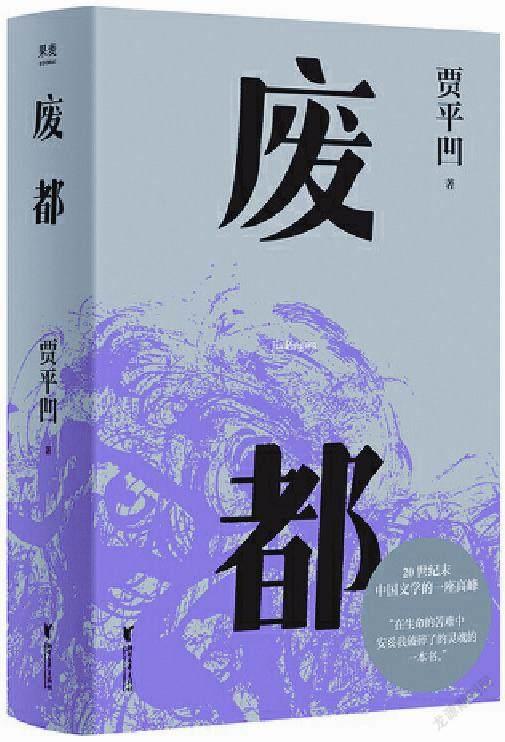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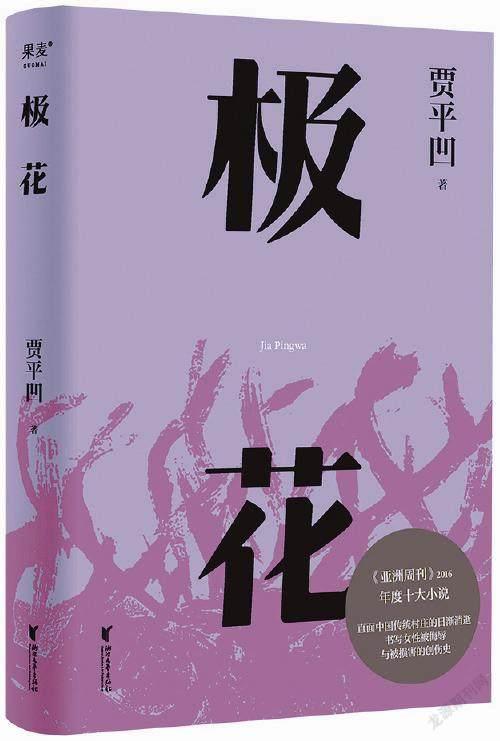
不过,贾平凹没有想到,201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又带来不小的麻烦。
《极花》也是写农村和农民,只不过取材于拐卖妇女的真实故事。引起麻烦的首先倒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他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与记者的问答。
记者问贾平凹,“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婦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是否“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则答说:“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了解的。”
记者继续追问,贾平凹也继续答话,可是越答越糟,竟然讲出这样的话:
“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众多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贾平凹以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的痛苦之上,女性沦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城市必然优越于乡村,隐藏了巨大罪恶的乡村消失就消失,“不值得缅怀”。
贾平凹却只对媒体说,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引起了公众误读。除此之外,他无意解释更多,因为作品写完之后,就应当让作品本身说话。
超越批判的可能
固然,我们可以回到小说《极花》本身及其写作过程,去反驳大部分脱离了文本的批评。
胡蝶的原型,是作者一位陕西老乡的女儿。老乡夫妇在西安城里拾破烂,女儿在饭馆里端盘子,却被人骗,拐卖到了山西。贾平凹听说后,立马和朋友联系了派出所,还自己出钱补贴出警的花销。解救行動的当晚,贾平凹一直焦急守候在电话前,直到派出所打来,通知解救成功。
但令贾平凹“惊得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的是,被救的女孩半年后又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在《极花》的结尾,胡蝶也回到了被拐卖的乡村,这并非作者一厢情愿的粉饰,而是有所本源的结局。
贾平凹逐渐发现,不管在城里生活多久,他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村人。
不过,我们还是应当承认,贾平凹的写作理想与互联网偏好的激烈控诉并不一致。他在《极花》的后记中说:
“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贾平凹认同揭露和批判的作品存在的必然性,原定的《极花》也是胡蝶要控诉,但作品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贾平凹慢慢也开始自问:“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
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避免时兴的“一种用笔很狠、很极端的叙述”,而贴近水墨画的写意,“从而克服将现成‘社会新闻简单移植进艺术世界的急切和粗糙,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可惜,理想终归是理想,落实到具体作品,恐怕力有未逮。读者未必能领会作者的用意,而作者还落下了“为拐卖妇女辩护”的骂名。
作家莫言曾经说,“贾平凹先生低调、谦和,这是有口皆碑的”,但时代已经不容许贾平凹低调下去。互联网舆论越来越希望作家不要躲进书斋,而能肩负起知识分子批判的责任。
贾平凹却依然故我,从不对“社会新闻”做直接的回应,甚至拿古人的对联自嘲: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2021年12月,西安因为疫情封控,贾平凹寄语“一定会战胜疫情,我们西安人一定会平安康顺”,引来不少人失望。
今年1月,“拐卖妇女”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贾平凹2016年接受采访说过的话又被人翻出来批判一番,贾平凹还是什么也没说。再来就是最近贾平凹的女儿入作协的争议,70岁的小说家也并未发一语。
贾平凹曾在《高老庄》后记中写道:
“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调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绽出一朵花来。”
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贾平凹最高的精神理想。他曾经不吝把这个意象赠给老乡刘高兴,一位快活的农民工,小说《高兴》的原型,因为刘高兴是“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
但是对世人来说,贾平凹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文人,仅仅“独善其身”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对于“独善其身”的可能性,很多人也深表怀疑。
——商州实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