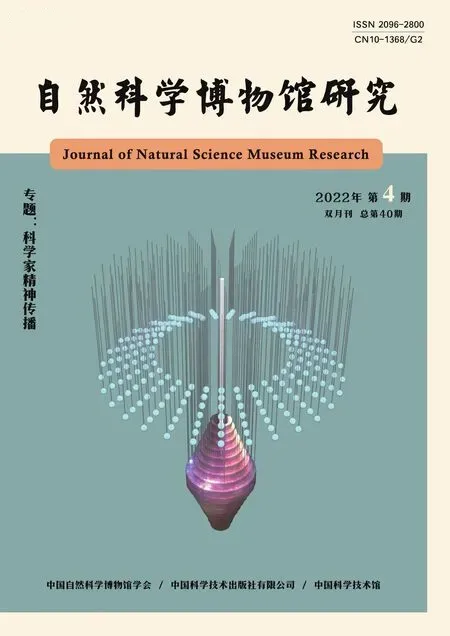从以“物”为中心的诠释到以“人”为中心的解说
——评《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第二版)
刘 巍
很多策展人都会遇到说明牌设计与撰写方面的困惑,比如如何确定自己撰写的说明牌是否符合展览主题和观众需求;成人与儿童观众、静态与互动的展品各需采用什么形式的说明牌;室内与户外展品说明牌的材质有何不同;每个说明牌的信息量该有多大;应使用什么字体及字号;排版使用横排还是竖排……不光是新手,有时连经验丰富的策展人也不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而一本实用的说明牌工作手册则会让策展人面对这些挑战时事半功倍。贝弗莉·瑟雷尔(Beverly Serrell)的《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第二版)(ExhibitLabels:AnInterpretiveApproach,2ndEdition,2015)正是这样一本可供策展人常备手边的工具书。
一、 关于本书作者
贝弗莉·瑟雷尔是美国博物馆界资深展览顾问和研究展览说明牌的知名学者。1979—2020年,接受她咨询服务的客户超过110个,其中不仅包括单个博物馆,如加州科学中心、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丹佛美术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等,还包括美国博物馆联盟、密歇根博物馆协会、加拿大博物馆协会这样的行业机构。服务的博物馆类型也十分广泛,包括历史博物馆、自然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儿童博物馆、科学中心、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天文馆等[1],这为她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
瑟雷尔的工作也获得了行业认可。2006年,美国博物馆联盟颁发了百年荣誉榜(Centennial Honor Roll),她被选为上榜的100位博物馆专业人士之一。上榜的理由是——“获奖者的工作支持了行业发展,并帮助美国的博物馆成为发现、启发、社区、快乐和终身学习的场所。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真正展现了对该领域的领导力和对公众的服务”。[2]
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说明牌、展览展品评估、参观过程数据分析以及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建构。她在这些方面各有著述,其中三本书聚焦说明牌主题,分别是《循序渐进制作说明牌》(MakingExhibitLabels—AStepbyStepApproach)、《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ExhibitLabels:AnInterpretiveApproach)第一版及第二版。在展览展品评估方面,著有《开放对话》(OpenConversations),《科学博物馆学习研究》(WhatResearchSaysaboutLearninginScienceMuseums)以及《试一试!通过评估改进展览》(TryIt!ImprovingExhibitsThroughEvaluation)。通过对观众进行无打扰的跟踪和计时,收集并分析关于观众参观数据以审视展览效果,也是瑟雷尔关注的重要方面。她所著《关注:观众和博物馆展览》(PayingAttention:VisitorsandMuseumExhibitions)一书,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她在职业生涯后半段比较关注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建构,《展览评判:卓越评估框架》(JudgingExhibitions:AFrameworkforAssessingExcellence)一书综合她以往著作内容,为建构“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现实标准。她近两年则关注了策展方面最基础的问题——主体理念,并于2020年出版了《主体理念》(TheBigIdea)电子书,尝试对此概念做出更加明晰的论述。
瑟雷尔不光著述颇丰,她还在《策展人》(Curator)、《观众行为》(VisitorBehavior)、《今日观众研究》(VisitorStudiesToday)、《博物馆教育杂志》(JournalofMuseumEducation)、《展览家》(Exhibitionist)等博物馆界知名学术期刊,以及美国博物馆联盟和亚太科技中心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上或单独或合作发表了80余篇论文及报告,彰显了其在博物馆界的学术影响力。
二、 关于本书
《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初版于1996年。彼时贝弗莉·瑟雷尔已在业界提供了12年展览咨询服务。本书在博物馆界备受欢迎, 因此2015年,出版商拟再版本书,并请她对第一版进行修订完善。
第二版与第一版的不同主要在于,关注了第一版面世后19年间博物馆学界的研究成果;更换全书配图;让博物馆相关人员撰写案例研究部分;提醒读者数字媒体的发展;而观众希望展品互动带有更明显的社交性质以及体验设计、信息设计、意向设计等展览设计新趋势正是博物馆专业策展人员今后要面临的挑战。
当然,瑟雷尔坚持并强化了本书第一版的结构与主要观点,因为她发现经过19年实践,这些观点并不过时,且为策展人员的说明牌设计与撰写工作提供了有益指导。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二十二章。第一部分为概述,界定了本书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包括“主体理念”“解说性说明牌”及展览说明牌的类型划分。第二部分分别从观众范围界定、类型细分、阅读层级确定、说明牌字数、多语种说明牌、如何撰写观众友好型说明牌、说明牌为谁发声等方面研究撰写以“观众为中心”的说明牌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第三部分从进一步提升观众体验的角度,就说明牌的层级设定、呈现模式、文字与图像的配合、其上所提问题、互动展品的说明牌和数字解说设备等方面展开讨论。第四部分重点描述说明牌的开发、设计、制作及评估过程,第五部分是结论,强调了研究与评估对说明牌整体开发过程的作用。
三、 本书对中国策展人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是北美博物馆说明牌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博物馆说明牌通常由对展览主题很熟悉的策展人撰写,但其缺乏说明牌写作方面的训练。因此说明牌要么字数偏多,要么简短得像“器物标识符”,它们的风格权威而专业,充斥着专业术语,观众往往难以看懂[3]。而博物馆人也不重视说明牌,有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卑微的说明牌似乎从未变成讨论的主题。然而,我们观众的大多数抱怨都是针对说明牌的”[4]。在此之后,观众研究与评估工作的开展让博物馆说明牌从之前刻板的教科书式风格向友好的对话式风格转变。
这种转变和社会发展及新博物馆学的提出相关[3]。首先,70年代后,北美社会文化的发展导致其需要建立新的方法和策略来处理各种文化内部和跨文化的关系。一些议题受到各界关注,包括“所有文化的平等性”“个体的与共同的”“内外之间的裂隙”“专家与普通人平等发声”“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平衡”等[5]。受此影响,博物馆对普通观众的重视程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其次,20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而1984年《魁北克宣言》的提出,标志着博物馆界对新博物馆学研究取向认同度的大幅提升。新博物馆学认为博物馆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工具,其核心是博物馆不是取决于“物”,而是取决于“人民”[6],要满足社区和社群民众的文化需求,提倡博物馆的大众化。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更加关注多元化人群的需求,说明牌更要发挥“解说”功能以实现博物馆与观众的有效沟通。由此也可理解为何瑟雷尔将“一种解说方法”作为本书副标题。
本书对说明牌的论述可从多个方面为我国策展人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说明牌范围的扩展与内容的精简
在以往观念中,“说明牌”特指放在展品或器物旁边的小型文字牌,而瑟雷尔在本书中,将说明牌的范围扩大到博物馆中与展览相关的各种文字说明文件。放在器物边的文字说明牌,在本书中被称为“示例说明牌(caption label)”,它与标题说明牌(title label)、介绍性说明牌[introductory label,亦被称为导向说明牌(orientation label)]、分区说明牌(section label)、分组说明牌(group label)一起组成了展览中的“解说性说明牌”。而“非解说性说明牌”则包括识别标签(ID标签)、捐赠者名牌、导向标识、常规标识以及致谢说明板[7]31。
“解说性说明牌”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它为解说服务,正如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工作的开创者弗里曼·蒂尔登(Freeman Tilden)所言,“解说的主要目的不是指导,而是激发;是呈现整体而非部分,并且必须针对‘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而非任何阶段。”[8]因此,策展人需要用整体性思维来设计和撰写解说性说明牌,标题、介绍、分区、分组及示例说明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分担了“解说”任务,所以不能如以前那般仅仅在示例说明牌上长篇大论,却忽略了其他说明牌的作用,而是要让所有“解说性说明牌”各司其责,共同讲好展览故事。同时,以“解说”思维撰写说明牌也意味着说明牌的功能不仅仅是提供诠释信息及鼓励观众参与,而是如现场讲解般更具有双向互动性。在本书中,标题说明牌标出展览名称,展览只应有一个标题且在所有材料中保持一致;介绍性说明牌应确定展览的架构和基调,其应放大印刷字号并提供简短的展览结构和定位信息,便于观众从远处阅读;分区说明牌介绍展览中的各个主题或区域,要将它们放置于观众视线之内;分组说明牌重点要回答观众“为什么将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展示?”这一问题;示例说明牌是特定物品的特定说明牌,它们应该涉及所要讨论器物的可见细节,而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的那部分,对示例说明牌信息能起到支持作用的分组和分区说明牌,应放在其附近[7]32-36。
如果每类解说性说明牌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则它们的篇幅长度完全可以大幅缩减。20世纪70~80年代,有不少学者针对博物馆说明牌的长度开展了实证研究,如斯蒂芬·比特古德(Stephen Bitgood)、明达·博伦及玛丽安娜·米勒(Minda Borun & Maryanne Miller)、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Hodges)等在安里斯顿自然博物馆、富兰克林研究所、米尔山儿童动物园,包括瑟雷尔自己在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研究都表明,与字数多的说明牌相比,观众更倾向阅读字数少的说明牌,并且说明牌上的主题越多,观众阅读的可能性就越小[9]。
瑟雷尔提出,根据研究,在有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一位成年观众站着阅读母语的平均速度是每分钟250个单词[7]97。策展人需要根据展览面积、观众一般参观时长确定所有解说性说明牌的总字数,再用总字数除以展品数量由此确定每一件展品说明牌的平均字数。因此她建议,标题说明牌的字数为1~7个单词,介绍性说明牌为20~125个单词,分组说明牌是20~75个单词,示例说明牌也是20~75个单词[7]43。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建议并不仅适用于博物馆,对科学中心的互动展品而言同样重要。瑟雷尔在本书中提到了美国探索馆的研究。他们发现:“减少对解说的强调或缩短解说的总长度可以增加观众积极调查的时间”,“与篇幅长的说明牌相比,短的说明牌则更会被完整地阅读”,“用图表说明观众与展品的互动,帮助观众弄明白该怎么做”[7]193。
因此他们在改进说明牌时,使用线条图代替某些展品的操作说明,如以下这幅如何放置小球的图示就替代了大段说明文字(见图1)。

图1 探索馆示例说明牌上对图示的应用
再比如这件名为“光岛”展项的示例说明牌,探索馆在多次测试评估后改为以下版本:[7]194
光岛
与光束一起玩耍吧
你能把白光分解成其他颜色吗?
用反光镜将一束光反射到中心光源周围。
你能将一束光反射多少次?
试着用光线“画”一个字母“W”。你还能用光画出什么形状或字母呢?
试着混合不同颜色的光。你能发出黄色的光吗?
你能使光束聚焦吗?也就是能让光汇聚到一个点上吗?
作为体积较大、形状不规则的开放式展项,“光岛”(见图2)用包含六个问题的简洁说明牌引导观众依次通过对光的不同操作进行实验,说明牌与展项设计完美契合,同时也防止过多互动元素分散观众注意力。如此设计传递的理念是——说明牌最重要的不是告诉观众信息,而是要促进对话,使观众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他们自己的假设。因此,篇幅过长的说明牌同样不适用于科学中心。

图2 探索馆开放式展项——“光岛”一角
近年来中国研究者及业内人士也意识到了说明牌的篇幅问题,如许璐[10]、王磊[11]、王劲松[12]等都提出目前博物馆说明牌文字偏多,内容庞杂,不利于观众形成理解。不过对此问题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比较突出的是张颖在西湖博物馆开展了观众参观时长计时跟踪研究。参考瑟雷尔的结论,她认为单个展品中文说明牌的文字不要超过45字,展板以100~140字为宜[13]。但此结论尚未经过严谨的论证,距离应用于实践也有较大距离。而针对科学中心说明牌的定量研究则几无可见。
(二) 主体理念应贯穿说明牌撰写过程
瑟雷尔认为主体理念“清楚地阐明展览的范围与目的,从而为整个展览团队的开发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焦点。”[7]7它是一个完整的、非并列的主动句,包括一个主语,一个动作(即动词)和一个结果(“所以会怎样呢?”)。如“我们对宇宙的所知大多来自于对光的解读”“作为一种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健康的湿地将会为人类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这样的句子就是主体理念。主体理念与“展览主题”类似,但并不完全等同。因为主体理念强调展览必须对观众有一个“结果”,即回答“这个展览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所以说明牌需要和观众的自身经历建立连接,以帮助他们实现自我意义构建,而不仅仅是对展览内容的高度概括。
主体理念为展品开发及说明牌的创作提供方向性指导,“每件展品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支持、例证或说明主体理念的方方面面。每一件展品的组成部分都应该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即‘它与主体理念有什么关系’”。[7]12
为什么主体理念如此重要?是因为瑟雷尔认为博物馆内说明牌数量偏多、其上所书内容主题多、碎片化,说明牌之间缺乏逻辑关系等问题,乃是由主体理念的缺失引起的。在展览开发各个环节(包括在说明牌撰写、设计时)坚持主体理念,则可有效解决以上这些问题。瑟雷尔还提醒说,儿童博物馆和科学中心更需重视主体理念的确立。这些场馆的展览往往被开发成“观众喜欢且不容易被损坏、巧妙而又价格实惠的设施”,但玩得开心并不是评估展览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希望呈现教育意义的展览,如展品之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则不利于观众在参观中完成自我意义的建构。
在瑟雷尔之前,已有学者对“解说主题”有所考虑。比如与弗里曼·蒂尔登同时代的威廉·李维斯(William J Lewis)认为“制定一个主题既能提供组织结构,又能使人清晰地理解。一旦选择了解说的主题,其他一切事情都会水到渠成……通过撰写主题,可以缩小和细化你的话题”。[14]而“解说主题”应该始终用一个完整的陈述句来表达,回答关于被解说事物的“那又怎样?”的问题。学者山姆·汉姆(Sam H. Ham)评价威廉·李维斯的想法促成了讲解领域的范式转变[15]108,因为李维斯将“解说主题”视为一个概念性工作,讲解人员进行创造性的解说规划时,可以利用它做出更好的判断。由此可看出瑟雷尔对“主体理念”的阐述很可能受到李维斯“解说主题”的启发,二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线解说员在多年实践中也认识到“主题”的重要性。他们用各种术语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如“大画面(big picture)”“中心理念(central idea)”“主要信息(main message)”“情节结构”(plot structure)等[15]111。这些概念运用于说明牌创作中,即如路易丝·拉韦利(Louise Ravelli)所言,每一个展览文本都必须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对应的就是瑟雷尔的主体理念,它为所有展览和说明牌的开发提供支撑。如今绝大多数博物馆策展人会在展览设计中考虑整体目标,重要的是将这种考虑延伸到文本结构中[16]。
(三) 观众研究与评估是撰写以“观众为中心”说明牌的有力支撑
观众是博物馆的服务对象。瑟雷尔认为,博物馆说明牌首先要满足观众的共性需求,然后再针对观众不同类型的需求服务。在共性需求方面,观众生理上有对身体舒适性及无压迫感空间的需求,参观会带来饥饿及疲劳感;在情感上,他们有对连续性的渴望、对好故事的热爱、发现和寻找模式能力的体现以及通过个人挑战达到自我实现的渴求。
观众在共性需求被满足后,会因学习风格、思维方式、动机及偏好方面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类型。在本书中,瑟雷尔列举了多个从不同维度划分的类型,如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多元智能理论描述的7种个体思考方式;约翰·福克(John Falk)创建的包含5种观众身份的模型;泰特博物馆(Tate Museum)的8个细分观众群体;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的5种观众类型;谢德水族馆(Shedd Aquarium)的6种观众群体;史密森尼学会安德鲁·佩卡里克(Andrew Pekarik)的IPOP(Ideas,People,Objects,Physical)观众体验模型等。
但是观众细分并不意味着说明牌只能专注满足某一类型参观需求,好的展览可以满足多种类型,关键是为观众提供清晰可见的、可叠加的多种选择。在此基础上还需考虑观众的参观偏好,包括他们是否喜欢按顺序参观、是否接受对参观节奏的控制、是否喜欢专家语气的引导、是否喜欢以语言刺激参观行为、他们在行为上偏好积极参与还是间接观看以及对嘈杂环境的忍耐程度等[7]78-82。研究清楚观众需求及行为偏好后,才能在说明牌的撰写与设计的实践中确定说明牌的阅读层级、字数、版式、材质、摆放位置及照明亮度,解决站在何方立场发声、是否提出问题、是否使用多语种、是否在说明牌中使用图示、是否使用数字解说设备等问题。
过去百年间,西方观众研究的方法从定性转为定量再到两者结合,关注内容从本杰明·伊夫斯·吉尔曼(Benjamin Ives Gilman)提出的“博物馆疲劳”到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S.Robinson)和亚瑟·米尔顿(Arthur W. Melton)的观众行为分析到阿尔玛·维特林(Alma Wittlin)的观众对话研究,再到后来各种观众博物馆学习与体验理论的提出,如乔治·海因(George E.Hein)的建构主义博物馆学习理论,约翰·福克(John Falk)与琳恩·黛安·迪尔金(Lynn Diane Dierking)的互动体验模型,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基于观众文化背景的博物馆体验民族志研究等,可以看到观众研究手段日益丰富,对其他学科的借鉴日益明显和深入,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均对这一领域发展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多学科融合的观众研究成果为展览说明牌的撰写和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武器。
我国博物馆在20世纪50年代即意识到要针对观众需求提供讲解服务。如黎明在1956年即提出,“如对小学五、六年级学生讲解同样的,对工人讲解应采用‘重点讲解’‘具体简要’‘通俗易懂’等方法;结合工人的生产情况,重点地进行讲解;通过讲解应使工人对祖国历史获得一个概括、全面、系统的了解。”[17]这些做法完全符合瑟雷尔对说明牌的要求——篇幅简要、用词易懂、与观众自身经历建立连接,最终形成完整的自我意义构建。可惜当时博物馆界并没有借此将研究引向深入,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出现关于观众研究的成果。如陆建松[18]、严建强[19]、史吉祥[20]、王娟[21]、郑奕[22]等人从观众满意度调查、展览教育活动效果、观众数据收集及分析等角度切入推动了我国博物馆观众研究工作。不过也应看到,总体而言我们在这方面还处于“为研究而研究”状态,“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23]。反映在说明牌研究方面,则是学界“尚未出现专门围绕说明文字,强调问题系统解决的应用理论专著”[24],前路漫漫,还有更多基础性工作要做。
除观众研究外,另一项工作对做好说明牌撰写及设计也非常重要,即“评估”。《博物馆说明牌》全书有240余处提及“评估”一词,除第18章和第21章的评估工作专论外,此词散见于全书各章,足见瑟雷尔对此项工作的重视。1990年,钱德勒·斯克里文(Chandler G. Screven)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前置性评估(Front-End Evaluation)、形成性评估(Formative Evaluation)、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Evaluation)及补救性评估(Remedial Evaluation)对应展览的策划、设计、施工安装、占用、补救阶段的评估模型[25]。该模型因为清楚实用而逐渐被博物馆界采用,瑟雷尔在书中使用了本模型对说明牌进行评估。
她认为:在展览项目深入展开之前,通过前置性评估研究潜在观众的当前状态。开发人员可得知观众现有知识水平、对展览的期待,以及他们的词汇在描述某个特定展览主题时所达到的程度;在展览开发和说明牌文本撰写同时开展形成性评估,能够对说明牌文字进行微调,以保证操作说明、信息内容以及词汇水平等与前来参观的观众相符合;展览开放后,开展总结性评估,可以对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进行补救,验证关于观众参观和展览影响的假设,同时还可以比对展览的成功之处[7]247。
在评估方式方面,瑟雷尔推荐在前置性评估中使用小样本观众访谈、焦点小组、观众小组等方式;在形成性评估中于展览实地测试说明牌原型,观察观众使用说明牌的实际情况,采集相关数据,询问观众意见,再根据意见做出调整和改进;总结性评估可以使用问卷、访谈、观察、计时跟踪、聆听观众对话、分析观众所摄照片等方式进行。
目前我国学人已经开展针对展览的评估研究,如边晓岚对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展览选题的前置性研究[26],施娴泓在某馆“物联网”科技展厅使用跟踪计时法开展的评估[27],赵星宇、姜惠梅、席丽对山东博物馆2018至2019年展览的教育效果评估[28],胡芳、宋娴对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展品信息可达性的定量评估指数体系构建以及针对上海科技馆“宇宙之谜”和“两栖、爬行动物”两个展品开展的实证研究[29]等。这些研究的出现表明我国学界对展览评估日益重视,但距离形成评估体系以及提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情况下,瑟雷尔关于说明牌评估的建议为我国学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方向指引。
四、 结论
贝弗莉·瑟雷尔作为资深策展顾问和说明牌撰写人,其《博物馆说明牌:一种解说方法》一书可视为说明牌撰写的实操手册。对我国博物馆人而言,可从本书对说明牌范围的扩展与内容的精简、主体理念在撰写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观众研究与评估为说明牌撰写及设计提供有力支撑等方面得到启示。应该看到瑟雷尔在本书中所提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取得离不开北美社会文化发展及新博物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而西方博物馆界长期观众研究和评估工作的发展为她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这些都值得中国博物馆界借鉴。中国科技馆组织翻译的本书中文版即将出版,感兴趣的业界同行可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