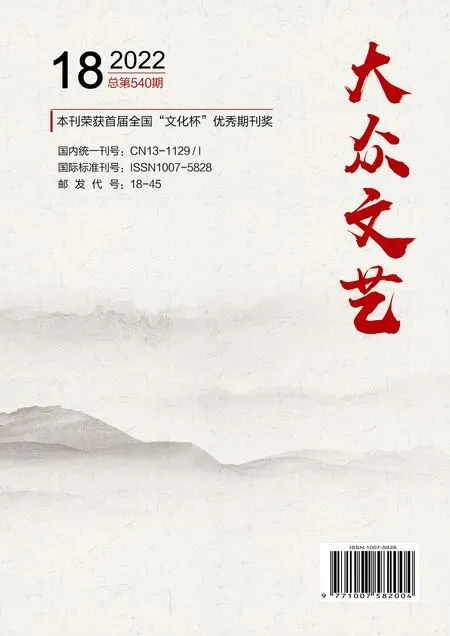冲突的悬置:另一种荒诞派戏剧文本
——以《花园宴会》为例
刘 畅
(南京大学,江苏南京 21093)
20世纪以来,戏剧进入了一个自身维度的新时代,即“后戏剧时代”,戏剧文本虽然不再成为戏剧的唯一指涉,但“后戏剧”文学依旧没有摆脱传统戏剧文体,它在戏剧中的存在形态成为一种评判机制。直至荒诞派戏剧的出现,这一局面才被打破,传统戏剧文体不再是独一无二,这种戏剧的新文体提供了一套新的语言方式和新的观念。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发展而成的戏剧流派,是二战后西方异化的物质文明对人精神造成的压迫的产物,马丁·艾斯林在辨析荒诞派戏剧概念时总结了几个特征:形而上痛苦感的题材、抛弃合理方法和推理思维、呈现人物语言与舞台事件的矛盾性,且每位剧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独立于其他人,参与建立了一种新的戏剧程式。
作为戏剧家的哈维尔并不如贝克特那样有名,他的作品通过反讽式的幽默呈现出尖锐的政治讽刺剧,有规则的结构和语言成为其特征。《花园宴会》是哈维尔独立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剧中背景为东欧极权时期,在高压政治的挤压下,主人公雨果学会说“废话”的能力,便得到了一种高人一等的权力。剧本中弥漫着大量生活中产生的废话,无理的文字堆砌和的结构逻辑使冲突被悬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戏剧语言的含混性,二、情节结构的对称性,三、符号的背后的悲剧性。
一、含混性:语言的错位与重复
传统戏剧语言具有动作性、艺术性的特征。动作性语言要引起冲突发展、推动情节进行,艺术性语言按照丁西林的说法,必须把平时的讲话或多或少的加以艺术化才能算是戏剧语言。在传统意义上的戏剧中,优美的语词与有目的性的、冲突性的话语成为人物对话的主要语言。
《花园宴会》中,通篇使用了含混性的语言,例如“可以了吗”“怎么样”“情况很糟”“你到底想干嘛”“你听到没”“没错”等短句。含混性即日常语言的本质特征,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场合都无法区分语词所描述的对象,不能与描述的对象之间的精确边界。哈维尔剧本中的语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日常语言,而是经过编排的、艺术加工后的、具有含混性的戏剧语言。在《花园宴会》的四幕中,每一幕都重复出现了许多日常的废话,例如“怎么样”14次、“没错”11次、“现在几点了”8次、“多么引争议的字眼”7次“不过是聊聊”6次、“听到了吗”5次、“可以了吗”5次、“那到底是谁在清算部?”4次、“你抽烟吧”3次,这些短句出现于剧本中,对剧情并无推动的作用,反而大量相似的语言堆砌,比日常语言还要夸张次数的出现,相同的句子不断在几个角色中游离,说话者不再说自己的话,他们只是在复述语言。整体来看,第一幕出现的含混性语言是最多的,剧作家有意使语言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压迫感,这与剧本发生的背景相呼应。“我对戏剧结构的强调,我的剧作中便有了一种接近音乐的成分……我喜欢将对白扼要重复,使其交替出现,借某个人物之口道出另一个人物的话,然后再由自己说出。”语言的错位与重复使剧本充满了混乱感,似乎这句话在另一个人口中说出对事件也不产生任何影响,被日常语言所奴役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动作性的冲突,极大的废话的比例使这些日常语言的组合变得荒诞,例如剧本中第一幕雨果自己与自己下棋时,父母与他的对话:
伯鲁岱可娃怎么样,现在到底怎么样?
雨果情况很糟糕,真的很糟糕。非常非常糟糕。
伯鲁岱可娃怎么样,现在到底怎么样?
雨果好得不得了,别担心!(移动棋子)死棋!
伯鲁岱克输了?
雨果没有,赢了。
伯鲁岱可娃赢了?
雨果没有,输了。
伯鲁岱克你到底是赢还是输?
雨果既是这边赢也是这边输。
这是一段对情节发展没有任何推动作用的对话,人物在做着无意义的事情,麻木地反复说着相似的话。传统的戏剧剧本中,剧作家要把台词写得具有趣味性、可读性,但在哈维尔的剧本中,将废话提升出来,故意制造逻辑的错误和不协调,让我们意识到废话在生活中的比例,以及其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可怕的。同时,除了压迫感,语言还在结构上承担了前后情节呼应的功能,这段对话与之后雨果在花园宴会中的一番说辞形成了互文性。在第二幕中,雨果掌握了说废话的能力,由此获得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既A又B”的说话方式与第一幕中“又输又赢”的对话前后呼应,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巧合的美感。
柏格森认为语言是事物本质的障碍,它把外物的真相从我们眼前障住,使我们只能看到精神状态的外表,而无法认识心里最内在的、人格的方面。在这种观点下,日常语言作为人生活基本的交流方式,并非人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达,而是一种加工手段,是一种精心雕琢过的外像,是在惯性中逐渐构建的社交话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语言工具的不信任使自古希腊以来的戏剧语言模式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基于确立人物关系而书写的对白语言转变为展示自我存在感的直觉性语言。荒诞派戏剧呈现的是剧作家基于自我处境而生成地对世界认知的感受,哈维尔的作品区别于其他荒诞派剧作家所呈现的,是基于极权时代下对语言的变态控制而产生的压迫感,它们往往是由日常语言堆砌而成的日常生活景象,反射着在极权挤压下的人们如同小丑般异化的生活方式。
二、对称性:情节的结构与逻辑
情节,即事件的安排。自古希腊戏剧时期起,亚里士多德便在《诗学》中将情节作为悲剧六要素中的第一要素,认为它是对行动的模仿,直至19世纪末,这种以人物的自觉意志为行动本源的传统戏剧形式才有了转向——叙事化倾向的戏剧危机。斯特林堡在自然主义戏剧《朱丽小姐》前言中提出与自己要写一个“缺乏个性”的人物,即一个不能用单一词汇描述的人物,这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性格配合行动”的戏剧形式。也就是说,剧本中的情节不再是人物性格的全部展现,朱丽小姐的悲剧缘起于多重因素,而这些因素并无必要在剧本中作为情节出现,因此,情节结构可以根据剧作家主观需求进行调整,它可以是跳跃的、不连贯的,这一观点直接打破了传统戏剧创作的思维模式。荒诞派戏剧作为象征主义戏剧衍生出的戏剧流派,继承了反传统戏剧标准的形式,将逻辑和理性抛诸脑后,跳跃式的情节和混乱的语言结构以直喻的方式呈现人类异化的荒诞性,打破固有模式的叙事方式,使读者不再沉迷于情节的发展中,而是能跳脱出情节看待戏剧本身,即跳跃式情节所带来的间离性。因此,《花园宴会》中的情节虽不连贯,但却是在一种形象化的模式中按照有逻辑性的结构进行表达,以一种简单明晰的方式来看(如表1):

表1
从整体上来看,剧本以对称式的时间节点呈现,碎片化的事件通过时间顺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结构,通过想象来补充那些隐去的情节:父母让雨果去参加花园聚会寻找卡拉毕斯——(卡拉毕斯不来的原因)——雨果评论伯扎克与男女书记的聊天并得到肯定——(雨果升官)——雨果以领导的姿态与清算部主任侃谈——(如何废除清算部)——建立了清算与开幕致辞中央委员会。剧中的对白语言并不能解释人物行为的动因,情节的缺失使剧情看起来荒诞无理,充斥着日常废话构成了对白的大部分,毫无感情的对话宛如被代码操控,在重复的语言堆砌和无厘头的情节发展中,剧中人物变成了语言和行为的机器,而真正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却被隐去。这样的情节结构必然会造成人物性格的缺失,或者说人物的自由意志不再是决定他们行为的全部,这正是荒诞性的根源,即当时社会环境与人的分离状态,因此主人公雨果以一种近乎雄辩的方式取得晋升时,它的过程便显得不再重要。哈维尔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无言地讲述着那些无法表达的东西——雨果参加宴会时做了什么行动使情节向高处发展?清算部又是如何被清除的?如果按照传统戏剧文体的书写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结构:雨果为参加花园宴会筹备——在花园宴会上用花言巧语使自己晋升——用得到的权利废除清算部——回家与父母交谈,显然,这样的结构会使表达的重心偏移,变成人物的成长史而非对极权环境呈现。
在搭建具体的情节时,哈维尔选择了一种聚积式的方法,通过情节的累积使情节的意义链条中断。例如在第二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出现了三次:
伯扎克大门口有什么新鲜事吗?你们在玩什么?还是在聊天?花园宴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书记谢谢,不过是聊聊——
女书记不过是聊聊——
这段对话在同一幕中反复了三次,每次都以不同的事件展开,第一次聊到生育、第二次聊到大自然、第三次聊到艺术与科技,情节结构的反复在戏剧中出现,通过反复的形式讽刺日常生活中的废话比例与生命的无用感。荒诞的人物对白在阻断剧中人物交流的同时,也阻断了观众与人物的交流,形成彼此间离的荒诞关系。尽管如此,哈维尔还是以一种缺席式的情节和对称式的结构,构建了一套自我逻辑,在第一幕中父亲提道“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栋梁”,在第四幕中又提道“他的血液流的是健康的中产阶级”,对称式的语言在结构上形成了前后呼应的对仗,看似荒诞的逻辑实际上正是捷克社会当时的现状。
三、悲剧性:符号的明喻与隐喻
荒诞派戏剧是战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戏剧领域的典型产物,最根本的特征是运用直喻(直接表现)的方式,以非理性的情节结构、舞台形象和语言来表达存在主义关于世界的荒诞性的哲理。同样是表现社会对人的异化,哈维尔不像贝克特或尤奈斯库一样塑造具有反差感的、特别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展现经由权力挤压后不得不产生的“废话”,对人的命运的极大改变,更关注的是捷克高压政治下人和人交流的变态,用非理性的形式“直喻”,展现权力机制对人的异化,被权力挤压后不得不产生的废话和60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荒诞感。
除了直喻,剧本中的背景、部门、人物也变成了抽象的符号:故事背景——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语言——权力,清算部——实干、理性,开幕致辞中心——虚无、谎言,父母——麻木的人,雨果——学会说废话的人,主任——趋炎附势的人,男女书记——随波逐流的人,哥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丑鼻子(道具)——人虚伪的面具。在人物的背后,指涉的是发生在捷克的社会现象,如果说“贝克特们”的戏剧来自二战后人的异化,那么哈维尔的戏剧则来自东欧极权下被后现代所挤压的人的变态,“你难道忘了吗?现在时代可不同了”这种变态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处,人们关心着无意义的事情,“开幕致辞服务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任务里,是扮演着捍卫人类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使命!”吹捧着掌握权力的那一部分人,“我们在您身上有太多东西要学了!”,也充满着人情的冷漠,“难道您希望我会替您向上提报?如果您因为什么错误的英雄主义而自掘坟墓——那我好好告诉您——我是不会提这种事情担保的”,哪怕在面对家人时也是冷漠的态度,“所以有一个布尔乔亚总比没有好,至少政治上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花园宴会》最初的写作动机来自伊万·维斯科切尔,他谈起行贿受贿的现象,并希望哈维尔以此为主题创作一点东西。按照哈维尔的说法,在当时捷克的社会背景中,作家代表民族道德良心的思想,他们代替了政治家:他们创造了捷克社会,保持了民族的语言,唤醒了民族的道德心,表达了民族的意志。“这种情况一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延续着并因此带有其自身的色彩:他们所写的东西似乎获得了一种加强了的辐射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极权主义者们便会把我们关了起来。”尽管剧中处处充斥着人的愚昧物质所带来的怪诞的喜剧感,但它却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性,当人在极权的压迫下不得不变成一个复述语言的机器,当语言因为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变成堆砌的废话,当生活中因充斥着废话而失去了意义,被异化的环境所异化人该何处寻找丢失的自我?在哈维尔的剧本中,可以看到处于危机状态的现代人,他们缺失了对知觉的肯定、对感情的信任、对意义的抗拒、对权威的畏惧、对秩序的服从,哈维尔正是通过以反抗极权的现实需要去重新解说悲剧的现代政治哲学意义。
结语
从结构上来看,台词语言的重复与表述者身份的混乱,使文本在同一时间中呈现出空间的层次感,脱离了传统戏剧的沉浸感;事件的缺席打破了传统戏剧文本的情节连贯性,沉默的事件曲折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整体上来看,剧本中设置的人物、事件、发生背景,具有象征意义。由于事件的缺席、情节的割裂、语言的断层、性格的缺失,戏剧文本中的冲突被悬置起来,以沉默的方式讽刺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后极权主义,形成了带有悲剧色彩的荒诞感。哈维尔在自传中阐释了人的荒谬感与其生命意义的关联,“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他在剧本中所书写的“荒谬”是对于意义缺乏的时代现状的反讽,是对于自我灵魂的一次拷问,是对于生存意义的一场审判,剧本中的时代和人物俨然成为历史图像的一角,但这部带有悲剧内核的荒诞派戏剧依旧可以在当代的语境中再次被审视。
①有三种翻译版本:《花园宴会》《花园聚会》《游园会》,本文采取第一种翻译方式。
②贝嶺主编,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M] .倾向出版社.
③贝嶺主编,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M].倾向出版社:81.
④贝嶺主编,哈维尔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M].倾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