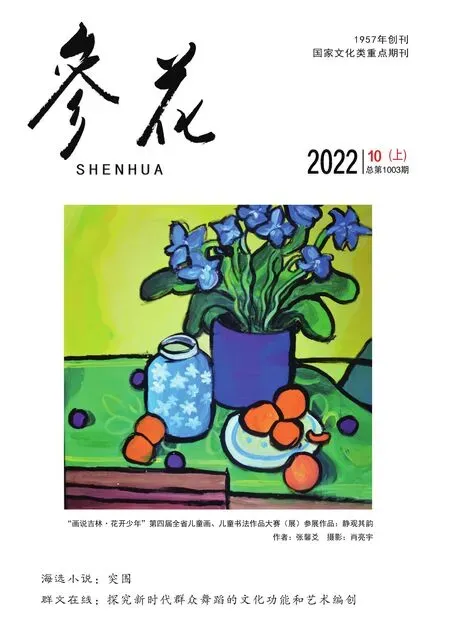六棵树
◎李治本
行旅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牵绊在心中,古树年轮的纹路,似文人苍劲笔杆下的句读,讲述一个故事,见证一段历史,记载一段传奇。故事已远去,树还在!
榧树
石鼓香溪是个避暑佳地,唯山真水,清澈盈人。每逢盛夏,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生热闹。
石鼓国家森林公园,野生树种繁多,黄檀、木荷、红果钓樟、铁冬青、南方红豆杉等随处可见,少则百年,多则千年,但榧树仅一棵。
探寻榧树,得要徒步几十里盘山路。脚下的山石路,显然是几年前修建的,蜿蜒穿梭在森林峡谷中。两谷青树翠蔓,蒙络摇缀,溪谷沿山石径并流,汩汩流动,森森龙吟,若隐若现的蒙蒙雾气,自下而上浮荡着枝叶。
按当地林业部门检测数据推算,这棵榧树植于北宋真宗、仁宗年间,似与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先生同到人间。苏东坡先生在杭州、湖州一带做行政长官时,就对名贵香榧知之甚深,视为至宝。
在远离人烟的幽谷里,我跨过六道碇步,踏踵沟壑六峦,荆棘载途,傍晚时分方见到这棵静影斑驳的榧树,“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凝视其躯干,心若静莲,世间可还有比与千年之眼对视那一瞬更奇妙的瞬间吗?
榧树超拔特出,独秀于林,耸峙土墩上,底部像圆形的打谷桶一般巨大,苍虬的枝干,上下左右伸展。它的高度,在于它的精气与内涵,在于它无可名状的特征,独一无二的躯体翩若惊鸿,虽沉默不语,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它才是石鼓之神、香溪的主人。
榧树周围茫茫森林一片,唯有一座寺庙紧挨着,梵音袅袅清润尘心,琼香缭绕瑞霭缤纷。这座寺庙,取了非常大气的名——龙王庙。龙王庙一般都建在有水的地方,而此地却是深山幽谷,为何建龙王庙?也许只有榧树目睹心明。
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山下的民众,便翻山越岭来到龙王庙焚香祈愿,求龙王治水,雨顺风调。这些民众,来到榧树下许愿祈福,将一条条象征吉祥、美好的红丝带缠在树上,乞求所愿,感恩所得。人如何用心,如何言行,必受何果报,一切众生就是在这果报中周而复始,言为心声,行必心使。
榧树的种类有米榧、香榧、圆榧、芝麻榧,唯以香榧最名贵,其材白色纹理甚美,且有香气,斐然彰彩。据《本草纲目》上说:“香榧子常服,治五痔,去三虫蛊毒,鬼痔恶毒……明目轻身……”
不能结果的香榧树,只能称榧树。虽如此,当地人亘古至今都称这棵榧树为香榧树,因为石鼓香溪的“香”字由来,与榧树密切相连。抑或这棵榧树,曾经也结过果,只是后人不得知而已。
榧树,四季常青,在石鼓峡谷中滋长千年,确是人类无法想象。它大气磅礴,欲静而不止,以不变应万变,在风中摇荡,与日月清和。
夜色蒙蒙,野性未泯的小生命,紧贴地面在那里蛰伏,旋而枕着粗壮的树根酣眠,静候它们的黎明。与之相依,沉入梦呓,黎明会被久长悠远的呼鸣唤醒。一天之中,清晨最值得感今怀昔,是让万物醒悟的最好光阴,心怀对黎明的无限向往,是每个生命的希望。只有苏醒才有黎明!
夜的脉动,生命的吟唱,以及山风的飒飒作响,一切相符相应,相因相生,毫厘不爽。
通透的绿,优雅萦然,结实的梦,清晰罗布。树的精神,是由文字流传下来的;人的精神,是从大自然中折射出来的。
枫香树
群山苍苍,静谧安恬,凹坞中的枫香树,昭然可见。一种如焰的斑斓,渲染了山村秋色,也染红了村民的心扉。
散落林壑深幽的民居,相距少则几十米,多则好几里,有青砖黛瓦,有夯土墙屋。户与户之间不叫邻居,称上屋、下屋,是村民安身立命之家。家的意义,无论多么僻壤,多么简陋,总是温暖的,无法舍弃。家,离自然越近,离喧嚣就越远。
清雾的微晨,舍屋炊烟逸出,缕缕丝丝,在山坳的森林中盘桓缭绕,家犬吠叫,晨鸡啼鸣,从凹坞上空传来,天幕高迥邈远。这种烟火气息,简约纯粹,这种原生态的氛围与城市喧哗如若两界,透出纯如自然的美好意蕴。
房前屋后遍布花草树木。一座小山丘长有三棵古树:一棵是松树,一棵是苦槠树,另一棵最大的是枫香树,有三十五米高。枫香树的雄伟挺拔和丰神俊朗,昭示了它的地位与神圣。当地村民对它爱护有加,一代一代地传承,还在树的根部修建了一座“土地公殿”,供奉土地公、土地婆,乞树生福,天平地安。出于对枫香树的膜拜,村民为孩子取名字时,不乏取个“枫”字的,寓意日后如树成材,成龙成凤,枫香百里。
到了晚秋,枫叶垂垂地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借以阳光的反射,捕捉到一种明艳的瑰异色调,红得无可比拟,黄得难以言状,如丝绸的褶皱色彩多变,又似寒栗的剑锋变幻莫测,连天宇的蔚蓝也相形见绌。
草木葳蕤而深秀,枫叶静美如处子。山村的孩子们,欢天喜地穿过村庄,越过坞口去看枫叶。此刻的枫香树,是霜秋时节最为灿烂、蔚为艳丽的时候。它伸长着枝叶,从四面八方指向天空,在黎明的曙光中熠熠生辉。无论从哪个角度,观赏它红黄色的斑斓,都能令孩子们感受到整个村庄如同火焰般燃烧的盛景。那叶似乎在为山村提供艺术范式,为孩子们讲述自然课程,由浅入深,由里及表。枫叶寥廓如许,童耳锐敏如斯。
枫香树的感召,让我不愿在村民家中逗留,举足前往。围着山丘,悠然漫步于枫香树下,为各种心境找到回应和表白,只有在这里才能清晰地、自由地欣赏到光射之下的别样秋韵,深谙红枫叶灿亮的醉意。人与自然越靠近,行止举动似乎越有自然意味,于是息调一致,自然而然。我不想离开枫香树,而枫香树也不愿离开这深山密林。我想说,人在领受过自然的静穆和恬适之后,绝不会宣讲乏味的教义。
心外无树,树外无心。欲探枫香之心,来不得半点浮躁,来不得一丝轻慢。时光流转大自然,不断地书写着各式习俗故事,穿过漫长年光的古树,也总是被赋予神秘色彩,它们宛若奔放不羁、泼辣豪纵的天才手笔。
暮去朝来,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想起从前的过往,思念自己的家乡。枫香树在大山孩子的眼里,无论在海角、在天隅,都早已深埋心底,成了乡愁记忆、眷恋符号。每当归来,他们都要到树下走走,与之合影,然又带着它再次远走他乡。天地与我同根,万物皆吾一体。
柞木
柞木,多产于我国西部、中部至东南部,而在南方的清湖码头石墈上竟生长了数百年,实属罕见。它伴随着清澄的清溪段须江水,见证了清湖码头的繁荣兴衰,烙刻着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三经清湖的足迹。
素有“上海大码头,清湖小码头”之称的清湖码头,能和响当当的上海码头并称,足见当年之繁华。它是连接钱塘江南源的水陆转运枢纽,也是浙江进入福建最后一个可通行大帆船的码头,有千余年历史。
夕阳西坠,余晖柔柔,须江水面漾漾灿灿,大大小小的船只纷纷靠岸,晚归的鸟儿悄悄地落在繁茂的柞木枝上,等候明天的朝阳。播撒美好憧憬的,不光是艄公,还有鸟儿。
艄公刘对予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哼着小曲信步回家。刚要离开江边,只见最后一艘鸬鹚船轻轻靠岸。鸬鹚船和华丽的茭白船相比,朴素狭窄,未引起刘对予的注意,反倒一位比他高许多的船客,吸引了他的视线。定睛打量,这位陌生人,四十上下,目光如炬,炯炯发光,透着力量和自信,一看便是一位不寻常的外地客。
外地客礼貌地向他作揖,自称姓徐,江阴人。刘对予笑言:“江阴有个徐霞客,听说不爱功名爱山水,一生好入名山游……”听罢,外地客连忙道:“惭愧惭愧,鄙人就是徐弘祖,号霞客。”
一缘一会,一面如旧。两人走到码头边的石块上,就石而坐。码头星罗棋布,江水滔滔不绝,两岸郁郁葱葱,天然良埠的港湾在眼前浮跃。徐霞客不禁感怀,眼中的清湖犹如家乡,水陆交接,船来人往,闲云潭影。刘对予谙知徐霞客钟情江山,无怪他三次到访。徐霞客第一次还是和其叔父徐芳若一起来的。
言之浅深,情之所钟。一阵秋风拂过,树枝摇曳微颤,朵朵卵形花萼簌簌飘落,两人恍然发觉,原来头顶之上竟有棵根深叶茂的柞木。树木伸长着躯干,静听他们的对话,默而识之,欣欣然。
日月照临,柞木成了他们友谊的见证,也成了他们来日不见不散的承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斯人已矣,不复临兮,但柞木一定还会记得这位翩翩披霞之客。
时间不随人意而停留,而柞木的绿荫,是循着光阴的变化而驻足的。澄莹的江水,带着柞木的思念和向往,流向钱塘江,汇入东海。
柞木,有棘刺,叶卵形,边缘有锯齿,树皮呈棕灰色,叶子青翠欲滴,叶薄革质,纹理美观,初秋时开黄白色小花,花梗极短,花丝细长,花药椭圆形,喜光耐寒,具有抗腐耐水湿等特点,是奇特的木本植物。盘根错节在石堪里,吸取泥石精华,勃发而刚劲挺拔。
每次去清湖码头,我总要去看看柞木。看它任随季节的流转,树叶却苍翠常青,而树根越来越深入地扎向石墈内里,以昂首的姿态,与巧夺天工的石拱桥、古韵悠悠的清溪锁钥遥相呼应。清湖古码头的气息,萦绕着青砖黛瓦,还有那苍穹的蔚蓝,总让我悦目娱心。
流水声就像美妙的音符,不断地流进我的耳朵。坐在徐霞客坐过的石改壁上,遥想当年,我的思想像天空那样清澈、鲜活、高远,领悟能力像江水那样广博廓大。天空一群大雁,以百舸竞帆的造型,由北往南向暖迁徙着,在柞木上空留声回望。那由树魂内生发的幽香,从缄默的枝干、成绮的霞光中和着清惠的微风缓缓弥散开来,馨香盈怀。
阅柞木,观码头,在迟暮的秋天,因为一簇簇娇嫩的黄花辗转回眸,雕镌记忆。一棵树,一道景,于每个崭新的日子,叠复着岁月的沉积,焕发出清湖码头新的生机。
银杏
一棵银杏树,是属于浙江江山还是属于江西广丰?两地人各持己见。此等事,前所未闻。
这棵银杏树,生长在江山广渡村的嵩峰寺前。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被列为广丰县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六日又被江山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何以两县(市)都发文?虽如此,举动足以肯定,是对古树名木保护的旨归。但究属哪一方,则莫衷一是。
此事引起浙赣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浙江、江西两省联合勘定,并在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上明文规定:银杏树属两市(县)的共同财产,共有共管,由双方市(县)人民政府联合发文、立碑和挂牌保护。一棵银杏树,两地保护,共同担责,这不正与我们倡导的爱树护绿、人人有责相契合吗?
其实,嵩峰寺前有两棵银杏树,明宣德年间柳道人建寺庙时所栽。一雌一雄,枝叶蓬蓬,冠如华盖。靠广渡方向这棵为雌,另一棵为雄,雌雄相对,夫妻相称,相随八百余年,既是雌雄恩爱的比喻,又是两地的友谊树、百姓的连心枝。
银杏树,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在高海拔的嵩峰山自然生长,实属奇迹。它又称白果树,苔藓覆根,青藤缠身,枝条倒挂,树干耸入云霄,冠幅西北东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是银杏树最为荣耀的日子,各地香客不远数十里,甚至上百里,翻山越岭登临峰巅,为银杏树贺寿。
两棵银杏树,形态各异,一棵只开花不结果,另一棵既开花又结果。我要说的是开花结果的雌树,不光是雌树的形态优美,枝干虬曲,还有雌性的伟大。《道德经》有言:“知其雄,守其雌。”
雌树的根、皮、果、叶、花都有良佳的食疗、保健效果和医用功效,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其皮果,曾救治过很多村民,他们携家人、邀新朋,一起上山点香拜树,表达感激之情。雌性银杏树成了他们心中的“神树”,冠以“树王”揄扬。
银杏树最美不过银杏叶,它既像枫叶那样,一到深秋就换上艳丽的盛装;也像松柏那样,在风霜冰雪中挺拔;更像芭蕉树那样,形态婀娜多姿。但银杏叶更有着自己的独特色调。尤其霜降时节,它会变成金灿灿的柠檬黄,通体精神透亮,枝梢晶莹剔透。轻飏间,叶子翩翩起舞,然又簌簌落下,给地面铺上厚厚一层“金毯”。不免让我想起郭沫若先生的诗句:“秋天到来,蝴蝶已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要泛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蝴蝶。”郭先生的笔下,银杏叶是鲜活的,而在我的眼里,它是澄净的、空灵的。
眼前迷人的场景,使我整个身心被莫名收摄,每个毛孔都充盈着怡悦。一股奇妙的释然荡漾在山巅,任我在幻化之中随意去来。放眼自然,秋光晕染,美丽如许,随时都能获得最甜美的温柔、最纯净的欢欣,熨帖着我的身心,隐于市、静于心、雅于境。
人活着,最大的诱惑,在于充满变数;而树活着,最大的使命,在于为人类造福。银杏树是一门语言,我们所获知的每个新事实,就是它的一个新单词。
行将日落时,一场大雪纷至沓来。鹅毛般的雪花,拍打着银杏的枝叶,少许银装素裹,黄白相间。山脊厚厚的雪衣,连同银杏芬芳馥郁的质美,在人们心底炫彩,在嵩峰寺炫然。
嵩峰山归美的不是云雾,而是银杏树;嵩峰山香火旺盛的不是嵩峰寺,也是银杏树。
柳杉
柳杉是山岭的风物,山岭是岭头的悠居环境。幽深僻静的岭头,因手工造纸传承一方,又因古树名木保护闻名遐迩。
岭头,从字面上不难理解为山岭之脊,实则仙霞山脉腹地。冠以岭头,该是指山腰上的古树群,以柳杉为首。
三百年前,岭头戴氏兄弟用一斗米从朱家手中买下这棵柳杉,世代精心护翼,绳其祖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柳杉归属村里,柳杉之于村民,一如对他们先祖一样珍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居心不良者,一心想将柳杉走私出洋,偷运日本,从中牟利。尽管他们巧舌如簧,但村民不为所动,群起而攻之。柳杉是祖先留下来的,是绿色的命脉,是村民们的精神支柱,人在柳杉在,柳杉必然繁茂屹立。彰明较著,柳杉如真被砍倒,村民定会伤心欲绝,嗟悔无及。且不论何种理由,这棵柳杉都是村民心中的圣物。即便在那个年代,在这样的高岭山村,人们依然赋予柳杉某种神圣的价值,过于灿然,甚于黄金,永恒而炫眼,讶然不已。
生态古树攸关人类存续,生态文明攸关人类发展,古人有古人的行为,今人有今人的举止。几年前,当地政府筹资几十万元,实施古树保护工程。垒石砌磡,培土抚育,清理沟渠,防止水土流失;平整路面,清除杂草,整修溪墈,创建“一牌一人一案”管护机制,设立保护牌,确立养护人,创建国家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柳杉就这样生长着,被屃护着,而它的最大愿望许就是一生抓紧泥土,浓郁苍劲,散发清新气息,造福村民。这时我才感到,土地能呈现它,阳光能照见它,风能拥抱它,而我的语言却表达不了它。
柳杉枝柯低垂,劲直坚挺,满盈的果籽,沐浴在清纯明媚的阳光之中,黄黄的、灿灿的,方圆几百里为“王”,却每每低调山间。柳杉属常绿乔木,树姿雄伟,树干通直,纤枝略垂,树形圆整高大,喜温暖湿润、云雾弥漫的山区气候,使它到了秋天都不会变黄,到了冬天也不会落叶,许是它的基因里有耐寒因子存在,所以气温下降叶子也不会枯萎。
我时常来到这个幽静的地方,紧贴柳杉,伏下观察,似乎感知我在树皮下所见流动的汁液,同样在我清爽的肉体内上升,脉动的体温,任凭山风轻拂,细雨沥沥,也不舍离开。有时,我整天坐在树下,沏着用山泉水浸泡的当地岩茶,慢慢品鉴,聆听着树枝已经在风中吟诵了千年的民谣。摆脱尘俗,超然的清华与贵气在树间流动。环境自然,心自然,则人生自然。
鸟儿挤在簇密的树叶下面,显得格外亲密,它们栖身枝头谈天歌唱,替明艳的阳光谱写新的旋律。曲调优美动听,宛若挥动相宜的琴弦,在茫茫森林和天幕中回荡,似是给我守望柳杉的乐伴,顿然间我兴会无穷。我观的不是柳杉,而观柳杉的人也不再是我。
那些一心想让自然为己所用,却不懂得珍惜自然、保护环境的人,其结果都是徒然的。岭头自然村的村民,用行动陈铺绿色情怀,舒心畅然。我满腹感激这些村民,给我们及后代留下片片绿荫。
山间的空气,滋养智性而让人灵感奔涌,悠然此境,体格会更加完美,心智会益发圆满。回眸柳杉,青枝绿叶,层次井然,自然气息的温润,陶情适性,无以复加。
黄檀
双溪口村的村民,大多知道黄檀是昂贵树木。它在世界古树名木排名中位居第三。不宁唯是,村民更知晓,黄檀木用作家具、斧头柄、刀柄、铁锤柄是最佳材质;黄檀木纹理致密,具有很强的韧性,是雕刻家的最爱,他们运用各种雕刻技法,将黄檀木雕琢成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品。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晓,黄檀木含有浓香气味,沁入人体会精神焕发、醒脑安神,用于降血压、降血脂、防止感冒发烧、增强人体免疫力、抑制各种潜在疾病的发生。
黄檀木,一树皆金,果不其然。
双溪口深山田边泥土上,五百多年前萌生出一棵黄檀,古朴雅致,郁郁葱葱,高过周围一切树木。这不仅是黄檀的生命力顽强,更是村民祖祖辈辈的周到呵护。岁月将这段安静的时光,尘封在山村的尘土中,镌刻感人故事在村落里。
村中老人讲,曾有人欲砍黄檀作农具,被村民制止,险些大打出手。黄檀,是大自然的产物,村民们视黄檀为宝,以黄檀为贵,不遗余力严防各种病虫灾侵蚀。一代代村民钟情的黄檀,在田间地头悄然生息。
古树是人类真正的朋友,在人类生存空间里,几乎唯有它会衷心伴随。尚未遭到人类污染和破坏的黄檀,有种难以言喻的神性。一年盛夏,久旱无雨,村民遭罪,庄稼遭殃。而此时,村民们却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烈日下的黄檀竟自动降雨。树上落下绿豆大小的“雨点”,几分钟就将庄稼淋湿。甚是怪象,天气越晴朗,阳光越强烈,“雨”就越大。众所周知,降雨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降雨云是不会下雨的,即使人工降雨,也是对大自然的“模仿”。而黄檀降雨,旷古未有,其玄妙不知所以。
村民们来到黄檀树下,饮雨侍渴,感遇忘身。
黄檀为慢生树种。每当阳春时节,树木开始吐放新芽,青枝绿叶勃勃生机,而黄檀仍在摇曳着光秃秃的枝干,既不争春,也不报春,故有黄檀贪睡“不知春”的说法。汉代王充《论衡·状留》谓:“树檀以五月生叶,后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沉睡状态的黄檀,时遇一场春雨即被唤醒,一夜之间新芽全发,这是黄檀独特的地方,也是黄檀与众不同的显露。
深山一派幽静壑寂,太阳破雾而出,黄檀跟光线臂膀相挽,游走在神奇的叶尖之上,透过枝叶缝隙,稀稀落落洒下点点斑斑的辉光,宛然颗颗宝珠,渐落在老迈的树根上,滋生着繁茂的干枝。黄檀向野性伸出了强劲的枝丫,在大自然中寻求自己的空间,仿若即便身在荒野,也会满怀欢欣,甘愿居留。
日落风生,我屡屡仰望田头的黄檀,以检验自己的鉴赏能力。皎洁的月色光华,透过枝梢罅隙在大地上变幻出各种天然图画,月对树遐朗,树对月清遐,人对月遐思,山村的夜晚如此美妙动人。树与人,在这无垠的星河里共行,相依相偎相随,如可朝朝暮暮。人的心里若常驻一抹自然美景,则危害难以近身,而沮丧也会远离。
黄檀属于濒危树木,奇珍异宝。相传,唐朝诗人杜甫舟上郴州,途经湖南耒阳时,见到一棵苍然的黄檀,甚是喜爱,凝视良久,后人就将此地作为“杜甫公园”,以示纪念。杜甫公园的黄檀与双溪口村的黄檀,形神兼备,虽隔千山万水,毫无关联,但同属奇树,佑福人类。在我看来,滋养人类思想劲干虬枝的韧性要素,恰好来自这朴野粗糙的树木。
山高山有魂,树大树有根。是一棵树,就会给大地留下一片荫,就会与人类有一丝自然的联系。在我心中,不止第一棵树是神奇的、灿然的、耀眼的,最后一棵亦是。
六棵树,散落在江山大地,是江山炫目的符号、绚丽的色彩,也是这片土地上充满人文意蕴的传奇故事。每棵树,都被列为古树名木,建档编号,捃摭档案馆内。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古树是自然产物,是天地之精华。然为生命,体蕴着生长的能量与养料。
绿,心静也,是生态;色,心声也,是自然。道法自然,回归生态,是人类文明的至高之境。人类的生存法则,离不开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呵护或破坏。
树是大地之子,人乃自然之衣钵,自然中的现象,现象中的自然。我与树相随,树与我相依,根在哪里,魂在哪里,家就在哪里。